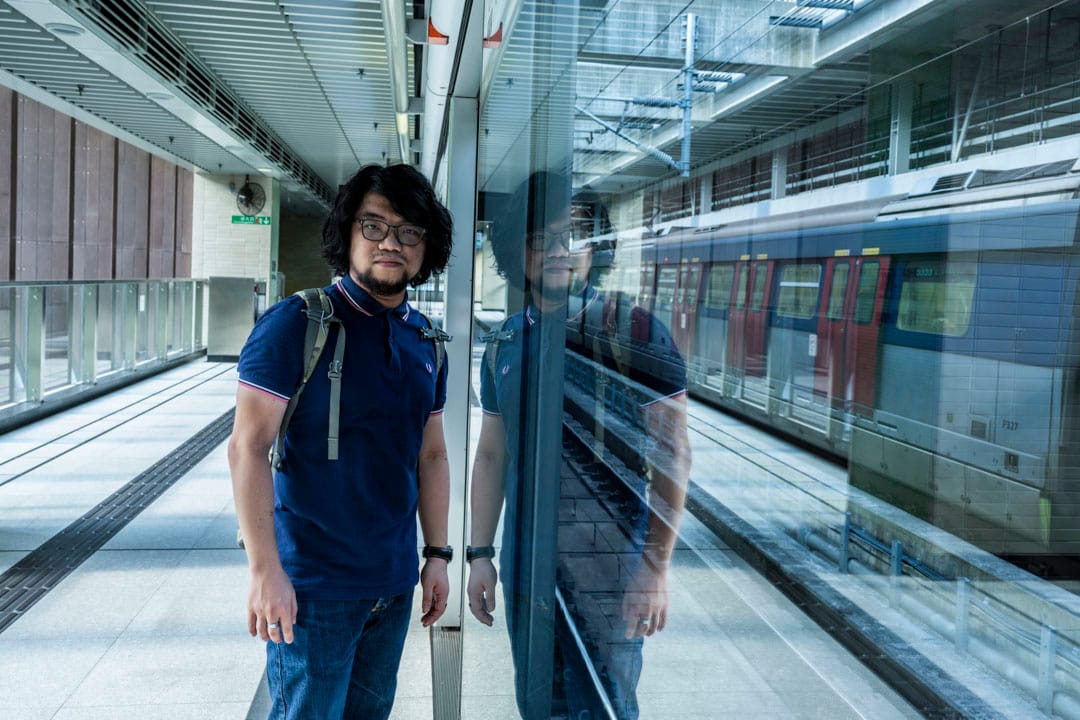【編者按】媒體人「紅眼」三年前親歷元朗721事件(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三年後寫下這篇文章,回顧這幾年香港人由遊行示威,變成走上街頭追星;打卡點由連儂牆變成明星代言廣告牌。他不習慣,也不想習慣,三年前的創傷仍在,只是情緒延後,裝作「好起來」。三年後,他覺得香港變了,香港人也變了,然而傷口未復元,帶着一份隱藏着的痛和憤怒,他剖白這幾年不同身份角色上的種種交織和種種落差——身為721親歷者的未解之痛;身為傳媒人的自我閹割;身為香港人的欲語還休。他對於這些變化感不適,但最後他控訴的其中一個人是自己。
(紅眼,專欄作家,影評人。《藝文青》總編輯。寫電影、電視劇、流行文化。寫小說。)
我還是不是2019年7月21日坐西鐵回家的那個我?
三年後,我今天仍然戴着口罩。別誤會,是另外一些原因所以戴着口罩,那些「事情」沒延續三年那麼漫長,它完結了、沉默失語了,甚至人走茶涼了。
香港順利慶祝主權移交25週年,但我仍記得今天是721事件三週年。記憶是不可靠,尤其短短三年之後,從法庭的審判以至某些已成為社會「共識」的說法,都跟我在列車上的親身經歷有些出入。我明明在場,但我還可以怎樣告訴人呢?我在某些渠道嘗試爭取一些聲音,但那些渠道已經消失,那些聲音正在等候審判。
作為土生土長的元朗人,接下來的三年,我都必須若無其事往來事發地點,但原來不是很難過。只是大家開始失憶,或不願意再談這件事,漸漸讓人產生幻覺,那天的白衣人真的出現過嗎?還是拍戲而已,抑或幽靈?那些在我身旁穿插而過的木棒和鐵枝,又是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