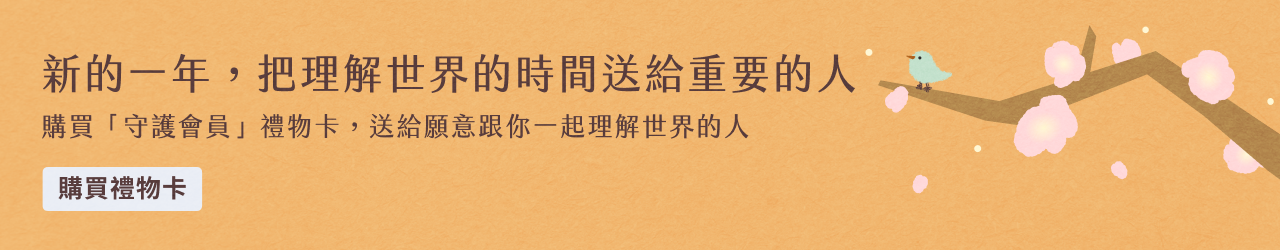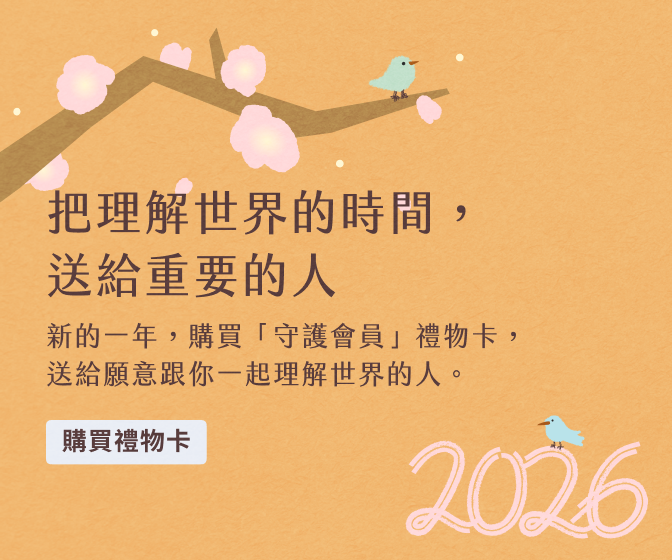速遞 Whatsnew
更多



流亡反對派馬查多計畫返回委內瑞拉,為何特朗普不選擇與她合作?|Whatsnew
一份報告認為由效忠馬杜羅的人士繼續治理委內瑞拉,會比馬查多的團隊更為成功。但反對派意見領袖仍認為,還未到完全放棄希望的時候。

編輯精選







/
僅限會員
失落的熱帶:香蕉種植園和不屬於這裏的人
這群中國人和越南工人,是兩個國家在不同歷史進程擁有相似處境的人。種植園將他們放置在了同一時空,是同樣沒有保障且不確定的生活,是不得已的選擇,是背井離鄉過一種農民生活。

評論
更多
系列
更多
欄目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