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带来的失序仍在剧烈且深远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封闭成为常态,权力的边界愈加模糊。以防疫为名、以爱国为名,反思、质疑甚至讨论的空间被进一步摧毁。我们又该如何守护自我的主体性、守护思考的自由?
阅读,修筑了最后一道闸门。端传媒和六名来自中国大陆的阅读者聊了聊阅读这件事。他们是翻译者、检修工人、大学教授、诗人、童书编辑和独立书店的店长。通过阅读,他们感受真实、认识社会、寻找自我,抵达一个远比脚下丰富、开放和广阔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中,阅读就是生活本身。它关乎人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安顿自身,关乎个体在潮流面前的自醒和坚守,关乎自由的思想如何作为一种应对时代的方式,赋予他们超越现实的力量。
每个周六,我们将与你分享一个阅读者的故事。今天是系列的第五篇,一个诗人说,他要在“地狱集中营的缝隙里,找到蜜糖的快乐”。下周六我们将发布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一个童书编辑讲述了儿童文学是怎样施展重建生活的力量的。
茫茫书海中,身体或被困居一隅,精神的远足却可翻山越海。愿他们的故事,也带给你力量。
点击阅读:
我们为什么阅读(1):如果这代人是自我的,那自我之上,还有什么价值?
我们为什么阅读(2):打工者身份是我的锚点,阅读让我更新对自身群体的理解
我们为什么阅读(3):我想了解,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和驱动力
我们为什么阅读(4):我关掉了自己的书店,继续建立书与人之间的连结
桑克,诗人、报社编辑(55岁)
我在黑龙江的一家报社干了三十年,做过文化、体育、科技、专题报导,现在是负责地方时政新闻的资深编辑。
业余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和写作。每天不管多忙,都要看几页纸质书,不然就觉得一天被浪费掉了。
小时候,我就爱读各种带字的东西,家里的天花板是用报纸糊的,我会把上面所有的报纸都读一遍。后来,我哥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会给我借回来很多书,小孩子的好奇心强,文学、历史、科学、天文,借到什么,我就看什么,也不管看懂看不懂。
对阅读的热爱延续了我整个人生。再大一些时,我开始狂热地买书、抄书。最早有买房的想法,也是为了装书。到现在,我的家已经完全被书给占满了,买书的频率才渐渐降了下来。想要挑本书出来读,经常找不到,抓耳挠腮的,特别痛苦。
从小养成的阅读习惯,也和我自我拓宽的意识有关,我读的书一直很庞杂,从文史哲,到科学、艺术、博物,等等,没有什么设限。但当写作成为了我生活的核心后,文学对我而言,就如同一颗恒星般的存在。其他领域的阅读更像围绕着它的行星和衞星,最终都会被我转到文学上来。
去年,我一直在通过翻译的方法,深度阅读爱尔兰诗人帕特里克·卡文纳的作品。
说实话,我读卡文纳的缘起非常个人化。卡文纳于1967年去世,而我是1967年出生的。这是我的一个个人习惯,找陌生作家或者作品的时候,经常会选一些关联我个人生活时间节点的人物或者作品。这些时间节点,算是一种导航密码吧。
刚开始,我译读卡文纳的一些短作品,像《给一个孩子》,觉得不俗,就一点点地开始看他更多的诗作。前年,我把他晚年的诗都给译出来了——所谓的晚年,就是死前的一段时间。
最近两年,我越来越感受到年岁在我身上留下的刻度。记忆力变差了很多,读书的数量、质量都不如以前。从前,读了什么书、哪一页写了什么,都会记得特别清晰。现在有的书读到一半,才发现自己做过笔记,有的甚至要读到结尾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看过。
死亡这个时间节点开始变得愈发吸引我。因此,想在一些诗人身上找到对付晚年、对付死亡的方法或安慰。卡文纳前,我把奥登死前两年的诗也都给译了出来。
卡文纳最有名的长诗叫《大饥荒》,是我去年读过的最好的一部长诗。他笔下的土地贫瘠与性饥渴之间的复杂关系,长短句结合的各种表现形式,还有句子的控制与节奏,简直可以与艾略特的《荒原》相媲美。这些作品距今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还这么有味道,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我:诗和艺术并非是进化论,而是单独发展的,它也并不是向前走,而是向上飞的。

阅读文学,是我保持清醒的一种方式,帮助我应对眼前的生活。
每年,我都会为自己列一个阅读计划。从主要框架,到下面的一些枝杈,都会提前制定好,严格按着计划走。像卡文纳,还有重新精读艾略特的诗歌和文论,都是去年计划内的阅读。我算是个比较死板的人,过去更是。如今我已经有意识地要让自己轻松一点,可以接受一些随意性的东西出现。
去年最后读的一本书,哈维尔•马里亚斯的《写作人:天才的怪癖与死亡》,就是一本“计划之外的书”。我把它称为“八卦书”。我们做文学的,更愿意看人,看人生,看生命。作者对那些久负盛名的作家个人化一面的重现,读来非常有意思。
特别喜欢、有感情的书,隔几年,我就会拿出来读一遍。比如《晚霞消失的时候》,这是一本80年代的小说,我少年时代就很喜欢它,到现在已经数不清看了多少遍了,一阵不读,就会特别想念它。还有《平凡的世界》,我经常会不太好意思说出口,它当然不是一本完美的书,有很多问题,但我愿意反覆重读,是因为它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多特别的意义。
但无论怎么说,一个人的读书视野总归是非常狭窄的。我也怕自己对新书产生隔膜,所以也会看每年的阅读榜单推荐,看一看年轻人在看什么书,他们看了觉得好的,我也去买来看看。和朋友还能经常见面时,我们的话题也通常从书打头。碰到感兴趣的,我就立刻记下来。
表面看来,文学是距离现实较远的写作,但究其根本,所有的文学都是与当下有关的。看去年读书时摘抄的一些文字,我经常会感到恍惚,好像不管在哪个时代,所有人写的都是一个东西。
疫情刚刚开始时,我正接手写一本杜甫的小说。为了完成它,读了三、四十本唐代文化史、风俗史研究的书籍,了解当时的衣食住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如果不交代背景,你会觉得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第一次完整地读完《生活与命运》,正是疫情最为激烈的时期,犹如小说中描绘的斯大林格勒巷战。去年,我又重读了它。书中写到办粮食供应证的官僚蹂躏,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复杂而细腻的关系,全部都是通过细节表现出来的。这些文化的分子和原子,对我们来说都太过熟悉了。有时不需要直接说什么,细节自己就会替你说出来。
我还重读了理想国M系列的几本书,像《耳语者》、《苏联的最后一天》,还有《苏联密档》。阅读文学,是我保持清醒的一种方式。我也在从中寻求更多的道德力量与精神慰借,帮助我应对眼前的生活。一句话,如何活下去。

我想要过一种审美的人生。
三十年前,我选择进入媒体,和我的个人兴趣其实关系不大。那时候,媒体待遇还比较好,在媒体谋一份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但做着做着,我也对记者这份工作本身燃起了更大的兴趣。它给我带来的社会启蒙,对后来的我影响深远。
但你知道,媒体在最近10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启蒙的理想也随之破灭。我现在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说,我已经不是做传媒的了,我就是个宣传干部。于是,在这个系统里头,我开始变得越来越自我边缘化。
只有写诗延续了下来。
从写第一首诗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十一年。我最早写的是中国的古体诗,与当代是不接轨的。写了很多年后,才开始接触、写作自由诗,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但写诗始终是纯粹个人的工作,与任何圈子无关。真要说起来,真正的诗人其实都离主流很远,但他们就是“主流”。这个“主流”是由共同氛围所形成的,别人看你们好像是主流,但你们都是独立、独特的个体。
诗歌是我认识世界的一双眼睛。我想要过一种审美的人生,想要享受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在诗歌中,这些想望都能被满足。它让我对生活和生命,都有了一种更加自由、更加深刻的理解。
也可能是最初的机缘,将我框在里头了。相比其他形式的写作,写诗启动的经验更丰富,是我觉得最舒服、最自如的表达方式。

我是必须好好活着的。它休想让我一直痛苦下去。我不仅要活着,而且还要在地狱集中营的缝隙里,找到蜜糖的快乐。
疫情这两年,我的生活始终处于不断被打乱、被限制的状态。哈尔滨疫情严重的两次,每两天要做一次核酸,连续做七次。它不仅干扰和改变着我日常生活的情绪与细节,也自然影响到写诗的心境,最终反映在作品的点点滴滴中。
这些情绪大多是消极、悲痛、激愤的。即使我在《每天笑呵呵》的诗里写,“每天笑呵呵,/看喜剧或者悲剧”,也都是这种影响的对立性折射。甚至还会催生因为居家隔离写作而不必上班,而略显变态的微喜,或者某种怪异的自由——就像我在《自由是什么》里写的:“虾米,别掺乎植物界的事,/别掺乎来不及反应的事,/别掺乎蔬菜的事,/别掺乎……”
当然,这种影响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再次印证了我对生命以及生活的认识——生命本质及其自身的要求,是不会随着环境而改变的,我不能因为这些强加给我的东西,而改变我对生命质量的追求。
我是必须好好活着的。它休想让我一直痛苦下去。我不仅要活着,而且还要在地狱集中营的缝隙里,找到蜜糖的快乐。
你从阅读里获得了哪些力量?欢迎来信或在留言区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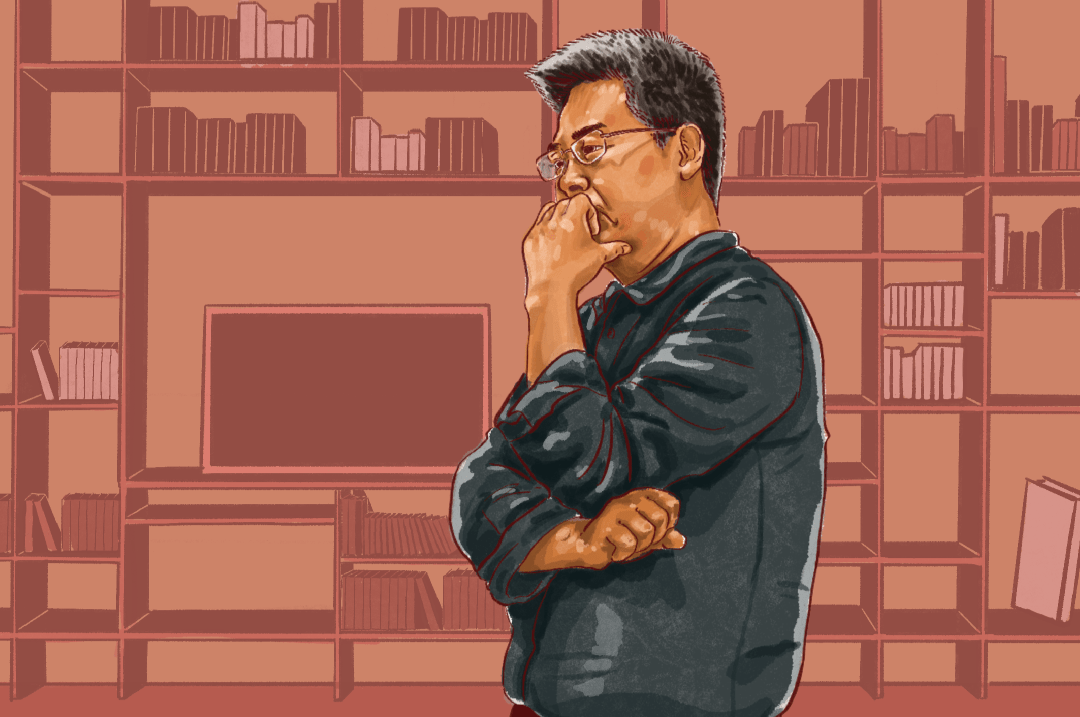




那本書應該是《晚霞消失的時候》?禮平的。上文好像寫錯了。
謝謝可唯的指正,此處確實寫錯了,我們已訂正書名。
思想是自由的,有誰能夠將它猜透?
飛一般掠過,好似黑夜的影子
沒有人能了解她,沒有獵人能用
火藥和鉛彈將它擊中,思想是自由的
我想自己所望,還有那幸福之事
一切都在寂靜之中,思想本該如此
我的願望和渴望,沒有人能將它阻止
它永遠都是如此,思想是自由的
我愛美酒,尤愛我的姑娘
唯有她最能討我歡心
我並不孤單,有我的杯中美酒
還有我的姑娘在身旁,思想是自由的
如果有人把我關在,陰暗潮濕的牢房
所有這些舉動都,徒勞無用
因為我的思想,擊碎了那些枷鎖
將牆壁一分為二,思想是自由的
所以我要永遠,與煩惱決裂
而且永遠也不要,受那憂郁的襲擾
每個人都可以永遠,在內心一邊放聲歡笑
一邊繼續保持那個念頭:思想是自由的。
1942年8月,當 Robert Scholl 稱希特勒為 "上帝的煉試" 被監禁時,他的女兒 Sophie 站在監獄牆前,用長笛為父親演奏了《Die Gedanken sind frei》這首歌。當 Reuter1948年9月呼籲 "世界人民 "不要放棄柏林時,成千的人當場自發地開始唱 "Die Gedanken sind frei"。
在風雲變色的今天和社會裡, 保持頭腦清醒和思想上不從眾, 自由的閱讀 於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甚至乎可以說是 精神上存活的必要手段。
在高度壓制化 和 集體意識化的社會, 從眾,跟主流,同官方 似乎是最“合理”, “正確” 的做法 , 也最合乎 「思維慣性」。 逆流去做個人的思辨,敲問, 反思, 尋找自己需要的答案和真相, 以 韋伯所言 的 “ intellectual integrity” 科學態度 寫實自己的生活, 真切感受, 需要非常大的意識韌性。 而 自由的閱讀, 是這種韌性培養的重要手段 , 也很費勁。
畢竟, 在這個個人注意力極短, 娛樂為上的社交媒體主導的社會中, 深度的專注閱讀,本身就是一種非主流,費勁的活動。
好喜欢的系列
古代文人仕途失意,就會在詩歌文學裏尋找慰藉。
現代亦如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