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拐上窑垣小径的斜坡,便听到此起彼落的敲打声音,呯呯咚咚呯呯咚,仿佛一大盘巨形的爆火花在小径上炸开来,而且是又硬又坚实的。

今天是我们的老房子造三和土地板的日子。三和土的日文名为Tataki,跟“敲打”同音,我以为是巧合,但原来做三和土地板的工法,真的是敲打。将沙土、熟石灰、盐卤混成三和土,洒在地上,经过一轮敲打增加密度后,再洒上一层,重复又重复。舖好后得将之搁上多天,待它硬化,结实。说来简单,但地板的厚度少说也有七八公分,手工不纯熟,造工不够仔细的话,地板便会起伏不平,而且一旦硬化了便无法修补。
想到这日本传统建筑工法已甚少人采用,我们希望让更多人有机会认识日渐失传的技术,于是把雇工匠的经费用来辨了工作坊,请工匠担当导师。招募活动的反应比我们想像中热烈,连续两天的工作坊合共来了二十多人,有些更是从冈山或神奈川驾五六个小时车到来。
我中午过后才匆匆赶来,刚巧大家正准备午休,便一起围著圆桌泡茶吃便当。做三和土地板是体力活,不熟悉的敲个三四十分钟,手臂便发软了。几个女生揉著前臂,分享著消解肌肉酸痛的方法。有些人则因为蹲太久了,边凝看庭园边伸展著腿拉著筋。室外晴空万里,初春的暖阳蒸发了寒气,大家的脸上漾著笑意与倦意。
日本早在东日本大地震已出现移居潮,灾难令人反思素有生活方式,不少人选择移居乡郊。近年疫情令旧有生活模式停摆,不少年轻人憧憬在乡郊低价买屋,DIY维修,建立居所。他们是否愿意应用传统建筑工法呢?

买什么百年老房?
窑垣小径在爱知县的瀬户市,因为车子无法直接驰进,两旁又大树参天,晴空万里的日子这里仍是幽暗的,有点与世隔绝的感觉。虽说是瀬户市内重要的旅游点之一,但即使在黄金周假期,这小径仍是行人稀落的。数年前,我们买下了小径上的一幢百年老房,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当时的自己定是神经失常了,才作出如此不自量力的决定。
我的伴侣金森正起是做金工艺的。做好一个铁盘子,放在室外日晒雨淋,养好几年,待它的锈长得够深了,费工夫将其除锈上漆或蜜蜡,明明是才哇哇落地的器物,看来却一把年纪。曾有古董商人把他做的铁茶托当古董卖,标的价钱比原来贵好几倍。他做铁器、铜器,也用铝金属做作品,但在日本最为人熟知的是手工珐瑯。珐瑯器皿百多前来都是被大量生产的工业制品,制作时会用到化学药剂。他费了多年时间研究,在野田珐瑯的老板及釉药公司的老员工无私的协助下,找到了不用化学药剂的方法,把珐瑯杂器当作手工艺来做。这样的一个金工艺家,有一个奇怪的癖好——看房地产网站。
某天晚上金森神情暧昧地对我说,他在房产网上看到一幢位于瀬户市窑垣小径上的老房子,“那里小路迂回曲折,护土墙啊、建筑物的围墙都是用烧陶工具拼成的。以往陶艺工匠们穿梭在那些小路上搬运陶瓷器呢⋯⋯汽车无法上去的。风景很有趣。那边难得有房子出售,要去看看吗?”嗯,地点离家不远,看看也无妨。

房子是陶瓷工厂老板加藤仲右卫门的故居,传了数代,后人无意继承,屋主住进老人院后,房子便被空置著。忘了是晚冬还是初春时,我们第一次走进这幢老房子,站在玄关上,湿气结住了尘埃的气味扑面而来,玄关后的厨房幽暗,十来个厨橱里叠满了器皿餐具与杂物,大厅里的巨型沙发、挂在墙上的电视、空调与祖先遗照,里间介护用的电动床、关于癌症的笔记,很多的家具、书、画作、衣物、家具、冰箱、洗衣机,甚至还有一个桑拿室,另外屋外屋内的三个仓库里,则是大量的陶瓷器、工艺品、生活用品、旧玩具⋯⋯屋主似乎是带著随身行李便搬离了,留下大堆大堆的生活痕迹。我站在那里看不出所以然来,金森向地产经纪询问价钱,知道房子的价钱,近一半是屋主将用来清理这些“垃圾”的。
“如果我们自己清理的话,售价是否可以大减?”听金森这么一问,我背一凉。
“如此独特的风景,该好好维护的。”
我的预感应验了,回程时,他已向我描画他天马行空的计划——自行清理屋中的杂物吧,修葺后作为旅馆吧,又或是咖啡厅吧。他雀跃不已。说起来,他一直都很希望我能开一家卖咖啡小吃的小店,我却因为小学时在香港便不分晴雨地跟父母摆路边摊,早厌倦了卖小吃的各种艰难,不想再涉足。我把自己泡在想像中的湖水里,任他说甚么都变得像来自世外的声音。
我以为过几天,老房子的事便会不了了之,想不到多天后,金森的父母也往窑垣小径参观了。看来他一直对房子念念不忘,工作休息时(他的工房位于父母家的旁边)忍不住跟父母分享了他模模糊糊的梦。一个多月后,我又被他拉到老房子去,他把梦再描画一次。“除了旅馆,还可以划出空间来办展览啊。”他手舞足蹈的,双眼绽出了星光。

我们沿著窑垣小径走回停车场,这修小路原是运送陶瓷的路径,以登窑用的烧陶工具拼成的围墙、护土墙,在日本极为罕见。本地人曾经把那些烧陶工具视为垃圾,把小径唤作“窑粪小径”。直到民艺运动时,柳宗悦及滨田庄司到来,对之赞颂不已,于瀬户一个叫本业窑的民窑的推动下,政府官员才有点明白它的价值。那天阳光穿过林木,几团光晕落在护土墙上,花草仍未长盛,显得草丛里用来防杂草生长的塑胶网尤其碍眼。金森跟我说著他与瀬户的渊源,这个千年的陶乡曾是他上大学的必经之地,几乎每天往返,他却从不知道窑垣小径的存在。“如此独特的风景,该好好维护的。”金森语重深长地说著,捡起了草丛里一些塑胶垃圾,塞进他随身携带的垃圾袋里。
我脑中浮现起老房子里大堆的家具与杂物、被随便用透明胶纸修补过的木窗櫺、破了皮的墙壁、长了霉菌的梁柱。房子已丢空了两年,听房产公司说,过去曾有两个人查询过,但日本人了解老房子随时成为子女的负担,而且修葺工程深不见底,查问了便却步了。老房子的围墙以陶板建成,屋顶采用的则是已停产的瀬户瓦,都是值得保护的历史与文化产物。我想金森定是不忍房子在年月里老化,任其好风景不再吧。
我们这才发现包工头对传统老宅并不熟。现代墙壁以合成木板建成,以化学物料帮助衡温,混凝土作地基,内埋防潮塑胶布,瓦顶下铺著化学防水物料;传统墙壁则由竹及泥土砌成,以石为地基,屋顶瓦片多只用泥土固定。
清不完的生活痕迹
决定要把房子买下来,已是大半年后的事。期间我们请了包工头来察看房子的状况,看有那些地方是非修不可的,确定我们负担得起初步的维修费用。然后,又过了数个月,房子总算正式归我们名下。
那时正值疫情,屋主居住的老人院对探访者有严格的限制,每次都得在他儿子陪同下,我们才能进出老人院。屋主两位儿子住在东京,好几次放下繁忙的工事专程跑来名古屋。他们都很乐见能在父亲身体仍然健壮时,为老房子找到买家。最终我们以近三分一的价钱成交,老房子后方连著几片建了房子的土地,也属于他们的,他们决定把土地权一拼转到我们名下。此举让我深刻地感到,对屋主的儿子们来说,或者说,在日本,房地产对下一代而言,不一定是人们乐意接收的资产。

取得房子的钥匙后,我们便开始收拾。面对满屋的杂物,我毫无头绪,金森则兴致勃勃。百年老房里有上百岁的物品,他钻进了每个仓库的每个角落,翻出淹没在尘埃里的旧物,一如所料有价值的古董已被带走,但他喜孜孜地淘出一些素烧茶壸与旧竹篮子等等,都是他喜爱的东西。
金森后来不知从哪里联络上一位正准备开设儿童食堂(为儿童供餐的慈善组织)的老太太。有天,老太太驱著小货车,来到窑垣小径的停车场,金森把房子里的冰箱、电视、厨柜、桌子、椅子、全新的食具等,分次堆在他新买来的电动手推单轮搬运车中,往返迂回的小径,塞满老太太的小货车。后来他还致电了好几家二手商品店,大部分听说房子的地理位置便拒绝到来了,还好最终来了一家,带走了暖风机、十一台空调等拆开后能作废金属变卖的电器制品。
他们决定把土地权一拼转到我们名下。此举让我深刻地感到,在日本,房地产对下一代而言,不一定是人们乐意接收的资产。
另有一家把家具运到东南亚地区出售的公司,来抬走了十数个抽屉柜子。电灯、沙发送给有需要的亲戚。屋主已过世的妻子留下大量画作,全表在画框内,我联络了一家艺术大学,打算把画框送过去,相信艺术系的学生们会用得上。簇新的衣物交到了二手店,器皿或装饰品陈列在屋外,任路人拿取。但仍有很多东西还是不得已地丢弃了,像各式各样的厨房道具、陈旧的洋娃娃、大量的雨伞、旧鞋子、无人问津的破旧小型家具⋯⋯把它们运到垃圾收集站时,顿感万般带不走,物质世界如此虚无。
现在走进房子,会以为室内空空如也,但若拉开关闭起的几道拉门,便会发现门后是如山的杂物。我们先把它们关起来,打算多花几年,慢慢清理。然后,维修工程准备展开了。
让建筑物有天能尘归尘,土归土
建筑师建议造成有型的古民家,但越谈我们退得越远,把房子看清也把自己看清,慢慢地明白到自己最终的愿望,就是很单纯地希望用传统建筑工法尽量还原建筑物原来的结构。
维修工程的进度比我们想像中缓慢。其中一个原因,是工程要启动时,我们才发现请来的包工头对传统老房子建筑并不熟悉。现代房子的墙壁都是合成木板建成的,木板与木板之间夹著化学物料来帮助建筑物衡温。以混凝土作地基,内里埋著防潮的塑胶布。瓦顶下则铺著化学的防水物料。

传统老房子的墙壁是由竹子及泥土砌成的,以石头作地基,柱子单纯放在石头上,不加固,至于屋顶瓦片多只用泥土固定。包工头只有建造现代房子的经验,也没有精通传统建筑工法的工作伙伴,之前的报价,原来是他猜想出来的。最终,他只为我们更换了被白蚁蚀过的横梁、维修了一些歪倒的建具。屋顶多处漏水,得赶在梅雨季时修好,但我们对修葺的方法却拿不定主意。我们想保留原来的瀬户瓦,却不肯定是否仍能用,若需要换又要找哪个产地生产的?我们花了数个月研究,问过几个做瓦顶的工匠,虽然众说纷纭,但总算探索出自己能接纳的方案。没料到,单是这些维修工程,已花掉我们大部分的预算。
另一个延缓了工程进度的因素,则是我们自己。清理杂物的工作暂停后,金森独力打掉浴室、更衣室、桑拿室——这些都是前屋主增建的,采用了大量的化学合成建材。与此同时,金森开始每个月与园艺师朋友,于窑垣小径上办维护山林的活动,并在庭园里作改善土壤的种种实验。我们还曾在老房子举行过《杜人》(もりびと)的观赏会,也是一部跟维护自然与土壤相关的电影。

另一方面,金森把建筑师朋友拉下水,开始为他最初的旅馆方案规划空间布局。建筑师朋友建议把哪里的柱拆下,把哪道墙推倒,镶上大片的玻璃窗,哪里铺混凝土,造成富有风格的古民家,越谈我们退得越远,把房子看清,也把自己看清,慢慢地明白到自己最终的愿望,并非大兴土木做出能彰显自己品味的帅气建筑,办民宿或艺廊也好,都不过是这空间的存在方式而非最终目的,我们很单纯地希望把前屋主以合成物料增建的部分全拆走,再用传统建筑工法尽量还原建筑物原来的结构。
好多年前金森曾独自拆掉山上一家小屋的内装,加上这次打掉老房子增建部分的经验,他亲身体验过建筑废料的沉重,知道有很多现代化的建材终将成为世代相传的垃圾。这令我们更加执著地,坚持修葺房子时只采用传统天然物料。即使有天建筑物将被推倒,所有建材仍能尘归尘,土归土。这幢老房子其实是瀬户市指定的景观重要建筑物,因为是私人宅邸,一直没向公众开放。有天我们会将它的大门打开,希望身处其中的人们,能连结到我们珍视的价值与日渐流失的文化。

与房子的感情,是熬出来的
我在社交媒体上写了众筹的事,竟得到香港朋友排山倒海的回应。最初计划修葺房子时,我们打算请工匠之余也亲自动手,除减省费用,也希望籍此与老房子建立更紧密的连结。
确定了自己的想法后,修葺改建的方向也明确了。粗略地说,就是拆去增建空间,在原来的骨架之上用竹子编成支架(竹小舞)造土墙,去除地板上的混凝土,改为三和土,还要维修部分的瓦顶及地基等。完成后,我们打算将这里作为艺廊,每年辨两至三次的展览,另外,也会不定期举辨放映会、音乐会,以及与工艺相关的儿童活动,算是小小的文化设施,运作方式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只是算一算,工程费用恐怕要费上千多万日元,而我们余下的资金不多了。烦恼之际,听说市内一些设施,都取得了政府的补助金,我们感到头上的云雾透出了阳光。
补助金的条件是,必须在网上集资,筹集到一半的工程费用的话,政府便会补上另一半。若集资不成功,补助金便无望。之前获得补助的,包括由陶器工房本业窑经营的瀬户民艺馆、旅馆Masukichi开辨的纪念品店等,主理人在市内外都有著丰富的人脉与支持者。至于我们两个,没什么可以吹捧的履历,也没什么经营经验来获取别人信任,实在没自信众筹能达标。心想不试白不试,若众筹失败了,就用仅余的资金作简单的维修,展览简单地办,待艺廊有收入了,才多投放经费,慢慢实践理想中的计划。

我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了众筹的事,没想到竟得到香港朋友排山倒海的回应。多年没联络的大学老师、以往的工作伙伴、二十多年前的旧同事、大学同学的中学同学、已移居海外的朋友、仅有一面之缘的艺术家⋯⋯还有京都的和菓子老舖亀屋良长的老板、日本的朋友们,给予我们超出预期的支持。众筹达标了,加上瀬户市政府的补助,我们筹得了近八百万日元的经费。我们为解决了经费问题而欣喜,同时感到肩上承托著大家的信任和善意,我们的脚步必须走得更用心。
最初计划修葺房子时,我们打算将工作交给工匠们之余,自己也亲自动手,除了为减省费用,也希望籍此与老房子建立更紧密的连结。筹备众筹期间,我们在网上结织到很多对修葺房子感兴趣的年轻人们。日本早在东日本大地震时已出现了一阵移居潮,灾难令人反思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不少人选择移居到乡郊,边工作边种田,半自给自足。这几年,可能因为疫情期间,向来的生活模式不得已停摆,更多的可能性也随之而生,新一阵移居潮又涌起。我们遇到的那些年轻人,大都憧憬著有天能在乡郊以低价买下房子,DIY维修,建立自己的居所。体验过传统建筑工法以后,他们会否愿意将之应用在自己将来的居所内呢?
我们带著这期望,请雇来的工匠办工作坊,我们的老房子成了体验场所,工匠向参与者传授竹小舞、土墙、三和土地板的制作方法。这也可说是我们回馈支持者的其中一个方法,让他们的心意化作种子,四处开花。

这天做三和土地板,是我们最后一个工作坊了,今天晚上,金森为了赶在翌日三和土变硬前作最后的润饰,大概会在老房子内留宿吧。工程展开后,他与这房子几近血脉相连。造土墙时,几个低于摄氏零度的晚上,因担心土墙内的水份会化作冰,令土墙裂开,他钻进睡袋,彻夜守在如同室外的工地里,点起火炉,为土墙保温。他与房子的感情,是熬出来的。
今年九月,亦即我们接收了房子近五年后,我们将会举辨开幕展,展出一些同样关心环境及文化传承的工艺家的作品。希望开幕当天,会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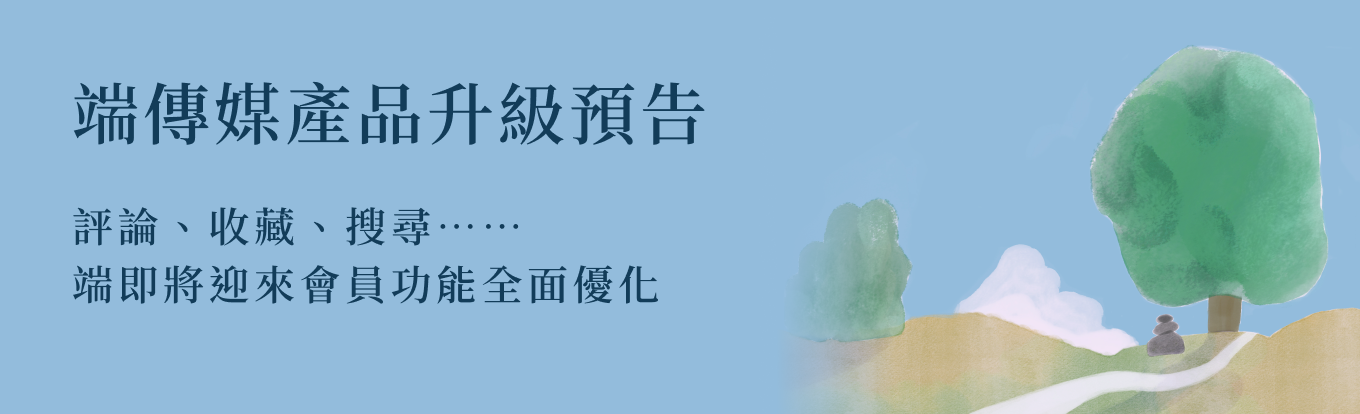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