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季風下的大福村
壯圍的冬天,是有味道的。
海風吹過來的時候,不只是冷,它還帶著一種鹹鹹的、濕濕的味道,像是海水在耳邊講悄悄話。風吹過防風林、竹圍、鋅鐵屋頂,天空常常灰濛濛的,偶爾飄著細細的毛毛雨,海邊變得很靜,只有風呼呼地叫。我們家——我、阿公、阿媽、還有媽媽,住在壯圍鄉的一個小村落,叫做大福村,那裡的人不是種田,就是養魚蝦,我們家三個世代都不曾離開過這裡。
大福村不大,從濱海公路走過防風嶺,就能聽見海聲。村子裡佈滿了大大小小的養殖池,田間和池間小路總是彎彎曲曲,兩側是低矮的磚房,像是一種默契的風景。早晨是養殖人家最忙碌的時候,水車打轉、飼料袋咕咕作響,空氣裡混著沼氣與鹽水味,一種只有這裡才聞得到的「海邊的土味」。
我們家就住在村尾的地方,出門沒幾步就是魚塭,再往南延伸,跨過兩三個村莊,就是蘭陽溪出海口。冬天的傍晚,正當養蝦戶打包飼料、村裡人漸漸歸來、雞隻紛紛回到雞舍的時候,阿公就拎著他那支舊的小電池,用電火布纏著一隻燈泡,戴上頭燈,接著騎他那台「風聲比引擎大聲」的機車,出門了。那是他工作下半場的開始,一天的嘈雜逐漸安靜,也是他開啟捕鰻工作最重要的時候。

小烏龜裡的鰻苗夜
我家在冬天會變成海邊的一部份。
宜蘭的冬天,加上東北季風的吹拂,每年立冬一過,壯圍的風就像改了個性似的,開始變硬、變濕,也變得不講理。海口總是暗得很快,連星星都不太亮。但就是在這樣的時節,我們一家人的生活跟別人不一樣。我不是待在家看卡通的那種小孩,我在海邊撿錢——準確來說,是在幫阿公抓鰻苗。
每年從11月開始到隔年2月底,是蘭陽溪出海口最熱鬧的季節。黑夜裡,海水隨著潮汐漲落,帶來成千上萬條細細透明的鰻魚苗。牠們隨著黑潮從遠方游來,從太平洋一路漂到台灣東岸。捕鰻人會穿上防水的青蛙裝,手持特製的弓形網,在出海口或沿海沙灘等候,趁著海水退潮的瞬間,一網一網拉起鰻苗,靠經驗、靠手感,也靠一點點運氣。
在壯圍,捕鰻苗是一種冬天限定的臨時漁業,也是許多家庭重要的收入來源。鰻苗雖然小小一尾,但價格最高時堪比黃金,故享有「海上白金」的美譽,主要透過外銷日本作為鰻魚飯食材,十分搶手。對於地方的工人、農民、甚至臨時失業的人來說,捕鰻苗是一種可以快速換到現金的方式,一夜捕撈得好,可能抵得上平常一個月的工資。因此,冬夜壯圍的海口,總有許多人們在寒風中守著潮水,也守著家計的一線希望。
夜晚的海口很冷,風裡全是鹹味和海沙味,頭髮總會被吹黏在臉上,船隻捕魚的燈光串起,就像是一條圍住太平洋的珍珠項鍊,微微映照著遠方的龜山島。我很常在等待阿公上岸的時候發呆,阿媽則會跟其他與丈夫同行的阿婆或捕鰻者閒聊,順便探聽大家的戰績。

我們在海邊搭了一個用帆布跟水管做的小帳棚,風一吹會發出啪啪聲。我們都叫它「小烏龜」,因為它彎著背,樣子就像一隻趴在泥灘上的烏龜,背殼裡裝著我們的冬夜生活,也是我們遮風避雨的庇護所,一躲就能躲一整晚的寒風。
小烏龜裡有塑膠凳、暖暖包、阿比仔(編按:泛指藥酒「保力達B」。在農村、沿海漁村,很多做工的人會把保力達當成「日常補品」,累了、冷了,就小口喝一點暖身,補充能量),和一盞等阿公上岸才能打開的舊燈泡,不是為了省錢,而是要把得來不易的電源全數留給鰻苗。
最痛苦的,莫過於在清晨離開冬天的溫暖被窩;有時,我會在半夢半醒間聽見那輛機車發動「啪啪啪」的聲音,混在清晨第一隻雞啼的空檔裡。窗戶透進微微的光,我知道,阿公抓完鰻苗回來了。動作一點也不拖泥帶水,青蛙裝早早褪下垂掛在牆壁邊,等待販仔開著小吉普車來我們家,一到就按喇叭,比我的鬧鐘還準時。他們動作比阿公更快,塑膠桶打開、鰻苗秤重、現金放下,販仔仔細挑揀鰻苗確認數量,再搭配阿媽不時的討價還價,早晨的一陣喧鬧中銀貨兩訖,快速完成交易。
我那時不太懂什麼是「走私」,只知道這些賺來的錢,可以讓晚餐加菜、可以活絡家庭氣氛,讓阿公短暫笑一下。阿公常說:「我什麼都不會,抓鰻仔爾爾(台語,指「只會抓鰻魚而已」)。」但我知道,他不是在抓魚,他是在把日子一點一點撿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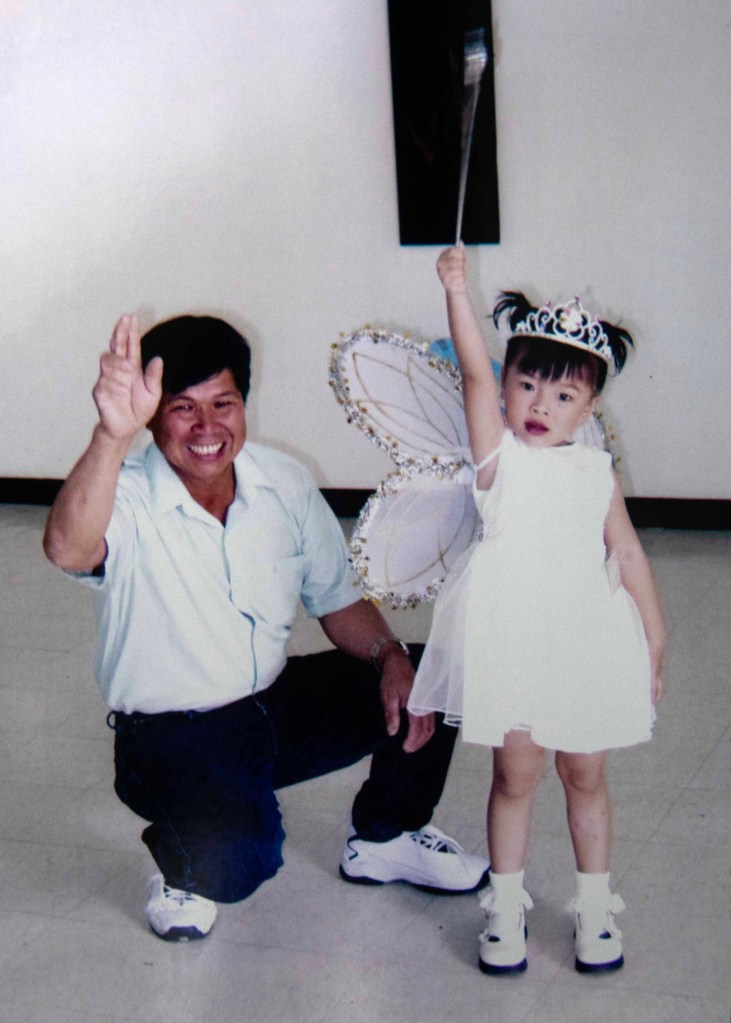
鰻苗情報員
小學的週末,別人是在寫功課,我是在學怎麼挑魚苗。
阿公那時才六十幾歲吧,皮膚被冬天的鹽風吹得粗粗的,臉上永遠都是乾裂和一道道小小的泥巴紋。海上作業時的他不愛講話,動作卻快得驚人。海風凍到骨頭,我穿著厚重的外套還直打哆嗦,阿公只套一件青蛙裝,一樣可以俐落地把弓形網從水裡拉起來。我和阿媽通常待在小烏龜裡等阿公上岸。每當他拉著一大張網從海水裡走回來,腳下黏滿濕泥,我們就會趕緊行動。
阿媽要戴老花眼鏡才能挑,但我不用,小孩子的眼睛利,我的任務是當他的眼睛,我得在網子一拉上岸時,負責打開那盞用電池綁著的燈,聚光在他剛倒出來的那堆濕答答的沙子與雞毛裡,有時還夾雜著沙蚯、塑膠絲,甚至是一堆誰也說不出名字的海邊小生物——找那些閃閃發亮、像玻璃絲一樣的小傢伙。鰻苗在光底下幾乎透明,但會一閃一閃的,那是錢在閃,我懂的。
情況好的時候,鰻苗大出,我們根本來不及多話,挑完一批,阿公就又要趕著下海。抓鰻苗的「翻桌率」愈高,代表抓得多、賣得快、賺得多。那時候的我,不懂行情,只知道抓得多,阿公阿媽總會眉開眼笑的,開心回家吃著熱呼呼的「蛋酒」慶祝;那是用紅糖、米酒和蛋煮出來的,材料簡單,就像阿公阿媽一樣,樸實而自然。
「抓鰻仔不是用眼睛看,要知道浪勢跟手感。」阿公邊說邊扛起那重得不像話的弓形網;一次,我堅持親自下海抓一把,費了好大功夫才撐起網子,一落下的隔天肩膀就印上一道瘀青⋯⋯。隱隱作痛的肌肉記憶讓我又不禁打了冷顫。恰好一尾晶瑩剔透的小鰻苗就在阿公拉開網子的瞬間,在泥沙之間鑽出來,我趕緊用指腹捏起鰻苗,倒入桶子裡,深怕指甲掐傷了苗,變成「白身」(編按:晶瑩的鰻魚苗,如果受傷死亡,軀幹則會由透明轉為白色,並漸漸失去活動力)就大事不妙了。
小烏龜只有在挑揀鰻苗時是明亮的,望著桶子裡游動的白金,那一刻,我忽然懂了,阿公不是在抓鰻苗,他在跟遠道而來的黑潮脈動打交道。

可能是年紀小比較不會遭起疑心,夜晚天氣好時,我也會到別人的小烏龜裡去看看,假裝去串門,其實是幫阿公「探敵情」。別人抓得多不多?用的是哪種網?站在哪個位置?我回來會小聲報告:「他們沒什麼啦,抓的量差不多喔!」阿公聽了有點不以為意,但會默默點點頭,隱約透漏一種「只有他能精準掌握鰻潮游來的黃金位置」的傲氣。
只有一件事我真的怕:上廁所。
晚上海邊很黑,真的很黑。狗會叫,人也陌生。全是叔叔伯伯、煙味、營火味,我這個小女生幾乎是唯一的「異類」。想上廁所得走到沒有燈的防風嶺後面,用雨鞋的鞋尖簡單挖個洞,尿完就地掩埋,就怕被看見、怕有人靠近。下雨天更慘,褲子會濕掉,屁股涼到像坐冰塊,也因為如此,望著那些能夠無所顧忌地在海邊暢飲的捕鰻人們,對我來說是遙不可及的奢侈。
有時天氣太差,阿公阿媽會改開車去海邊。到海邊,如果待在小烏龜,在海邊守著漫漫長夜對一個孩子來說太折磨了。有時候我累了,那裡就是我的第二個庇護所,可以默默爬進車子睡覺。但我記得,每回醒來時,我已躺在家中阿公的床邊,陽光斜斜照在他臉上。那張臉——皺紋像乾裂的河床,皮膚黑得像被木炭刷過,眼下浮著淡淡的黑青,像海水退潮後還殘留的濕意。
在鄉下,大多數人沒能受到太好的教育,年紀輕輕就得出外工作。阿公本業是個工人,白天做板模,冬天晚上接著加班補鰻,工期銜接之間還耕田種菜,工程交替時再耕田種菜;阿媽則是典型的女工,隨著大時代經歷過加工出口的黃金時期,做過成衣,也做過家庭代工,最後在家附近的白蝦加工廠做夜班。而大福村可以說是個不夜城,不管是鰻苗還是蝦子,那都是晚上的事。兩夫妻就這樣慢慢養家,一代過一代,也從沒聽他們喊過累。那時候我還小,但我心裡早就知道:這樣的日子,不是誰都撐得住的。

鰻仔王的雙面人生
外面的人不知道,補鰻苗這件事,是「抓來補洞」的行業。
真正入冬之後,海風把意念吹得消沉,吹得田裡人家錢包也乾。這時候就會出現一群人——他們會無聲無息地冒出,有些騎來的機車沒車牌、也不戴安全帽、雙眼無光。他們不是來看海耍浪漫,是來補洞的:補經濟的洞、日子的洞、債務的洞。有些是賭徒,有些是剛被工地開除的,也有些是毒蟲,揹著弓形網時腳步虛浮,彷彿漁具是沉重的枷鎖,大家只是在夾縫中求生存。這樣的一群人,冬天就在海口成為臨時同事。
阿公就在這樣的圈子裡。
但他跟他們又不一樣。平日裡,他基本上不菸不酒也不賭,唯獨冬天,偶爾喝一兩口阿比仔暖身,或抽幾根交際菸,但一定抽得不多,因為白天我會打開機車座蓋檢查,從零錢和加油站發票堆裡翻出菸盒,然後丟掉。
以前,他很少對外提起自己是捕鰻的。如果問他做什麼的,他會搔頭靦腆的說:「沒啦!以前做板模工,現在半退休種菜兼當清道夫,種菜兼做自行車步道的清道夫啦!」他覺得抓鰻苗不是一份「正經工作」,感覺補鰻的都是混混、沒出息的,他不想讓人以為他也是,刻板印象裡的那樣。
但海邊的事,海知道。
他在那一圈人裡有個名號,叫「鰻仔王」。不管別人多早去、站在哪個點、用多貴的裝備,最後最滿的那一網,通常是阿公的。他的動作穩、眼力準、出手快,一拉網就像表演一樣。鰻苗的出現總是一陣一陣的,論誰也抓不準,苗況不好的時候,才是我們的團圓日。晚飯餐桌上,阿公會突然說起:「欸,最近新來的誰誰誰跑來跟我請教哪個點位最好抓苗,早就跟他說過了,要看技術啦!」他描述的眼神發亮、嘴角帶笑,彷彿一夜回到那片風聲混著鹽味的海口,站在浪邊的是他年輕時那個板模工、養魚人、補鰻王。

我後來才明白,阿公的世界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外面世界裡那個過度謙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是的「老灰仔」;另一個是海口裡最準、最快、最會抓鰻苗的「鰻仔王」。現在他七十幾歲了,每到冬天還堅持要下海。我們都怕他跌倒、受寒,但他總說:「不去不行,讓人搶了我的點,看笑話啦。」他不是怕少抓一點,他是怕少了人記得他曾經是誰。
補鰻不是一份工作,那是他的舞台。
小時候的我只知道抓鰻苗可以換到錢;進入青春期後,我一度討厭海邊的風味,覺得全身都黏上了「矮人一截」的味道。我刻意遠離那些吱吱作響的帆布與破風帳棚。但有時夜裡還是會夢見小烏龜帳棚裡那盞昏黃的燈泡,一閃一閃,像阿公眼裡的光。
是一直到大學,我才重新理解那一切。
那時我考上了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有一次在「民族學」的必修課堂上,教授談到傳統技術的知識系統與地方文化,那一瞬間,腦海裡忽然浮現出阿公拉網時的背影。我第一次有種強烈的直覺——原來阿公的補鰻不是「沒用」,是沒人懂。
我開始蒐集鰻苗相關的資料、做田野筆記,重新回到壯圍海口看了好幾個冬夜的鰻苗燈。我寫了一篇研究報告,那是我第一次用文字說出:我阿公是鰻仔王,他懂海、懂潮、懂風向,他的知識沒寫在書本裡,但卻是活生生的「地方專業」。
後來我鼓起勇氣寫信給韓玉山教授,提到我從補鰻人的田野出發,想繼續深耕人與海之間的關係。在他的鼓勵下,一步步走進了更深的海,而我越往知識的世界裡走,就越發覺:那片海邊泥灘,那些被人輕看的補鰻人,才是這條研究路最初也最深的根。

風知道,海知道,我也知道
後來我念了漁業科學研究所。
不是什麼高大上的志向,也不打算當學者,只是越走越覺得,有些事情不能只是放在記憶裡。研究鰻苗的過程裡,我一頭栽進法規、海洋政策、走私網絡、棲地變遷;但最讓我著迷的,還是那些夜晚帳棚裡的微光。研究所的身份讓我有些自由,我開始辦活動,練習寫計畫,推動海邊文化的在地導覽。最讓我驕傲的是,我終於說服阿公,讓他來當講師。
一開始他很抗拒,「講什麼啦?我又不是老師。」但我拿著麥克風塞給他,「你只要講你怎麼抓的就好。」第一次的他站在海風裡,我幫他拿著小蜜蜂,聲音一開始很小,還會講一半偷笑。但一群小孩圍著他聽,還有人問他:「抓鰻苗是不是很厲害才做得到?」他愣了一下,然後慢慢講起來了,講潮汐怎麼看、講網目的大小、講哪一年遇過大出⋯⋯他像在講一段他自己都快忘了的傳說。
講完那天,有人鼓掌,我看著穿青蛙裝的他滿身大汗,但眼裡裝得全是滿足和成就感。那之後他每年冬天都等我,「什麼時候還有活動?要記得揪我喔。」那片海邊,終於不是他覺得丟臉的地方,而是他的舞台。

我後來畢業了,沒有留在學術界,輾轉去了巴黎,又路續到加拿大、阿布達比,流轉於這個偌大的世界接案當自由口譯,最後回來台灣,決定落腳航空業,每日往返台北和宜蘭之間的通勤職員。上班後的日子變得規律而安穩,但每逢冬天,我知道那是屬於我們的季節,我還是很期待利用週末時間,朋友也好、以前的同學也好,甚至是座位旁的同事也好,我喜歡邀請大家去壯圍看鰻苗捕撈——除了對家鄉獨特的使命感,還有因為我知道阿公還在等那個麥克風。這是屬於我生命的流,像鰻魚一樣在淡水與海水之間洄游,我總喜歡回到宜蘭,跟大家說說這裡的風土滋味。
有一次,我終於帶他去了台北的日本料理店。他抓了一輩子的鰻魚,卻從來沒吃過一口正式的「鰻魚飯」。那天我們坐在吧台,他望著師傅刷醬、炙烤,一臉好奇又有點感慨。「喔~這就是日本人要的喔?」「對啊阿公,你的鰻魚,最後就是這樣上桌的。」
他咬了一口,說:「哇~甜甜的喔,還不錯耶。」
我笑了。抓了五十年多年鰻苗的手,終於握住了那道料理的筷子。我想,那一刻他應該有那麼一點點懂,自己其實不是什麼「沒本事」的人。他做的,是世界另一端也會吃下去、會感動的事。
海知道,風知道。我也知道。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