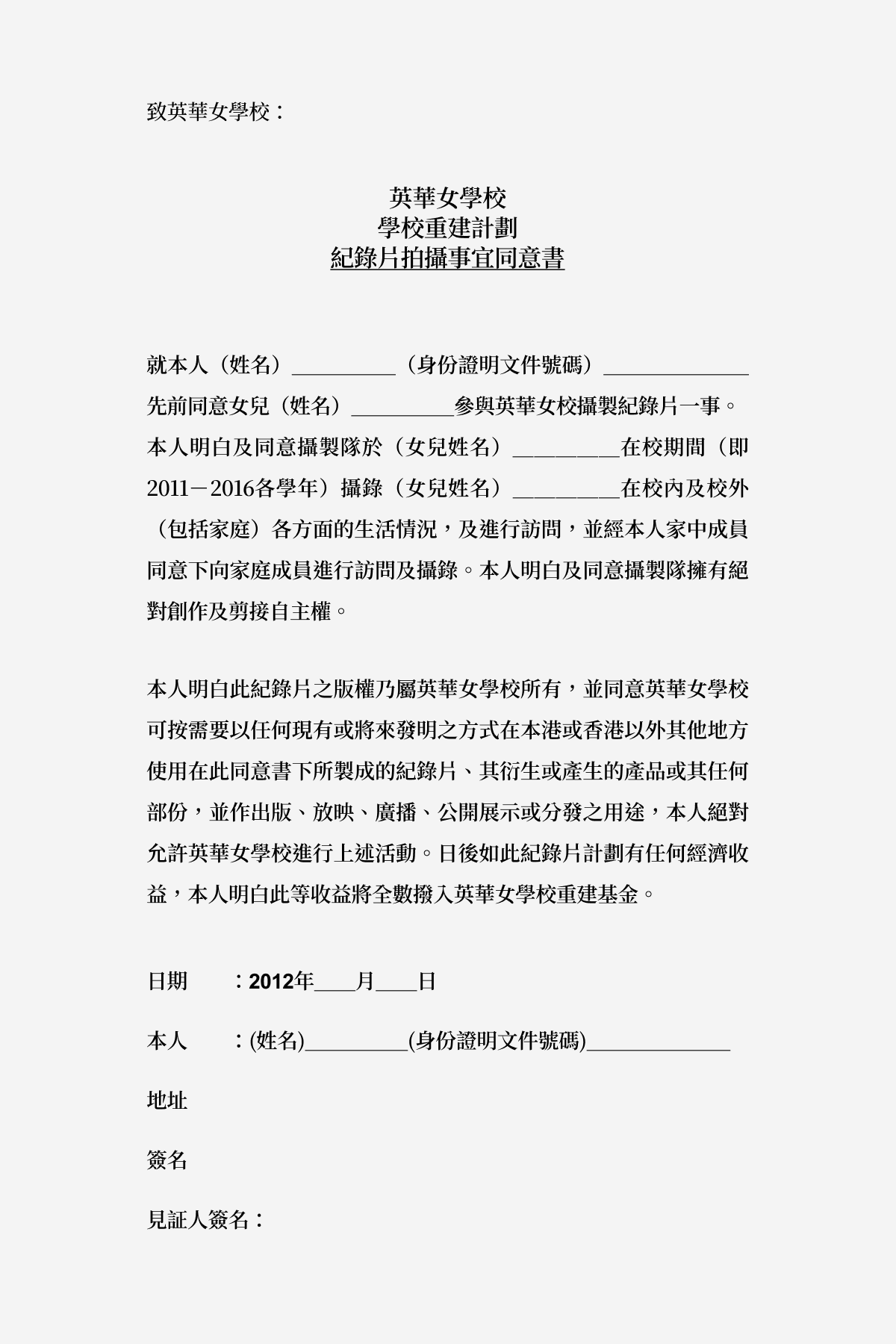
「腸」表示,根據《香港合約法》基本原則,合約雙方都要有付出/代價(consideration),才可以構成合約。付出(或代價)對其中一方可能是金錢(酬勞),可能是服務,雙方有此代價交換,合約才會成立。只確定單方面付出的「合約」,於合約法內不構成效力。相關報導中公布出的同意書中,學生屬無償跟拍,因無酬勞,所以雙方的協議不具備合約的約制力。
即便撇除合約法內的效力,「腸」認為,事件還涉及其他法律要素,比如「資料當事人」對個人資料的自主權。2016年,歐盟成功為「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立法(或稱之為「刪除權」),提倡資料當事人有權要求刪除被不當使用的個人資料。香港《個人資料(隱私)條例》訂立於1996年,寫法相對比較落後,但一般大致會跟隨歐盟私隱法下相稱性和公平性等相關基本原則。在香港《個人資料(隱私)條例》內,個人資料指可以令人辨認到資料當事人身份的資料,《給》片使用的訪問片段影像絕對屬於此類。
《條例》下的「第1個人資料保障原則」規定,收集個人資料需要有合法目的,合法功能,合法用處;其次,收集資料應為合理所需,不可以過量(或必須與所用目的相稱);第三,收集過程要公平。儘管法例一般並無要求先有當事人同意,方可收集其個人資料,但當事人潛在或實際上的反對,仍可能會影響資料收集手法的整體公平性。尤其是,收集資料者除了需要具體地向當事人說明資料將用於的目的外,更有法律責任進一步解釋收集是否必須或自願、當事人可否拒絕、拒絕的後果為何和是否有權其後要求查閱已被收集的資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