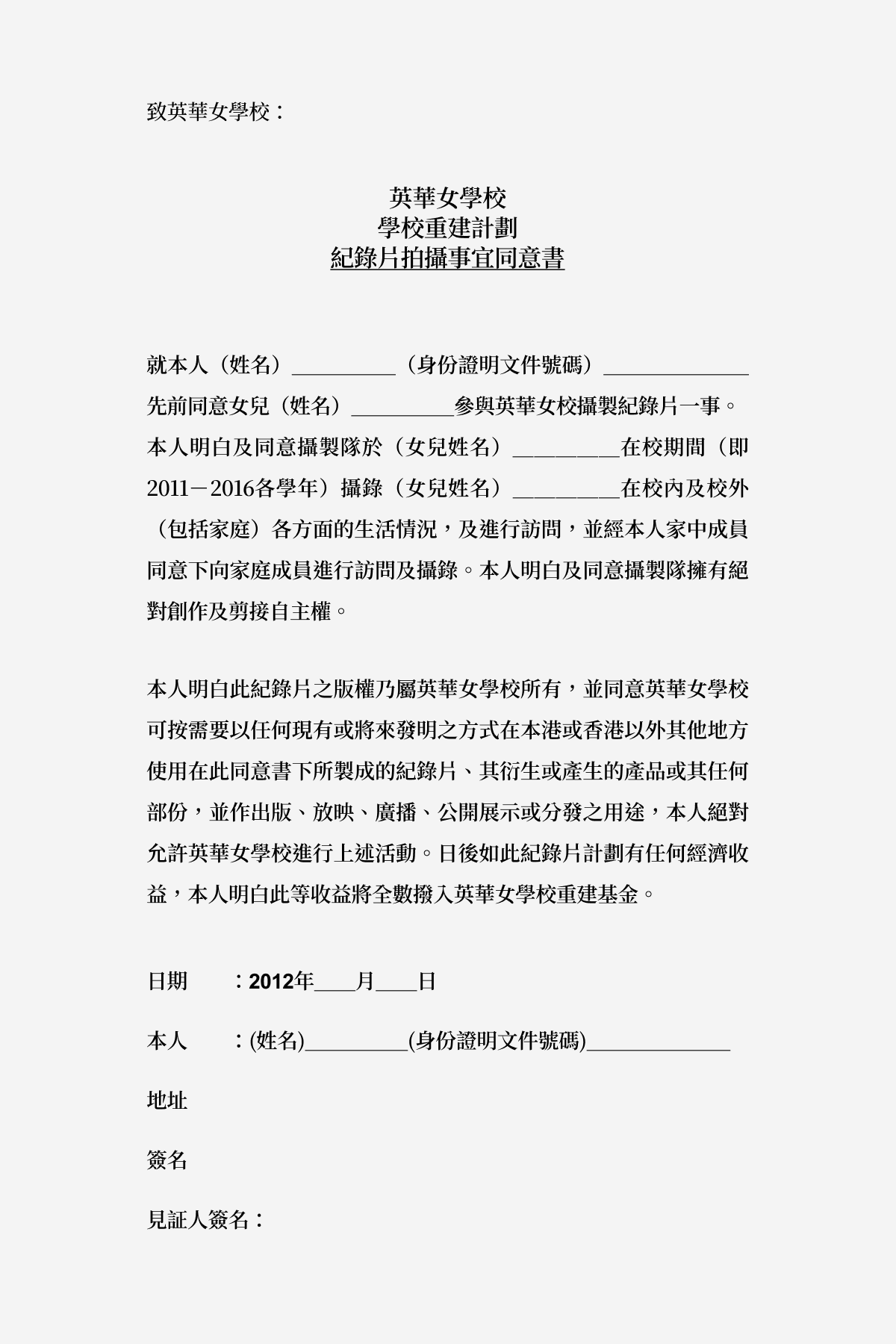
“肠”表示,根据《香港合约法》基本原则,合约双方都要有付出/代价(consideration),才可以构成合约。付出(或代价)对其中一方可能是金钱(酬劳),可能是服务,双方有此代价交换,合约才会成立。只确定单方面付出的“合约”,于合约法内不构成效力。相关报导中公布出的同意书中,学生属无偿跟拍,因无酬劳,所以双方的协议不具备合约的约制力。
即便撇除合约法内的效力,“肠”认为,事件还涉及其他法律要素,比如“资料当事人”对个人资料的自主权。2016年,欧盟成功为“被遗忘权”(right to be forgotten)立法(或称之为“删除权”),提倡资料当事人有权要求删除被不当使用的个人资料。香港《个人资料(隐私)条例》订立于1996年,写法相对比较落后,但一般大致会跟随欧盟私隐法下相称性和公平性等相关基本原则。在香港《个人资料(隐私)条例》内,个人资料指可以令人辨认到资料当事人身份的资料,《给》片使用的访问片段影像绝对属于此类。
《条例》下的“第1个人资料保障原则”规定,收集个人资料需要有合法目的,合法功能,合法用处;其次,收集资料应为合理所需,不可以过量(或必须与所用目的相称);第三,收集过程要公平。尽管法例一般并无要求先有当事人同意,方可收集其个人资料,但当事人潜在或实际上的反对,仍可能会影响资料收集手法的整体公平性。尤其是,收集资料者除了需要具体地向当事人说明资料将用于的目的外,更有法律责任进一步解释收集是否必须或自愿、当事人可否拒绝、拒绝的后果为何和是否有权其后要求查阅已被收集的资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