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記引發的代際衝突,也走向了集體舉報。幾位中國高校的教授或退休教師公開表態支持方方後,均遭到舉報(罪名為支持港獨、台獨或批評中國共產黨)而被學校調查。在這一點上,方方日記和香港反修例運動所引發的輿論大字報殊途同歸。不同之處在於,後者在主流輿論場沒有討論空間,前者還能「負隅頑抗」,發聲回擊。
方方譴責帶頭者是想回到文革的「極左分子」,紅三代導演葉大鷹也表態因為「痛恨用政治口號煽動仇恨的那些人」而聲援方方,科技日報總編輯劉亞東則將攻擊方方的年輕人稱為「反對改開的新生代」。
另一邊的陣營則把「文革」的帽子丟回去,胡錫進回應方方,「你自己的詞庫裏有相當多『文革時代』的暢銷詞」,身為紅三代的「意見領袖」兔主席更為直接:「上綱上線貼標籤,在年輕人看來,這才是文化革命遺物。把極左帶回的其實是方方本人。」
無論哪個陣營才是文革回魂,代際矛盾都在這場衝突中清晰可見。兔主席對《武漢日記》在美國預售的點評受到眾多年輕人的認同:「這本書會作為重要素材被輸入到國際反中輿論裏,成為 『反中產業』 的一部分。它註定將為國際反中力量添磚加瓦,提供寶貴彈藥。」
一、方方日記面對的新問題
對方方的攻擊並無新意,無非「造謠」、「負面」、「遞刀」等說法。作為新現象出現的,其實是輿論容忍尺度的極速收縮。承受大量責難的《武漢日記》,內容可謂相當剋制,不僅時時體恤基層公務員的辛苦,被醫護人員感動,誇讚年輕志願者,為新增病例的減少而開心,甚至被全民指責的前武漢市市長也在日記中得到理解。方方要求的問責,僅限於湖北省和衞健委的官員,對政治體制沒有一聲質疑。也因此在真正的體制批評者眼中,《武漢日記》太過温和,沒有切中實質問題。
「難道我們這些活着的人,為讓自己生活得輕鬆,就可以不幫助他們這些枉死者追責嗎?」這樣的句子已經是《武漢日記》中相對最激烈的言論,但是跟十年前體制內改革派的言論相比,都不算出格。
2008年汶川地震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曾援引憲法,發表文章《哀悼不哀悼是公民的自由》;2011年,同為北大法學院教授的賀衞方公開批評重慶的「唱紅打黑」,表示應該通過司法改革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即便到了習近平「新時代」的2015年,經濟學家茅於軾也在文章中直言「任其(官員侵犯公民自由)存在下去,中國實現法治民主將遙遙無期。」這些言論當時也引來官媒的攻訐,但是在輿論生態中並非特例,也沒有遭遇方方式的民間圍攻。「煽動顛覆」、「境外敵對勢力」之類的政治話語,在當年公民意識尚有一席之地的輿論場受眾有限,甚至可能遭到網民嘲諷。
時過境遷,一場瘟疫降臨,來自體制內的追責聲音,幾乎只剩方方。華中師範大學教授戴建業稱她為「單槍匹馬」,在這個意義上十分準確。而方方面對的是一個更加保守的輿論年代,她說這是一場瞞報導致的「人禍」,年輕人大受冒犯,反問「你是說這是中國的鍋嗎?」;她說湖北官員的表現是中國官員平均水準,年輕人聽着也很難受,表示「過於主觀」。
方方的困境,在於她面對的新世代,是真正把官方的意識形態內化為自身問題意識的一代。他們舉報方方和詩人王小妮,熟練地定罪,「顏色革命」、「境外勢力」、「帝國主義」,並非圖一時嘴快,而是真心相信如此。他們被斥責舉報可恥,反而會深感委屈,因為政治教科書和共青團中央的微博教導他們,舉報是國家給他們的權利和義務。當然,這些政治詞彙是用在舉報中的「書面語」,在日常討論裏,方方的罪名則是「歪屁股」,是「踩一捧一」,也是「遞刀子」。
一場新舊之爭,同時也是代際戰爭圍繞方方日記而起,成為疫情後中國社會最顯著的撕裂。一方是職業網評員帶領的年輕世代,另一方則是仍然希望澄清「公民和政府的關係」的湖北大學教授劉川鄂,強調「啟蒙常識」的南京大學教授丁帆,說明「文學是良心的事業」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家新等人,都已經過了人生中途。戰火不止於社交媒體,甚至燒到了不少人的家庭群、校友群。
光怪陸離之處在於,新的世代承接的話語體系比上一輩人更為陳舊,更接近1950、60年代的中國(例如一個基層年輕警察引用《毛選》痛批方方),但是從全世界民粹嶄露頭角的潮流看,他們毫無疑問又是新的。而被當局打散的「公知」時代殘留的啟蒙話語碎片,和改革開放後體制內的開明派餘音,相對於年輕世代的「保守」,這些聲音卻更加「進步」。新舊交戰,究竟孰新孰舊,難以辨認。

二、遞刀論和「叛國」
方方的《武漢日記》在國外翻譯、出版,成為這場新舊交戰最核心的衝突。一度因扮演開明派而被網民貼上「公知」標籤進行嘲諷的胡錫進(3月19日還為方方做了有限辯護),也及時調整姿態,在4月8日擺明立場:日記被拿到美國和西方去擴散,一定會被國際政治利用,從而損害國家利益。
遞刀論在支持方方的陣營看來不可理喻,他們的回應路徑,一是「瞞報疫情、訓誡醫生才是遞刀」,二是「照此邏輯,國外的負面消息也是遞給中國的刀」。問題在於,遞刀論已經拒絕在是非(價值)問題上繼續糾纏,而乾脆後退了一步,承認「家醜」也不可外揚,第一條回應路徑失去了對話可能。第二條回應路徑,正好切中遞刀論的另一面——不能把刀給敵人,因為我們要攻擊(反擊)對方。
從4月27日開始,央視《新聞聯播》連續半個月播發評論,指控美國甩鍋、污名化中國、隱瞞疫情真相、散播政治病毒、把天災變成人禍、玩弄美國民眾生命,攻勢迅猛。《人民日報》不時轉發《紐約時報》對美國疫情失控和失業人數上漲的報導。外交部也在5月9日發文,逐條反駁美國對中國的指控,甚至直接否定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存在野味交易。在此之前,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拋出病毒是由美軍帶到武漢的陰謀論,早已在國內的輿論場引起共鳴。
《環球時報》5月11日一篇社論,講出了當局對中美關係的現實判斷:「美國對華指責已經完全上升到輿論戰的級別。」央視和外交部的宣傳攻勢,以及社交媒體上大量關於美國疫情的負面消息,正是中國參與輿論戰的彈藥。方方《武漢日記》在海外出版,因此才被遞刀論者圍攻。他們口中的西方敵對勢力、帝國主義、反動派,不僅僅是極左毛粉(如方方所言)的招魂,而是基數更龐大的國家主義者進入「戰時狀態」對方方的指控。
前文提到,方方《武漢日記》的言論尺度,放在十年前的「公知時代」並不算出格。當年不少評論者呼籲憲政改革,批評維穩勞民傷財,借西方經驗反思中國現實,也甚少會有「遞刀」罪名。主要原因,在於當年中國仍然遵循着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國際形象不如今天一般好勇鬥狠,而同時,民間的政治討論也被看作是關於中國自身發展的不同意見,雖經常與西方民主體制對比,但那時並沒有明確的「敵人」形象。
在當下,由於中國近年加速的外部擴張,遞刀論者所感受到的「列強環伺」的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真實的。從特朗普稱中國對疫情暴發負有責任,再到美國密蘇里州起訴中國要求賠償,以及中國官媒連篇累牘地指責美國抱有冷戰思維、重返麥卡錫時期,加上雙方互相拋出的病毒陰謀論,和2018年開始的經濟脱鈎,已經說明兩國結束了「戰略接觸」,進入近似於冷戰的對抗關係之中。
全球疫情暴發後對中國顯露出敵意的不止美國,法國總統馬克龍公開批評中國在抗擊疫情時有所隱瞞,英國外交大臣拉布表示未來可能就疫情跟中國「算賬」,澳大利亞也展開了對疫情起源的全球調查,甚至親中國的伊朗都對中國疫情數據表示過懷疑。
不過,與其說遞刀論者因回應外部威脅而進入「戰時狀態」,毋寧認為這樣一個歷史時刻正是他們所渴望的。胡錫進幾天前公開宣稱中國需要在短期內將核彈頭數量擴大至千枚的水平,引起廣泛贊同。同一時間,解放軍少將喬良在香港接受採訪,表示當下未到武力統一台灣的時候,應該以民族復興為重,在微博被網民批評為「投降主義」。民眾對宣示武力表現出來的熱情,甚至比鷹派軍人還要高漲。
對宣傳系統來說,只在國內批判西方敵對勢力已經不足以爭取民心,人們渴望見到霸道、強硬的對外宣傳。《人民日報》4月份在微博發了一系列海報,對比中美政府的抗疫作為(中國「全力抗疫」,美國「甩鍋推責」;中國「公開透明」,美國「詆譭抹黑」),然而即便是親政府立場的網民,也不滿意這個做法,他們評論「你應該發給美國人看,發微博有啥意思」,「中國在國際輿論上吃虧了,人日立即在國內說美國壞話……盡窩裏橫」。
「外宣軟弱」是不少網民對宣傳系統不滿的表達,民族主義情緒召喚的是趙立堅「戰狼式」的對外攻擊,哪怕作為武器的是陰謀論。對宣傳系統的不滿甚至發展出這樣一種論述來批評審查:因為對內的宣傳審查太過嚴格,媒體完全服從於政府,導致記者沒有戰鬥力,缺乏鬥爭經驗,在輿論戰之中無法和西方對抗。換言之,在輿論戰的大背景之中,內部的媒體監督被認為是一種練兵,有助於壯大外宣。
在最近一場網絡研討會中,自由派知識分子錢永祥、劉擎、周濂、周保松四人就對當下中國排他性的「愛國主義」表示了擔憂,並認為危險之處在於這種話語背後的壟斷性。如果順着這個思路推理,當「愛國」被一種論述所壟斷,那麼其他所有的異議都將有可能承擔「叛國」的指責。
因此才能理解,為什麼方方從未在《武漢日記》中否定中國體制,反對者卻不斷在這個話題上做文章——擴張性的民族主義需要意識形態武器做內部動員。新四大發明代表的科技進步,留學生愛國宣言壟斷的比較政治,全球抗疫競賽輸出的自信敘事,共同催生了擴張性的民族共識——中國體制具有優越性,一種混合了文化、種族和政治制度上的民族自信。

三、第三帝國的幽靈——極端國家主義
方方的《武漢日記》寫到後期,有相當大的篇幅都在與「極左」筆戰。她解釋自己所說的「極左」,是指用階級鬥爭語言批鬥她的烏有之鄉郭鬆民等毛左,而非網上罵她的年輕人。
方方和毛左結下的仇怨,可以追溯到2016年出版小說《軟埋》後,三名前中共高官發文批判,認為她否定了土改政策,為地主階級翻案。而方方擺明的立場是,極左是改革開放最大的阻力。雙方接續的是「姓資姓社」的陳舊歷史爭論。至於攻擊她的年輕人,方方則用「不明真相」一語帶過。
聲援方方的紅三代葉大鷹,所站定的思想立場,也是改革派對文革舉報狂潮的反思,是鄧小平時代「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的歷史經驗。但他同樣期盼更強硬的對外宣傳,是絕對的民族主義者。足球運動員郝海東也支持方方,他的「公知」屬性則更強一些,他講「獨立思考」,用「五毛」和「小粉紅」標籤對手,也用三聚氰胺奶粉、毒疫苗等社會事件進行批判回擊。和方方跟葉大鷹相比,郝海東無疑更具自由派的啟蒙意識。
圍攻方方、葉大鷹、郝海東的大部分年輕人,儘管也學會不少文革話語,但是他們並非傳統的極左,也不是被極左矇蔽的「不明真相的群眾」,而是呼喚強人政治家領導大國崛起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對他們來說,方方三人究竟是改革派還是公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都批判了國家。儘管只是微不足道的批判,但是在中美對抗的「戰時狀態」之下,無疑也是一種「叛國」。
從歷史維度看,當下中國對強人政治的召喚所接近的年代,比起文革前的1950年代,更接近第三帝國到來之前的1920年代。
理查德·J. 埃文斯在《第三帝國的到來》中重現了這個戰爭來臨之前的年代:失落的德國人渴望一個強硬的中央政府,帶領他們通過民族復興運動,恢復往日的德意志強國,提升德國的國際地位。他探究了納粹黨活躍青年的使命感來源於何處,答案是為了德國的民族團結,德意志文化的繁榮,對一戰中德國戰敗的創傷記憶,以及絕對的愛國理想。
當下針對少數不同意見人士大規模的圍攻和舉報,所反映的現實是,極端的國家主義觀念正在橫掃輿論場,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保皇黨還是改革派,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只要這種批評被認為會遭到西方敵對勢力利用,它就會遭到猛烈攻擊。
這也是曾經的「公知」群體的無力感所在——劉擎在談論當下的愛國主義情緒時是沮喪的:「忿忿不平的情緒一定要長大,否則會把國家帶向災難,比如德國從一戰後被欺壓到全民想要報復。」周濂也表達了自己的困惑:「現在是是非黑白顛倒的一個時代,人們普遍認為偏愛、死忠、愚孝才是真正的愛、忠、孝,而以理性、客觀、中正為恥。我們面對的是這麼一群人,怎麼辦?」
這場由方方日記引起的輿論風波,迴盪出的是越來越國家主義的青年聲音。而隨着年輕一代對批評政府的聲音愈加敏感、對鬥爭經驗的愈加熟練,思想光譜上無論什麼顏色的人,可能都將不得不以對國家的絕對讚美,來換取自己未來的安全。
(張美悅、李瑞洋對本文亦有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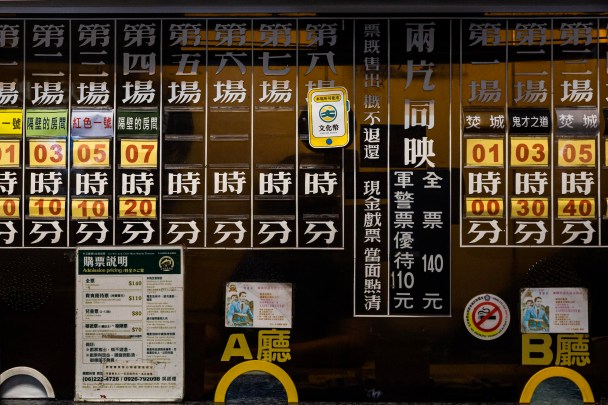
楼下那个ATTT好好笑,一个生动的内地精致利己主义者画像,大概从来没有共情过真正弱势的但却与你无关的人事,幸运又冷漠。我并非方方的支持者,然而“批评方方的自由”说得更是轻巧,以几千、几万为计数单位的辱骂体现的可不是“批评的自由”,换了任何一个普通人如你,可以接受每日有几千几万人在网络上揶揄讽刺你再轻巧地这样讲吧。就像跟随帝吧出征喊打喊杀的人也会在自己的微博被无缘无故封掉的时候大喊冤屈哀叹自己记录的生活痕迹湮灭。只是没想过时代的一粒沙会落到自己头上罢了。
這樣說吧,你能活著,也是國家的恩賜,你還談什麼自由。國家要你的性命和財產,你也要立即奉獻。
作为一名中国年轻人,感觉自己被代表了。网络上有很多对方方口诛笔伐的,但年轻人占比究竟有多少呢?而维护芳芳的一派中,年轻人也不在少数啊。这两派之间并不是代际之争,而是意识形态的割裂。只不过维护方方的年轻群体天然携带更多激进情绪,在传播中更占便宜,造成一种年轻人无脑当前锋的错觉。
五毛全面滾出端傳媒!
再补充一点,还有一种希望壮大外宣力量的论述是,呼吁拆掉墙,这样才能把“香港的真相”传递到墙外去,才不会纵容墙外抹黑和胡说八道。
madlex6
1、“建議你去看看台灣記者們對反修例運動的採訪live,他們不懂粵語,受到的待遇卻十分友好。”
那是你看到的部分,我和你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吧:1、我的一个印度朋友,学了好几年的中文,在香港说普通话打车,被的士司机臭骂,我朋友非常愤怒;2、我的两个大陆朋友,在香港街头两次被人莫名其妙的泼水泼可乐,就因为他们说普通话;3、我的一个香港新移民朋友,小孩在香港读书,因为自己原生家庭来自大陆,说普通话,被小朋友活生生孤立,他只有九岁,就要面对这些莫名其妙的仇恨,导致自己产生了严重的自卑和自我怀疑;4、我的一个在港资企业的朋友,在11月区议会选举结束以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她的香港老板十分得意洋洋的对她炫耀:你们中国人就是废柴,前面叫得凶,投票的时候就不来;5、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在一次铜锣湾逛街的时候,突然遇到暴徒闹事,她想拍一段视频,突然被五六个一米八的黑衣人围住,强迫她删除手机里的照片,这才给放走。
以上五个是我听到的,他们所有人都政治冷感,到香港只为挣钱、读书、移民、生活,除了这些以外,我还看到过往上有日本人因为说普通话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所以你说我骑劫台湾人新加坡人?不好意思,我骑劫所有说普通话的人,因为你所看到的现场,不会说粤语的台湾记者受到友好待遇,从我周边的例子来看,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如果我一个人就能知道这么多,全香港有几十万上百万说普通话的人,他们这种因为你这类傻逼而导致的恶心经历该有多少:)
2、說到底就是在現場,你無法打消你是中國人而給示威者帶來的疑慮,這是十分現實的問題。
这个问题又回来了,你们如果要针对你们口中独裁无耻又专制集权的邪恶政府,那就去找他们算账,仅仅因为我是大陆人的身份,我人畜无害的在香港待着,无法消除给他们带来的疑虑,我就活该挨打,这还他妈的是现实问题?!我的大陆人身份还变成原罪了?这问题难道还要我来解决?拜托,是你们自己分不清楚好吗?照你这么说,1930年代,犹太人就因为他们的身份问题,无法消除纳粹对他们的疑虑,他们就活该被扔到集中营里面拿去榨油做肥皂呗?你确定你有逻辑吗?你是智障吗?你打算搞种族屠杀制造下一个卢旺达吗?
3、你猜猜,你用英文講“I'm Chinese”會不會被當成洋人對待?躲在普通話這一標籤後面,非常怯懦。
照你的意思,我堂堂一个中国人,在香港的街头,连说普通话的权力都没有了?我还得说英文才能避免挨打?你的心里还是对洋人跪着的洋奴才吧?你的膝盖见到洋大人就会发软吧?我算是明白为什么网上有大陆人出门需要几个白人朋友陪着了,我也理解为什么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泽会说出他对于自己的身份很羞愧了,原来你们见到洋大人真的会腿软下跪,自己心里默默的就把人种分出了三六九等,洋大人最大,你们港台人其次,大陆人垫底,你们是高等级华人:)
4、香港人就是不喜歡中國人,因為大部分中國人就是共產黨的幫兇,而這個標籤就是你們這些粉紅或者“理客中”的中國人自己造成的。
大部分大陆人,和全世界的老百姓没什么区别,他们平时政治冷感,共产党什么的他们一点也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柴米油盐,他们觉得政治很无聊,像我这样的人在现实当中都是少数而已。我刚才说的周边的五个例子,都是政治冷感的大陆人。可他们就是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你们喜欢贴标签,给大部分大陆人贴帮凶二字,足见你被垃圾媒体洗脑洗成了怎样的智障,你这种人,连批判文革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在文革时期,搞武斗会比当年的红卫兵更狠:)遇到了问题就甩锅,这种loser做派,你们在多次堵机场、堵地铁、堵隧道的过程中展现的淋漓尽致,真的是傻逼至极:)
“为什么方方在从未在《武汉日记》中否定中国体制“多了一个在字。
“来自体制内的追责声音,几乎只剩方方“一句并不完全准确,体制内发声的高校教师不少,但相关文章和音频大多被封杀殆尽。方方日记虽也被微博和微信反复屏蔽,但总的来说没有遭到官方禁绝,就在严密审查下的舆论场中显得突兀了。
此外,同意作者对于代际差异的判断。有时发觉,授课老师的思维比学生还要开放,用词也更加谨慎,不会使用盛行于社交平台、贬义色彩特别强烈的词汇。“又红又专”的老师尚且能被当作某种典型样本进行分析批判,年轻人却代表着未来社会成员的主流,建构着我们将被深深卷入的未来。
正如陈纯所言,“我们如何正视越来越多年轻人比体制自身还要反动的现实?”
@ATishero 你看,你又騎劫台灣人新加坡人了。把香港人對中國人的反感擴大為對講普通話人士的歧視。建議你去看看台灣記者們對反修例運動的採訪live,他們不懂粵語,受到的待遇卻十分友好。說到底就是在現場,你無法打消你是中國人而給示威者帶來的疑慮,這是十分現實的問題。你猜猜,你用英文講“I'm Chinese”會不會被當成洋人對待?躲在普通話這一標籤後面,非常怯懦。香港人就是不喜歡中國人,因為大部分中國人就是共產黨的幫兇,而這個標籤就是你們這些粉紅或者“理客中”的中國人自己造成的。當然,如果是支持民主自由的中國人,那就是手足了,也許你不知道運動中那些公開支持香港而被迫流亡的講普通話人士吧。
@weber
“你身為中國人,自認為自己怕被打就有資格去香港掃射屠殺,另一頭一堆人在討論日本人屠殺中國人就是不能被討論、提及的萬惡,對比之下真是好笑。”
1、你真的懂语文么?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说我怕被打就有资格去香港扫射屠杀了?你看不懂反问句?我是在对下面一个留言回复的反问啊,到了你这里就变成陈述语句了?另外你也认为自己怕被打就有资格去香港扫射屠杀不对是吧?那么你又认为香港人游行示威伤及无辜是可以理解的?这得多人格分裂虚伪至极才能做出这种双标的事情:)
2、另一堆人讨论日本屠杀中国人不能被讨论。我没有看到这种言论,你不要随意拿来往我身上套,我只对我自己的言论负责,不要为了说服我找一些其他地方别人的言论,不要干碰瓷的事情:)
@Weber
“你說香港人是為了"崇高"的理想...? 不,至少我從台灣這邊看到的都是非常基本的要求。所謂的"崇高"應該是港人在遊行時的自我約束,尤其是在初期為了自我團結,讓人人都會願意上街,所以才會抱持著"和理非"這樣的崇高要求上街。甚至可以說,這種你所謂"崇高"的自我要求應該也是為了製造"穩定"這種基本需求而產生的、因為"穩定",香港人才能平日上班、周末遊行,你也才能自認為到香港不應該被當地人打死。
可是創造"穩定"的基礎一直在崩塌。”
是崇高的理想还是基本的需求,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没有标准答案,你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争个对错,认为你是真理,OK啊随你怎么说我无所谓。但你绕来绕去,不就是想说政府混蛋所以老百姓不信任政府,不愿意和平理性游行么?那你不想和平理性游行,去打政府啊,该烧哪儿烧哪儿去啊,干嘛要打无辜路人?干嘛威吓警察家属?A欺负了你,你不去搞死A,反而把无关无辜的BCD拖下水打的半死,然后告诉他们这都是A逼我的,有人强奸了你,然后你去把他的邻居打死了,这得多么虚伪才能说出这种话?这得多Loser才能干出这种事儿?你还有脸辩护?
@weber
“早在反送中運動爆發前,台灣人在香港說普通話就會有令人厭惡的風險,而台灣人多能表示理解。而你對其他地方的住民要求這麼多只是為了讓自己能放心逛街? 呵。”
台湾人多能表示理解?谁给你的权利代表的台湾人,我找了周边三四个台湾朋友给他们给他们看你这段原话,他们没有一个能表示理解。我还有个中文说得很好的印度同学,他曾经有过在香港说普通话被香港人厌恶的遭遇,他感到十分愤怒!香港人讨厌北京,就要连同说普通话的大陆普通民众一起讨厌?那川普说Chinese Virus的时候,在美国的亚裔人就活该挨打应该被理解了?有你这种人,我算是理解为什么杨安泽会说出那么自卑的话了,会那样的跪舔美国人了:)
另外,香港对我来说不是其他地方,而是我居住的地方,我对我居住的地方只是要求他们在游行示威的时候不要伤及无辜,这个要求很多?我想放心逛街这有什么错?合着他们讨厌政府讨厌北京痛恨体制,然后我非得在逛街的时候活该被他们打一顿,然后还要对他们表示理解才行?你确定?这是多么虚伪的一套东西啊!
@ATishero:
你說香港人是為了"崇高"的理想...? 不,至少我從台灣這邊看到的都是非常基本的要求。所謂的"崇高"應該是港人在遊行時的自我約束,尤其是在初期為了自我團結,讓人人都會願意上街,所以才會抱持著"和理非"這樣的崇高要求上街。甚至可以說,這種你所謂"崇高"的自我要求應該也是為了製造"穩定"這種基本需求而產生的、因為"穩定",香港人才能平日上班、周末遊行,你也才能自認為到香港不應該被當地人打死。
可是創造"穩定"的基礎一直在崩塌。
早在反送中運動爆發前,台灣人在香港說普通話就會有令人厭惡的風險,而台灣人多能表示理解。而你對其他地方的住民要求這麼多只是為了讓自己能放心逛街? 呵。
你身為中國人,自認為自己怕被打就有資格去香港掃射屠殺,另一頭一堆人在討論日本人屠殺中國人就是不能被討論、提及的萬惡,對比之下真是好笑。
madlex6 小時前
好好笑,為甚麼相對外國人,示威現場示威者要對一個講普通話的人更為警惕反感?因為大部分講普通話的人更為匪諜,更會為共產黨做事,更會偷拍人像進行起底。某個冷氣仔是否可以直接答我,是否存在這種風險,示威者是否應該自保?yes or no?揮舞歧視大棒的時候,卻身體力行助紂為虐,以客觀中立為名,行支持強權之實,實在無恥啊,中國人。
这我就奇怪了,你们反感共产党给人扣帽子,怎么自己给别人扣帽子扣得这么起劲,讲普通话的人在香港几十万上百万,还有好多台湾人新加坡人,他们都是给共产党做事?都是共匪?自己怕被起底就打人?那我走在游行人群当中我怕被打是不是应该端着冲锋枪把他们都突突了呢?我也害怕啊。非怪暴徒会不小心把几个日本人给打了,可能是他们普通话说得太好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承认,该割席就割席,你们为了崇高的理想去争取,去游行,没人说你们什么,但我就是看不起你们过程中做了这么多错事坏事还要圆谎,还什么不割席,还要找理由,找出各种荒唐无比的理由,怂逼,无耻,虚伪,双标:)
taka1
我發現港台很喜歡用太監比喻大陸自由論,太監淨身後,會說那東西是不好的東西。如果用你扭曲的言論自由比喻,你可以不淨身,可以站著小便,但每次小便你那裡都要割一刀,這不是太監自由的體現麼?
请问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说言论自由不好了?要想说服我就偷偷加点料,你还真是有本事哦:)我对方方无感,她的日记看了一点,写得就那么回事,我不赞同递刀子的论调,这很蠢,她写得那些玩意到处道听途说找不着根据,无聊的很,也不至于干死这么大个国家。但我对她成天把所有批评她的人都归为极左红卫兵或者什么五毛战狼感到非常反感,怎么着你敢写还不敢让人批评?批评一下就是政治迫害?就是极左五毛文革复辟?那合着我们还没有批评她的自由了?必须所有人都对她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你这作品必须要拿诺贝尔文学奖这才行?说难听一点,这和当年柴玲说的要故意惹共产党开枪让学生血流成河就是一个性质,俗称政治碰瓷,幸亏不上当,指不定这会儿这个女人在盼着有人删掉她的账号封了她的嘴巴呢,那样她就更有理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饱受集权体制迫害为自由民主发声的民主斗士了,你们也可以给批判共产党添砖加瓦了:)
某些中国人的语言是不是越来越粗俗了?天天就是屁股歪、抄作业、递刀子,有种当街拉屎的感觉。不想跟这些人对话。
如果說70後乃至85前是中港台三地青年主流價值觀較為接近的兩代人,那麼90後00後則是中國大陸與港台青年主流價值觀分道揚鑣的兩代人。這十年來,青少年接觸最多的不再是港台文化,而是以泛韓及新興本土文化為主流。伴隨他們成長的是螢幕上的古今霸道總裁/皇帝,手機遊戲裡的王者英雄,這些icon 無一例外宣揚的是「霸道」「弱肉強食」「強人統治」。80年代~90年代流行的文化反思,人文關懷,西風法雨在過去十年已被新世代拋棄。從新世代對歷史人物的情況可見一斑:維護(皇權相權台諫)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宋仁宗被視為窩囊無能,獨裁專橫殺伐決斷的康雍乾則在影視化中化身古代霸道總裁偶像,獲得無數女性追捧。如果說10年前的毛左絕大多數都是男性,近10年來的新興左派愛國青年中女性比例則急遽升高,無論是國內討伐還是翻牆誅敵,女性網民都積極參與,且戰術和話語術絲毫不弱於男性網民。正是由於新世代中國年輕女性的參與,戰狼人數倍增,令人有紅色巨浪席捲網絡,世代決裂之感。
"她可以自由自在的说着她想说的话,她有说话的自由别人有攻击她的自由,这不正是言论自由的体现么?"
我發現港台很喜歡用太監比喻大陸自由論,太監淨身後,會說那東西是不好的東西。如果用你扭曲的言論自由比喻,你可以不淨身,可以站著小便,但每次小便你那裡都要割一刀,這不是太監自由的體現麼?
好好笑,為甚麼相對外國人,示威現場示威者要對一個講普通話的人更為警惕反感?因為大部分講普通話的人更為匪諜,更會為共產黨做事,更會偷拍人像進行起底。某個冷氣仔是否可以直接答我,是否存在這種風險,示威者是否應該自保?yes or no?揮舞歧視大棒的時候,卻身體力行助紂為虐,以客觀中立為名,行支持強權之實,實在無恥啊,中國人。
记得王丹曾在刘晓波葬礼上说共产党的诸多作为表现出精神病人的病理特征,我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晓波自己还曾经说过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呢,然后说自己不在乎被骂,这才是精神病吧。
感谢端的深度文章
真有意思的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忧虑,可现在方方的微博已然保留着,没有人删她没有人关她,她可以自由自在的说着她想说的话,她有说话的自由别人有攻击她的自由,这不正是言论自由的体现么?
嗯嗯,你开心就好。
对不起,我漏掉了一点。其实没有人长尾巴。
有的人自己长尾巴,就以为别人也长尾巴,还大力往别人的屁股后面的空气跺跺脚,煞有其事的说,哈哈,你的尾巴被我踩到了!
正常人難道不該更關心刀從哪來嗎
遞出去之前是要用來砍誰呢
被砍的人紛紛在說別把刀遞出去 被砍的人也成了砍人的人 是怎樣病態的中國文化
“跪舔”不过是一个轻松的非严肃的一个俗语而已。其主义意在指出被标榜的的所谓不卑不亢的态度在实际从我看来并非如此。所谓“洋垃圾”这样带明显侮辱人格的词汇我是不取的,而且我也反对其使用,所以不知为何其在此被提起。
反正我只想指出“港台人对西方人都学会了不卑不亢”这样的观点并以此来证明比中国人高人一等的做法是有些可笑的。如果有人的尾巴感觉被踩到了,那还烦请各位将尾巴收得离屁股紧些。
现在国外真正的问题并非是存在对中国的批评,而是对中国情况的真实反映太少。中国就像个“黑洞”一样,数据不可信,官方声明不可信,外媒受限制,所以各种阴谋论就大行其道,因为任何夸张的想象都有可能是真的。你的掩盖让他们怀疑更深,你的自吹自擂他们毫无兴致。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从一个普通市民的心态,反映出你欣慰的和失望的,你感动的和厌恶的。
《武汉日记》真的写的很soft了,我甚至希望拿给尽可能多的老外看。
至少我,无法和我的长辈讨论政治问题。
至少我,无法和我的长辈讨论政治问题。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对于别人只有两种态度,一是俯视,二是跪舔。如果任何人没有俯视“洋垃圾”,那一定是在跪舔“洋大人”。我以为樊记者的遭遇,说明在香港存在着歧视内地人的现象。如果这都可以被解读成跪舔,那么我开始理解这些人大概不需要尊重,只需要歧视(或者在他看来,那才是正常)。
楼下说道香港人和台湾人学会了不对洋大人卑躬屈膝的让我笑了。香港人和台湾人也许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但是在跪舔洋大人这一点上可是一点都没和中国人有什么两样。
随便举个例子吧。纽约客的樊嘉扬在去年在采访反修例示威者。作为纽约客的记者,樊氏的立场应该不需赘述。她跟着一群白人记者一起采访时,示威者大多对她友善配合。而她自己单独去采访时,示威者就对她嗤之以鼻,不理不睬,甚至辱骂。请问,这算哪门子的不卑不亢?
其实跪舔洋大人也无可厚非。亚洲没有哪个地方不是这样的。就是亚洲第一发达的日本国人和本身就是白人的土耳其人在这事上也一样。但想在这里面找点优越感就有点可笑了。
递刀论中,仿佛方方不写,事情就没有,媒体报道就没有,外国人就不知道!
已经看得很淡了 新时代的愚蠢红小将就闹吧 给兔主席这些利益集团里的人牵着走 最后只能坑了自己 反正我走为上策 他们有自食其果的一天
结尾对于第三帝国统治的描述非常发人深省,感谢作者
深度好文,关于大陆不同派别的中年人和年轻人的分析,值得一看!
于是,正应郭文贵先生那句:习近平和王岐山二人对中国的伤害是前所未有的,之后三五代人去排毒也未见得能彻底清洁。习近平满脑子文化大革命,小时候藏地窖吃生茄子留下阴影,现在一听说茄子就吐。王岐山同朋友在私下都常年鼓吹强奸、奴役和杀人的合法性,大邪大奸之人。记得王丹曾在刘晓波葬礼上说共产党的诸多作为表现出精神病人的病理特征,我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国家被认知障碍,人格变态和杀人凶手所绑架,“新文革”的表现难以避免,不同在于民众的自发性墙倒即停、一碰即碎。感到心疼,祝福中国!
国家主义的滚滚车轮已经在高速行驶,迟早要把我们每个人碾在身下。
義和團,文革,小粉紅,用極端民族主義,受害者情結,自卑情意結,換湯不換藥的配方調配出同樣扭曲的心態。
龍應台曾經呼籲中國人面對「洋人」要不亢不卑,現在看來似乎台灣人做到了,香港人做到了,中國人走回去了。
to 楼下: go ahead,你所做的,快做吧
所以说,香港年轻人对中国人的定位是很准的,就是: 赤 纳 粹。 对付纳粹分子需要说服教育吗?纳粹分子只配和他们所供奉的第X帝国一起被消灭。
方方的问题是她体制内享受特权的身份,而非日记本身。她对事实和矛盾的规避已经够多了,简直可以说是体制内的变相维护者。
最后就是方方既然想成为群众意见领袖,挨不同意见的人批评不是正常吗. 当然很多人会轻易的说反对方方的都是被洗脑的,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 .
郭晶的日本没什么舆论反应是因为她没有刻意塑造人设. 其实很大程度 方方自己把自己刻意塑造成为迫害的对象,他日记我倒是没看,但是偶尔看到一些她发的微博,字眼多是文革 被迫害,极左之类的字眼,这是引起骂战的很大原因. 至于是不是真的文革复辟,如果只看微博,就下结论,那也太随便了. 现在互联网发达,每个人都能对一个复杂社会现象轻易下结论.
@spongenee
文革不是把所有人都杀死好么?我作为一个父母家父辈都在文革中挨整的人的后代,完全不同意你的说法。你这种说法和本文中说的“偏爱、死忠、愚孝”没有区别,完全把别人一棍子打死。
至少我的家庭教育没有教导我可以去随意举报与你意见不一致的人。
不是很懂,有另一位作者郭晶也寫了一本武漢封城日記,也是出版到世界各地,為什麼引起的舉報聲浪就沒那麼大?因為郭晶沒有批評到政府嗎?
发动群众斗群众。 左毒比病毒对中国的伤害更加深
根据我身边得同学来看,很多人压根没打开过方方日记,跟着网评员喷就完事了。。
不斷升級思想輿論的手段也最終会被其反噬
你說能夠從文革中活下來的都是怎樣的人呢
那些人的孩子又會受到怎樣的家庭教育呢
活下來大過一切 不惜將其他人陷害 代代傳承
我的上条评论错别字订正:「鉴定」应为「坚定」。
私以为作者有一个核心的事实不全面,就我自身的经历来看,持「递刀论」的「反方方者」们并不都是年轻人,中年人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部分(不过他们在网上的声音可能确实要小一些)。这些中年人,就是各种阴谋论的鉴定拥护者和传播者。
前些天我随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吃饭,席间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位支持方方的叔叔,于是他受到了众人的「围剿」,理由包括但不限于「递刀」、「你疫情期间去做志愿了吗,我们去了耶,你没有资格说」、「你的思想有问题」、「方方写日记可以,外国出版不行」。
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比较容易理解,我一直疑惑的其实是,为什么这些亲身经历过文革、改开等等进程的这一代中年人,还会对类似于「递刀」之类的话语体系深信不疑,还会对「方方们」不断发起围剿?
說的對:
最正统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支持老大哥”,而是“不想”
老大哥不需要你那点支持,老大哥不差你那点支持,老大哥不想让你支持
我看来是政府放任舆论互咬,用心险恶啊。
同时也绝对不要高估这种舆论的影响力,中央有关部门只要满不在乎的打一个响指就能让这些声音不留痕迹地消失
即使现在,这种新的国家主义也没有超过犬儒,政治冷感和利己主义在中国的绝对统治地位。愤青们只会用代价最小的网络舆论,线下的自发国家主义行为几乎没有。而且网络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决定了很难判断国家主义在线下有多少代表性。
回樓下: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一個14億人口大國掀起的群眾狂熱根本就不是一件可以置若罔聞的事,正如20年代初醒起的法西斯帶來的是將近10年的戰爭與動蕩不安。大風起於青萍之末,民族主義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崛起絕對是一件需要警覺的事。
不過如果你不是住在地球,那當我沒說
为这些年轻人而遗憾,在花季培养了这种文革式思维,将来要用多少个十年去觉醒?
一,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并没有多少政治好奇。二,受过高等教育且生活有余力的年轻人掌握的信息来源渠道并没有外界想像的那么少。三,大家各过各的生活,不必咸吃萝卜淡操心。
当今中国的情况和1920德国的确很像,但一个重要区别是,当今中国的国家主义很大受到政府塑造的影响,而非当时德国完全自发产生的。现实是,自由派言论在社交平台立即被删帖封号(甚至发布者面临入狱危险),从幼儿园到大学充盈着“爱国”(实为爱党)教育,政府强制在各大网络平台首要位置安放包子讲话和官方宣传(包括提防颜色革命之类)。当自由派观点具有“天然的”危险性和劣势,而国家主义爱党主义无论在哪都是绝对的政治正确时,当自由派观点几乎绝迹,而对政治好奇的年轻人面对着无处不在的党国宣传时,年轻人不倾向党国主义反倒奇怪了。
心理上,自由派言论的易被举报、自动删除乃至入狱危险造成了对发布者的充分惩罚,致使价值观已然形成的自由派也倾向噤声。而举报自由派的易成功构成了奖励,塑造了下一代对自由价值观的蔑视和对党国主义的支持。
共党成功实现了习近平的舆论目标。不知共党高层在看着这一代的年轻人时,是否像大卫在契约号上看着异形胚胎一样,露出充实而欣慰的微笑呢?
中國國內的公共輿論被控制到只能有一種風向,所以有這種情況也不會覺得意外。中國不能只有一種聲音是烈士的遺言,但是黨的存在讓討論都不可得。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