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過去一年世界可曾平靜?過去一年的銀幕世界又特別精彩嗎?電影總是大眾的白日夢,如何解讀過去一年的現實,真實,與夢境?第96屆奧斯卡金像獎將於3月10日(東八區3月11日上午)在加州洛杉磯杜比劇院舉行,也是藉著這份世界關注的提名名單,盤點過去一年重要電影的時機。
我們為此邀請了香港、中國大陸、台灣、澳門、居英、法、美各地的十六位華語影評人,作為端傳媒文化版的「駐場影評人」。首先是「聊『透』奧斯卡」部分,影評人們將從時下重要議題入手,解說過去一年銀幕世界與奧斯卡入圍熱門作品,這類似一場紙上對談,同一電影不同的觀點呈現才最有趣。
此外在「賭局」部分,駐場影評人也對「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四大獎項投票,得出一個華語視界下的投票結果,比較我們的賭盤預測與奧斯卡賠率或會有饒有趣味的發現;同時,影評人們還在回顧過去一年電影的同時,為我們組合、推介不同情境下的最佳觀影配方。
投票和頒獎前,先來「聊『透』奧斯卡」。我們選擇的核心議題是:戰爭與時代、女性/性別、取消文化、技術vs我們,分為四篇文章刊出,每篇四位作者執筆。今日是第四篇,討論在2023年不斷翻新人類認知的AI及時時刻刻撼動我們的技術革命,執筆者是影評人疲憊嬌娃小楊(紐約)、紅眼(香港)、朗天(香港)、十二辰子(巴黎)。
Part A 當我們在對某一種技術感到焦慮的時候
影評人 /疲憊嬌娃小楊
女性視角流行文化播客「疲憊嬌娃」的主播之一,現居住紐約布魯克林。與其說是影評人,不如說是非常雜食的內容攝入者。關注科技,身份議題,以及科技行業中的身份議題。
這個夏天,屏幕上的故事和現實中的技術發展形成了奇妙的互文。銀幕上的《奧本海默》講述了人類自以為掌握了科技的力量,卻創造出了可能毀滅自己的工具的故事;2023年年初GPT4問世之後,整個夏天到處都有人在撰寫「AI是(或者不是)人類的下一個奧本海默瞬間」的文章,甚至有人自比愛因斯坦寫信建議建造原子彈、呼籲美國要比敵國搶先一步。雖然誇張的敘事背後有大量的商業因素推動,但看到ChatGPT淺灰色的對話框裏吐出完整的劇本和流暢的代碼後,我們很難不開始思考一些終極問題。
一直以來,人們總是認為創意工作是人的專屬領域,機器無法取代;而隨著生成式模型的問世衝擊了這一點。模型創造文字和視覺內容的能力讓好萊塢大公司垂涎欲滴,並引發了編劇和演員行業的劇烈反對。
這不是人類第一次面對技術帶來的存在主義焦慮。另一部奧斯卡最佳電影候選《可憐的東西》設定在1887年,當時的人類也面對相似的自我審視:隨著19世紀中期麻醉劑和抗菌技術的成熟,醫學突然擁有了無限的可能性;科學怪人和弗蘭肯斯坦的故事也隨之流行起來,成為承載「人類到底是什麼」這樣的思考的媒介。當改造的主體成為女性,我們作為觀眾也能隨著電影進行一個很有挑戰性的、關於剝削和主體性的思維實驗。
然而電影在處理人體改造的時候耍了一個小手段:Baxter父女的科技樹在設定中比整個世界要高一層,改頭換面(字面意義上)的外科技術並不是社會共有的。然而在現實中,科學發展是一種社群行為,有不同倫理觀念的人會去出於不同的動機——無論是好奇還是經濟利益——去實踐同樣的技術。如果bella這樣的技術真的存在,那這個世界上不會只存在一個bella;多少丈夫會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夠像bella一樣只有三歲小孩的智商、易於控制?富人是否會希望自己的傭人擁有動物的大腦、希望自己擁有年輕人的器官?技術總是會沿著現有的不平等,包括經濟階層、包括國境線流動,加劇現有的問題、創造新的問題、塑造新的社會現實。
藝術從來都是隨著技術的發展而演變的,沒有人能夠逆轉時間、把已經出殼的技術賽回雞蛋裏;生成模型一定會被融入我們未來看到的優秀作品中。
這樣的流動已經開始了。一直以來,人們總是認為創意工作是人的專屬領域,機器無法取代;而隨著生成式模型的問世衝擊了這一點。模型創造文字和視覺內容的能力讓好萊塢大公司垂涎欲滴,並引發了編劇和演員行業的劇烈反對。在2023年的編劇工會(WGA)大罷工中,編劇工會採取了一些原則性的立場:「創意」本身只能夠被人類所有;語言模型只能夠成為生產工具之一,不能成為創意的所有者本身。藝術從來都是隨著技術的發展而演變的,沒有人能夠逆轉時間、把已經出殼的技術賽回雞蛋裏;生成模型一定會被融入我們未來看到的優秀作品中。是否使用模型、如何使用模型的決定能否留給創作者本人來做,還是會被管理者消減成本的決定裹挾?

科幻作家Ted Chiang在採訪裏說,當我們在對某一種技術感到焦慮的時候,我們所擔心的往往是資本主義本身。當我們在奧本海默中討論技術變成武器的時候,我們恐懼的是大國爭霸敘事湮滅生命本身的價值;我們在花月殺手中討論石油帶來的財富的時候,我們恐懼的是整個系統根據種族、膚色、身份標籤,將一部分人劃分為非人;我們在討論大模型迭代掉編劇和演員時候,我們恐懼的是資本主義體系下勞工的價值。
《奧本海默》電影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鏡頭,是在撼動人心的原子彈測試之後,奧本海默將原子彈交付給軍方的瞬間。炸彈被裝在一個小小的木箱子裏,放在一個不起眼的軍用卡車背後;瘦小的奧本海默站在基地門口,有點無措的看著卡車沿著土路搖搖晃晃的開走。科技本身並不保證能夠解決技術帶來的問題;當技術離開技術人員的手心、進入現實世界之後,更艱難的討論才剛剛開始。
Part B 人工智能的夢醒時分
影評人 /紅眼
專欄作家,影評人。香港文藝雜誌《藝文青》總編輯。寫電影、電視劇、流行文化。寫小說。
雖然說 AI 大行其道,從文字到影像等不同創作範疇都被入侵,最近還有名為「Sora」的影像運算模組,能依據簡短的文字描述自行「創造」影像,或者 AI 電影已經山雨欲來,但看今年奧斯卡的入圍片單,感覺又是另一回事。當下最具時代性的電影作品,幾乎都跟科技保持距離,甚至越來越遠,唯一跟 AI 扯上直接關係,是僅入圍最佳視覺效果及音效兩項「技術獎」的《AI 創世者》(The Creator)。可惜的是 AI 並沒有創世,反而呈現出一個乏善可陳的縫合世界。
導演 Gareth Edwards 從過去的《哥斯拉》和《星戰外傳》拾級而上,到《AI 創世者》應該算得上是荷里活科幻特技領域的代表。無疑《AI 創世者》的電腦後製技術確實精湛,場景華麗浩瀚,視覺效果出眾,敗筆卻是電影劇本一塌糊塗,只是將荷里活過去十多年票房大賣的科幻橋段及人機衝突背景拼貼在一起。後期製作涉及大量人工合成,這一點並不意外,但更值得商榷的是《AI 創世者》連劇本都讓人有種 AI 自動生成的粗糙感,沒創意及熱情可言,如果不是用演算法整彙出賣座科幻商業片的套路,那就代表編劇(像 AI 工具一樣)做著一些如此公式化的創作。
當我們在對某一種技術感到焦慮的時候,我們所擔心的往往是資本主義本身。
《AI 創世者》既缺乏深度探索人類與仿生人共存的未來想像,徒具世界觀而空洞無視野,而且角色行動前後矛盾,男主角愛上仿生人並且與繁殖人機後代,雖有大膽奇想,但於理不通,感覺就似 ChatGPT 隨機堆砌一個看似有趣的劇情,演員的台詞感覺斷裂,就好像由他們去扮演 AI 如何演繹人類說話一樣詭異。當然,《AI 創世者》還是相當符合當下某種「看科幻片,就是看視覺特技已經足夠」的片面觀影心態,如果純粹看視覺特技就覺得值回票價,劇情和演員的機械式演出可以略過不談。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Spider-Man: Across the Spider-Verse)跟《AI 創世者》似乎是在某種意義上的相反,因為它是真正在華麗出色的視覺效果之上,能夠繼續創新、變革。作為這個動畫系列的續作,《穿越新宇宙》比起上一集更見尖銳,在繪畫風格多變,視覺元素豐富得有點眼花撩亂的同時,故事卻精準地跨過了少年成長故事,把觀眾引渡到的反超級英雄、反霸權主義的核心主題。一個反叛、不服從命運的蜘蛛俠,試圖對抗已經建立起威權體制、從守護者變成暴君的蜘蛛俠正義聯盟,不但跳出了當下超級英雄電影氾濫的風氣,甚至借用了觀眾對荷里活濫拍超級英雄大片的厭惡,電影裏裏外外的創作意念都令人驚嘆,但偏偏在電影大獲好評的同時,《穿越新宇宙》捲入壓榨幕後製作團隊的醜聞之中。兩大製片人 Phil Lord 和 Christopher Miller 被指控在製作過程裏嚴重剝削動畫師,一邊反覆重寫劇本一邊要求製作團隊超時工作,待遇苛刻,導致團隊內部相當不滿。這與我們所憧憬(或恐懼)的 AI 技術取代人類有著殘酷的落差,猶遠雖近的 AI 假象背後,好的作品可能並不是建基於人工智能的發展水平,而是一群有血有肉,長期過勞付出的動畫製作組。
猶遠雖近的 AI 假象背後,好的作品可能並不是建基於人工智能的發展水平,而是一群有血有肉,長期過勞付出的動畫製作組。
綜觀整屆奧斯卡之中,我最喜歡的一部機械人題材,反而是意大利導演 Pablo Berger 的首部動畫長片《再見機械人》(Robot Dreams)。電影與 AI 技術、仿生人危機這些宏大議題無關,反而回到我們對人工智能的想像原點 ——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科幻作家 Philip K. Dick 逾半個世紀前的同名小說,啟發了當初的《銀翼殺手/2020》(Blade Runner),也成為了《再見機械人》的註腳:如果機械人會發夢,它們會夢見一個怎樣的世界?機械人會有夢想嗎?但人類社會殘酷悲涼,夢醒以後,機械人開始懂得人情冷暖,學會珍惜與取捨。在我心目中,《再見機械人》才是今年唯一一部打動人心的 AI 作品。
Part C 令人窒息的後人類思考
影評人 /朗天
作家、編劇、影評人、文化策畫、大學客席講師,著有《後九七與香港電影》、《香港有我:主體性與香港電影》、《永遠不能明白的經典電影》等三十部作品。
已記不清首先聽(或看)誰說,人的定義,其實是與技術發展密不可分的。在古代,「聖人」以仁義道德區分人禽,「哲人」以符號使用或理性操作將人從其他動物當中超拔出來。他們顯得如此「原始」,只不過因為在他們處身的社會裏,還沒有生物技術、大腦科學、遺傳因子研究和相關的科技應用。
也許不是太多人確認,1812年前,根本還沒有「科學家」(scientist)這個稱謂,研究科學的學者自稱自然哲學家。正是技術發展到特定水平,人們不得不面對衝擊,扔下舊標準重新界定自己身份。今天,我們已逐漸習慣視愛情為安多酚和多巴胺的成果,用0與1的數碼互動解釋靈魂、思考碳生命之外的矽生命,以及借用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的思辨唯物主義(speculative materialism)思考後人類(posthuman)處境。

是的,去年奧斯卡影片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獲獎電影《奇異女俠玩救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裏,其中一個平行宇宙想像,再沒有人類,只有兩塊石頭並置山頭,卻成為不少觀眾拍掌叫好無限認同的一幕。環顧今年提名競逐奧斯卡主要獎項的十數部影片,延續這種嘗試循技術發展「思考」人類/文明命運的創作方向,仍所在多有。
多年來抑制優生學、人工智能、入夢術的人類文明機制,大抵將漸漸被視為妨礙進步的阻力。移除它們之時,就是我們的末日,並以「後人類」之名得到歌頌和追求。
年度話題之作《奧本海默》(Oppenheimer)借回顧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半生,重提科學最終會為人類謀福祉抑或成災劫的老掉牙問題。基斯杜化路蘭放下不少前作喜愛搬弄的燒腦扭橋科幻設定遊戲,重拾經營敘事策略的初心,把一代「偉大」科學家的暗黑面,與他如何從榮光下墮的史實鋪述交織揭示,不能不說是有心之作。影片根據的傳記《美利堅的普羅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以盜天火以益人類,結果幾被永恆咒罰的天神跟主人公相比,容或誇張,然九成忠於原作的電影始終把暗藏的叩問扯出,以片末的連鎖反應喟嘆為反思釘上記號。我們認得出的話,可只會把其所指藏於心內?
與《奧本海默》的「含蓄」相比,同期上映而和它一起構成雙璧現象的《芭比》(Barbie)就外露多了。假如《奧本海默》算是一部不像傳記電影的傳記電影,《芭比》就是一部比廣告更像廣告的非宣傳電影;意識形態鮮明,導演姬達嘉域(Greta Gerwig) 徬彿是照著女性主義角色成長的公式和理論拍攝似的,甚至讓觀眾見證一次男性奪權建立父權制度,女性同盟又如何反攻自救的過程。猶幸宣揚不流於說教,電影到最後顯示出的自省向度,令影片的成績不致令人尷尬。
有心的觀眾當然留意到,《芭比》的女主角到最後選擇做人類,固然象徵了男權建制中走出被物化之路的女性自主選擇,但「不做娃娃」的意義也顯突了人(包括女人)之為人的人性考量。「洋娃娃」是否「前人類」?「後人類」弄不好會否成為一種後退,沒有真的向前走,反而倒退為「前人類」的狀況?看完《芭比》我竟然產生了類似的思考。
由是,閱讀《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大抵就可正面回應這重思辨了。全無意外地,影片的瘋狂科學家(威亷達福的角色),只要披上「也是受害者」的外衣,他的人體實驗到最後也顯得可愛起來。大部分的觀眾都全面認同他和女主角(愛瑪史東飾演的角色)的所作所為。後者更由於植上了嬰兒腦,母女合一,其成長(特別是在男權性剝削下)便宛如突破萬惡父權的革命結晶。壞人(以暴虐變態的軍人丈夫代表)被降伏、改造,好人集合起來,與怪異的實驗動物(狗頭雞身、人頭羊腦)「以後快快樂樂地生活在一起」,根本就是一場波希(Bosch)的《人間樂園》(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噩夢,但我們不以為忤,甚至樂於達成。多年來抑制優生學、人工智能、入夢術的人類文明機制,大抵將漸漸被視為妨礙進步的阻力。移除它們之時,就是我們的末日,並以「後人類」之名得到歌頌和追求。

Part D 數字編碼的夢境
影評人 /十二辰子
坐標巴黎,歐洲電影產業在職,企圖讓寫影評成為終生副業。
從菲利普·K·迪克1968年的經典科幻小說到2001年斯皮爾伯格執導的《人工智能》,人類對於人工智能的構想始終帶有對自身生活的投射,成為我們現實生活中倫理、哲思、道德的鏡像思考。而如今,隨著真實世界中AI技術的飛速發展,那些一度只能出現在文學和電影中被人類遙遠窺見的情景,已經越來越多的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隨著AI技術在現實世界中的快速發展,為何我們在電影敘事中對這一主題的探索似乎總在停滯不前?是否我們對AI的想象已被固有的敘事模式所限制,或者是我們還未能充分利用電影這一媒介來探索與AI相關的更複雜、更富挑戰性的議題?
自2022年OpenAI像改變世界般的將ChatGPT植入我們的生活後,整個2023年,創作者們一直在適應這個發展速度遠超我們預期的新現實,而電影從業者是其中的一分子。通過觀察2024年奧斯卡最佳視覺效果的入圍名單,我們或許能夠窺見技術是如何在輔助和提升視覺表達方面發揮作用的。然而,那些以AI為中心主題的影片也同時在不斷提醒我們,我們仍然需要對人機之間的倫理問題與社會責任保持警惕。面對職業被AI替代的不安,這種深層的危機感正逐漸侵蝕著創作者及其創作中的世界。

實際上,這種擔憂不僅來自於實際的生存空間被壓榨,更體現在真正的被替代感的可能性上。AI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影視作品中常見的主題。在今年的奧斯卡最佳視覺效果入圍名單中,《AI創世者》和《碟中諜7》均將人工智能作為其敘事的核心元素。然而,它們對AI的處理方式與之前的AI主題作品相比,並沒有顯示出太大的創新或差異。在《AI創世者》中,AI的描繪聚焦於探索人類與人工智能在未來可能的共存形式。其中仿生人被描繪成幾乎全知全能的存在,但實際行動上卻都在輔助人類,在劇情中扮演了類似工具人的角色。而《碟中諜7》中的AI是各方爭奪的重要資源,只是充當推動劇情發展的動力。儘管科技不斷進步,這兩部影片在探討人機關係方面並未提供更深入的見解或挑戰現有的敘事範式。
這種情況引發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隨著AI技術在現實世界中的快速發展,為何我們在電影敘事中對這一主題的探索似乎總在停滯不前?是否我們對AI的想象已被固有的敘事模式所限制,或者是我們還未能充分利用電影這一媒介來探索與AI相關的更複雜、更富挑戰性的議題?並且,始終有人類樂觀認為AI並不能取代人類在創造性工作上的能力。但進一步思考,我們所引以為傲的人類獨有的創造性,(如同人類總認為自己獨有的移情能力),究竟指向了什麼?有人曾說:人類無法創造他未曾見過的事物。如果人類的所謂「最高創造性」不過是已知事物的重新組合,那麼這種創造性真的超越了想象的界限嗎?考慮到AI生成內容是遵循人類自然語言邏輯的,它如何能夠創造出它自身無法想象的事物呢?這種關於AI是否能夠展現真正自主創造性的討論和擔憂或許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又或許,這是因為在人工智能迅猛發展的當下,那些真正意義上的跨越性進步尚未到來。人類與人工智能的共存關係也仍舊只是停留在理論和想象的層面。這也解釋了為何人類難以進一步想象出更為遙遠的未來景象,並且為何我們對於這種未知的未來世界始終抱有恐懼。

如同掀起討論度卻沒有實質上進展的人工智能,我們在今年的片單上也同樣未能看到一種技術層面真正的提升。尤其處理歷史片上,雷利斯科特的《拿破侖》、斯科塞斯的《花月殺手》,也包括諾蘭的《奧本海默》都呈現出一種較為刻板的、教科書式的視覺效果。當然三部影片都以真實歷史為基礎在此之上進行演繹,堅持實拍鏡頭甚至膠片攝影無可厚非。《拿破侖》的導演斯科特更是強調自己覺得不會使用CGI和AI技術,以便不讓觀眾覺得一切是假的。這部影片和《花月殺手》都試圖在真實感上下功夫——尤其是前者還原18世紀的燭光戲和後者在原住民土地上拍攝火光景觀的理念,都令人聯想起庫布里克在1975年拍攝《巴里·林登》時就嘗試過的夜戲拍攝。當然,《花月殺手》在對歐塞奇文化上顯得更有「人文關懷」,為了在視覺層面上區別開,所有歐賽奇人單獨在場的場景都使用35mm膠片拍攝。他們借希望於膠片的粗粒感能將原住民的自然與原始的特性以及他們人與土地的聯結展現開來。
人類無法創造他未曾見過的事物。如果人類的所謂「最高創造性」不過是已知事物的重新組合,那麼這種創造性真的超越了想象的界限嗎?考慮到AI生成內容是遵循人類自然語言邏輯的,它如何能夠創造出它自身無法想象的事物呢?這種關於AI是否能夠展現真正自主創造性的討論和擔憂或許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除了上述幾部作品在攝影上的努力,整個片單裏還是有一部能夠讓人在視覺上眼前一亮作品《蜘蛛俠:縱橫宇宙》。作為《平行宇宙》的續集,這部打磨多年的動畫作品很好的延續了之前的風格,完成度依舊能讓人大呼過癮。動畫用不同風格展現不同宇宙,利用幀數的改變詮釋不同角色、用動態畫面還原漫畫之感,將樓宇建模錯位擺放來使得視覺上達到最佳效果等等一系列的構思,都彰顯了創作團隊在視聽語言構思上的創新與才華。雖然拿一部動畫來與這幾部歷史戲比顯得不太公平,但這樣一部作品或許能在將來反過來讓實拍電影拿去學習和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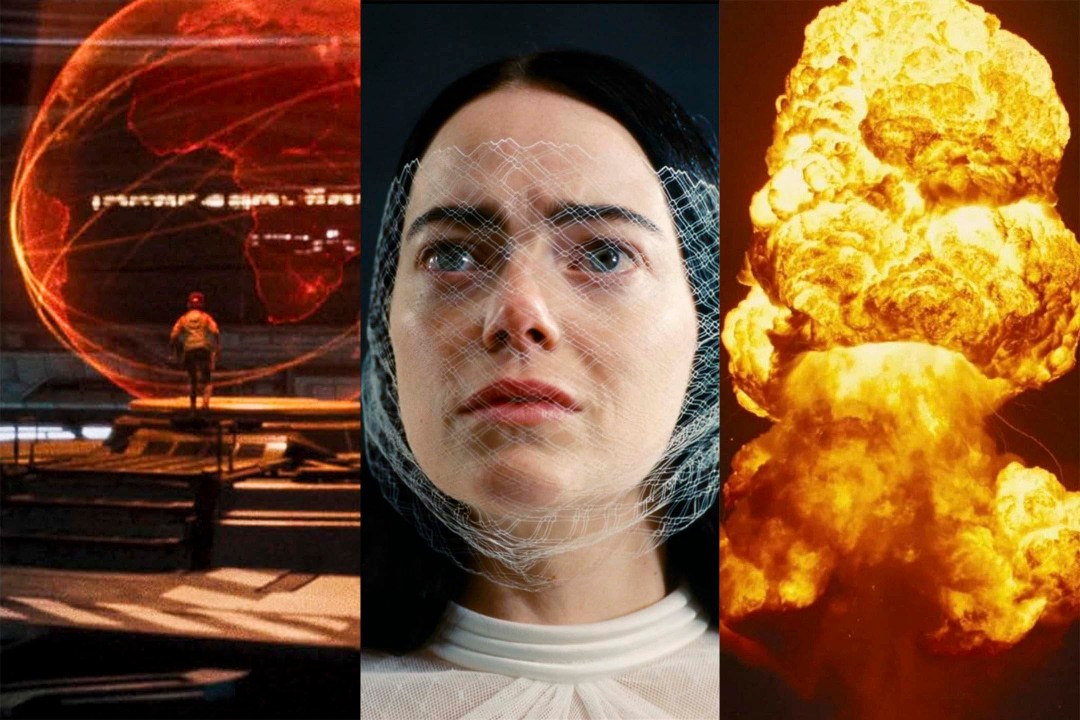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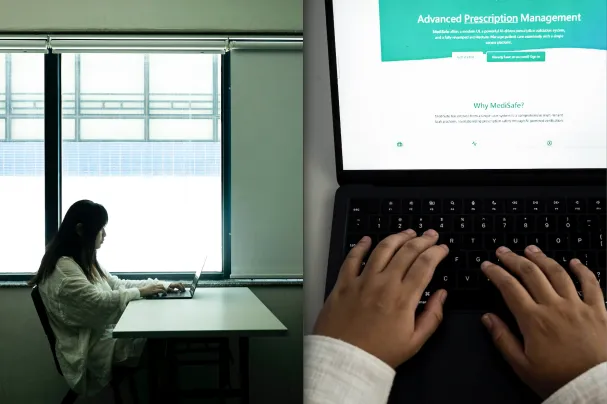

謝謝 十二辰子 ,寫得很好。
《再见机械人》(陆译《机器人之梦》)的导演Pablo Berger是西班牙人,不是意大利人,而且这个电影提出的人和机器之间的相处模式的问题才应该要好好重视,可惜都没看到什么讨论
辰子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