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步法之三:考現學
「我想把整個香港紀錄下來」
孫永雄(Carlos):Instagram「街影Vanishing Hong Kong」版主
「香港一向變得快,近年政治不穩定,政治上爭取不到什麼,國安法你又不能講什麼,我們再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了,那不如好好記錄香港剩餘的東西。」
Carols許下了一個像不可能、但又持續進行的願望:走遍整個香港,把整個香港記錄下來,然後才離開香港。
「你想記錄香港什麼?」
「香港所有東西。」
「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走不了。」他苦笑。
Carols的電腦有幾百個檔案夾,把香港逐一拆解為不同的類別:「交通工具」、「政府」、「自然景觀」、「舊事物」、「老店」、「宗教設施」、「醫療設施」、「傳統文化」、「商業大廈」、「街市」、「城市面貌」。其中唐樓類,他分為了「待拆唐樓」、「戰前唐樓」,底下再分不同地區,如上環、土瓜灣、深水埗等。唐樓他是一棟一棟拍下來,內部細節,磁磚,空間間隔,窗花等,有上千張,數量龐大,「但影了1%也沒有。」他也開始搜集不同的舊物。
他就像做此時此刻「香港考現學」的記錄與研究。所謂「考現學」,由日本關東大地震而衍生,在摧毀與重建之間發生的文化現象,其後延伸變化為路上觀察學、生活學、風俗學等不同流派,打開了日本人對當下周遭事物的關心。
考現學入門
作者:今和次郎
出版社:行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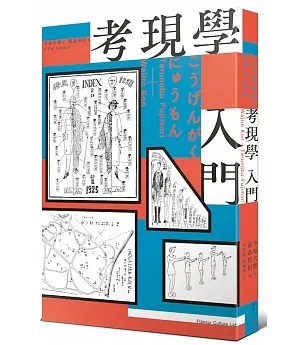
《考現學入門》作者今和次朗,從民俗學興趣,轉而都會大道上的考現學,是受到關東大地震的衝擊,因見證「所見之物」的毀滅,卻也在災後焦土上的臨時住宅、吊掛、豎立在臨時住宅各處的招牌,發現其造型趣味及人堅韌的生命力,「像是從焦土灰燼中冒出新芽嫩綠一般的新鮮」。漸漸,今和次朗從「臨時住宅」為起點,進行路邊的採集,開始觀察銀座風俗調查,貼近於「現象」,而非只是「物件」。
而Carols的紀錄與採集,同樣是因香港在社運後及疫症期間的雙重拆毀及消逝之下而發生。 他1991年出生,本來計劃30歲前,到日本Working Holiday,但疫症之後,哪裡也不能去,就這樣過了30歲。
「我本來很討厭香港。這兩年因為侷住(被迫)留在香港,多了留意這地方。兩場社會運動後,也見證這地方的變化,變的速度超乎可以理解。香港一向變得快,近年政治不穩定,政治上爭取不到什麼,國安法你又不能講什麼,我們再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做了,那不如好好記錄香港剩餘的東西。」他在2020年11月開了IG PAGE「街影Vanishing Hong Kong」。
「我自己因為做了這個專頁,過去兩年,食過很多未食過的食物,入過很多未入過的店舖,和很多根本不會聊天的人聊天。」

他約記者在石硤尾地鐵站等,他從深水埗走過來,一陣夏季獨有的急雨,我們撐著傘,散步到近九龍塘的南山邨。經過主教山,他訴說某一次遺憾。「因為返炒散的工(去打零工),錯過了拍下主教山封前的最後一刻,機會沒有了就是沒有。這兩年我不敢放假,好像一放假,就有些什麼又消失了,會覺得內疚。」
記錄整個香港的心願宏大,於是這種「消失」、不可再來的遺憾,「遲了一步」,一再反覆出現,長期困擾著他。
Carlos生命中第一個「遺憾」與「消失」發生在小時候。他未搬去深水埗前,是在天水圍天耀邨出生與成長,「我記得樓下有間玩具店,我常常去看玩具。但2007、08年時領匯翻新商場,玩具店消失了。」後來他曾上網查找玩具店的舊照片,但一張也找不到,結果他找到港台某劇集剛巧影到半格影像。「真的只有半格,幾秒的鏡頭。」
「為什麼我每天都去,卻沒有拍下照片?我想,其他人或者有這似曾相識的感受,不如
我拍下全香港的照片,為自己又好,幫其他人又好,就盡量拍多一點。」
「留在這地方的兩年,迫著我們見證(香港的)消失,這一下衝擊很大。」他說,同時這兩年,他才發現香港之大,原來他很多東西未曾見過、光顧過,很多地方都未曾走過。所謂「考現」,也是未來的「考古」。
「主教山後來還有機會再看到,但很多舊店、舊建築沒法子追回來,很心噏(心中失望愁鬱)。幾次都因為返工(上班),見證不到最後一刻,後來我決定盡量不接Job,幸好之前返全職,儲了點錢,用積蓄頂一頂。最近差不多用光,所以真的要停一停。」Carlos以前在城市大學讀書,畢業後在附近的又一城商場上班,他總是不嫌遠,走十五分鐘來南山邨吃午餐。他很瘦削,皮膚很黑,一碗餐蛋麵分幾輪吃,最後也沒有吃完,然後說不如繼續走走。
他帶著記者走過屋邨中庭,舊式街店靜謐而落寞,下雨更甚,很多一格格的小店無人經營,鐵鏈把店面的架生(謀生工具)都捆在一起。仍然開門的老店主,開著收音機,就忙著手上的小事小活,一日更多時日是閒坐「過日辰」(消耗光陰)
他指一指,一間叫「良姑洋雜」,順手拈來,說起以前的「紙紮店」叫「文房」,因為六、七十年代很少文具店,買文具就要去紙紮店,有售包草紙、文房四寶及紙紮等。我們走過白田邨的一間酒樓,Carlos說,以前多數屋邨都有一整棟酒樓,以前的人喜歡飲茶,但慢慢人口老化,老人家沒有人照顧,經濟下滑,也越來越少人飲茶。整棟酒樓經營不下就空了。「常見到屋邨在某一棟樓有間老人院,其實之前都是酒樓改建。」然後他從酒樓,講到五、六十年代酒家和茶樓的分別,再講到快餐店、茶餐廳、冰室、西餐廳的分別。
「留在這地方的兩年,迫著我們見證(香港的)消失,這一下衝擊很大。」他說,同時這兩年,他才發現香港之大,原來他很多東西未曾見過、光顧過,很多地方都未曾走過。

這兩年間,就像重新換了一雙眼睛來散步、觀察香港。他本來就喜歡散步,比起搭車,有更多機會發現周圍的事物。他以前經常從南山邨行去石峽尾,深水埗,長沙灣,荃灣,一直走。但從來沒有拍照,也沒有研究歷史。「齋行(純粹走路)。純粹八卦,周圍望,也沒有深入挖掘,也不會找資料。」他也會想起2018年的自己,尚且輕鬆地拍照,無憂無慮,影下「懶日系」的女仔相就滿足。「靚是靚,但十年後我再回望,沒有什麼意義。」
Carolos的獨白
我正職是攝影師,2019年後因為疫症被炒了(解僱),其後一直沒有做全職工作,兩年來把時間花在紀錄香港這件事上。也發現,原來紀錄香港,工餘時間根本做不了。要辭職才能做到這件事。(笑)
我從小到大都很八卦,很多事想知原因、原理。點解係咁?點解唔係咁?(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不是這樣?)中學時操(操練)試卷寫答案,我除了找對的原因,也會找錯的原因。這種性格是我做這個專頁的原動力吧,就是因為八卦。
紀錄香港,最重要是保持八卦心態,事出必有因。例如最近做「廁所歷史」,是因為紙紮店老闆講起以前「抆屎」(擦屁股)用草紙,然後我就好奇,以前是怎樣去廁所?「屎坑」是不是真的有條坑?怎樣沖廁?(笑)
「香港最美是六十至八十年代,即香港起飛年代。我九十年代出生,沒有經歷獅子山下的年代,人情味濃、繁華璀璨的年代。做這個紀錄,也幫助自己了解以前的香港。」
這兩年舊店消失得很快,建築物也是。我覺得香港一向變得快,十年就大變一次。但近年變的速度超乎可以理解。最貼身的是身處的社區,變得冷清了,以前光顧的店都關門大吉,去過的建築物都拆卸,消失得很突然。令我發現「香港」正在消失中。想到自己兩年前的生活太忙碌,又旅行又返工,根本沒有時間理會這地方。
因為疫症,留在香港,迫著我們見證其消失,衝擊很大。
其實人也好,物件也好,都是過客,必然在你生命中消失,除了你自己陪到自己一輩子,沒有物件是一輩子。我不介意他們消失,但介意他們白白地消失。
好像我小時候在天水圍經常去的玩具店,什麼痕跡也沒有留下,記憶像虛幻的而你找不到存在的證明。很難受,也很不真實。我自己因為做了這個專頁,過去兩年,食過很多未食過的食物,入過很多未入過的店舖,和很多根本不會聊天的人聊天。

我在天水圍成長,十年前很少出去玩,九龍幾乎沒有去過,以前大家都說彌敦道的霓虹燈,五光十色。我沒有見過,這是一個遺憾。所以這兩年,我迫自己多走多看,因為一切都會消失。
告訴你,我的性格很內向,不會和陌生人分享,一開始我不敢找街坊聊天,但自己要改變,才能做好「街影」的專頁。老街坊都願意分享,有的常說忘記舊事,我就從不同人身上一句一句積累下來。
一開始,我的專頁只是放一些散步時拍下的照片,沒有文字,沒有口述歷史,但網友問一些問題,我就回答。我想不如寫出來,有些歷史考據沒有人講,也寫得不深入。不如以我的角度講述一次,過程中因為與網友互動,補充了他們的想法和故事,內容慢慢多元化。
過程中很難避免去講歷史,事物存在總有原因。見到這幾年,大家的意識提升很多,年輕人對香港歷史的研究越來越多。
以專頁與網友的互動,再不是由我定義社區的歷史,而是大家一起重構那段記憶、歷史。
「街影」的計劃,是做給未來的自己,也是給未來的香港人,所以寫上「致十年後的我們」。
以前好討厭立場是「藍」的人,但因為個專頁,竟然和這班人聊天多了,開始明白為什麼他們這樣想。我仍然不同意其立場,但會尊重他們。我鬧(批評)完你,你鬧完我,改變也不大,不如講講舊時。我們無人知道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歷史是無價的。
我正在寫第一本書,關於不同老店的紀錄和訪問,暫時紀錄了七十間左右,這不是正統的歷史書,有點像時光機帶回以前的香港。關於老店,我覺得自己不是為了訪問而找他們,反而想和他們建立關係。他們見到我會記得我,問我近況。哈,我不想「哨完鬆」(做完就拍屁股走人),每次我有什麼不明白,又可以回去問他們。
香港最美是六十至八十年代,即香港起飛年代。我九十年代出生,沒有經歷獅子山下的年代,人情味濃、繁華璀璨的年代。做這個紀錄,也幫助自己了解以前的香港,過程之中,也以自己的角度保存了一段歷史。
所以專頁講到:「見得到的歷史」。
我是否懷舊?我不是懷舊,也不是用來賣錢。最希望讓大家見到真實的舊香港。
香港是一個神奇的地方,現在變成這樣,因為以前發生過的事,我想找出來。無論是精神、文化也好,看到以前的香港,就知道怎樣看現在的香港。最希望大家看完這個專頁,領悟一點什麼。
之前講到紀錄的動力來自於八卦,但我想動力更是來自未來,未來的我回望現在的我,未來的自己一定慶幸那時的自己正堅持這件事。
所以「街影」的計劃,是做給未來的自己,也是給未來的香港人,所以寫上「致十年後的我們」。
「香港是一個神奇的地方,現在變成這樣,因為以前發生過的事,我想找出來。無論是精神、文化也好,看到以前的香港,就知道怎樣看現在的香港。」

散步法之四:不迷路的城市漫遊者
「獨自一人,孤獨永恆」
林兆榮:臉書「藝術.交通.散步.林兆榮SwingLam」專頁版主
2022年三月某夜,榮仔在太子散步到界限街火車橋底,發現一幅牆上經年的油漆剝落,近乎一則城市寓言,九龍皇帝定墨寶就在這個時候,如同神諭,以戲劇化的方式重現。在明報,榮仔描述一個尋常的夜間散步:
「平日經過這裏,很喜歡看界限街基堤道交界的三線蛇形雙白,看看一分鐘內有多少車沒有跟隨道路的扭動,直接輾過雙白線?⋯⋯回望橋墩,卻發現牆上的灰油脫落,透出被遮蔽多年的九龍皇帝曾灶財墨寶。」後來消息在社交媒體轉發,吸引很多人到橋底拍照留念。
榮仔接受報章的訪問時說了一句:「我覺得老香港又在跟我打招呼了。」
有別於其他透過散步來矢志記錄香港、研究香港的年輕人不同,他似乎隨心隨性,不必然是從歷史角度觀察,或者時代責任或者使命。「我都不太懂得梳理『散步』這件事,我好像觀察很多,也同時好像不觀察,應該大部分人都這樣悠閒吧?」
我們從水泉澳邨散步回去沙田地鐵站前,經過馬路橋底下,見到牆身一句塗鴉,竟也是來自冥冥中的呼應:「獨自一人,孤獨永恆。」榮仔立即拍下來,他覺得這句塗鴉比起記錄與不記錄,研究與不研究之間,更貼切地描述到自己散步的狀態,是近乎一種個人、私人的空間經驗與記憶。「一個人散步,發吽豆(放空發呆)就是目的所在。」
波德萊爾曾在《巴黎的抑鬱》一書中,曾寫過:「把自己的孤獨跟群眾結合,又在忙碌的群眾之中保持自己的孤獨狀態⋯⋯孤獨、沉思的散步者,從這種普遍的神魂交遊之中,汲取獨自的陶醉。」
班雅明透過研究波德萊爾及巴黎,提出「城市漫遊者」一說,他如何置身在人群,而不是隱沒在其中,在街上晃蕩閒逛,放大感官,巧遇各種偶發的風景、人事。對於班雅明而言,巴黎向他揭示「迷路」的藝術,漫步是他的方式和主題,用來閱讀現代城市的空間及其內在的本質。
「把自己的孤獨跟群眾結合,又在忙碌的群眾之中保持自己的孤獨狀態⋯⋯孤獨、沉思的散步者,從這種普遍的神魂交遊之中,汲取獨自的陶醉。」——波德萊爾

榮仔是「懷疑人生就去_ _」成員,藝術家,巴士迷,也是城市的研究者。早年他已作過很多有趣的日常倡議,如製作《巴士內功心法》,鼓勵人結合步行和巴士,走出的士的路線,鼓勵人探索港鐵以外的交通模式;另外他曾經辦步行展覽「11號全日遊街」,記錄他多次在香港跨區的長途步行,根本也是個「城市漫遊者」。
昔日媒體找他談步行、城市觀察,他多數選擇沙田作為起步點——香港第一代的新市鎮,他出生和成長之地。其後,他搬去第三代的新市鎮將軍澳,生活了十數載。他說:「沙田是我閉上眼晴也識行的地方。我和家人、小學、初中識的朋友約在新城市等,會約在很老舊的地方,如在噴水池等啦!在body shop等啦!在報紙檔等!明明這些地標都已經消失了。」
只要朋友和他提起這些地方,腦海的畫面就是二十多年前的沙田。
「在沙田,我散步很閒適,它已經入了我的身體。世界上應該沒有另一個地方給我這種感覺。」他有時害怕如此熟悉,再難找到新角度、新想法,重新感受到這地方。「就像別人去旅行才覺得新奇,自己住的地方反而沒有感覺。」
「在沙田,我散步很閒適,它已經入了我的身體。世界上應該沒有另一個地方給我這種感覺。」
「沙田還有令你興奮的地方嗎?」
「嗯,是情懷令我興奮。」
他在散步的過程拍了兩次特別的照片,第一次是拍下新城市廣場的麥當奴(麥當勞),說要拍給移民的弟弟看,「M記(麥當勞)搬來這邊我都不知道,要拍給他看。」回程路上,他拐入村落,拍下一間三層高的村屋,說起已移民了三十年的阿姨曾經住這裡。「拍下來傳給她看。」
一開始,我們從城門河起程,在橋上望著河水向外流,波紋的摺痕微毫而不止地散開,錯視令你感覺橋不斷向後退,一切都在動。榮仔想起小時在沙田畫舫、即他爸爸戲稱「茶樓船」去飲茶。明明是石屎建築,他每每向外一望,見流動的河水,就覺得船在航行。
他提起社交媒體熱議被拖走而最後沉沒的珍寶海鮮舫。「香港仔的珍寶海鮮舫和茶樓船不同,珍寶海鮮舫要你慶祝升班、考完試才有得去。我最後一次去是為一位來港的日本藝術家洗塵,他的行李滯留在機場,連一條底褲也沒有。我安慰說,來,我們去珍寶海鮮舫洗塵!」

「很喜歡八十、九十年代的香港,我仍未出世,但從一些港產片帶我回去那條街、那個年代。即使是爛片,你也會感激那些爛片。」
珍寶海鮮舫於榮仔而言,和海洋公園,山頂,尖沙咀海傍都是同一種事物,在他的「香港經驗」的系統中,有記憶以來已經存在。「有人不解大家對珍寶海鮮舫的眷戀,說沒有了就沒有罷。珍寶海鮮舫,你食過嗎?你沒有感覺,但我有感覺,然而它未必要你食過才需要懷念,它本身就是圖騰。不代表它是資本家的工具,它就不能成為一個城市的圖騰。」
榮仔有個特殊才能,他腦海中能構成清晰的香港地理空間,好比GOOGLE MAP定位。他無法追溯究竟因為自己小時喜歡乘巴士,周圍遊歷,才喜歡研究地圖,還是因為喜歡究竟地圖,才喜歡巴士。自小他已經沉迷地圖,巴士路線倒背如流,兩者環環相扣。
即使第一次去某地點,腦中自有一條清晰的路線。香港的地理概念,就像他的掌中之物。榮仔說:「我在香港很難迷路。」
「我有朋友不斷轉換城市居住,一點問題也沒有,他也會想念香港,但不是我這種情況。我生命中,再難找到另一個地方有如此透徹的了解,也不可能再有了。」他說的是以孩童年歲,細緻的觀察與身體經驗,烙印在記憶中即等於永久。
2022年3月他和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開了「懷疑人生就去_ _」專頁,更感受到「拍下來」、「記錄」的一小動作,本身就是其意義,竟感通到已移民外國的離散群體。
「我們拍的片慰藉離開香港的人,特別我拍了沙田的散步片,很多沙田街坊很久沒有回來,說很掛念,透過條片,我像幫他們行過一遍。原來在任何時候拍一些(散步)片,做一些記錄,是有用的。就像我自己,很喜歡八十、九十年代的香港,我仍未出世,但從一些港產片帶我回去那條街、那個年代。即使是爛片,你也會感激那些爛片。」

榮仔的獨白
「在2008-2018年這十年,新城市廣場迎合大陸遊客來光顧,迫(擁擠)到死,如果那些商舖,不是服務沙田的居民,我們慢慢就沒有歸屬感了。」
我成長的沙田發生過兩個大變,一是在1997年,八佰伴執笠(關門大吉)。那間八百伴是當年全香港第一間敢在新市鎮開的百貨公司,以前一向只集中在銅鑼灣一帶。1997年經濟不好,我很記得執笠後,新城市廣場一大片空間,極度蒼涼。
另一次是在2003年,沙田另一個地標音樂噴水池拆掉。記得小時見著噴水池一起音樂,商場的燈暗一暗,音樂噴水池就會亮燈,水噴上八層樓高,小時侯很覺得「係一件事」(是一件可以關注的事情)。
在2008-2018年這十年,新城市廣場迎合大陸遊客來光顧,迫(擁擠)到死,如果那些商舖,不是服務沙田的居民,我們慢慢就沒有歸屬感了。
現在的新城市廣場,沙田大會堂和周邊的商場等,小時記憶中的新城市廣場,沙田大會堂和周邊的商場,物理上是同一個地方,但在腦海裡分裂成兩個地方。兩者的空間構造是一樣,感覺到自己對這地方的記憶正消退中。
2012年我已經開始步行香港,第一次我從將軍澳,徒步行到元朗。後來發展到從屯門行去油塘,赤柱行去小西灣,上水行去尖沙咀等路線。十多年前,推動我以這種方式散步香港,純粹因為失業。寄出去的求職信像投到外太空,很沮喪,不想花錢,又想做點事,步行是最好了。
我仍記得第一次步行,從將軍澳去元朗,近黃昏時已經走到荃灣地鐵站了,翻過大帽山就到元朗,但開始入夜,心中掙扎了二十分鐘,究竟上不上山好。最後,我還是買了枝水,上山了,還事前打電話給元朗的朋友,說自己從將軍澳散步來元朗,找他們晚餐。他們覺得我痴線(注:瘋了)。
那年代沒有智能電話,我用Nokia手機,也沒有地圖在手,只帶了相機、筆和紙,胡亂拍照,記下時間點,做點記錄。過程中,任由身體帶我走,腦海中自然形成那些路線。在香港很難迷路,因為我的定位能力高。你蒙著我的眼,丟我在一個某角落,不是太深山的話,我都有信心能走回家。
「在香港散步不會覺得沉悶,因為景觀變得很快。有人不喜歡公共屋邨,很快就穿過,一穿過就又到了一個全新的地方。那些轉化來得很快,香港很適合徒步行走。」

當時這樣長途步行,一半能紓解到我失業的苦悶,你離開電腦在做另一件事,能為你創造新的經驗和記憶,甚至後來得到別人的注意,覺得挺開心。但另外一半又不能解決,一個人散步,有時會自我對話、鑽牛角尖。事實上,除了兩次即興步行,其他步行都有人陪。
有人陪,和你傾計(聊天),是伴酒小菜。自己行,就看風景,「發吽豆」是目的所在。
現在少了很多長途跋涉的散步了,因為自己習慣把時間表填得滿滿。現在比較常是和朋友吃完飯,很飽,不如從尖沙咀散步去九龍灣那種。
在香港散步,你不會覺得沉悶,因為景觀變得很快。有人不喜歡公共屋邨,很快就穿過,一穿過又到了一個全新的地方。例如在旺角,唐樓密集,突然有個朗豪坊空降。你過了旺角的火車橋,突然變得安靜。那些轉化來得很快,香港很適合徒步行走。
「我小時覺得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身在哪處,就如同自己,已經把香港的路線、空間仔細地記入腦。後來才發現不是,很多人都不是。有的朋友Physically在香港生活,原來他從來不在香港。」
在香港,我喜歡散步民居,像水泉澳這類地方。你會問,公共屋邨有什麼好看?以水泉澳邨為例,如果懶學究(一定要很學究),它究竟怎樣從一座山,劈個空間出來?怎麼擺那些樓?又如何決定哪條路是主幹道?商場設置在哪裡?最重要的民生設施又在哪裡?你沒有親戚朋友住附近,這一輩子你也不會走進來,可能藏有很多新奇的事物。
剛剛一開始談到,我小時覺得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身在哪處,就如同自己,已經把香港的路線、空間仔細地記入腦。後來才發現不是,很多人都不是。有的朋友Physically在香港生活,原來他從來不在香港。
小朋友的觀察很細緻,記得三歲的我,能一下子記著這地方的所有,小時候畫城市,如欄杆多少根支柱為之一格,一架巴士上面有多少釘口,通通細緻地畫下來,將記憶的能力都投放在城市一事一物。長大後,這些記憶很紮根,很多東西是這樣建立回來。我三十多歲人,如果有一百歲命,未來有六十年命,住在另一個城市,也未必有這種「能力」。
我的生命裡,再難找到像香港這地方,我對它如此透徹了解。



真好
諗起 十年 入面嘅《冬蟬》
异乡散步爱好者,赞完上篇来赞下篇。对了,Wiki上以前也有类似的活动,散步时拍个旧路标或老建筑,可以上传到网上。这样大家一起努力在各地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