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跨太平洋的重逢
「沒有媽媽,你是怎麼生下來的?」
隨著Wilson即將升上小學二年級,這個來自同學的疑問,讓身為父親的Jude與Will,更加堅定了帶他親自拜訪生命起點的決心。
8月的一個午後,陽光灑滿亞利桑那州,將礫石前院曬得發燙,空氣聞起來有股乾燥的塵土味。前院矗立著一根銀色的旗桿,頂端的美國國旗與下方的亞利桑那州州旗,在萬里無雲的藍天底下緩緩飄揚。
門廊上,產下Wilson的代理孕母Emma,正帶著她的兩個女兒笑著等他。
「嗨!」Emma開心地打了聲招呼。
八歲的Wilson戴著棒球帽,褲腳一高一低,略顯靦腆地走下車。他繞過車尾,腳步帶著一絲猶豫,與Emma一家保持著一段試探性的距離。Emma向著大女兒介紹到:「這位是Wilson!」
「感覺他好像從未離開過美國,像是在這個家裡長大的一樣。」Jude在遠處拿著手機,記錄下這這個難以言喻的時刻。行前他曾內心忐忑,畢竟已時隔多年,能共度一餐便已足夠,沒想到Emma一家的熱情遠超預期,彷彿Wilson的名字早已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共度了美好的週末,」Jude回憶道,「這三天發生的事情像是一場戲,我自己都無法寫出這種劇本。」這趟旅程,不只是一場久別重逢,更是Wilson探索生命起源故事的開端;而此也契合了,他們從一開始就與Emma達成的共識:他們之間希望建立的,絕非單純的商業交易行為而已。

從深櫃到人父,一個孩子的誕生與家庭的重生
時間拉回2016年,Jude與Will遠渡重洋,做出「人生至今最正確的選擇」。這個選擇不僅讓他們迎來了兒子Wilson,更意外地撬開了Jude深藏多年的櫃子,讓他的人生軌跡徹底轉彎。
「從我有記憶以來,就不斷被灌輸著成年後要結婚生子、傳宗接代的觀念。」Jude生長於極度傳統的家庭,從大學時期就與Will愛情長跑多年,對原生家庭只能選擇隱瞞。早在兩人交往十年之際,身邊就曾有女同志友人們提議,要不要「各取所需」共組多元家庭,讓一個家庭裡擁有兩個爸爸、兩個媽媽。即使後來計畫未果,但想要成為父親的心願,已在Jude心中悄悄點燃。
不過,「成為一名父親」的想法,並不是在傳統文化觀念下隱若成形,在台灣作為一名同性戀,自始便缺乏對養育子女的想像;而這樣的匱乏,則給予Jude有別於傳統男同志的自我定位——當名父親,讓自己能付出愛也獲得愛,並在陪伴孩子成長過程中,讓自己重新長大一次,也在過程中,回望與省思自己的成長歷程。
然而,生長在異性戀家庭的他,難以想像一個「沒有媽媽」的家庭會長怎樣。Will當時其實不覺得一定要有小孩,但仍選擇支持伴侶的決定。於是,Jude開始了漫長的探索,他說自己的個性就是「有問題就去找答案」。
他們始終處在懷疑與找尋的循環中,即便解答了原先的懷疑,但更大的懷疑又讓他們重新找尋答案;直到代孕過程中,他們仍未停止探問。
他四處探詢,並訪問身邊已婚有小孩的異性戀朋友們對於男同志養育小孩的看法。他記得,一名學長告訴他,如果從傳統社會來看,有爸爸媽媽的異性戀家庭是「滿分十分」,「雖然你不可能是滿分,但絕對也有八、九分」。另一名女性友人則反問他:「你怎麼知道幾年後同志家庭不會出現在電視上?」果不其然,隨著台灣社會對於同志族群日益友善,知名品牌金蘭醬油在廣告裡就曾出現「兩位媽媽」一起下廚的畫面。
在這場無限自我懷疑中,Jude認知到,不可能所有的疑惑都有釐清的一天,這趟探索之旅,更像是對自我的提醒與建設。他把自己與異性戀家庭相比,「有多少人做過這樣的探索與建設?有多少人會因為缺少這樣的探索,而質疑自己生養子女的資格?」他覺得他已經問夠了自己,並對眼前的新生活逐漸自信起來,他相信Will會與他相互支持。

早年,同志婚姻在台灣尚未合法化,遑論人工生殖與代理孕母。許多想要有小孩的同性戀伴侶,選擇到2015年前尚未禁止代孕的泰國尋求解方;經濟條件更好些的,則會飛往美國或紐西蘭。由於代孕所需費用高昂,Jude與Will也曾思考過,「就算我們真的有這筆錢,有沒有其他更想做的事?」
直到2015年底,Jude與Will終於決定聯繫代孕公司,2016年正式簽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起初,在媒合捐卵者時,就花了許多時間。Jude還記得,第六位捐卵者因為生父與生母有酗酒前科,不符合代孕仲介的規定而被排除,這也讓他們深刻體會到,美國代孕制度的嚴謹。所幸,在媒合到合適的捐卵者,兩人與第一位代理孕母Emma視訊後,雙方很快地一拍而合。
「過程中,我感覺到對方充滿善意,比較不是純商業行為。」Jude表示,視訊前,仲介公司會嚴謹地要求準家長們(intended parents)做足功課,提醒哪些事情一定要親自懇談、哪些事情則交給律師。例如在懷孕過程中一旦發生意外,雙方有哪些共識?假如寶寶出生後健康出現狀況,又該怎麼處理?至於代孕所需的相關花費,則一律交由雙方律師洽談。
此前,他們不是沒擔心過「剝削女性」的指控。Jude說,自己受到早期台灣電視劇中「顧小春」一角的影響,弱勢女性迫於現實成為代理孕母,進而遭到經濟優勢一方壓迫的無奈,讓他自問:「我會不會也成為壓迫的一方?」

當Jude開始與美國代孕仲介接觸後,他開始慢慢地翻轉過去對代孕根深蒂固的認知。「在美國制度背景下,代孕比較不是一個上對下的關係,而是高度自主的合作關係,」在Jude的經驗裡,他觀察到美國代孕呈現僧多粥少的情況,是孕母選擇合作的家庭,不是他們想要誰、就可以是誰。
他們的代理孕母Emma當年僅21歲,與在警界服務的先生育有一名三歲的女兒,並打算生養更多兒女。Jude曾問過Emma,如果在代孕過程中發生意外,導致她無法再生育自己的孩子怎麼辦?Emma坦承,在決定成為孕母前,夫妻也曾討論過這問題,但因為他們已經有了一名健康漂亮的女兒,基於想要幫助無法生小孩的伴侶,願意承擔無法再生育的風險。同時,Emma也大方表示,自己因為要照顧女兒無法外出工作,代孕收入讓他們有機會提供孩子更好的生長環境。
「我們所接觸到的孕母,非常大方分享投入這個計劃的動機,這份工作對他的生活以及家庭的影響,以及後續運用這份收入的規劃。」 Jude說,自己固然擔心落入「壓迫」的指控,但他也同意,在這樣的關係中,必須回到孕母是怎麼看待自己的身體的,不要太快將對方代入弱勢的形象中,「這才能讓雙方處在平等的立足點。」
隔著汪洋大海,Jude回憶,雖然不是親自懷胎,他仍經歷了許多忐忑不安情緒,除了害怕懷孕過程各種可能意外,更擔心如果寶寶生下來不健康,自己會不會後悔。Will則安慰他,每個孩子都是上天的禮物,無論如何,兩人都會盡力將其撫養長大。而貼心的Emma經常傳來寶寶超音波照片、胎動聲音,與Jude和Will分享孕期的進展,安撫了Jude內心的焦慮。

預產期前兩個月,兩人飛往美國探視Emma,這是雙方第一次實際面對面,在陪同Emma產檢過程,隔著肚皮,Jude和Will第一次感受到寶寶即將來臨的胎動。臨行前,Jude對著寶寶喊話:要在阿姨的肚子裡乖乖長大,平安抵達台灣。不料,寶寶比預產期提早了兩周,收到Emma傳來消息當下,Jude腦袋一片空白,Will則趕緊重新訂機票、改住宿,準備提早飛往美國。
而原先遲遲沒有在家中出櫃的Jude,沒想到在Wilson出生後,爸媽很快地接受了家中的新成員,甚至父親直接在近三百人的大家族中,直接幫他「大出櫃」,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所有親戚。
Wilson出生後沒多久,同婚公投開始在台灣沸沸揚揚,Jude笑說,2018年底,父親煞有其事地幫孫子舉辦周歲喜宴,邀請全家族親戚出席。為此他決定豁出去,準備一場台語短講,趁機幫公投拉票,一名叔叔還上台與他合照,允諾要用這張照片幫他多拉十張票。
曾經,Jude以為,有生之年父母能接受他的同志身份,就已死而無憾,沒想到Wilson的到來,讓父母不僅能夠接受他的同志身份,還讓他體會到整個家族的支持,「不僅大人給孩子的愛很純粹,孩子給大人的愛也是,」他說這是他在養育Wilson中體悟到的事。

當「生養權利」成為台灣的法律與倫理難題
Jude與Will這趟昂貴而幸運的旅程,也正凸顯了台灣本地的法律困境。
1985年,台灣首例試管嬰兒誕生,為不孕者開啟新希望。1996年衛生署研擬《人工生殖法》草案,曾考慮有條件開放代孕,但因爭議過大,導致立法延宕。直到2007年3月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人工生殖法》,受術對象卻嚴格限定於「不孕夫妻」。
隨著晚婚晚生社會趨勢改變,越來越多女性希望婚育脫鉤,加上2019年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後,同性伴侶也希望爭取擁有孩子的權利,讓《人工生殖法》再度被提出修改討論。國健署在2024年7月預告《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擬開放同性伴侶、單身人工生殖合法,原本代理孕母也在增列適用範圍內,卻因引發反對聲浪,目前官方擬採取脫鉤方式處理。
這場風暴中,男同志首當其衝,被視為代孕需求的最主要群體,成為反對方指責「剝削女性」的顯眼箭靶。媒體人鄒宗翰因撰文分享到海外代孕經驗,認為台灣人對於代孕的反感來自於性別教育的缺乏和對於孕產環境的不安,在討論過程中,因為對代孕的不了解, 讓正義感轉為對於男同志的憎恨。這篇貼文,隨後引來輿論大肆批判,直指「剝削就是剝削,沒有不剝削的代孕」。
9月上旬,台灣北區高中模擬考作文題目為「我的媽媽是代理孕母」又一次引爆輿論爭議,認為考題偷渡支持代孕的立場,讓代孕議題在台灣延燒。
「沒有人有權利使用他人的子宮。」長期關注性別議題的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黃捷直言,目前,台灣在代理孕母的討論上,經常以需求方為出發點,代理孕母制度在沒有妥善配套前,不應該往下走。她認為,即使同志和不孕族群有其需求,但這樣的需求不應建立在剝削女性上。從醫學角度來看,懷孕生產過程勢必有風險,產後也可能會有憂鬱症等併發症,讓「生產外包就是風險外包」。
她尤其擔憂,華人家庭注重傳宗接代,一但貿然開放,極有可能家族裡頭的經濟弱勢女性會被迫負起代孕責任。她也提醒,國際上過去曾經發生夫妻透過代孕生下不健全的孩子後選擇棄養,這些都是台灣開放代孕需要面對的議題。

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杜瑛秋也認為,女性子宮不應買賣或作為他人使用的工具,尤其台灣在人工生殖手術上,為了提高成功率,經常一次植入多個胚胎,造成懷孕女性更高風險。她認為《人工生殖法》跟代理孕母應該脫鉤處理,優先開放單身女性、女同志配偶使用「自己的身體」,透過人工生殖技術產下「自己的小孩」。
至於代理孕母,杜瑛秋表示,因涉及將女性的子宮當作他人的生產工具,影響範圍涉及人權、健康、兒童福利等議題,應該要制定專門一套法律,而非放在《人工生殖法》一起修法。杜瑛秋也指出,台灣社會目前仍存在血脈迷思,認為「一夫一妻及孩子」才是完整的婚姻家庭,造成許多女性承受生子壓力。實際上,有許多孤兒等著收出養,婦援會期待可以改變傳統文化,讓收養成為替代方案。
然而,對長年推動代理孕母解禁的民眾黨籍立委陳昭姿而言,這不僅是需求,更是基本人權。因子宮先天性發育不全,她回憶,大學時面對先生積極追求,自己深知無法生孕的體質,將在華人社會裡面對巨大壓力,因而選擇拒絕。然而先生鍥而不捨,最終仍打動她的心。
1985年,台灣第一個試管嬰兒誕生,讓兩人升起無限希望。當時陳昭姿想著:「先生有健康精子、我有健康卵子,我們只是欠缺子宮,就可以擁有自己的孩子。」於是,在先生的鼓勵之下,她開始挺身而出,倡議代理孕母在台灣合法化。
從撰文投書報紙,到開記者會、參加Call in節目,陳昭姿坦承,一開始站出來,讓她與家人承受許多壓力,也收到許多攻擊與支持的信件。但也因此讓她得知,除了和她一樣先天子宮發育不全以外,有些女性因為罹患癌症必須切除子宮,或是因為車禍導致骨盆受傷,阻斷了懷胎生育的可能。這樣的體認更讓陳昭姿深信,台灣擁有先進的人工生殖技術,制度上更應替不孕族群設想。不料法案倡議多年,「拖越久問題越多」,想要生育的族群又多了同志和單身女性,陳昭姿形容,代理孕母在台灣已經成為政治議題。
即使後來選擇收養了三歲大的兒子,全家人感情和樂,但受到早年社會傳統傳宗接代觀念影響,在陳昭姿的語氣中有著難以消解的遺憾,以及對於夫家深深的虧欠。
她說,不孕症患者屬於「隱性的身障族群」,國家應保障其基本人權包含生育權。她也舉知名企業輝達(NVIDIA)為例,輝達在美國全額補助員工進行人工生殖與代理孕母,「難道輝達也在剝削女性嗎?」她認為,在缺乏妥善法規情況下,才造成代理孕母遭剝削,以目前全世界已有三十多國開放代理孕母來看,代孕糾紛低於1%,她質疑,台灣目前離婚率高達三分之一,難道我們要因此禁止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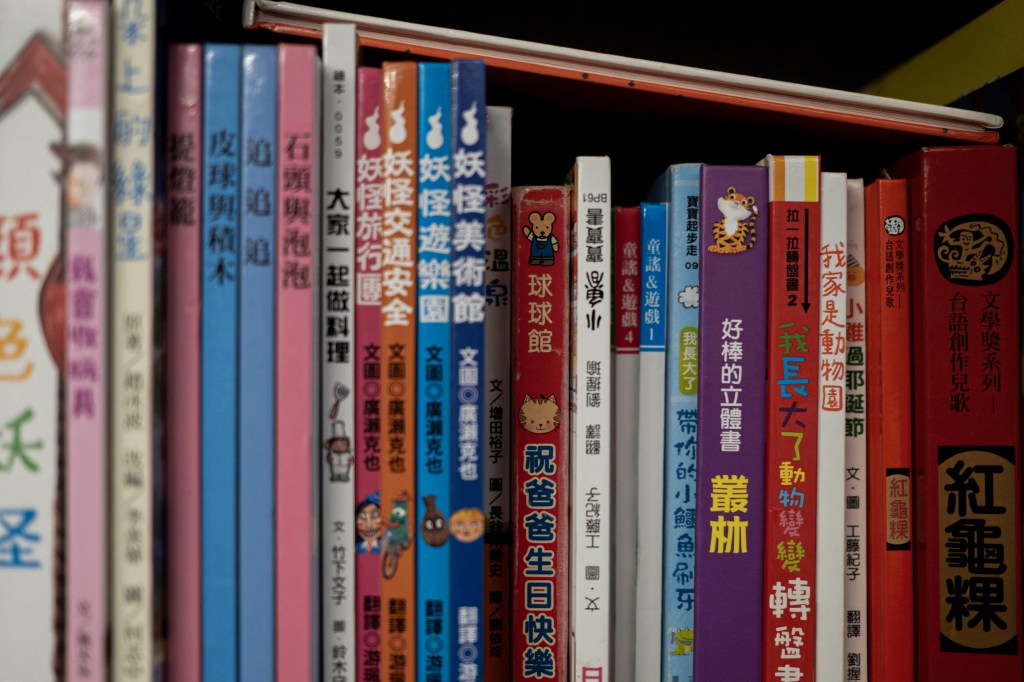
在代孕之外,另一條漫長而充滿考驗的道路
面對台灣法律的停滯,除了像Jude一樣遠赴海外,也有人主張,只要打破血脈迷思,收養是另一條路徑。然而,這條路同樣崎嶇,非外界想像中容易。
台灣同志婚姻合法化沒多久,名為「Men Having Babies」的非營利組織,帶著來自美國的代孕仲介公司,鎖定想要擁有孩子的男同志族群,到台灣舉辦說明會。為了解代孕流程,阿端與Nilson花錢買了門票參加,和許多伴侶一樣,因為高達18萬美元的代孕費用而卻步。當時他們想著,如果花了台幣幾百萬讓寶寶含著金湯匙出生,後續還剩多少育兒經費?也許是看準美國代孕要價不菲,在說明會過程中,還有中國代孕廠商混入,遊說他們「在中國只要一百萬就能搞定」,甚至如果代孕不成,「半價就能再做一次」。
還在猶豫期間,阿端與Nilson的友人收養了一名女兒,他向對方探詢得知,收養過程歷時長達兩年,對方以自身經驗建議阿端,可以在決定要不要到海外代孕的過程中,同步考慮收養,替自己爭取更多時間。於是,阿端與Nilson開始研究收養流程。
「成為收養家庭跟找代孕,就像是天跟地的差別。」比起代孕準家長可以獲取許多資訊,阿端形容,收養家庭在過程中「比較沒有話語權、處於很被動的位置」。由於勵馨基金會的收養流程一年只有兩梯次,參加前得先經過面試兩次。阿端形容,當時他們像是「搶演唱會門票般」,得不停打電話直到接通,才有機會拿到參加說明會資格。
在台灣現行制度下,收養是以孩子的福祉作為優先考量,收養家庭必須在一個月內繳交自傳、身體健康檢查、良民證、收養計畫書、親友推薦函等文件。阿端清楚記得,還得回答十幾題申論題,包含小時候父母教養方式、雙方家務如何分工等。這些考驗都是阿端與Nilson事前難以想像,兩人幾度為了準備不完的文件爭吵,甚至讓收養計畫暫時喊停,歷經了半年左右的伴侶諮商後,雙方還是希望收養孩子。這次,阿端與Nilson把自己關在漫畫店裡頭,像是在寫大學報告似的,終於靜下心來寫完了所有的題目。
繳出資料後通過背景審查,頭才洗了一半。緊接著第二個半年,阿端與Nilson必須去上各種強制課程,包含親職教育、收養法律、身世告知、親密關係、兒童發展等。由於課程隨機分佈在週間,並規定伴侶雙方都不能缺課,又讓阿端與Nilson蠟燭兩頭燒,為了工作請假吃足了一番苦頭。
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三個半年,社工開始到兩人家中進行家庭訪視,個別與共同跟社工面談,期間長達三、四個月後,社工會將訪視與面談結果寫成報告,搭配五分鐘介紹影片,看一下居住環境,再交由外部與勵馨委員審查,確定雙方可以成為合格家長。
即使在收養過程中,社工會強調不是要找有錢的家長,而是可以提供孩子穩定環境的家庭。理念上希望可以累積出比待出養孩子更多的合格收養家庭,藉此符合小孩最佳利益,而不是讓大人挑小孩。但從制度設計上,阿端表示,收養家庭若是沒有一定的社會文化資本,難以應付繁瑣的申請文件,以及投注大量的時間。

權利與倫理之間,在光譜兩端尋找共識
這場爭辯的核心,在於兩種價值的碰撞。一方是渴望完整家庭的生育權,另一方則是捍衛女性不受剝削的身體自主權。
與美籍伴侶育有二子的Lily,在2023年9月時,替一對中國準家長產下一子。以自身代孕經驗來看,Lily認為,美國與台灣都是自由民主人權高的國家,假設真有女性因為開放代孕而遭剝削,勢必有許多管道可以引發關注。Lily因為喜愛小孩,加上過去懷孕過程順利,在朋友介紹下成為代理孕母。過程中與準家長投緣,仲介也給予許多支持。
在美國,第一起合法代理孕母協議於1976年簽訂,而第一起有償代理孕母則發生在1980年。代孕法規由州政府層級管轄,各州規定差異頗大,加州、伊利諾州明確允許且支持商業代孕,紐約州直到2021年才將代孕合法化。而內布拉斯加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根州則禁止或拒絕在法律上承認代孕合約。此外,也有許多州要求代理孕母合約必須經過法院批准。
從數字上來看,美國的代理孕母產業是全球最大的產業之一,該產業的規模已從2018年的60億美元,成長到2023年預估的179億美元,預計2032年將達到1290億美元。
置身這個全球的龐大產業中,她以自身經驗為例,Lily除了事前審慎評估過代孕的風險外,她稱自己個性屬於「理性中的理性」,不太會受到情感羈絆,懷孕過程中,就把自己當成寶寶的「房東阿姨」,對於能夠替不孕症夫妻圓夢,她感到十分開心。在Lily所居住的馬里蘭州與生殖中心所在地加州,種種規範下,Lily並不覺得自己的子宮有被「被商品化」的疑慮。

即使美國代孕產業成熟,但Lily認為,準家長需要跨越的不僅有經濟門檻,也需要負擔時間成本,「台灣明明有先進的生殖技術,不能開放很可惜」。儘管一些倡議者提出倫理疑慮,認為付錢讓女性懷孕生子,會讓她們面臨被更富有、更有權勢的準父母剝削的風險。Lily表示,會需要代孕者是「少數」,願意代孕者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只要法規完善、讓彼此互助,不要花這麼多成本,就可以造福更多需要的台灣人,讓想要有小孩的願望成真。
Jude說,在自己實際接觸後,他觀察美國在代孕制度上,無論是醫療、法規以及保險等都相對完整,得以保障孕母及雙方的權益。不過,在金錢考量以外,讓他更在意的是,他不希望代孕只是「一個過程」,而更希望是一段關係的開始與延續——他認為這對於孩子未來的成長與自我認同有一定影響。
美國RSMC生殖中心院長Dr.Harari則對端傳媒表示,台灣早期選擇赴美代孕的多以異性戀夫妻為主,特別是因為高齡、生育困難或醫療因素,需要第三方輔助生殖協助的家庭。近幾年開始,同性伴侶以及單身人士的比例逐步上升。他認為,制度設計必須考慮社會文化背景,沒有一套制度能「完全複製」到另一個地方。比較重要的是,法律在制定時,必須同時兼顧倫理爭議的討論、醫療安全的落實,以及當事人權益的保障。
「真的沒那麼多男同志想要有小孩。」阿端觀察到,即使同志婚姻在台灣合法化,但身邊登記結婚的男同志遠低於女同,更不用說想要養小孩。對於男同志在這一波修法討論中,被推上「剝削女性」風口浪尖,他認為這樣的指控過於簡化,對男同志社群有失公允。至於其他反對論點包含,可能會發生弱勢女性被迫替家族中的不孕症男性傳宗接代,阿端也認為這樣的立場太極端,法規可透過三等親內不能代孕等方式避免。更何況,依照台灣現行規定,政府無權阻止人民到國外尋找代孕。

「大家都不是彼此的敵人。」黃捷期待,代理孕母必須從倫理、風險、醫療技術等面向一件件拿出來討論,才有機會在保障女性身體自主權與生育權中尋求共識。
在剝削與壓迫的爭議中,在Jude眼裡,這一切的爭論最終都回歸到家庭的本質。回憶起這趟訪美之旅的尾聲,Jude拿出事前準備的大卡片,裡頭有Wilson畫的插畫,以及自己寫了長達三張信紙的感謝信。
Jude表示,當Emma看完卡片,她忍不住紅了眼框,強調Wilson一家對Emma一家來說,已是「永遠的延伸家人(extended family forever)」。從疫情一路延後到現在的實體會面,讓兩個家庭更加深信,原來「可以把幸福帶給別人的人,自己也能得到幸福」。
「在代孕上投注的金錢,或許可以讓我們經常奢華出國旅行,但我們因此有了Wilson,帶我們去了再多錢也到不了的天堂。」Jude最後告訴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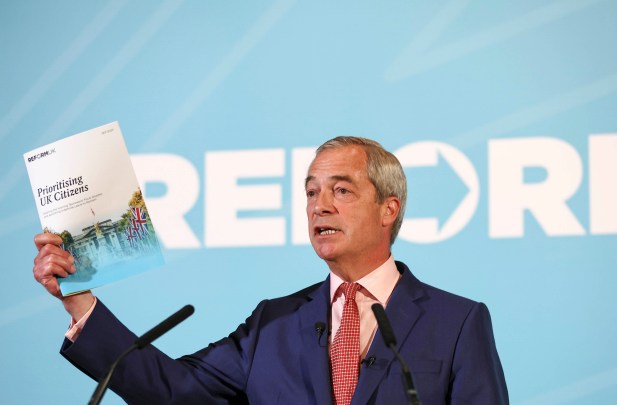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