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要谈论一本分析后真相文化的书,也是一本学术界中的得奖作品。传播学有三数个国际学术协会,当中包括国际传播学会以及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两个协会均在二十年前左右设立了年度最佳书籍奖。今年,讲述俄罗斯新闻业和政治文化转变的《丧失真相》(Losing Pravda)一书(注),同时获得两个学会的年度最佳书籍奖,是历来首次。
Losing Pravda
书名:《丧失真相》(暂译)
作者:Natalia Roudakova
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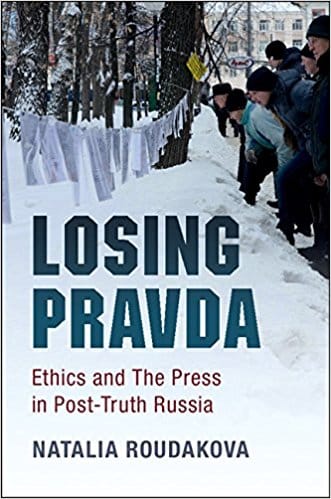
今年,讲述俄罗斯新闻业和政治文化转变的《丧失真相》同时获得两个学会的年度最佳书籍奖,是历来首次。笔者相信,不同背景和在不同岗位上的读者,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别具价值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