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哲翰的《数位利维坦君临的前夕》,端传媒的评论总监曾柏文曾经如此引荐:“黄哲翰尝试做的,是在台湾的科技乐观主义氛围中建立一种对抗论述,拉出讨论张力。他笔下看似的厚重悲观,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撞击’。”
我认为,这是该文最重要的价值。过去我曾在其他地方反省过那种科技至上的正能量满溢。这篇文章在勾动我的共鸣之外,也不禁让人感叹:这类“撞击”恐怕终究难撼那只不仅庞大,还一直装睡的乐观主义巨兽。
为此,我想要再拉出另一条轴线,为刚硬的撞击之外,添上一股柔韧力道。称数位利维坦一文“刚硬”绝非贬意,而是取其偏向技术决定论的姿态。同样地,称其“偏向技术决定论”更非批评,即便黄哲翰于文末有一点想要与此保持距离(也就是强调并非主张工具逻辑将主宰人类社会发展),但我反而认为,正是技术决定论式的观点,才可能有如此强大撞击力道的启发:它让我们得以直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Heidegger)曾指出的,现代科技的危险深渊。
所谓的柔韧力量则是去问:除了撞击外,我们还有没有扭转未来的可能?在“数位利维坦君临的前夕”,渺小的我们是否有改变的“机缘”?我想要提供另一种视野。
科技结构下,人的共谋
数位利维坦一文,虽然在最后总括网际网路的“工具逻辑”为问题根源,但其整个论述其实更细致地将问题指向:数位化作为新工具带来的影响,与所谓“消费逻辑”的结合。
用我比较习惯的方式来说,这就是科技特性与社会文化互动的结果。
任何科技物虽然都一定有其特性,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必然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脉络相关。换言之,网际网路或数位化科技本身的特性,并不“就”导致极端主义对立态势等种种问题,而是在结合“消费逻辑”下,导致人们快速地、反射性地偏向了对立的极端。
不过,数位化工具带来的影响,不只是科技与文化互动下的产物。我们作为使用者日常持续、反复的使用,也进一步维系了这整体的文化现象。例如,我们持续使用脸书,当然就维系了它所导致的极端化对立、同温层等效应。这听起来像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但其实并不必然。
抽象来说,这是一种“结构-建构”间的循环。也就是说,在巨观层次上,每种科技物的普及使用在特定社会文化脉络互动下,都将带来结构性的影响;但同时,这样的影响并非单纯“决定论式”的力量。实际上,它要能持续作为“事实”,需要透过人们日常使用的实作才能不断再制。
以脸书为例,脸书就是利用演算法生产“投其所好”的资讯来吸引使用者的依附。而之所以是“投其所好”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资讯,正是当代消费文化的互动作用。但是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上,也是因为使用者不断为脸书标记(按赞、分享)“其所好”,重复实践著“消费文化”,整个同温层才会构筑起来。也是如此,过去脸书才能“厚颜”地卸责说:这不是我演算法的责任,而是使用者的选择。
换言之,如果我们都只看“结构-建构”循环的其中一半,就无法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脸书的卸责方式正是跳到“建构”那一半,巧妙地忽略自身演算法带来的结构效应。而对我而言,认识到“结构-建构”完整循环的意义是:既然我们今日面对的种种问题,都不单纯是网际网路或数位化工具造成的,而是我们自身同时也(可能有意或无意)“共谋”地参与其中,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就有改变的能力与可能呢?
我认为,这个改变的起点不仅是揭露数位利维坦的身形,进而了解数位化工具如何与特定文化互动带来了结构性的影响,更是要先认识到自身其实“选择”(而非必然)参与其中,同时也正维系其作用。接著,我们才有可能反问自身:有没有不必然如此的其他选择?有没有另一种“使用方式”?
也就是说,脸书(以及其他所有科技物)虽然有其既定的运作方式,但那并不是铁板一块。人作为使用者并不是一种机械式的延伸,只会或只能“跟著规则走”。实际上,正相反的情况是,我们经常看到使用者“挪用”科技物。
例如,前阵子我看到的经典例子是智慧手机的挪用。虽然智慧手机一般被认为是消费式电子产品,让人们能够享受各种个人式多媒体娱乐,以及即刻连结的满足。但雨林连结组织(Rainforest Connection, RFCx)就“挪用”其即刻接收、传递声音的技术机缘,将旧智慧手机改造成智慧型雨林监测器。
脸书也是如此。虽然在消费文化的笼罩下,我们习惯了脸书不断喂食自身“所好”的资讯。但如同我刚刚说的,这是透过使用者的选择才产生的结果。而就像黄哲翰也看到的,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在一些案例(例如318运动)看到,使用者挪用脸书的可能性。
向深渊行去,更巨大的挑战
现实地说,不管是揭露数位利维坦的“撞击”,或是上述谈到的那种探索“不必然如此”的转向,可能真的都效果未知。原因不仅在于数位利维坦的强大,更在于当我们再深入探索下去,便会撞上更高的那道墙:不是数位独裁,而是笼罩人类社会已久的“科技极权”。
网际网路、数位化科技绝非突然之间带来全面压迫性的“独裁”现象。相反地,比较适切的方式应该是将其视为“接班人”。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它是科技极权政体中即将登基的新主。
美国传播学者 Neil Postman 在其经典著作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中,说明了科技极权政体是如何在过去几世纪间形成的。简略来说:十七世纪以前,所有工具的发明与使用都受文化导引的时期;之后,工具开始逐渐脱离文化的控制,甚至开始企图取代文化的“科技统治”时期;以及最后,完全取消了其他文化的“科技极权”时期,也就是从约莫十九世纪末直到今天。
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来理解,这个过程,就是科技以及科技内蕴的理性,逐渐取得主宰地位的过程。从原本由宗教、神话等信念引导人如何过生活、如何使用工具,到“理性”开始宣称其有别于宗教、文化信念的独立地位,并且带给人们关于“进步”的理念,加速了科学与科技的发展。最后,科技极权政体中,科技与技术理性甚至几乎取得了“唯一”世界观的权威,指导著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务。
我认为,数位利维坦正是这一科技极权政体的新主。Postman 指出,科技极权政体中爆炸的资讯量,取代了传统信念体系,解答人们生活的各种疑惑。数位利维坦则不仅是回应问题,更是引导甚至决定我们的认识与行动。这大概可以从现今各种“智慧装置”预先为人搜寻、筛选甚至完成各种行动中看见。
若是如此,一方面,挑战数位利维坦等同于挑战笼罩人类社会几世纪的科技极权政体。其中的问题,恐怕不是反思网际网路或数位化工具就可以解决的,它更涉及了长久以来对于科技及技术理性的反省。(注1)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可能跨过同温层的阻碍,在效率与利益计算至上的技术理性面前,恐怕寻求“共识”仍是难如登天。
也正是因为如此,像是义大利哲学家 Gianni Vattimo 才早已转向探寻理性、共识外的其他出路。在他看来,也许不是沟通、共识,而是“多元性”才可能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规范性判准。延伸地说,这意味著在正视、尊重多元的前提下,与其强求透过沟通达到唯一的共识,也许“对话”带来的视野扩大更可能避免我们走向极端。(注2)
另一方面,也唯有认识到这一更巨大的挑战,我们才不会认为问题只出在“某个”科技物(例如网路或脸书)上。或者,才不会单纯地认为:既然不爽就不要用就好。因为,“不爽不要用”这种个人(消费)式的解答,最终只会带人们走向穷途。在科技极权的政体中,我们只会退到什么都不再能用的末路。
因此,反过来,我们不该轻易“退用”。相反地,如同我上文所说的,作为使用者,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自己选择使用了什么,进而才可能思考如何“不必然如此”使用。如同法国社会学家 Michel de Certeau 所说的,也许我们无法轻易逃离这个系统(科技极权政体),但我们仍有可能在其中进行战斗。
(曹家荣,国立政治大学社会学博士,专长资讯社会学)
(注1) 前阵子,政大哲学博士纪金庆就刚好有一篇好文章在反省技术理性带来的问题,可以参考:〈现代社会解救方案:消解“技术理性”的神话,重新定义“什么是理性”〉。
(注2) 关于Vattimo的论点,可以参考政大社会系黄厚铭教授的讨论:〈资讯时代的最低限伦理:G. Vattimo《透明社会》的诠释伦理与多元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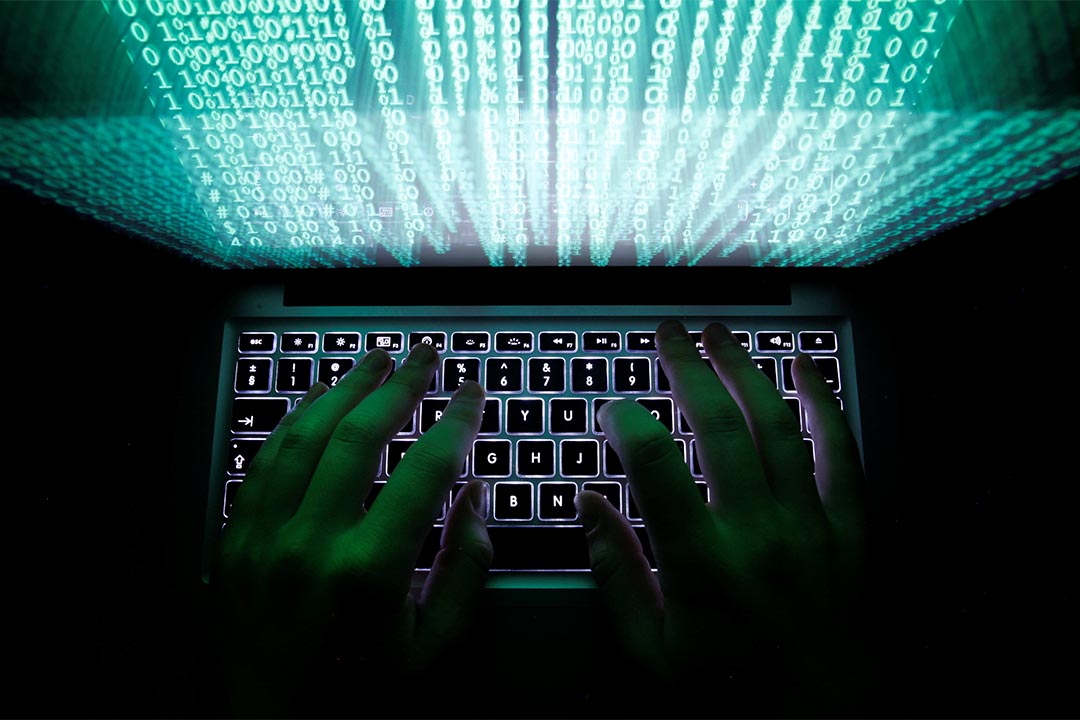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