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來,歐盟因難民潮與恐攻威脅,陷入極端主義(extremism)興起與內部分歧等嚴重危機。人們普遍認為,歐盟若要走出困境,就必須深化區域合作,共謀政治經濟的對策。然而在諸多危機的背後,歐洲議會議長馬汀‧舒爾茲(Martin Schulz)卻看到了一個更深層的面向。
就在去年巴黎發生恐攻後,舒爾茲連續投書德國《法蘭克福匯報》與《時代週報》,高調呼籲歐盟各國亟需合作共同制訂一部《網際網絡基本權利憲章》(Grundrechte-Charta für das Internet)。這是他繼2014年9月之後,針對歐洲自由民主之政治秩序所遭遇的重重挑戰,再次重申的同一記處方。
舒爾茲認為,在區域合作與政經對策之外,捍衛「公民參與」和「多元意見」才是對抗極端主義、繼續穩定歐盟的基石。然而這兩項基石,如今正受到數位化浪潮的強勁威脅,並且連帶讓極端主義的發展一發不可收拾。
如此的見解乍看之下或許令人錯愕。因為數位網絡的發展,常被人們寄以希望,認為它將促進資訊傳遞、實現直接民主、並有助於公共溝通。但舒爾茲的觀點卻幾乎與此相對。
對此,人們會疑惑:一、數位化的效應怎麼會無力化公民參與、阻礙多元意見的形塑?二、數位化浪潮與極端主義間,有什麼關連?三、即使前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這是具體的現在式、還是模糊的未來式?
讓我們從第一個問題開始依序梳理。
數位化導致規範失靈與崩解
當人們將生活中越來越多層面連接上數位網絡,成為「大數據」的樣本,並訴諸演算法與人工智慧來做決定時,首先浮現的是「個人意志受到侵犯」的問題。至今,我們已不可能有足夠心力,針對每個細節來決定是否同意資料儲存,是否接受演算法與人工智慧的遊戲規則。
這意味著,數位化作為一種新工具,實質上已在人類專注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外,全面衝擊個人自主的防線。其所瓦解的,正是西方過去150年來,歷經教訓與努力所保障的基本自由權。在理論的意義上,數位化的效應,應視為開放社會既有規範的失靈與崩解。
在現實中,隨著科技持續創新,倫理問題也將大量浮現枱面。例如:汽車智慧駕駛系統,可否被允許在遭遇意外狀況時進行緊急迴避?演算法可否被允許運用在企業徵才或學校招生,可否被用來為求職者篩選工作,並決定其生涯發展的可能性?是否能以提供預防性照護與有效調配急救資源的理由,要求心臟病患配戴智慧型監控裝置?乃至於,人類社會是否將從智慧型手機、智慧型家庭、智慧型城市、無可逆轉地一路滑向以國家為主角所運作的全面性「數位極權」或「智慧型獨裁」?
至今人們還是常用「個資保護」與「隱私權」等概念,來概括理解數位化對自由社會既有規範的挑戰。嚴格來說,這是不充分的;其也顯示人們仍欠缺相應概念,來理解上述問題。而相較於歐洲社會的高度敏感,亞洲社會對「個資」與「隱私」問題,往往更缺乏關注。或許這能解釋,對於歐洲將該議題提升到如此的政治高度,我們為何會感到些許陌生。
催生反射衝動形成的人格
數位化的威脅,不只是在注意力範圍之外「偷走」我們的隱私、限制我們做決定的能力,乃至於取代我們的工作位置。它對人的「自由」的瓦解,恐怕將更加徹底。理由是:數據之海所捕捉到的形象,將遠超出我們對自己的認知,因為那涵蓋了許多出於下意識的反射衝動行為。當數據儲存得越全面,對反射衝動捕捉得越細緻,情況就會越弔詭:隨著演算法對我們的預測越加精準,越能夠導引我們的行動和決定,我們卻越遠離我們原先所認識的自己。
這種由各種行為數據聚合起來,而非出於原生社會脈絡的陌生自我,可被稱為我們的「數位孿生姊妹/兄弟」(der digitale Zwilling)。演算法根據我們的「數位孿生」形象,在人類意識能力的範圍之外全面篩選資訊,既引導人的行為,又重塑人的性格,這才是所謂「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的真正狡獪之處——它並非只是單純創造「迴音效應」,讓人們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在這個過程中,它還將誘導人們,逐漸把人們推往由反射衝動所形成的倒影人格,讓我們在自滿自足的封閉想像裡,逐漸自我異化。在那裡是如此地舒適,甚至連個人對自己的想像都被代勞了。
「過濾泡泡」與其說是製造「迴音」的機制,不如說是根據「消費邏輯」去刺激反射衝動的機制。它的功能在於逐漸剝削人的自我想像中,來自教養與社會化的成分,然後重新透過刺激反射的衝動來形塑,作為供應流量、推動消費的燃料。隨著「去教養、去社會化」的趨勢,「公民」身份與「意見」的多元性,都會逐漸失去立基點。
演算法所「期待」的,是一群視野越來越自我,但反應模式卻越來越直覺──因而也越加趨同的數據來源。無論數位化創造了多少新的可能性,當它與消費邏輯結合,就必然產生反公共與反多元的傾向。這是自由社會必須面對的第一項挑戰。
越趨倚賴直覺詮釋與標籤化判斷
接著回答第二個問題:數位化將如何為極端主義推波助瀾?
數位化潮流在結合刺激消費引擎的現況下,反映出表裏極端不對稱的結構:表面上,網際網絡的特徵是去中心、去層級、點對點、並且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其內裏,權力則高度集中在如 Google、Amazon、Facebook 等少數巨頭手上,表現為「贏家通吃」的樣貌。
總體來看,這個不對稱結構,是一套集中權力與獲利的永動機制。當掌握大數據的權力越集中,它就越有能力滿足人們對資訊的全方位需求,也動搖了原有的社會共識/世界觀,並將人群的集體意識,帶向「去中心、去層級、點對點連結」的狀態。當人們越是處於這種狀態,就越順從直覺反應,成為生產數據的動力來源,推動網絡權力的擴張與壟斷。
為了更具體地闡述上述過程,我們把鏡頭拉近到個人層級來看:網際網絡作為平等地對所有人開放近用(Open Access)的新媒介,其首要效應,就是強迫消解知識專家和傳統媒體對資訊的結構性壟斷。這樣帶來的好處是,個人自此可從原有權威解放,更有機會「獨立思考」;但壞處則是,個人也因此「被迫」進行各種獨立思考──在失去了原有知識權威與世界觀,直接暴露於巨量而缺乏脈絡的資訊流,並且處於點對點之超量人際互動的情況下(上述這些都只要打開臉書或推特即可體驗),人的本能傾向自選一套方便易懂的世界觀,並仰賴這套世界觀,讓自己成為知識偵探與詮釋主宰。「過濾泡泡」的陷阱如此精巧地而理直氣壯地向個人招手。
於是,「讀者已死,作者滿街跑」的大腦補時代正式揭幕。當時局越不確定、時事資訊越趨複雜矛盾,個人傾向選擇的世界觀就會越單純;解釋越包山包海,人們越渴望簡潔有力的答案。對於演算法而言,個人越是依賴自身權威,他的思考與行為也就越容易被預測。面對各種資訊,既彈性疲乏又過度亢奮,是在「過濾泡泡」中獨立思考者的基調。
如此特質的個體,將跳脫複雜的原生社會脈絡,在數位世界裡片面擷取資訊和意見,黨同伐異,形成政治意義上的虛擬社群。這些數位社交活動如此巨量、簡短而快速,遠超過個人的社交承載力與情緒負荷量,使人更加重倚賴直覺詮釋與標籤化的判斷,以便有效率地篩選連結與隔離的對象。
同溫不同層的數位政治社群
於是,需要長期培養的共識,不再作為維繫社群的必要條件。維繫數位社群所需要的,是可立即辨認的「異類」。對異類的高度敏感,不只針對社群外,同時也發生在社群內。由於缺乏理解與共識的基礎,社群內的其他成員都是潛在的異類,個人始終要持續觀察其他成員的立場,必要時還要推敲其弦外之音、進行政治正確審查,確保彼此仍是同志。
人們可以因為一句話、一個讚而成為臉書好友,同樣也可以因為一句話、一個讚而刪好友。如此表面「同溫」但並不真正「同層」的數位政治社群,會產生一種弔詭現象:對特定政治信念與世界觀的構思、主張與辯論,將在「政治社群」的社交中逐漸退位,並被標籤化判斷與直覺反射式的回應所取代。也就是說,數位政治社群在結構上,即蘊含了去政治化、去社群化的傾向,它將與「過濾泡泡」上映照出來的個人倒影難分難解。
「數位獨裁」來臨速度驚人
所謂「極端主義」,若單純從形式上來看,不考慮其具體內容,它就是一套對事態極度簡化的政治信念,主張貫徹純粹的原則,能立即激發個人直覺反應,並展現極高的排他性與行動能量。由此看來,數位政治社群彷彿是為各種極端主義量身打造的溫室——一個在封閉環境中培養「殘酷的單純」(brutal simplicity)的溫室。
或許這樣的溫室,就是當「數位利維坦」(Digitaler Leviathan,利維坦原為《希伯來聖經》的一種怪物,在Thomas Hobbes的同名著作中,被用於比喻集權政體)完全掌握人類社會後,其治下所呈現的標準地景。但是,「數位利維坦」君臨的那一刻,究竟會來得多快?
今年1月,九位來自不同領域的著名專家在德國《科學光譜月刊》(Spektrum der Wissenschaft)聯名發表長篇聲明,警告即將來臨的「數位獨裁」,並提出如何實現「數位民主」的建議,大致呼應了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茲的政治呼籲。這些專家們的警告基於一項事實:人類社會全面數位化的速度,超過一般人的想像。
該篇聲明指出,光是2015一年產生的資訊量,就超過人類有史以來到2014年之資訊量的總和。其預測在10年內,全球會有1500億個彼此互聯的數據測量裝置,遍佈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大小物品中;屆時每12小時數據量就會翻倍一次。10到20年內,工業國家現有的工作崗位將有一半被演算法取代;全球前500大企業將在10年內消失40%。而人類在幾乎所有領域中的智識能力,被人工智慧所超越的時間點,預計最快就在2020年,最遲則不晚於2060年。
如同舒爾茲,這九位專家也把上述對未來的預測,具體連繫回歐洲當前極端主義的興起。據此,我們可把後者視為數位化潮流撕裂原生社會、召喚「數位利維坦」的初期症狀——當前歐洲所面臨的政治危機,事實上正是一場翻天覆地之巨變的冰山一角。本文的最後部分,便以他們的投書與聲明所呼籲的對象——德國社會為實例,藉由梳理上述「初期症狀」的具體發生脈絡,來回答本文開頭提出的第三個問題。
主流媒體失勢,壯大極端勢力
近來德國極端主義的興起背景,可回溯至2003年開始的勞力市場開放與社會福利緊縮,所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及社會不安。連帶地,越來越多民眾失去對體制的信任。隨即接踵而至的歐債危機與難民潮,讓民眾找到了反對體制的契機,質疑現行體制的政治規則與社會共識。風暴的核心,就落在對主流媒體的批判。
今年5月初出爐的最新調查結果顯示,已有超過六成的德國民眾失去對主流新聞媒體的信任,認為其受到體制的操縱、排擠特定意見,並且只片面呈現事實。媒體研究者對此的解讀指出,自去年難民政策引爆爭議後,主流媒體為了防堵反伊斯蘭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延燒,以壁壘分明的二分法來定調:「你是要歡迎難民,還是要站在邪惡的一方?」結果適得其反,摧毀了民眾對媒體的信任。
以往德國媒體在凝聚社會共識上表現良好,80到90年代之間,都還有7成以上民眾認為媒體能為其喉舌。但在近年來的變局下,德媒已喪失這種能力,讓不少反對難民政策的民眾轉而透過社群網絡串連。於是,數位政治社群的遊戲規則接手,使越來越多的網民被「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與「德國替代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簡稱AfD)等極端政治勢力吸納。
Pegida與AfD皆是以社群網絡傳播為主力的新型政治勢力,兩者也都在極短時間內迅速壯大。簡單地對照主要政黨的最新民調支持率與臉書專頁追蹤人數:傳統的兩大黨基民盟(CDU)與社民黨(SPD)的支持率分別有33%跟21%,兩者臉書專頁都有10萬人追蹤;AfD支持率僅13%,但追蹤人數卻高達27萬。
當這種新型的政治社群指控主流媒體時,他們也失去了一切客觀可靠的消息來源。為了支持其「正確」的世界觀,他們硬是建立了一個「過濾泡泡」裡的平行世界:一方面,他們擁有為其世界觀喉舌的整套資訊體制,包括網路新聞媒體 Metropolico、反伊斯蘭部落格 Political Incorrect、政論雜誌 Compact、專門出版聳動陰謀論書籍的出版社 Kopp等;另一方面,其支持者也大量片面擷取部分主流媒體的資訊──例如偏保守者的《世界報》(Die Welt)或報導風格聳動的《焦點週刊》(Focus),再混入符合其世界觀的詮釋,製造出客觀的表象。
透過這樣不斷自我證實的方式,這類極端政治社群將各類反菁英、反帝國主義、反美國、反伊斯蘭的論述斷章取義,形成一套鋪天蓋地的陰謀論:在美國帝國主義與親美政治菁英的操控下,歐盟一方面與俄羅斯對立,另一方面試圖利用難民潮將歐洲伊斯蘭化、摧毀歐洲原有的文化脈絡與社會反抗,藉此完成極權控制的目的。
假消息滲透真實世界
當然,並不是每個支持群眾都會相信這麼牽強的陰謀論。但當它作為一群核心意見媒體的信念或暗示時,必然帶動周遭群眾反公共、反多元、排除他者的效應,使得群眾的政治信念透過網絡傳播的「迴音效應」,在「過濾泡泡」中不斷自我增強。
甚至,人們也被鼓勵以成見為基礎,開始於生活中實踐「創造性詮釋」——想像出一系列的假消息,例如:「拜仁邦社會局發放性服務兌換券給難民」、「兒童嘉年華因擔心恐攻而停辦」、「某小鎮的連鎖超商Lidl因難民偷竊頻傳而被迫關門」等等。過濾泡泡裡的世界,開始滲透現實世界、消解了真實與虛構的邊界。
此一發展,讓過濾泡泡中的「真理先知們」,自信地跨越德國戰後社會禁忌的束縛,露骨地發表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言論,並大膽起用過去納粹使用的污名化標籤,如「謊言媒體」、「民族叛徒」(Volksverräter)等,最後讓社群網絡充斥著出於直覺反射的仇恨言論。
面對社群網絡上越滾越多的仇恨言論與網絡霸凌,自去年下半開始,德國政治人物如聯邦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台譯梅克爾)、聯邦司法部部長馬斯(Heiko Maas)等,紛紛要求 Facebook 等社群媒體嚴格規範,乃至於24小時內刪除仇恨言論。作為「過濾泡泡」營運者的Facebook,第一時間僅標舉「公民勇氣」(civil courage)的大纛,鼓勵對仇恨和霸凌進行「言論反制」(counter speech)。這不但被批評為將社會責任外部化,同時也反映了Facebook 奉行的數位世界運作法則:利用對立衝突來刺激流量。(註一)
誰也無法擺脫的排除他者遊戲規則
然而在社群網絡的世界裡,其實從來不缺言論反制。這一點,只要去看綠黨(Die Grünen)與AfD的支持者在對方專頁上的言論混戰,就能略見一二。在這些論戰中,綠黨支持者不但無法真正「反制」AfD的極端世界觀,其本身甚至也不得不藉助標籤化(或所謂「簡潔有力」、「易於傳播」、「本日最中肯」、「一句話打臉」)的方式來批判對手。
例如綠黨「臉書小編」在5月1日的這一則貼文,就引發下方留言區的長串混戰。該則貼圖標題為:「AFD:來自另一個時代的政治」。貼文意為:「回歸核電、退出歐盟、女性該在廚房、同性戀該戴枷示眾、必要時可監禁兒童......,AfD的政策是對我們現代社會的宣戰。若你不願倒退回黑暗的過去,請起身行動並分享此圖。」
在此我們看到:在體制之內堅持捍衛開放社會民主自由價值的綠黨陣營,即便對AfD批評有據,但在社群網路的宣傳上,同樣無法擺脫以「標籤化」與「刺激直覺反射」等方式來擴大影響、凝聚政治力量。開放社會與公共價值的捍衛者,亦助長了「過濾泡泡」的遊戲規則,進而可能落入另一種反公共的陷阱。
瓦解共識與共同價值的危機
最後,讓我們卸下「數位利維坦」、「智慧型獨裁」、「數位孿生」、「過濾泡泡」這些為了方便解說而使用的花俏譬喻,回歸樸實的結語:
網際網絡只是工具。但就像其他所有工具一樣,網路這種工具,也包含特定的內在邏輯。使用者無論自覺或不自覺,都會被這個工具邏輯所影響,改變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據此,本文的意圖,並非在強調某種帶著陰謀論色彩的工具邏輯,主宰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性,而是試圖釐清網際網絡這個工具本身的內在邏輯,以及其所帶來的效應。
分析德國案例,也並非暗示讀者將這個案例普遍化,甚至拿台灣或香港的現象來對號入座。因為,數位化普遍的內在趨勢,遭遇不同的社會歷史脈絡,第一時間將各自呈現不同面貌。例如,數位化在德國為保守極端主義的興起推波助瀾,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與美國的杜林普(Donald Trump,台譯川普)現象互相對照;但是 2010 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及 2014 年台灣的 318 運動,卻是相反地,透過數位政治社群集結追求進步與開放,衝撞了保守、封閉而壟斷的體制。
然而在種種差異背後,我們仍能看到一個普遍而共同的趨勢。當今世界危機層出不窮,使越來越多人從原生社會脈絡解離,並被排擠到體制外,轉而藉助看似「平等開放」、「促進直接民主」的數位網絡來聚集社群力量。在另一方面,體制內的人們,也無可避免透過數位網絡來集結,來回應體制外的衝撞。體制內外的人,均不免下意識地服從於數位網絡的工具邏輯。最後,這個發展形塑出的社群性格,將有可能出乎意料地瓦解,人們所欲捍衛的共識與價值,甚至使人不再自由。
為了明確掌握此一趨勢,並使之能進入公共討論的視野,我們不能繼續訴諸現有的概念框架如「個資保護」、「隱私權」、「網絡倫理」、「極端主義」等,將問題化整為零分別處理。我們需要的是全局視野,把數位化、全球化、經濟危機、難民潮,乃至於氣候變遷等,放在系統性的脈絡下來考察。如果我們無法察覺、不去回應,無力將數位網絡這套工具「人性化」,那麼,陰謀論般的工具邏輯,就會在不遠的將來主宰人類命運。
(黃哲翰,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院博士研究生)
註一:直到今年4月,由於聯邦司法部部長馬斯的持續施壓,Facebook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訪德時才坦承Facebook面對仇恨言論的問題過於顢頇,並與聯邦司法部達成24小時內處置仇恨言論的共識。6月初,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平台更與歐盟達成共識,未來將會在24小時內處置仇恨言論與恐怖主義宣傳;儘管如此,馬斯仍不滿Facebook至今的表現,其並非總是能在承諾的時限內刪除仇恨言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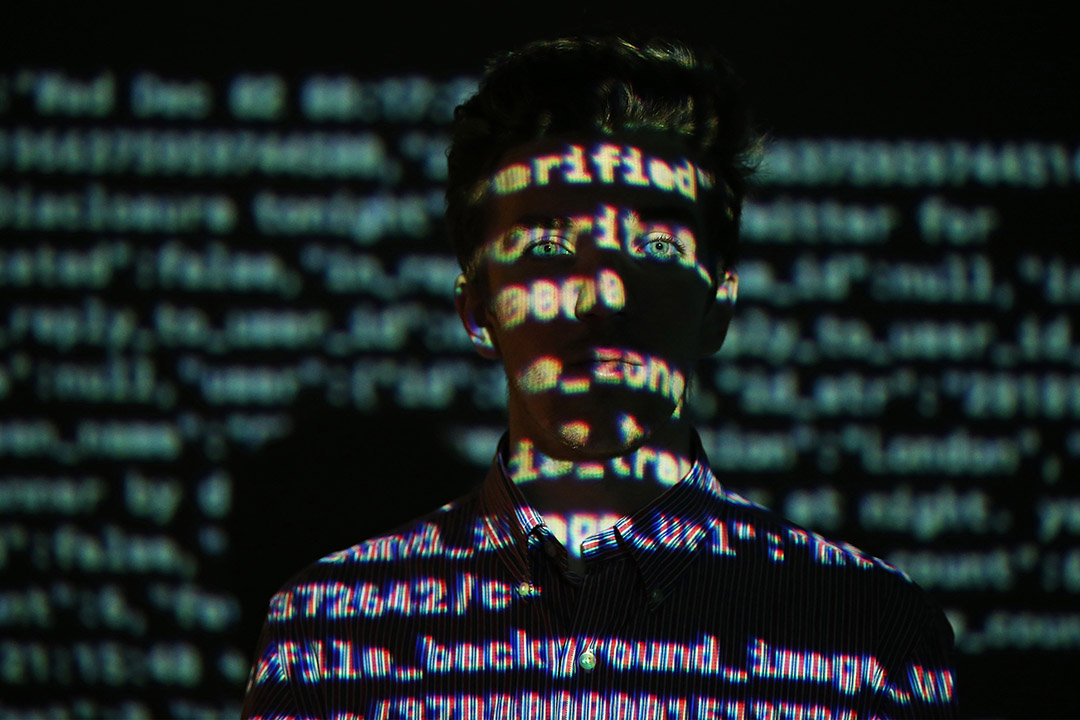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