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时间6月17日,埃及第一位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在庭审过程中突然晕倒,在送往医院后被宣告死亡。前总统穆尔西之死几乎没有在埃及社会激起任何波澜。讽刺的是,因为阿拉伯之春下台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早已被埃及法院下令释放,同自己的家人在红海岸边沙姆沙伊赫(Sharm El-Sheikh)居住。
七年前,当穆巴拉克下台时,穆尔西还是一个几乎没有公众影响力的穆兄会成员。七年后的今天,在埃及执政的依旧是一个从军队出身的总统。曾经是最大的反对派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大部分中高级成员要么被逮捕,要么已经流亡海外,失去了在埃及的政治动员能力。开罗美国大学解放广场校区外墙最后的革命涂鸦也最终被清理。
2010年由突尼斯小贩自焚引发的阿拉伯之春似乎从来没有影响过这个古老的国家。正是在这段看似停滞的时间内,中文读者的老朋友何伟(Peter Hessler,彼得·海思勒,《江城》、《寻路中国》与《甲骨文》的作者)在埃及居住了五年。这五年时间中何伟对埃及社会所做的细致入微的观察,都记载在了他在穆尔西去世前不久刚刚出版的新作《埋葬之所:埃及革命考古》(The Buri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中。
The Buried: An Archaeology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Peter Hessler
Penguin Press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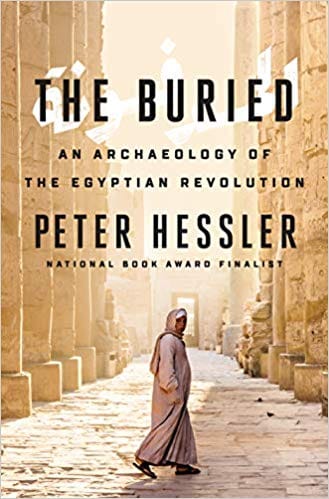
因为埃及政府禁止外国记者在翻译的陪同下出席对穆尔西的审判,学习了埃及土语的何伟是少数旁听了埃及政变之后对穆尔西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开庭审的外国记者。在他的眼中,穆尔西并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也没有什么个人魅力。他的上台部分上是一种偶然——穆兄会一开始准备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海拉特·沙特尔(Khairat el-Shater)没能通过过渡政府的候选人审查,只得将穆尔西作为“备胎”推出。
在选举之前,穆尔西只是一个有些典型的穆兄会成员:一个受过理工科教育,但是又相信阴谋论(注一)的专业人士,在穆巴拉克时期还曾经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遭受过牢狱之苦。在何伟和他周边的普通埃及人看来,穆尔西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演讲者,他所讲的内容常常空洞无物,完全没有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1956-70任埃及总统)那样的感染力。更重要的是,穆尔西既没有提出吸引人的愿景,也没有提出能将埃及拖出经济困难的可行方案。当这样的方案出现的时候,他和穆兄会又缺少足够的意志将相关的方案贯彻下去:作为一个伊斯兰主义者,他连增加烟酒税以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都没有办法推行下去。在何伟的观察中,不少将选票投给穆尔西的埃及人并不一定是伊斯兰主义的支持者。他们只是寄希望于穆尔西不同于旧政权残余推举出来的代表,能够为埃及带来一丝改变。
事实上,包括取代穆尔西上台的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在内,自萨达特以来的埃及就没有什么政治人物可以称得上具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领袖(Chrisma,卡里斯马)气质。按照韦伯的说法,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不但极具个人魅力,还是能够开创新的传统。塞西之所以被埃及人接受,并不是因为塞西是一个能将埃及带出泥潭的出色政治家,也不是因为塞西是个极具个人魅力的公众人物。作为阿拉伯之春之前军队的情报部门首脑,塞西一直深谙保持神秘的重要性。他是如此低调,以至于即便他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接受过交换项目的学习,美国外交决策机构对他也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埃及公众了。这也是为何在穆兄会上台之后,塞西能获得前者的信任成为新的军队首脑。在何伟看来,塞西之所在穆尔西执政后受到很多埃及人的欢迎,是因为革命后的不确定性重新使得埃及人寻求一个强人领导,而作为军队首脑的塞西恰恰满足了埃及人的这种想象。在何伟的笔下,塞西像极了马克思笔下的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拿破仑三世)。塞西之所以受到非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精英支持,不是因为塞西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塞西与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普通民众转而支持塞西,不是因为塞西带来了改变,而是塞西维系了他们过去熟悉的生活方式。

但是缺少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并不是埃及社会问题的根源。何伟认为,这只是埃及社会更普遍状况的一个缩影。埃及社会在普遍意义上缺少领导力(leadership)。埃及人自己也常说,埃及所缺少的就是“制度”(nizam)。埃及的革命是在缺乏领导和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在何伟的观察中,在穆巴拉克下台的前后,不论是埃及军政府、自由主义者和左派还是穆斯林兄弟会,没有任何一股政治势力有既有组织能力来进行制度建设。何伟的这个观察补充了学术界对于埃及社会的判断,也与我于2015年在埃及的观察相吻合。
在阿拉伯之春之前,自纳赛尔以来便浸润着军方背景的政府尽管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国有经济,却很难真正影响一般民众。埃及并不是没有机会建立一个能够深入社会的动员机构,但是一旦当这些动员机构真正成为制度,威胁到执政者地位的时候,执政者就会反过来拆散这些机构。极具威信和个人魅力的纳赛尔这么做过: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军队威信扫地,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成为了纳赛尔唯一的政治挑战者,他便亲手削弱了自己建立的这个机构。何伟认为,穆巴拉克在军队之外另外扶植警察力量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政治学家米格代尔(Joel S.Migdal)指出,这种拆解使得埃及国家陷入了不断失败的恶性循环。长期的后果是,旧制度下埃及庞大的官僚体系成为了一种分肥网络而不是动员网络,以至于当军政府真的开始行动起来对反对力量进行镇压的时候,它也是毫无目的和节制的。在我2015年夏天在埃及南方旅行时,穆尔西竞选的招贴画竟然还没有被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清理干净,而它对示威者的镇压已经导致了上千人的死亡。埃及这种弱国家的特质在阿拉伯之春的这几年动荡中显露无遗。
这点对埃及革命中自由派和左派也一样适用。
他们最为自豪的是一点是,埃及革命是多中心和自组织的,并没有单一的中心。但在何伟看来,这种多中心和自组织并没有那么多其他观察者所赋予的玫瑰色的色彩。这种所谓的自发性其实是革命无目的无方向的遮羞布。没有核心组织和诉求给阴谋论提供了土壤,也让示威者和警察之间的冲突带来了更多的伤亡。最终,无方向成为了革命的阿喀琉斯之踵。埃及年轻的示威者们更加相信街头政治而不是常规政治,他们的目的是一次性的动员而不是持续的制度建设。这种不信任在穆尔西上台一年之际达到了最高潮。2013年四月,五名埃及青年成立了名为“反叛运动”(Tamarrod)的草根组织。这个组织很快开始征集希望罢免穆尔西的民众签名,并收获了不小的成功。在运动初始何伟采访这个组织的成员时,提议说他们应该改进一下自己的签名征集表格,加上签名人的联系方式,以便之后组织签名参与者。这个提议迅速被受访者拒绝,他还反问何伟,难道“反叛运动”要给几百万人打电话吗?最后,“反叛运动”迅速被埃及军方渗透,成为了他们实现自己政变目标的工具。“反叛运动”声称自己将所收集的2200万签名分开藏在了开罗的四个不同位置,但这些签名最后也没有了下文。埃及的左派运动也是如此。在政府的长期打压下,他们没有完整的组织力量,与工人的联系仅仅停留在在街边的咖啡馆与他们聊天,却幻想着将革命引导向他们所期待的方向,而没有意识到人们可能只是对名不副实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有些怀旧。革命运动的无方向最后将埃及革命引向了最悖谬的结果:军政府重新全面掌权。
更重要的是,不同于通常对于埃及的认识,何伟认为埃及最重要的反对力量之一的穆兄会是一支被夸大的力量,穆兄会自身也有意维持这种被夸大的形象。首先,穆兄会在政治上极度缺乏政治经验。虽然是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最大的反对派力量,他们对掌握政权却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当2007年穆巴拉克的继承问题第一次成为埃及政治中的中心议题时,穆兄会高层拒绝了一个高级成员建立影子内阁的提议,他们认为等到掌权那天再筹备政府也不迟。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穆兄会一直对外宣称希望同其他各方共享权力,却在获得议会大多数席位之后出尔反尔,推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在赢得总统大选后,穆兄会后更是采取了一种政治投机的心态,他们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经济振兴计划,倒是希望通过与军方合作弹压自己的政治对手,实现赢家通吃。在没有足够的能力在短时间内解决埃及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同时,穆兄会也没有办法维持民众在选举中给予他的支持。何伟猜测,穆兄会并不像它宣传的那样,有着深入村庄和社区的基层组织。除去防止被政府镇压的原因之外,不想被外界了解到自己同样薄弱的组织能力也是它试图保持神秘的原因。在穆尔西下台之前,何伟有机会采访了穆兄会的多位高级官员。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官员对穆兄会究竟拥有多少成员要么讳莫如深,要么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各种数字。他认识的基层穆兄会成员则以各种理由推脱带他参观穆兄会引以为豪的社区服务。在穆兄会获得较多选票的南方,何伟发现在这里穆兄会在地区一级之下就没有组织了,成员的数量也大大少于省一级穆兄会干部所声称的数目。两者的结合使得穆兄会即使赢得了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也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
著名的埃及史学家马索特(Afaf Lutfi al-Sayyid-Marsot)曾经哀叹,当代埃及的诸多问题在于埃及的政治是以个人恩庇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样的组织方式有一个重要的后果:埃及国家悬浮于埃及社会之上,并不能真正地影响社会。埃及出生的政治学家纳齐赫·阿尤布(Nazih N. Ayubi)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埃及。在他看来,“尽管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是‘硬派’(hard)国家,不少甚至可以说是‘严酷’(fierce)的国家,它们中很少有真正的‘强’(strong)国家。尽管这些国家有着大规模的官僚组织、强大的军队和严苛的监狱系统,在遇到收集税收、赢得战争或者形成能将国家从强制或‘法团’(corporative)的层次提升到道德或知性层次的真正的(文化)‘霸权’屏障或意识形态时,它们却可悲地软弱。”何伟在埃及转型时期的观察为这种悬浮和脱节提供了日常生活中的证据。小到村庄的头人,大到一个省的省长,他们治理方式都惊人的一致:有需求的人在他们的门外排成了长龙,为的是直接向他们提出各式各样的个人要求。不同的群体之间也因此不存在任何有机的连接。埃及各个势力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的缺乏与埃及精英阶层的这种悬浮息息相关。
但何伟对于埃及社会的终极诊断并不在此。除了对当代埃及社会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之外,何伟还往返于开罗和上埃及的考古现场之间,并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向读者介绍了古埃及的历史常识。与一般对古埃及历史的简介不同的是,何伟非常强调对相关的事件和人物进行社会史的解读。有意思的是,这种社会史的解读带来的却是一种带有刻板印象的观点。在何伟看来,当代埃及的问题并不能用它的近代历史进程解释,而是可以追溯到法老时期。我们也就能体会为什么作者将这本书取名叫《被埋葬的:埃及革命之考古》。在书的开篇,何伟就介绍了古埃及的两种时间观,一种是静止式的“永恒”(djet),一种是如尼罗河水般涨落的“循环”(neheh)。何伟笔下埃及的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极强的连续性似乎就陷在了这两种时间观中。真正的变化无从寻找,埃及人国民性中充满着的矛盾则是这种停滞永恒的主题:他们发明了宏伟的观念,却没有充实观念的内容;他们抱怨埃及没有制度,却又笃信各种阴谋论;他们参与革命,却没有为后革命时期做好准备;他们昨天支持穆尔西,今天却又支持塞西;他们一方面渴望民主,一方面又期待强人统治。这种以内在矛盾为核心的国民性在何伟笔下就是埃及缺少制度,精英与普通人脱节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何一轮革命示威就像是一个循环,将埃及又带入了革命前相似的境地。
我猜测,同大部分在埃及生活过的外国人一样,埃及的经历可能给何伟同样也留下了一些心理上的创伤。何伟将埃及社会的问题归结于这样一个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答案,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另一方面,除去关于国民性的带有明显东方主义的论断,何伟又太过相信埃及人对自己国家的诊断。他完全采信了埃及人对自己的批评:埃及缺乏制度。既然没有制度,那么埃及的政治经济学也就不再重要。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全书中很少出现对于埃及军队的批评,而后者正是埃及“国中之国”(deep state)的代表:小到制造火车餐食中的饼干,大到经营沙姆沙伊赫的旅游度假村,埃及军队几乎控制了埃及40%的GDP。正是如此,何伟在相关问题上的沉默显得尤其引人瞩目——当然,这里可能有顾及受访者和自身家庭安全的原因。
瑕不掩瑜的是,何伟作为我们时代最出色的非虚构写作者之一,为我们再次提供了非凡的阅读体验。本书的不少部分已经作为单篇的文章发表在了《纽约客》杂志上,其中的一些人物,比如垃圾工萨伊德,在埃及卖情趣内衣的浙江商人等等也因为这些文章的中译而广为人知。但是这些文章的收入并没有减少《被埋葬的》一书的新鲜程度。何伟在书中展现了更加完整的故事,并使不同的人物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他的行文在不同人物、地点、时空之间熟练地穿梭,像极了小说中的视点人物写作手法(POV)。通过小人物的经验,勾勒出宏大的动荡时代,减轻了何伟行文中带有一点点东方主义色彩的描述,也在全书的最后展现了孕育在日常生活中未来变革的可能性。这正是何伟不同于一般埃及观察者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作品中的永恒魅力。
(张博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博士研究生)
注一:穆尔西在南加州大学获得了材料学博士学位,但他坚信美国自导自演了911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