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討論與女權的行動主義日漸坍塌的2025年,人們對性別議題的討論熱情終於由一系列事件引燃:安徽績溪、甘肅蘭州對海棠女作者的跨省抓捕、南京紅姐引起的全民狂歡、大連工業大學全網實名開除與烏克蘭電競選手Zeus交往的女生、maskpark偷拍房間。
當我們為政府對maskpark偷拍房間的視若無睹感到憤怒、認定烏克蘭選手Zeus才是應該被懲罰的對象,卻又為南京紅姐被刑事拘留而叫好時, 所忽略的一個事實是:中國大陸事實上根本不存在專門針對於偷拍的刑法,僅在《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2條中規定,偷拍可處以最多十天的拘留並五百元以下罰款。
換句話說,無論我們所期待的、反對的,還是已被刑事立案的案件,都是刑法中的同一條,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64—367條「傳播、製作、販賣淫穢物品罪」。較之於韓、日、港、台關於偷拍的專設條目,中國大陸作為「妨害社會風氣罪」之一的「傳播、製作、販賣淫穢物品罪」,在許多時候表現為將性作為一種管控手段,而非將人視為保護對象。這類管控背後的邏輯,是一個父權制政府對異性戀單偶制以外的情慾關係的本能敵意。
在目前中國大陸的公共情緒中,固然有作為既成事實的男女性別對立情緒、女性對政府一以貫之的性別歧視的不滿,但在輿論沸騰而行動匱乏的現實之下,也確乎存在着一種公共意識導致的困滯:在人們要求公權力的保護時,卻不得不面對着必須讓渡個人慾望於公共道德的、隱秘衝突。

好的淫穢色情,壞的淫穢色情
以「傳播淫穢色情罪」所施加的刑事懲罰,其司法目的並非對被傳播對象的保護,而是對被傳播內容的鑑定。
在海棠作者被捕案件中,年輕女性通過書寫來擺脫自身被社會凝視的客體位置,並通過對虛構性關係的想象、操縱來抒發現實情慾。以年輕女性為主體的作者與讀者,對現實生活中傳統的異性戀關係的反叛與尋找自身主體性的嘗試,成為一個正在面對生育率危機的父權制政府的打擊對象。
對比更早(2017年)被捕的耽美作者深海先生,通過專家證人對其作品《奧德賽人魚》文學性的論證駁回了公安對其「淫穢色情」的鑑定,海棠作者的作品顯然在尺度上更為大膽,也更加體現女性慾望的邊界。無論是NP、雙性、GL、GB或其他更小衆題材,這些類型並不只是「獵奇」或「放縱」的幻想,而是女性在文本中試圖掙脫傳統異性戀規訓、尋找自身情慾主體性的重要路徑。
海棠作品中其實充滿了「黃暴」內容,這些文本並不完美,它們往往混雜了對主流異性戀文化的模仿與扭曲,甚至會複製某些父權制結構(例如abo這類設定對傳統男女關係的模仿)。但與此同時,它們也是女性用自己的語言和慾望來描繪性的這一嘗試。她們不再被動接受以「賢妻良母」為核心的情感劇本,而是通過書寫重塑自身在性關係中的位置和能動性,證明了女性的慾望真實一面:女性所渴望的,並不是父權社會給女性「以愛為名」所設定的,必須以建立家庭為前提的、和男性的一對一關係,也不是女性必須在關係中扮演作為妻子和母親的社會身份,慾望必須為此退讓。
因此,即使海棠文學或許還存在着對現實世界的模仿,女性的書寫也讓慾望在這些結構中不斷地做出偏移、挪用和重構:女性可以主動發起關係、拋開社會約束、表達對身體控制與快感的渴望。這些敘述讓人看到:女性的慾望並不是天生羞恥的、等待「喚醒」的,它真實、複雜、矛盾,遠比國家話語中「生育工具」或「家庭守護者」的單一角色更為多維和生動。
地方公安對海棠女作者對抓捕引發了網絡泛女權社群的共情,並導向了一系列公共行動:為取保候審的作者們捐款、年輕的女性律師與媒體人最早開始對海棠作者的系統性營救、聲援。 共情源於一種共識:女性有權利為自己的情慾找到出口,這樣的行為不應該被審判。要沒有傷害到其他真實存在的人,那麼文學作為慾望抒發方式對一種,就應該是合理的。政府應該將抓捕海棠作者的警力用於防治性騷擾、偷拍等會讓受害者受到實際損害的現實行為。
政府應該將抓捕海棠作者的警力用於防治性騷擾、偷拍等會讓受害者受到實際損害的現實行為。
在政府對南京紅姐的處理中,很多女權主義者將南京警方對紅姐的快速刑拘視為對被偷拍男性的保護,並將其與政府對maskpark偷拍群組的忽視作為對比,以論證政府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卻忽視了一點:在中國事實上已經廢除了對性工作者的刑事處罰的前提下,以「傳播淫穢色情罪」所施加的刑事懲罰,其司法目的並非對被傳播對象的保護,而是對被傳播內容的鑑定:
紅姐的視頻展示了中國男性不受傳統異性戀制度規範的性慾望,並因為拍攝對象的數量衆多,可能讓公衆意識到這種不受傳統異性戀規範的男性性慾望或許正是一種人性自然,這對以異性戀單偶製為唯一核心建設家庭制度的政府來說,無疑有着暴露意識形態與人性自然自相矛盾的風險。
如果我們願意承認女性的慾望可以是漫無邊界的、不需要預設色情小說的唯美,那麼紅姐事件中的性關係所遭遇的抨擊,可以說是對對這種觀點當頭一棒:紅姐與發生性關係的對象,至少在視頻中顯示的是一種知情合意、也並沒有傷害到其他人的性行為,然而卻因為畫面的暴露,收到了前所未有、並空前一致的攻擊。
之所以強調知情,是因為無論紅姐是否事先隱瞞了自己的性別,但在視頻裏私下的、一對一的關係中,紅姐與另一方之間顯然並不存在強迫。如果只是因為紅姐的穿着,就認定紅姐視頻中的男性是受到紅姐「欺騙」,反而是否認了男性自身的生理慾望:否認自己是因為面前的對象與私密的情境產生性慾,自我欺騙慾望的來源是來自於見到紅姐真人之前的、想象中的「異性戀規範」。
這顯然是與事實不符的,認定男性的慾望可能被欺騙,無非是在社會規範的「性道德」中,扼殺真實慾望的又一個例子。
紅姐事件中,認定男性的慾望可能被欺騙,無非是在社會規範的「性道德」中,扼殺真實慾望的又一個例子。
當然,公衆還是從某些角度論證了紅姐與視頻中的男人們被批判的合理性:紅姐的行為可能傳播艾滋、嫖娼行為應該被批評、那些男人可能是在出軌。然而,如果真正以嚴謹角度批判,去看看紅姐的視頻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截圖或文字描寫,那麼前兩點都是可以被輕易駁斥的:紅姐在性交中有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安全套),他和很多人發生的性行為是完全免費的:很多時候對方甚至空手而來,連網傳的西瓜、牛奶都沒帶,性行為只是為了自身慾望的滿足,這顯然超出了嫖娼的認定範疇。
至於是否存在出軌,如果我們認定大連理工大學的當事人女生無論是否出軌都不應該受到公共批判,那也必須承認,視頻中的男性或者紅姐是否有固定伴侶,同樣屬於對方的私德範疇。
異性戀男人聲稱與紅姐發生關係的是同性戀、順性別女人否認紅姐可能存在的跨性別身份、性少數群體暗自慶幸這件事被異性戀男女互相推諉⋯⋯還來不及對同性戀的性觀念進行批判,紅姐在全社會的否定中就已黯然退場,以被捕的結局守護了父權制的「基本面性慾正常」。紅姐被刑拘的唯一法律依據來自「淫穢色情罪」,官方這麼做是為了掩蓋男性情慾超出異性戀範圍的部分,公衆同意這麼做是因為這是衰老、醜陋、不堪的畫面。
公眾所認知的「真正美好的性」本質上是一個圈套,或許只存在於三個地方:
一:商業社會里onlyfans中那些精緻人類(主要是白人)的性關係。
二:父權制中,以愛為名,實則依然是作為父權制家庭結構的單偶制異性戀關係。
三:進步話語中,性可以完全自我選擇的幻想。
當人們說出「這樣的畫面讓人噁心」時,忽略的是,自己所看到的固然是被偷拍的畫面,但這些畫面在事實上也是個體的慾望、衝動,是人類最本質的行為之一。因為「感到噁心」而對個體慾望、尤其是紅姐作為衰老、醜陋的底層性少數群體與性工作者的慾望進行抨擊,事實上與淫穢色情罪的暴政如出一轍:禁止父權制規範之外的性出現在公衆視野中,也默認不符合規範的性慾是可以被公權懲罰的。
當我們以審美,以道德來論證什麼是好的性,什麼是壞的性,什麼是無辜的淫穢色情、什麼是有罪的淫穢色情時,被審判的永遠是失權一方,被鞏固的也永遠是父權異性戀國家體制。
將審美、道德凌駕於自身的慾望之上,本質上或許也是一種失權的體現——海棠作者的被捕恰好說明了女性在性慾望的弱勢,即使只是停留在紙面上的性慾望也會面臨被非法的困境,關於真實性實踐的討論則更加遙遠。當女性還在分辨好的淫穢色情,壞的淫穢色情時,忽略的正是:性慾望的自主性往往與我們自身的主體性相連接,與女性對性的道德與審美要求相對應的,正是順性別異性戀男性不可撼動的性慾望的合理:男性為自己的性慾望合理化了曾經的「嫖宿幼女罪」,合理化了性騷擾、合理化了偷拍、合理化了無比龐大的性產業。
諷刺的是,當紅姐被全網羞辱、女性試圖以「紅姐嚴選」來回應男性的蕩婦羞辱、紅姐視頻中的其中幾位主角在社交平台上收穫的反而是關注與打賞——男性霸凌其他所有群體的主體性即體現在此:父權制社會永遠容忍男性對女性的一切慾望,如果男性表現出超出這一規範的慾望,則將以紅姐的消失與男人的「被騙」為之遮掩。
淫穢色情罪對兩件公共輿論事件進行相同處理,一則引發爭議、一則引發肯定的社會反應,體現了父權制政府關於性自由的惡法,是如何通過公共構建的審美與道德,實現對弱勢群體的自我約束,岌岌可危卻依然實現了自身合理性的構建。國家機器是藉助道德與審美以超越法律可以抵達的範圍,以暴力的形式對個人慾望進行管控。當我們以審美,以道德來論證什麼是好的性,什麼是壞的性,什麼是無辜的淫穢色情、什麼是有罪的淫穢色情時,被審判的永遠是失權一方,被鞏固的也永遠是父權異性戀國家體制。

好的偷拍 壞的偷拍
大連女生「辱國格」事件,支持者試圖用私人道德上的「無錯」來抵消公共道德上的「有錯」。
在大連工業大學對涉事女生以有辱國格的名義開除學籍而引起軒然大波時,面對着行動空間的緊縮、線下的聲援行動難以進行,大陸的女權主義者只能以網絡辯護作為對當事人女生的支持,行動主義的退行與網絡辯論造成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不得不沉溺於事件本身的細節中。
我們看到很多辯護引用烏克蘭電競選手Zeus的澄清:Zeus是一位單身男性,所以和他發生性關係並不存在道德問題,當事人女性也是被偷怕的受害者,應該受到政府的保護而不是傷害。
這樣的辯護看似合理,實則暴露出一種悖論:社會對女性的性道德判斷,始終處於國家主義與父權制的雙重框架中。
在「辱國」指控下,大連工業大學的女生與烏克蘭電競選手Zeus的這段關係被賦予了「集體道德」的意義——即女性身體是否忠於國家尊嚴。而在私人辯護中,性行為是否合法則轉向「私德」的評判——是否破壞他人婚姻。支持者試圖用私人道德上的「無錯」來抵消公共道德上的「有錯」。
然而,在父權邏輯下,「集體道德」永遠凌駕於「個體選擇」。無論Zeus是否單身,當性行為發生在女性身上、並在公衆空間中暴露出來時,它就被迫成為一個「公共事件」——她的身體不再只屬於她自己,而屬於「民族形象」、「社會風氣」乃至「國格」的延伸。這正是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根本規訓方式:公共可以隨意介入私人的邊界。需要論證的並非是私人道德的無暇,而是對公共道德入侵私人邊界的抵抗。
這正是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根本規訓方式:公共可以隨意介入私人的邊界。需要論證的並非是私人道德的無暇,而是對公共道德入侵私人邊界的抵抗。
試圖介入私人邊界的並非只有集體道德,女權主義者以私人道德的無瑕並強調其偷拍受害者的身份為大連工業大學的當事人女性辯護,然而,檢索一下事實材料,如果女生對被拍攝其實是知情的,如果Zeus在社交網絡上的表現,確實是一個明顯存在Yellow Fever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呢?
在女權主義者試圖提供一個完美受害者的範本時,其實也在矮化當事人女生的自我選擇:她並不知道這是一段可能存在私德問題的關係,她並不能為存在私德問題的性關係承擔責任。在這樣的辯護策略中,無法面對道德問題的的人,就會從國家主義者變成了試圖捍衛女生的女權主義者,因為完美的性關係與女性應該選擇完美性關係的主體性,恰好也是女權主義作為一種進步話語給其受衆營造的幻想。
在中國公民社會萎縮,行動主義難以為繼的當下,女權主義作為一種進步話語,也不得不從公共倡導退縮到對女性個人生活的捍衛。這種對個人生活的捍衛,也涉及到女性在親密關係中的選擇:要選擇健康的關係,反對一切不對等的性行為,要識別PUA、拒絕Yellow Fever,要永遠不被物化,也不「主動掉進」物化關係之中。
在這樣的進步規範下,女性的個體被重新政治化,日常選擇也被嵌入到一種政治責任倫理之中。問題是——這種對「選擇正確」的要求,恰恰製造出了一種新的焦慮與不自由:她必須在結構壓迫中「做對事」,否則不僅會受到傳統父權的審判,也會被進步陣營視為「對運動的傷害」。
在行動導向被迫從女權主義中剝離的當下,中國社交網絡的性別進步話語,反而與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高度契合——它鼓勵女性自我提升、自我修正、自我負責,把原本結構性的問題轉化為個體道德與理性判斷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脫離行動主義的性別進步給受衆提出了「自我照顧」作為私人領域的最高責任,這種自我照顧在親密關係中的意思就是必須擁有健康、有利於個人發展的親密關係。
作為一個和外國男性交往的中國女性,大連工業大學的女生所遭遇的惡意在互聯網上並不少見,幾乎所有和外國男性結婚,尤其是和黑人男性結婚的中國女性,都會在為自己辯駁的時候強調:這段關係健康、平等,比大部分親密關係都更好,這不只是女性作為弱勢群體的道德焦慮,也是進步話語讓我們無法想象,或者說無法承認:女性的個人慾望或許與「我必須永遠做出對的選擇」這一教條相違背。
在親密關係中,或許也存在對道德、可能性風險、平等都相違背的慾望,這種慾望可能是一個成年女性的自主選擇,並不是被男權社會欺騙,而是她願意且有資格選擇讓自己快樂,而不總是正確。

在親密關係中,或許也存在對道德、可能性風險、平等都相違背的慾望,這種慾望可能是一個成年女性的自主選擇,並不是被男權社會欺騙,而是她願意且有資格選擇讓自己快樂,而不總是正確。當女權主義話語落入個體道德主義陷阱時,它無意中製造出一個只能在完美條件下成立的自由——對女性來說,這並不是真正的自由。在女權主義者也無法接受當事人可能對親密關係中的自我物化並不在意時,這種對於女性的要求甚至與國家主義同構。
與大連工業大學事件同時,女性被國家主義羞辱的憤怒讓maskpark偷拍事件被重新大範圍關注,女權主義者要求國家對 telegram 上的偷拍群組進行整治,然而在正當憤怒的掩蓋下,一個被系統性忽略的事實是——在經濟下行的當下,中國的境外色情群組內所傳播的內容往往並非全為「偷拍」,其中相當一部分內容來自性工作者的產出,是處於經濟下行、無勞動保障邊緣狀態的女性(及性少數)為生計主動生產的色情製品。
在中國大陸以淫穢色情罪對成人內容的打擊背景下,一個父權制政府沒有意圖分辨何為侵犯權利的偷拍,何為女性對自身身體與慾望的自主勞動;「打擊偷拍」與「打擊性工作」往往是一併完成的。而在女權主義的呼籲中,這種區別也常被忽略,甚至主動消除。在權力面前,一切看似「淫穢」的圖像都被歸入同一個懲罰系統,性工作者也在「打擊偷拍」的正義名義下再度失去發聲的主體位置,被當作「必須清除」的污穢。
女權主義者在偷拍恐懼下對國家權力擴張的渴望,事實上也是父權制政府的有意為之: 在有意不設立偷拍相關專法而用「淫穢色情罪」來進行選擇性執法時。
因此總的來說,當所有人,包括女權主義者們,將政府對於淫穢色情罪的使用視為對男性的保護與對女性的無視乃至懲罰時,淫穢色情罪反而鞏固了自身的合理性:我們要求國家機器對公民的性自主權進行保護時,卻忽略了這其實是國家機器對公民進行情慾審查、或者說情慾清洗的工具。
我們要求國家機器對公民的性自主權進行保護時,卻忽略了這其實是國家機器對公民進行情慾審查、或者說情慾清洗的工具。
好的淫穢色情、壞的淫穢色情;好的偷拍、壞的偷拍;好的性,壞的性——女權主義者真正需要爭取的,從來不是對個體道德的評價,也不是國家的主動介入。性不是純粹的私人行為。它之所以被高度關注、被立法、被判定、被羞辱,是因為性在現代社會中承擔着遠超個體體驗的功能——它被用來界定道德、建構民族、維繫權力結構。圍繞「好的性」與「壞的性」的劃分,從來不是出於保護個體的初衷,而是出於對社會秩序的維護、對集體道德的恐懼與對政治正當性的需要。
女權主義若希望在此情境下保有力量,要做的不是等待國家去「保護女性」,而是揭示國家本身如何作為父權結構的延伸,在日常治理中持續定義誰可以成為受害者,誰可以擁有身體,誰可以自由地慾望。在這個意義上,性別平等的政治並不建立在每一個人都選擇了「正確的關係」,而是每一個人——即使選擇了不被看好的路徑、即使擁有邊緣的慾望、即使進入了非理想的性關係——仍然不被拋棄、不被羞辱、不被作為道德懲罰的對象。
性別平等的政治並不建立在每一個人都選擇了「正確的關係」,而是每一個人進入了非理想的性關係——仍然不被拋棄、不被羞辱、不被作為道德懲罰的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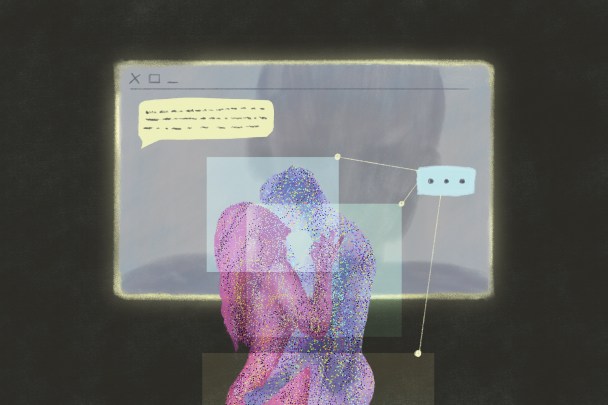

弦子说mask park事件里牵扯到的电报群组有性工作者自发传播的视频,而我其实更觉得maskpark事件里传播的视频大多数是偷拍+未授权传播的。其他的没有什么异议。我觉得弦子把理论结构与逻辑写得很清晰详细了。个人提升、自我道德要求是重要的,但只因为不够进步就把一个人打成敌人是不可取的。
紅姐偷拍事件,我認為重點是未經當事人同意進行偷拍,並放上網賺錢。
假設1:紅姐是男跨女的女性戀者,她隱瞞自己的性別身份引誘女性到家中性交,本文作者會如何評論事件。
假設2:紅姐是女跨男的順性戀者,他隱瞞自己的性別身份引誘女性到家中性交,本文作者會如何評論事件。
假設3:紅姐是女跨男的同性戀者,他隱瞞自己的性別身份引誘男性到家中性交,本文作者會如何評論事件。
我絕不是攪事搗亂,是認真地設置不同場景去思考事件本質。
「包括就海棠事件分析各界對弱勢性別群體的多重尋租、並就紅姐和鄭州打人事件分析男性群體的恐同的雙標和驅逐。」
這一句更是寫得非常不專業,完全就是改寫了原本兩篇文章作者的原意。第一篇海棠事件明明文中就說了海棠是是女性向文學網,文中提到的讀者和作者絕大多數是女性,用弱勢性別群體明顯是拉上了文中沒怎麼提到的酷兒團體,這是作者的原意嗎?第二篇引用的文章,作者明明針對的整個異性戀以致社會上對於家庭和戀愛的想像,不論是男性,女性,甚至部分酷兒族群對於事件的回應,作者都有表達了不認同,怎麼就變成了「男性群體的恐同的雙標和驅逐」了?最簡單的邏輯謬誤是「男性群體的恐同的雙標和驅逐」中的「男性群體」包含非順直男嗎?所以編輯是覺得中國的男性非異性戀也是在恐同和雙標?
不針對作者弦子,只針對端的編輯:那一段編按文字真的是極度不專業。引用最近發生的兩性對立事件全都是女性比較「占理」的時間,反而熱度更高的時間,比如白盼雪事件,還有“你不必嫌弃我的残疾,因为我不会成为你的妻子和朋友”的熱梗,以及武漢大學楊姓畢業生的事件就只字不敢提。是端也覺得她們也無法辯護純屬活該嗎?(我可不這麼認為,而且這幾則新聞對於男女對立,性別之間邊界以及對彼此的想像也有很值得討論的地方)。
“性别平等的政治并不建立在每一个人都选择了“正确的关系”,而是每一个人——即使选择了不被看好的路径、即使拥有边缘的欲望、即使进入了非理想的性关系——仍然不被抛弃、不被羞辱、不被作为道德惩罚的对象。”
谢谢弦子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微博上弦子的账号很久没有更新,也无法进行关注,账号肯定是被限制了。很多时候,总会去看看弦子的微博,想着弦子会怎么发帖分析社会上那些有关性别议题的“新闻”,最后还是在端这里看见了。
端传媒为何没有点赞功能,留痕支持
“並就紅姐和鄭州打人事件分析男性群體的恐同的雙標和驅逐。”
端的那篇文章真的只是分析了男性群體的恐同的雙標和驅逐嗎?😅 恐怕這不是作者的本意吧?
弦子写得太好了,有点绕!但是写得真好,不过 Zeus 的名字是不是写错了?
感謝指正,已修訂!
當然,我說的那些並非反對作者的觀點,相反我還是挺認同作者的看法。就像文中提到的,不論是男權主義者還是女權主義者都在通過賦予國家機器權力的方式推進自己的議程,然而這個不斷強化的國家機器並非雙方能掌控和主導的。這也使得雙方與其說是呼喚國家機器下場,有時候倒不如說是在討好國家機器,就好像是在父母之前爭寵的兩個小孩一樣😅。
好文
這種來自於社會,組織甚至是公權力介入私人關係的壓力就像是前線士兵呼叫的空中支援以及火力打擊。你能想像而烏前線的士兵在被火力壓制以後不向上級呼叫空中支援砲火支援,只靠手上的武器開打的嗎?😂 而且這種公權力介入私人生活的傳統從古代中國的家天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即使是皇帝也沒辦法去擺脫。更何況是在現代還要靠男女對立雙方去建立共識去維持?
性別平等的政治並不建立在每一個人都選擇了「正確的關係」,而是每一個人不被拋棄、不被羞辱、不被作為道德懲罰的對象。
這個真的很難吧😳 不論是男權主義者還是女權主義者,他們都認為現在他們就處於一場戰爭之中,而all is fair in love and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