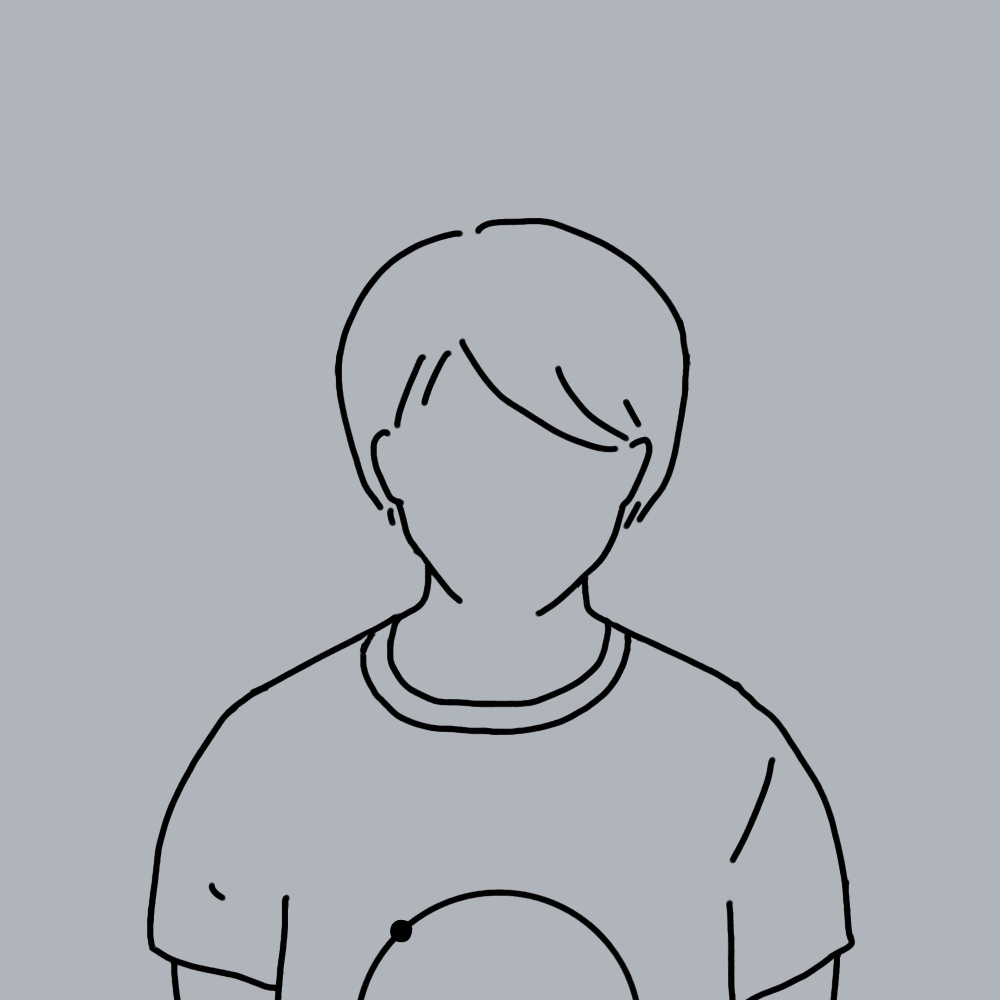2025年4月,我在思考自己之後還能不能順利入境美國。我上一次入境是2024年10月,進行美國大選報道的時候,那次拿著J簽(訪問學者簽證)的我居然沒被拉進小房間二審覆檢,直接被放行。但半年間,美國翻天覆地--今日,哈佛所有拿著F簽(學生簽證)和J簽的國際學生﹑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們,隨時會因為哈佛公然對抗特朗普,拒絕取消DEI計劃和親巴勒斯坦學生團體許可等要求,而被取消簽證。
這是特朗普第二次向國際學生開刀。上一次是疫情高峰的2020年7月,當時所有美國大學全面轉網課,但特朗普透過ICE宣布F及J簽的持有人必須回校園上實體課,否則將被逐離境。那時我在美國,是受影響的J簽之一。最後多家大學入稟控告政府,特朗普政府撤回政策。
但那已是5年前,法院仍能制衡白宮的時代。如今針對精英學術界的大驅離的規模是美國史上鮮見,甚至可能大於麥卡錫時代的獵巫,或者二戰前後針對猶太學者與德裔科學家的入境限制。當然我們早就知道,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更有準備,更不怕挑戰美國所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或者說,他的目的,就是顛覆美國民主體制內的所有紅線,而限制總統權力的枷鎖,他將會一一擺脫,做法或者是公然違抗法院命令,並且用語言進一步測試底線(例如提出可能用驅逐委內瑞拉移民的方法驅逐美國人)。
正如普利策獎得主,以寫東歐極權史聞名的Anne Applebaum說的:對特朗普來說,一切都像玩遊戲--他不在乎傷到的是誰。你沒看錯,他在挑戰美國民主的底線;但問題在於:美國有全世界歷史最悠久﹑最運行有度的民主制度之一,為甚麼脆弱如此,特朗普才上任百天就搖搖欲墜?
一直以來,比較深入的美國觀察者常用「backlash」(反撲)來理解特朗普或極端保守主義組織或思潮的崛起。「反撲」的框架的背後是一套動態的美國史觀:在美國歷史中,每當自由派或進步派得到一點制度成果,保守主義就會大舉反擊。 1950-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沸沸揚揚,最終取得《民權法案》立法等成果,但這些成果卻催生了美國政治史上最成功的「反撲」策略「南方政策」(Southern Strategy):共和黨在1960年代開始,有意識地吸納南方白人對民權運動的不滿,用文化戰爭、種族暗示(racial dog whistling)、反精英語言等方式,鞏固自己在南方州份的票源。
另一個例子就是茶黨。2008年奧巴馬當選,成為美國史上第一名黑人總統後,標榜反稅﹑反大政府﹑高度懷疑聯邦權力並高舉州權(在美國的南北戰爭的歷史語境,擁護州權是阻撓進步改革、維護保守秩序的象徵)的茶黨運動迅速崛起,並且擁攬了共和黨內外一大批「信徒」。奧巴馬和自由派當時高舉「改變」(Change)的大旗,但茶黨幾乎是立刻將「改革」﹑「自由」的形象據為己用,並且打著「反暴政」的旗號,用州權來反對奧巴馬的醫保政策。
自特朗普勝出選舉,許多評論人都把DEI放在討論的核心。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因為DEI的政策「推得太過火」,以白人﹑保守異性戀男性為主軸的群體感覺他們的利益被損害,所以特別容易受特朗普和其盟友的極端論述吸引。這些評論者有右翼份子,但有些甚至是同情自由派的。這個側重點,明顯忽略了特朗普上任後一系列操作的邏輯:他並不是在「校正」美國的民主,而是在完全重寫美國政治的規則。例如他正準備推動的「Schedule F」改革,就將讓數以萬計原本具保障的文官可被任意撤換,原因只需要是「不夠忠誠」。制度設計原為防止政府變為個人家臣團,但特朗普正用法律修改回頭將整個體系私人化。這跟DEI有任何關係嗎?顯然沒有。
因此,我開始懷疑「反撲」是不是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好的框架。去年10月在採訪大選期間,的確有許多人跟我說因為民主黨和賀錦麗「容許囚犯在獄中變性」﹑「放任青少年在學校變性」,所以會考慮支持特朗普。但說這就是一場反撲,似乎抹去了許多細節:首先這些絕大部分都不是事實,而是有系統地灌輸給大眾的一套世界觀;其次,數據顯示愈不看新聞,愈無法全面掌握信息的人,就愈容易持這種觀點。所以,這真的是保守主義人士看不過眼進步人士的「囂張」,所以必須舉著「拯救美國價值」的大旗,把類似DEI等「矯枉過正」的政策推倒嗎?在選民的層面,我認為可圈可點;在特朗普的層面,就更明顯不是--他的目標從來不是DEI,或者甚麼性別二元,而是一場深層的權力重組,而代價將是美國的民主制度。
那麼,在美國內外的我們,能如何理解我們身處的現實?這大概是你的問題,也將是我們報道﹑解析﹑評論的方向。美國總統上任首百日一般被視為被視為施政黃金期,端傳媒的「特朗普百日」專題,嘗試解讀特朗普發出的政治信號:他的目標到底是甚麼?他眼中的這個新的美國,到底會長甚麼樣子,而且誰會為此付上代價?美國社會以及整個世界,如何感受到這些政策帶來的震盪?
我們重訪了一年前曾參加巴勒斯坦紮營抗議的華人師生﹑也訪問了特朗普2.0時代的中國留學生;我們也書寫了被特朗普中止美國旅途的滯港難民的故事、以及USAID被削減開支後的全球影響。接下來,我們即將刊出關於特朗普的外交路線以及全球關稅戰等等議題的報道與評論,還有馬斯克的DOGE的「結業盤點」。請按此閱讀「特朗普百日」專題。
我們也藉此重新啟動我們的美國新聞信《美國時間》。在現代世界,曾定義「全球標準時間」的霸權有兩個:一個是19世紀的大英帝國,另一個是二戰後的美國。「美國時間」不止是華盛頓的政策節奏,更是一套主導世界秩序的價值座標,我們在它的規則下生活、報道、對齊時差。但如今,當這個秩序漸趨瓦解,「美國時間」的意義,也正在發生改變。《美國時間》新聞信將紀錄﹑報道﹑拆解這些轉變,讓我們在「美國時間」崩解的時空裡仍能互相溝通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