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上篇:《福島核災復原(上):經歷核災,日本人也是第一次|端對談》)
本篇標題取義自馮蘊妍的散文《在工業廢墟中寄望植物》,她提出這個問題:在工業污染的持續後續(aftermath)中,如果既沒有即時的出口,也沒有終點線,我們該如何希望?工業污染災難「之後」,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時間和存在?(英文原文可見Critical Asia Archives)
日本政府將這些措施無窮無盡地放大,就是一個雄心壯志的做法,也可以說是一個最符合這個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利益,因為這樣的話就可以用最快的時間去證明給所有人看——日本的除染已經成功了,所有東西都回到正軌了。
「除染」的假象
端:政府自己有一套對污染的測量,不過我們也看到民間有自己的測量方法,例如在污染水上都有不同參數的爭議。這些測量結果可以如何借鑑呢?怎樣看政府和社會在科學和專業問題上的這一類博弈呢?
譚萬基:政府的除染工作是參考了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在切爾諾貝利時的一些所謂除染的技術,但是如果追回原始文件的話,其實現在所謂的農地除染、又或者是剛才蘊妍說過的用水壓槍洗這些技術,當時IAEA是不鼓勵廣泛大型應用的。例如你家後花園,如果有一個被污染的地方,你就可以刨一些泥,(文件)說得很清楚,如果那是你家後花園的話。
但是日本政府將這些措施無窮無盡地放大,就是一個雄心壯志的做法,也可以說是一個最符合這個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利益,因為這樣的話就可以用最快的時間去證明給所有人看——日本的除染已經成功了,所有東西都回到正軌了。
當時日本申請東京奧運,安倍晉三給了一個承諾,說東京奧運的時候福島已經沒事了。搞奧運是一個什麼標誌呢?1964年日本第一次從戰後廢墟經歷高速的經濟成長,通過奧運會向全球證明日本已經站起來。第二次(這一次)的東京奧運其實也有一個這樣的意思。所以我覺得,政府一開始推動的那些除染工作,其實都不是以福島當地人的福祉來做的,這和他們幾十年之前在福島建核電廠的心態一樣,就是以東京人、首都人的利益為依歸。
在這個背景下,我在飯館村看到,有一班人不理這些事。我問他們想做的是什麼,他們就說用農耕來實驗一些方法,而他們實驗的方法是能夠重新種植包括稻米、菜。2016、17年,政府所有除染工作完結、檢測完成、重新開放,這之後他們才開始做。但是我跟的「福島再生會」,他們2012年已經開始試種第一次,到2014年已經開始種出輻射能穩定地低於政府安全標準的稻米。換言之,想重新耕種的人的生活可能是推前了很多,也令他們可以提早準備怎樣回去。
馮蘊妍:有關現在日本東北的農業支援政策,福島大學的准教授石井秀樹提出,現時的政策傾向引入一些科技、機械協助擴大生產力。但他研究南相馬種植油菜花和飯館村種雜穀米的實踐,指出農業支援的目的不限於如何最合理化生產力,而是怎樣在做農業的同時保存社區,尤其是有些種植農已步入晚年。如果單止以「生產力」去衡量農業的復興,可能就會選擇放棄一些不利的土地,集中在生產力高的土地。但他提出我們也應該要注意農業的社會價值。
張政遠:農民是有很有趣的一種想法,對於稻米文化有一種重視。我們也認識一些福島縣釀酒的人,對於核災的問題反而不太願意接受訪問,會覺得「我已經復興了,重新在賣酒,你又走來,好像在傷口上灑鹽,會影響到酒的銷量。」
另一批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漁民,他們並不是由零開始,因為漁民基本上災後在漁村裏一直等待,等重新拿魚。他們的想法也相當有意思,希望趕快將海的污染減低,盡量停止所有污染的排放,令這個海可以重新拿到魚。他們還造新的船,希望之後幾代都可以捕到魚。我們去的一個地方叫新地村,就看到這樣的漁民。
但是因為東電和政府希望排放污水,令他們覺得沒有兌現先徵求漁民同意的承諾,出現了相當大的不滿。其實早前有一套紀錄片叫「福島漁民物語」,這個導演一直在跟進很多我認為是官方以外的、被遺忘的聲音。我們通常聽得最多的是漁民代表,但漁民代表也不一定能反映很多漁民的意見,尤其是獨居漁民的。所以除了農民外,漁民也是很需要去跟進的。
其中漁民了解的自然,令我很有深刻的印象。我們覺得海是在那裏的(out there),在我們看到的地方,但漁夫想的海其實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他們為什麼反對排污呢,因為不希望這個水排放到身體裏成為一部分。
我最近也跟「福島復生會」的會長田尾先生談過兩句,他說「除染」主要是國家項目,通常是搞道路工程,開一些大型的剷泥機。但是對農民來說,其實更加適合除染的就是農具,但是國家的除染就不會讓農民參與。搞道路工程的人完了之後就發現,他們不懂得搞,當地人也是得不到任何恩惠的。

我們覺得海是在那裏的(out there),在我們看到的地方,但漁夫想的海其實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他們為什麼反對排污呢,因為不希望這個水排放到身體裏成為一部分。
譚萬基:我自己做田野的時候,跟一個來自北海道幫忙搞除染的工人談過一次,他就說,「我怎麼會懂(怎樣除染)呢,我只會開剷泥車而已。我來到,我就挖咯。你教我啦,怎麼挖5cm表土?大型的重型機器喔,怎麼挖?所以他們大部分就覺得,挖多好過挖少,挖多一點不虧。但是對農民來說,你就害死他,因為你將表層最肥沃的泥土弄走了。挖了這些東西之後,日本政府就用山沙填了這塊除染之後的農地,而這件事就令到很多農民不再想復耕。
還有另外一個我做田野看到的笑話是,某塊地會突然插了一些旗,寫著「地力回復中」。就是除染之後的地,在上面再撒一些一粒粒的肥料。
你說這個方法是誰教他的呢?我問過東大一些教授,他們都很厚道,說「嗯,不知道這個方法可不可行呢」?那就是不可以喇。
我們現在對災後想回去的人的論述,都會用一些大的分類(category),譬如漁民、農民、村民。但我覺得都要小心的,以飯館村為例,我們以為很多人是全職農民,但我調查所知,很多農民其實本身是一半,半農半X的,可能冬天會去做貨車司機來維生。我不知道漁民是不是這樣,但其實當我們想像一個農民、想像他們和農作物、米的關係時,也要小心刻板化:他們之所以有動力去做一些復耕的工作,或者所謂對抗政府的運動,其實都未必跟農民身份有關。
舉個例。在飯館村,為甚麼會分了兩派,然後有一派站出來說要爭取賠償呢?其實是和他們傳統上爭取自主(的經驗)很有關係。飯館村在2000年左右,自己搞了一次很大型的辯論,就是會不會和其他村「合併」。叫了大家、吵了大架、搞了幾年,結果就決定不併村。而當時所謂領袖人物,在2011年之後組織了其他村民,一起去爭取另一班人。所以這種村和村、或者不同的地方之間,各自的地方史,是需要了解的。
馮蘊妍:整個日本在核電廠問題上,其實都有多次住民投票的運動,可能是關於建不建核電廠,或者是核電廠延長運作的爭議,當中有過成功反對興建核電廠的案例,如1996年的新潟縣卷町。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公共性的地方自治問題。
地方財政依賴核電產業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犧牲體系或者不平等背後,有一個「你肯建或你肯讓我研究、我就會給你錢」的這個財政依賴的問題。

公民社會、政策溝通
馮蘊妍:我有一個問題,大家怎樣看現在核廢料處理的方法?有一些就是等放射能水平降低的時候再利用,譬如去年有一個住民説明會,有關打算在(東京的)新宿御苑將那些污染土用在那裏的花園上。其實除了311的核廢料,早在2005年的時候,日本已經有一個叫做クリアランス制度(Kuriaransu,為“clearance level”中“clearance”的片假名),就是核能發電廠的拆解等產生的資材中、放射能濃度低的部分,可以視為一般產業廢棄物,根據相應的制度進行再利用或處置。
我自己會覺得,首先就是基準的問題要怎樣去決定?但我想問多一點兩位,因為你們更多在現場。
譚萬基:我覺得,第一如果從環境正義的角度來說,這些廢料到了政策推動下,是會不平均地分去不同的社區的,而在現在的制度底下呢,有錢的人是不會「享受」到這些廢料的。
但是說到這裏,我覺得既然核災是一個沒有人可以避開的問題,那麼這些所謂「低放射性廢料」它是否可以再用,正正就是要問我們自己——因為其實這個世界沒有乾淨的地方了。
你怎樣回應你的用電,你怎樣回應東電仍然不停鼓吹重開,怎樣回應日本政府要「國策」?我覺得與其討論集中在那些東西好不好用之外,另一個焦點其實就是問,在你自己的生活裏面,究竟可以做一些什麼動作和決定可以影響到這些政策?
馮蘊妍:有關環境正義的問題,我可以補充一個政策背景。有一個叫「電源立地地域對策交付金」的東西——你肯建核電廠和相關設施的話,就給你錢。上個月東京新聞有報,使用過的核燃料已經開始沒有位置擺放,電力公司就想覓地建新的。
其中一個接受了這樣我們稱為「原発マネー(nuclear plant money)」的就是山口縣上關町,那個地方本身就想建核電廠,但3.11之後就凍結了,因此本身想通過建核電廠拿到的補助金沒有到手。 即使未到興建,只要願意接受調查,也可以申請補助金。山口縣上關町答應讓中電公司進行調查,研究在町內建設使用過的核燃料的中期儲存設施的話,就可以申請「電源立地等初期對策交付金」,補助金最多提供1億4千萬日元。
所以地方財政依賴核電產業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犧牲體系或者不平等背後,有一個「你肯建或你肯讓我研究、我就會給你錢」的這個財政依賴的問題。
張政遠:在飯館村內,正正(將會)有這樣一個實驗室,叫做「中間貯藏設施」,擺了一輪的泥土在那邊,好像可以再利用。這是一個前導實驗(pilot study),可以儘管看看它的實效,有很多評估方法,專家會跟進。
我個人了解,這個是解決不完「中間最全設施」裏面所有的污土的,再利用的只是一小部份。而且這些中間最全設施擺30年之後,要找一個新的地方再擺,很有機會繼續犧牲。所以我認為只是解決問題表面的一些做法,一個更加大的污染是不能夠再有效利用的。
我有些朋友在東電工作,他們有個論點是,現在國際能源價格高企,用核能可以舒緩電費。我的反駁就是,短期電費會再便宜一點,但再有一些事故的話,我們已經知道你們是不能夠處理核災問題的。 他們的想法好像是就算不再建新的核電廠,也可以再利用現存的核燃料,「不浪費」,「用左先」 (用了再說)。

當東電有這樣的思維的時候,民間要怎樣有新的回應呢?
災後其實要真正面對的問題是民主化——怎樣有不是國策的東西產生?防災專家也終於有一個反省,就是很多時候他們只不過是看到數據,知道防災的機制怎樣搞、知道工程上怎樣去解決,但他們不懂怎樣跟一般市民溝通。
災後其實要真正面對的問題是民主化——怎樣有不是國策的東西產生?首先就是每個地區層面都應該有一個一般市民可以發言的空間,讓意見分裂的人都有機會坐在一起聊。比如在「哲學咖啡」做的活動裏,防災專家也終於有一個反省,就是很多時候他們只不過是看到數據,知道防災的機制怎樣搞、知道工程上怎樣去解決,但他們不懂怎樣跟一般市民溝通,因為他們的訓練裏未試過跟人溝通,沒見過農民、未見過漁民。
透過活動,起碼學到溝通:專家所要面對的是一班「人」,他們不一定知道你在說什麼的。聊天就是為了解釋,出現災難之後防災的處理是怎樣的呢?我們做個模擬給你,可能大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但我們怎樣討論避難?你們原來是怎樣想的呢?我們作為專家會怎樣想的呢?有沒有一個可以增進了解的地方?
馮蘊妍:說起哲學咖啡這個不同立場對話式的實踐,我就想起在日本的公害史上,70年代開始其實有很多關於「技術者」,包括中小學老師、大學教授、研究者,怎樣和民眾溝通的討論。背後是居民運動的處境。如宇井淳在70年代開始搞了15年的自主講座「公害原論」,面向民眾分析很多關於國內國外的公害的事件、也和一些當時反公害或者反對興建工廠的運動有連繫。
1972年開始到2005年,有本雜誌叫《技術與人間》,裏面有很多現在叫「市民科學」的,那時候的社區、包括理科的中學老師,研究他們地區的一些公害,那時候公害還是很多,可能會寄稿給這本雜誌。雖然它可能不是一種對立聲音交流的平台,但是由70年代開始延續的挑戰專門性(expertise)和草根之界限的、技術的社會史上十分重要的嘗試。
而京都大學原子爐實驗所(現・京都大學複合原子力科學研究所)也在1980年開始舉辦「原子力安全問題ゼミ」,到2016年迎來了第112場。他們是公開的研討會,討論核安全的問題,有些很技術性的,譬如核電裡面的結構是怎樣,或是反對興建核電廠官司的法學根據。他們也請過烏克蘭的專家講解切爾諾貝利事故。有以上一些連結「技術」、「運動」、「市民」和「學習」的實踐。
譚萬基:我接觸過的一些一般市民,他們說到核電的時候,感覺和政遠那位東電朋友有些不同,他們大部分人的心態都是「我們無可奈何要用核電」。從事核電行業的人,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用這種心態去對核電,但像剛剛那種話,好像是已經忘記了311的教訓。
311告訴我們的就是,311絕對不是天災,福島核事故是一個人災,是一個人類造成的災難,並由地震和海嘯引發。從一開始選點的時候,就已經有設計失誤,到2000年第一次除役討論裏面的一些檢討報告,裏面的政策失誤⋯⋯各種的失誤加起來,才會有福島核災這件事。
如果我們忘記這些東西,就說核電已經安全,貿貿然重新啟動這些核電廠的話,其實我會反問他們還記不記得那些失誤的、錯的東西,吸取了什麼教訓?而且當時是幸運的:當時的4號機組是儲存了一些用過的核燃料,如果當時燃料池的水蒸乾了的話,所釋放出來的核污染是夠污染整個東日本的。分分鐘整個東日本要撤離。
如果我們忘記這些東西,就說核電已經安全,貿貿然重新啟動這些核電廠的話,其實我會反問他們還記不記得那些失誤的、錯的東西,吸取了什麼教訓?

何謂「再生」?
端:剛才大家說了很多民間的研究或者一些努力,但是其實我們看到國家和企業在應對的時候,它們會承認一些問題,但不完全承認所有的問題;它可能解釋一些問題,但不解釋所有的問題。從公害史的角度來看,這些表現是不是都在重複發生的?日本政府有沒有採取過一些應對公害的措施,令大型的公害是有可能減少的?
張政遠:在公害如何解決的問題上,其中一種我認為最危險的思維就是,從上個世紀到今天,我們或多或少仍然有一種「技術萬能主義」的心態。公害有問題?那透過某種技術除害呀。環境技術不夠先進?我們用一種更加先進的技術去解決問題呀。
我們以為一種新的技術是帶來一個解決方案,但這個新的技術也有各種環境的負荷或者污染。現在我看到另一個可能出現的問題是,以福島為例,他們知道核電廠不會再用了,就想透過風力或者太陽能發電得來的電力去生產氫氣,去造就一個稍為乾淨的環境。但是這個技術會不會也帶來 一些新的污染,包括電池的污染,或者太陽能發電站其實是令到一些生態危機出現。
其實今天我們完全是沒有解決問題,也都是大家互相推卸責任。東電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好像不單止是忘記了自己的角色,而且覺得其實自己沒有什麼責任。如果只是為你提供更便宜的電力,就好像已經是在造福人類了。
譚萬基:飯館村有一間「可再生能源企業」,就是飯館電力。在一些荒廢了、或者沒有用的農地上建太陽能電板。我想說的不是剛才政遠提到的新的污染或者其他環境負荷的問題,而是,就算我們表面上看它好像是生產了一些非核的燃料的電力,但其實都可能是在走回舊的體制裏面。
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飯館電力所生產的電力,是經東北電力輸出去,當初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太陽能板生產的電力先給當地居民使用,剩下的電才賣給東北電力。但東北電力不肯,跟他們簽這個約,就要將所有的電全部賣給他們。這就好像當年福島第一核電廠,你生產的電力要百分之一百賣給東京一樣,就好像在重複這個體制。
這就好像當年福島第一核電廠,你生產的電力要百分之一百賣給東京一樣,就好像在重複這個體制。
馮蘊妍:日本環境社會學會初代會長飯島伸子,有用「被害構造」(social structures of pollution victims)來討論這個現象,她的理論的特別之處在於,不是我們直觀上的環境問題,而會囊括各方面的傷害,如藥害、工傷、或是有關消費的傷害。比如去剪頭髮,無論是剪髮那個人的一些勞災,或者是被剪頭髮那個人受到化學液的損害,她全部都連串起來。這是日本國內環境社會學討論環境問題和公害時,以什麼為討論對象的一個理論脈絡。
如果是說政府的政策的話,1970年有一個《公害紛爭處理法》,1972年有一個《公害等調整委員會設置法》, 就是可以去做一些調停。在我自己的田野也是,70年代有農村要求古河礦業去賠償對他們農作物的損害。
但是賠償是不是等於解決呢?如水俁病患者認定運動的緒方正人,他途中放棄了認定申請。他在『チッソは私であった:水俣病の思想』寫道,如果自己在對面的立場,如果他是那個工廠的人,他是不是也不會作出同一個決定呢。於是他說了「チッソは私であった」(窒素是我)。如果以「加害」和「被害」的關係去看,他當然不是加害者,他爸爸就是因為水俁病過世的,他是一個受害者。但他認為如果在一個時代來說,他同樣是活在那個經濟發展的時代,並於其中消費。
再延伸一個點就是,解決不等於完全沒有了那個物質,剛才我們一直討論的都是這些。緒方正人也寫,賠償對人來說可能是解決事情的方法——當然只是一個說法,不可能是拿了錢就沒問題——但對於死了的魚、用了來做實驗而死去的貓,這些賠償是不通用的。給了賠償也換不了原來的大海。
在此之上,我現在也在想,要怎樣去思考「再生」,像是谷中湖,2022年的研究指出,水中的重金屬濃度是下降了,砷、鎘和鉛也沒有超標(根據「人の健康の保護に関する環境基準」),但底下的泥的砷和鋅的濃度還是有超標的(分別根據「農用地の土壌の汚染防止等に関する法律」和「農用地における土壌中の重金属等の蓄積防止に係る管理基準」下的標準)。而包括谷中湖在內的渡良瀬遊水地在2012年登錄成了《拉姆薩公約》下的濕地 。那個圖像(image)是,有一些污染了的泥土,上面就有蘆葦,蘆葦形成了一個自然生態,裏面有一些瀕危動植物,然後它又登陸了國際濕地公約。在污染仍然繼續的前提下,什麼為之解決,什麼為之再生呢。
在污染仍然繼續的前提下,什麼為之解決,什麼為之再生呢。
譚萬基:我想對我來說,命題現在就是,我們現在是不可以再問一個所謂 live without 的問題,而一定是問 live with 的問題。Live with 那些污染物,就算不說曾經被污染的地方,說現在的有機堆肥(organic culture composting)。你試一下去驗最有機的肥,你一定會驗到塑膠微粒( microplastic)在裏面是嗎?
在我的研究裏,其實你可能一開始都聽到,我問的問題都是和技術有關,技術怎樣幫農民回到一個曾經被污染的地方。但其實做著做著我都有反省。以田尾和飯館村的村民為例,其實他很強調一樣東西:縱使我們怎樣應用技術去除染也好,如果我們同一時間不去想除了人和人之外,人和其他生物的共生的話,其實所謂「再生」也是一個假象來的,只會回到技術至上主義帶來的、國家最想有的進步和經濟發展。
我開始轉向思考,究竟技術是什麼呢?在這個充滿環境危機的時代裏面,技術怎樣促進我們和其他非人的物和事去共生呢?這是我覺得另外一個大家可能要想一下的課題。

張政遠:好贊成。這真的是哲學問題,何謂技術和共生?
不過我也想說一點。在水俁和谷中湖,我見到最令人擔心的一個畫面,不只是湖或者只是海,而是它怎樣美化這個災區。兩個地方我都找到他們現在稱為「戀人之聖地」的地方。因為谷中湖是心形的,而水俁灣的海邊也是戀人聖地。在一個這樣的論述之中,我們要記得原來戀人聖地裏有一個被遺忘的災害史。
另一方面我也相當同意不要對災區刻板化。其實當地人都很不喜歡,他們很要求我們不要先入為主地把這些地方看作純粹的、單一的災區。在水俁我碰到一個潛水的先生,他帶我看水俁的大海,說海水很漂亮,我說不是吧,我真的不相信。但如果你潛入海,原來是會見到一些海馬、珊瑚。
我原來以為是死海,但原來有生命力,有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生態。因此進入這些災區或者這些地方的時候,也跟著當地人看一看,他們呈現的另一種景象,是重要的。
張政遠:從當地居民的角度,我想他們當然不想你揭傷疤,但是從外面的想法就是,事情發生了,一定要將他們的記憶有所傳承。 所以博物館變得重要,在這(博物館)裏講完,其餘的地方就正常生活。
馮蘊妍:在我的田野裏,這種掙扎不只是發生在當地居民和政府之間,而是參與在記憶傳承的人之中都會有這些張力。例如足尾和下游之間,有一個草木水壩,是用來沉澱礦毒的,即使在官方資料中也會見到此用途的說明。有到底要叫這個水壩為「多目的水壩」、只是其中一個目的是沉澱礦毒,還是說有直接叫它「礦毒溜」?對在下游生活的人和農民來說,叫它「礦毒溜」,就是說我們生活在礦毒的水上面,用礦毒的水灌溉啦?但是在記憶礦毒仍在進行中的立場上,就該這麼直接。
谷中湖也是,一方面有保存谷中村遺跡的運動,另一方面有關注保存濕地的運動。在我的田野裏,就像一邊有一個災害論述,另一邊有一個自然再生論述,我未必是想批判它好還是不好,就是在思考有關兩者的交集與不交集,以及100年之後的境況。
端:今天的討論有講災害的層次:如果東京是一個中心、福島已經是一個邊緣;如果福島是一個中心,飯館村可能是一個邊緣。所以「福島」兩個字裏面的層次很豐富。我們也有破除兩種印象,一種是廢墟死城式的想像,一種是「除染了就光明乾淨沒問題」的印象。大家也說到危機是一個 ongoing 的過程,要一直和這些危機共處。
那麼什麼是「治癒」、什麼是「復原」,會不會有一兩句總結的話?
譚萬基:我想對我來說, 家園是很重要的。推動大家回去也好、推動離開也好,怎樣維持一個「家」是極之關鍵的。為什麼一個六十多歲的伯伯,他要這麼著力回去,把家弄得乾乾淨淨的?就是為了他九十歲的爸爸能夠在死之前回到家,舒舒服服地住一陣子,吃到他們那塊田種的米,這個就是他們的動力。
相反也有些人的動力是,我一定不可以再留在這裏,因為我要為了子女出去,重新建立家。
而日本政府,或者很多科學家和專家是很忽略這件事,覺得「家」是你說去哪裏就去哪裏。
張政遠:有一位災民的說法讓我很有印象,就是「心的復興」,こころ(kokolo)的復興。當年聽到之後我都很慚愧,我們以往想的復興純粹是一個物理上的復興,想要一間樓我們建給你,想要一條路我們搭一條橋,這個層次。但是失去了三代同堂、祖田荒廢了的失落感、整個社會已經沒有了支持、家人離世⋯⋯這麼大的心靈創傷不是能輕易解決的。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說,我們需要遺忘,面對這麼大的傷痕,怎樣讓這個創傷可以告一段落呢?
我真的感到有一線希望的地方,就是飯館村。不僅有一班老人家去緬懷,也真的有些年青人搬進去,其實會有很多衝突都不一定,但起碼有一些新的景象,不是只是「送死」的想像。

我們以往想的復興純粹是一個物理上的復興,想要一間樓我們建給你,想要一條路我們搭一條橋,這個層次。但是失去了三代同堂、祖田荒廢了的失落感、整個社會已經沒有了支持、家人離世⋯⋯這麼大的心靈創傷不是能輕易解決的。
馮蘊妍:我想用兩個意象去總結。石頭和森林。石頭是一個關於死者和過去的連繫,如福島縣大熊町大熊未来塾的木村紀夫先生,他搜尋他二女遺骨,並在他家的後山放了一個地藏。新潟縣的阿賀野市的水域,也有雕地藏。他們和熊本交換了用彼此地區的石頭所刻的地藏。足尾礦毒事件反對運動的基地、群馬縣館林市的雲龍寺也放了阿賀的地藏。足尾已經廢村的松木村,和渡良瀬川下游的谷中村的墓石,到現在都還在,大家也會去掃墓。熊本水俁的「本願之會」,也在埋了水銀污泥的地方放置親手刻的「魂石」。
我覺得好像有一個共通的石頭意象放在那個地景裏,打理它或製造它,未必是一種解決的方法,但可以是一種療癒,以及和過去及死者產生關係的方法。
另一個是森林。森林同樣連繫了足尾、水俁和福島,在足尾的礦山因為硫酸氣體而山枯,有些組織就在那裏建森林。其中一個組織「森林人計畫」(森びとプロジェクト、Forest People Project)除了在足尾,還在南相馬種植「森林的防潮」。因為防潮堤的倒下是一瞬間的,但有森林的話反而可以緩衝。他們叫這個作「生命的森林」。指導「森林人計畫」的植物生態學家宮脇昭也和《苦海淨土》的作者石牟礼道子有過對談,討論將熊本水俁埋下了水銀污土的土地,再生成一片森林。
無論是石頭也好,森林也好,同是超越了人類個體的時間。石頭可以放很長時間,森林是就算你再加快復林,可能也要十幾年才能製作一小片森林。所以就好像把治癒、面對災害,或是在公害之中生活的這件事,不用「解決」這個字,而是以超越了自己本身的時間的角度去存在於其中。
譚萬基:我覺得最簡單的治癒方法就是,去那裏見到福島的人,和他們一起吃福島的東西、喝福島的酒,對他們來說就是最大的治癒。
那個回去種花的人,一開始是種最好賣的桔梗,但發現原來他不懂得要修剪掉旁邊的花束,才能讓頂上的那朵花開得又美又大。解救他的是2017年回去種花的原村民,教會他怎樣種才美才能賺到錢。我們講記憶傳承,其實這也是記憶、技術的傳承,而我們看不到,博物館也不會說,但它就是這樣傳承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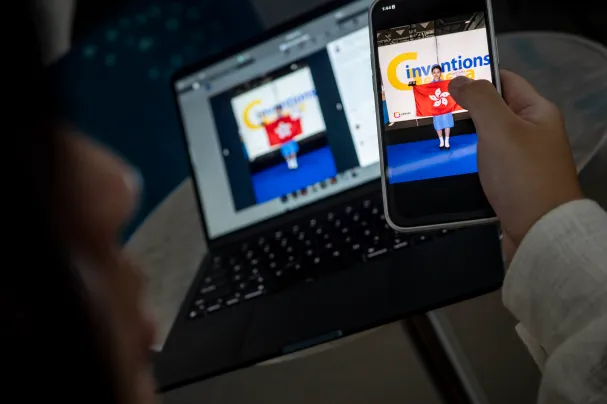

非常好的对谈!尤其是当地居民的角度,日本媒体上都好少见有这么详细的探讨,读完觉得收获很多,阅读的过程也很愉快,谢谢分享。
我認為311是天災,無人預計得到地震+海嘯。
這篇上下的對談,很有質素和涵養,這才是讓人值得課金給端~!
文中圖片描述所提到的Soma Nomaoi似乎應該譯成「相馬野馬追」更加妥當。
這兩篇對談真是太精彩了
特别好的一篇文章,感谢
上下兩篇對談,有好幾個段落,假若無人指出來、深究,往往不能發覺問題所在,但其實認真想想又是理所當然:
//我怎麼會懂(怎樣除染)呢,我只會開剷泥車而已。我來到,我就挖咯。你教我啦,怎麼挖5cm表土?大型的重型機器喔,怎麼挖?所以他們大部分就覺得,挖多好過挖少,挖多一點不虧。但是對農民來說,你就害死他,因為你將表層最肥沃的泥土弄走了。挖了這些東西之後,日本政府就用山沙填了這塊除染之後的農地,而這件事就令到很多農民不再想復耕。//
受教了,我有種香港地區行政的既視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