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還沒有忘記讀到《SLAM DUNK》「第1部完」的激動⋯⋯容我更直接地表達,當時剛升上高中,這部漫畫這樣中止,讓我第一次從閱讀經驗中認識到「憤怒」是什麼。而今日,許多讀者好像都為《THE FIRST SLAM DUNK》吹奏「要看」、「必看」、「流淚」、「切勿劇透」、「只有井上才可超越井上」之類的「影評」,讓我訝異的其實是一群人還未消化「《SLAM DUNK》終於有動畫改編得最圓滿的版本」這回事。這股積累二十多年的鬱悶,在社交媒體幾乎一律以正向情緒來回應。
誠然,電影的確照顧一大群不認識《SLAM DUNK》的陌生觀眾,為大家帶來類型漫畫史無前例的精緻再現:場景比例與人物動態完美無瑕,既滿足了新觀眾,也餵飽了許多飢餓二十多年的老讀者。井上雄彥《THE FIRST SLAM DUNK re:SOURCE》「五千字」專訪最近也瘋傳,他花了大篇幅來講解漫畫到電影的改編過程,一般讀者看來,這確是一次真情剖白;但在漫畫老粉如筆者看來,細述電影改編之由來,卻似是仍然無法挽救這部「未完成」的作品,反令人更感到作者是在粉飾作品的不完整。
在許多人眼中,一項容許球員把皮球灌進籃框的運動,或許僅是一項十人追逐皮球的遊戲,人們未必知道這場遊戲的影響力在哪,更可能為近月在香港掀起的如此熱潮摸不著頭腦:香港尖東某商廈外牆大型電子屏幕上,電影廣告閃現的五個漫畫人物到底是投射出怎樣的文化簡史與底蘊,而廣告那一度在維港海面反映的動漫倒影,到底在說著怎樣的故事?正如近月在香港島,每當貼有五個球員畫像的紅色電車叮叮駛過,總有人駐足打卡,但也有人不以為然;各大媒體刊登的電影廣告、大小影迷觀映電影前後的打卡中,也同樣未能有人立即解釋出,由電影《THE FIRST SLAM DUNK》在香港近期帶出的熱潮現象之由來。
在我看來,《THE FIRST SLAM DUNK》這部電影理應可重新帶起關於1990年代香港次文化現象的討論,但正如香港次文化圈消費者一直習慣的狀況那樣:大家工作真的太忙碌,抑或真的不擅長討論自己身處怎麼樣的文化現象裡,難免停留在「消費」層次。《THE FIRST SLAM DUNK》作為文化現象,於香港一代人有多重要,其實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因此本文在討論電影好壞之前,不得不從香港的1990年代說起,那個Discman(隨身聽)盛行、和記推出天地綫(黎明代言的限定區域收發信號的廉價手機品牌)、好景樓上之「四仔冇格仔」(以售賣盜版與色情光碟知名的旺角好景商業中心;四仔冇格仔指無馬賽克的色情光碟)、版權意識尚停在蠻荒⋯⋯的年代。
我們可以理解成1990年代文化於今日香港的勝利回歸;讀者嚮往美好香港消逝的年華,一群又一群不管是出於呼應潮流、還是死忠熱愛的粉絲,均以消費行為回應這部作品的到來,每人都認同「青春就是不完美的」這種井上式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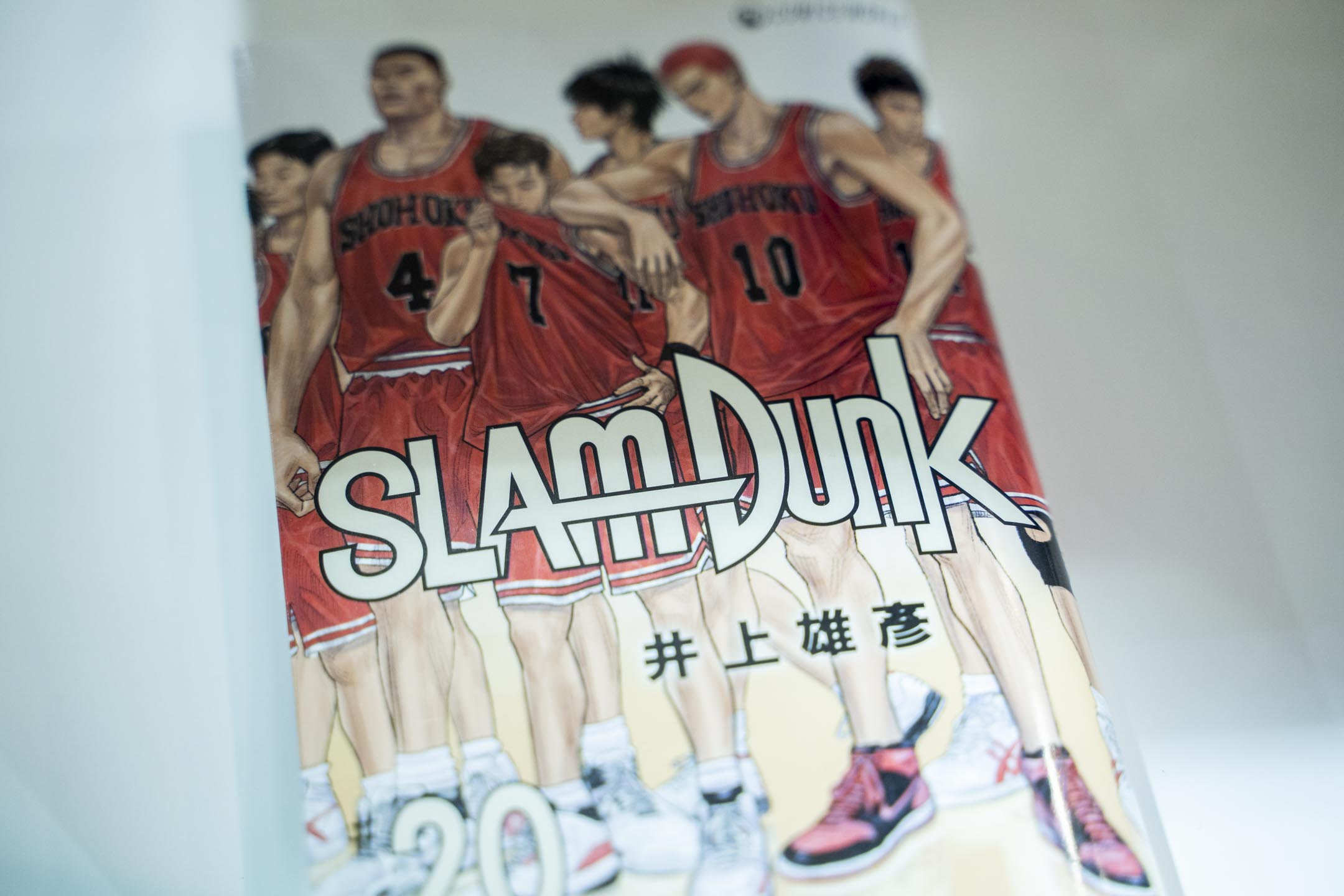
1990年代香港次文化:於今勝利回歸?
1990年代香港少年,最嚮往的是搞笑文化。大家看著周星馳由兒童節目主持人,轉型到電視劇佻皮演員,再進軍電影世界,成為無厘頭搞笑大師;人人的話題,都是「飲啖茶食個包」(《蓋世豪俠》中周星馳名句)。而瞄準其時佔香港人口20%的青少年市場的,有才子倪震與邵國華(資深電台節目主持人)創辦的青少年雜誌《YES!》創刊;有以搞笑方式二創各路明星名曲,如華少將鄭秀文《如何掉眼淚》惡搞改為《姨婆掉眼淚》;有影響至近年紅遍香港的Youtube頻道「試當真」也都照跟名目來試玩的校花校草選舉;又有「YES!!卡」這種攻佔香港文化達三十年之久的派生產物。
加之譚詠麟張國榮之「最受歡迎男歌手」樂壇長年爭端餘波;四大天王主宰樂壇橫掃整個亞洲;再有日本從任天堂紅白機升級至超級任天堂、甚至發展出Game Boy手攜式電玩入侵中小學;日劇與日本明星入侵青少年生活圈⋯⋯等等這些,其中的漫畫、明星照片與明星卡,均集中於旺角信和中心販售,令信和中心成為日港次文化交流的重要地標。而彼時尚有大量無視版權條例的再生產行為及成品,集結整個旺角,蔓延至好景商場販售的色情光碟——在街巷派發宣傳卡片時,附帶機械式的一句招牌叫賣:「四仔冇格仔」(色情片不打馬賽克)⋯⋯
香港的1990年代常被評為以次文化麻醉人心、紙醉金迷的時代。在回歸前各種身份認同論述中,都帶有彼時日本流行文化、香港次文化的印證。而近年政治動盪後,香港又竟發展出互動式流行消費文化,無意間造就了類近1990年代消費文化於香港的重臨。
其時許多香港文化學者(如周華山等)的著述中,1990年代都被評為以次文化麻醉人心、紙醉金迷的時代。在香港回歸前的各種身份認同論述中,都帶有彼時日本流行文化、香港次文化的印證。加之近年香港於政治動盪後,又竟發展出互動式的流行消費文化,受眾越來越需要甚至主動營造這種情緒依賴,而這些都無意間造就了類近1990年代消費文化於香港的重臨。
《THE FIRST SLAM DUNK》上畫前後,在時代廣場開設紀念品POP UP專賣店,場次即日刷爆,電影票房又以千萬計,我們可以理解成1990年代文化於今日香港的勝利回歸;讀者嚮往美好香港消逝的年華,一群又一群不管是出於呼應潮流、還是死忠熱愛的粉絲,均以消費行為回應這部作品的到來,每人都認同「青春就是不完美的」這種井上式思考。

未完成:26年了
今日無人可繞過的《SLAM DUNK》熱潮,源自《週刊少年JUMP》連載《SLAM DUNK》的1990年代(1990-1996),那是NBA(美職籃)人才輩出的火紅時代。在整個1990年代的籃球熱潮裡,《SLAM DUNK》佔據了香港與台灣青春少年的成長與成熟期,包括由它連載的1990年、終止連載的1996年,以至於後續不斷討論故事終結或否的兩個十年。
這26年來,這套漫畫總是不斷有「續集」傳聞流出,一陣陣微小的風聲,都在紙媒與網媒間激起讀者大大小小的情緒反應。而《SLAM DUNK》作者井上雄彥作品的機靈感與精緻感,是在連載《SLAM DUNK》之中期才漸漸成形的。
事實上,1990年代初香港最火紅的漫畫,一定不是《SLAM DUNK》,而是鳥山明《龍珠》、車田正美《聖鬥士星矢》、高橋陽一《足球小將》等等,若非香港譯者趁林子祥主唱、黃霑作詞的《男兒當自強》(黃飛鴻電影主題曲)熱潮,把《SLAM DUNK》譯成《男兒當入樽》,在當時的香港要一部籃球漫畫可與上述漫畫內容與銷量比下去的話,應該難以達成?
井上雄彥在《週刊少年JUMP》連載最後一期的最後一幕,寫上「第1部完」,令許多讀者都認為它會有第2部。這個以文字表達的「未完」並非草率,後來的20多年證實井上雄彥每部新作都是「未完」,無結局可言,收不了場。
若非香港譯者趁林子祥主唱、黃霑作詞的《男兒當自強》熱潮,把《SLAM DUNK》譯成《男兒當入樽》,在當時的香港要一部籃球漫畫可與上述漫畫內容與銷量比下去的話,應該難以達成?
根據井上雄彥的說法,《SLAM DUNK》有它本來設定的結局;但字面上看,它就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須知當年「第1部完」這幾個字,構成了許多青少年的期待感,人人都在準備著第2部的來臨,包括我自己,每周自北區乘火車到旺角,沿亞皆老街左拐彌敦道越過山東街後直奔信和中心,登上一家影印小店,仰看店東把《週刊少年JUMP》等期刊「分拆上市」,複印每部連載漫畫當期內容,每期每部情節盛惠港幣五圓。而我們就乖乖掏出硬幣帶著大約二十個版面回家,在火車車程一讀再讀。

痴心錯付:狗血腥味的愛回家故事?
今天許多老讀者說這電影準備二三四刷,於我來說,當年比念書更勤力的反覆閱讀,間接構成了今日我這個老粉評價它時有多公允——如今不少粉絲說要看完電影回家重溫漫畫,而我早於青少年時期每天重溫這些香港版《週刊少年JUMP》(港版名叫《EX-am》、《天下少年》)尚未翻譯的內容,甚至會為它們購置日語辭典試著對譯,香港出版後,我又會用炒賣明星卡賺來的錢買香港版與合訂本。
這整個過程包含了我對漫畫的情感寄託,於今,《SLAM DUNK》老粉絲鍾情了20多年的作品,終能在銀幕重遇,這股情緒的累積終要爆發。昔日青少年都成了半個老頭子,有了點錢就任性贖回自己的青春,在這無邊際的許願池裡,紛紛向電影「蘇粉」(souvenir諧音縮寫)投幣許願。信和文化忽然復興,人人把戲院當成自己的青春聖殿,向銀幕高舉雙手深深膜拜。只是如今看過電影,我才發現那寄託情感的歲月所醞釀的,竟成為日積月累的癡心錯付,這是老讀者看電影再多四五六刷都難以彌補的傷痕。這電影的確是毀掉了我過去那段日子的反覆期待。
昔日青少年都成了半個老頭子,有了點錢就任性贖回自己的青春,在這無邊際的許願池裡,紛紛向電影「蘇粉」投幣許願。信和文化忽然復興,人人把戲院當成自己的青春聖殿,向銀幕高舉雙手深深膜拜。
於我而言,電影3DCG技術的最大貢獻僅此一項:漫畫人物終於有了擬近人類體態的動感和效果。但請不要忘記,在這26年裡,我們觀賞的不再是宮崎駿,而共同經歷了新海誠作品的洗禮,觀眾於日本動畫作品群中受浸後,篤信動畫說故事形式的無拘束與多變可帶來思想上的滿足。回頭再看《THE FIRST SLAM DUNK re:SOURCE》電影增刪加減後,竟是帶點狗血腥味的「愛回家」故事,即是在免費電視台黃金檔期會有佈滿生離死別情節的劇目,動靜編排自有它頗準確的節奏與規律,可是上映至今連同優先場在內已近一個月,其間似乎未有人認真來問:
電影為什麼要刪去櫻木花道與河田美紀男競技的情節?筆者看來這無疑是整個上半場最精妙的佈局,它是一個運動員初哥櫻木花道的重要成長簡錄,漫畫強調訓練有多重要的一個明證,是作者用兩個同樣有身高、有天份的球員互相比較,也是運動員經常面對的對決情境。偏偏電影改編時,追加宮城一家坐著哭、站著哭、抱膝哭,甚至要躲到海邊岩洞哭的情節,難道這真的比櫻木奮起搭著赤木晴子肩膀說自己真地喜歡籃球運動,更感動人嗎?
在這26年裡,我們觀賞的不再是宮崎駿,而共同經歷了新海誠作品的洗禮,觀眾於日本動畫作品群中受浸後,篤信動畫說故事形式的無拘束與多變可帶來思想上的滿足。

最值得保留的情節:電影刪掉了
對比漫畫,電影共刪去12處情節,包括流川楓求教陵南靈魂人物仙道彰,仙道說曾遇過比自己更強的球員叫北沢(仙道記錯了沢北的名字);也包括安西監督在比賽前一天的各種行動與提示,甚至在賽前不惜走進場館廁所,扮偶遇激勵問題少年。
回顧電影上映前近兩三個月裡網民的疑惑和討論,常有人對宮城良田擔當主角頗有微言,筆者熟讀《SLAM DUNK》,因此認為這是嶄新卻不意外的決定:宮城良田雖然欠缺中投與遠投的能力,在山王一戰之前的一場賽事中,也描述了他因身高而缺乏自信,但他的運球能力和快攻反擊能力都是球隊(流川楓覺醒前)最好的。在進軍全國大賽前的關鍵一戰中,他曾在仙道彰嚴密的防守中成功上籃得分。
電影主角宮城良田的成長證明,是安西監督在比賽其中一個關鍵時刻正式委任宮城為突擊隊長,而電影刪去了這一段,儘管這是安西監督在比賽期間對宮城良田的靈敏與速度的首次認證,之後才有彩子在宮城掌上寫上鼓勵他的文字。
這樣的刪節,把原著最有爆發力量的熱血按捺住,消隱了安西監督最重要的功能——問題少年需要像他一樣的大人,導正少年的精力用得其所,這恰是整套漫畫作品最令讀者感到安慰的情節。電影刪去了原著最值得保留的情節,也刪去漫畫最重要的信息。
這樣的刪節,把原著最有爆發力量的熱血按捺住,消隱了安西監督最重要的功能——問題少年需要像他一樣的大人,導正少年的精力用得其所,這恰是整套漫畫作品最令讀者感到安慰的情節,告訴世人本來沒有希望的大人世界裡,總會有這樣的一個大人存在著,要是遇上了,就可拯救一眾莽撞少年,知道自己的專長後,甚至可代表全國出外比賽。可惜的是,電影刪去了原著最值得保留的情節,也刪去漫畫最重要的信息。
若井上雄彥沒有創作過《REAL》和《浪客行》(台譯《浪人劍客》)而得出今日的電影版本,老粉或許會原諒他的。今日用煽情劇集的方式演繹《SLAM DUNK》故事,到底是想說我們逃不過1990年代次文化的低質成份,還是想說他抬不起自己當年的運動漫畫精髓?櫻木花道父親病倒或是死亡的那個情節,難道不是問題少年的遺憾嗎?為宮城良田在服飾上繪畫的伏筆,比沢北榮治父親自小培育孩子成為籃球員的情節有更重要嗎?
今日用煽情劇集的方式演繹《SLAM DUNK》故事,到底是想說我們逃不過1990年代次文化的低質成份,還是想說他抬不起自己當年的運動漫畫精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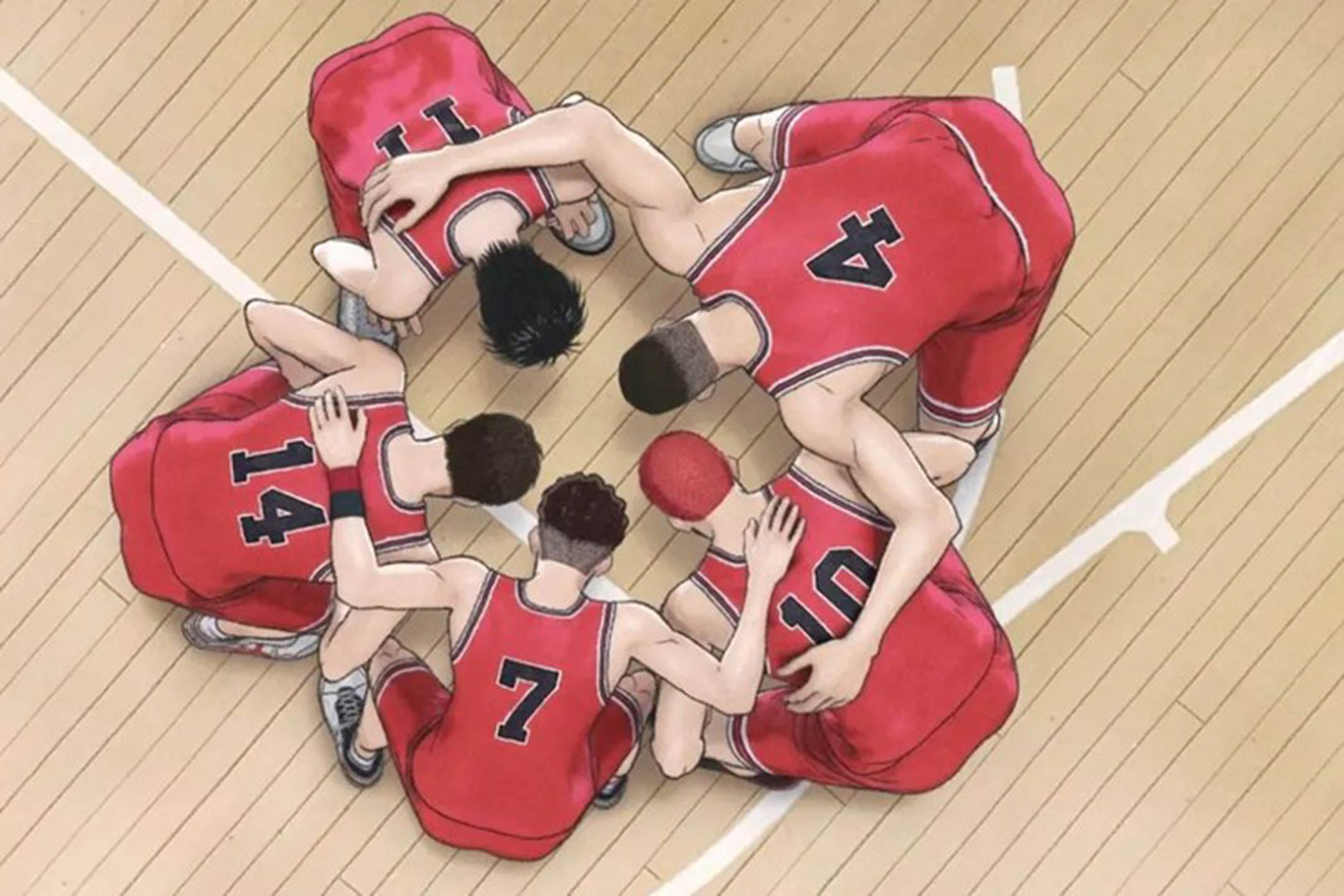
可以只是消費「熱血」嗎?
這些年來,井上雄彥創作了另一些作品來「回應」《SLAM DUNK》續篇的訴求,似乎完全沒有理會讀者,志在新作,結果又創作成另一批未完的作品。而單看漫畫《SLAM DUNK》「已完成」的部份,忠實讀者會讀到幾個可發展的情節,包括以Shaquille O'Neal為原型人物的森重寬路過時與故意想挑事端的男主櫻木花道的擦肩事件,到底會不會成為日後賽事對決的伏筆?當讀者於今日帶著這些期待走進戲院觀賞電影,走出戲院時,卻相信這又是一個「未完」的結局。
井上雄彥在專訪中以「五千字」,「花言巧語」討好新讀者,讓人覺得他有多認真來再創作這部老作品,而自己又有多深刻地來思考漫畫與動畫的距離,並試著用創作的「直覺」來解釋一切;然而,他卻解釋不了為何電影的「未完」感覺,比起漫畫的未完成,來得更突然。電影刪去了許多比賽的重要情節,而這些情節其實是呼應現實世界至今仍存在著的話題:
問題少年一旦依循大人制定的遊戲規則(考試及格才可參賽),他們在得到什麼的同時,又會失去什麼?初哥籃球員受了傷還堅持上陣,到底是怎樣的一種覺悟?運動員練習的過程與成果,怎樣影響一場賽事?這些明明值得「再創作」的內容、值得仔細討論的題目,竟被一片叫好與唱好的聲音淹沒,而眼前這個香港,明明是26年後的香港,於今一下子,好像又回到只會歡呼、不會思考的時代。
這是個滿佈回憶陷阱的年代,讀者一旦掉進消費行為裡,那種被粉飾的商業操作,會讓人以為自己擁有了自己的專屬回憶,亦即如1990年代文化工作者經常批評的那個香港和過度消費的現象。

一部《SLAM DUNK》包含了1990年代NBA輻射全球的籃球熱,合訂本為每一回結束時繪畫的人物Q版與幽默細節,反映了那個年代以搞笑為王道的潮流現象,也當然值得思考。而老粉要問的是,「第1部完」山王之戰的終結,當年作者與出版社的爭端,難道到了今天還未是作者可親身交代的時間?井上雄彥在眾多訪問裡,都顧左右而言他,到今日「五千字」專訪似乎還待交代,且不管電影改成怎麼樣的一部作品,試問老粉的憤怒又幾時才可消化掉?
動畫明明有所突破,達成當年難以達成的效果,還有什麼話要說、值得說?香港紙媒工作者看來也無人嘗試認真討論,只管消費它的「熱血」;而網絡上又一直讀到稍有質疑就被攻擊的反應。回撥香港1990以至1980年代身份認同的討論,香港每首歌曲歌詞、每部電影作品的人設與對白都被納入討論範圍的激情年代,在偌大的次文化洪流中,又有各路文化工作者把一部部來自日本的動漫作品認真檢視,向讀者分析怎樣建構日漫在香港的黃金時代。
這是個滿佈回憶陷阱的年代,讀者一旦掉進消費行為裡,那種被粉飾的商業操作,會讓人以為自己擁有了自己的專屬回憶,亦即如1990年代文化工作者經常批評的那個香港和過度消費的現象。再看今日香港重新接觸日本動漫的各種迴響,如果這就代表了香港大部份動漫迷的思考,作品有個圓滿句號就滿足,那麼昔日一眾創作人與評論人共建的1990年代,就由它埋在一片歡呼聲裡便好了。誠心希望讀到一篇認真討論作品的文章。




將當年SLAM DUNK漫畫之成功歸因於港版譯名男兒當入樽,實在是低質得不能再低,難道於譯名為灌籃高手的台灣SLAM DUNK就沒火紅?
對未完成很執著的話請看看Eye shield 21,山王戰勉強繼續下去,水平就大概就是神龍寺戰後一樣。
有人提到現代籃球,28年前構想的籃球賽就有現在最流行最高效的利用單擋無球走動catch and shoot,而河田身為中鋒射三分更加是最近幾年NBA才流行的事了。
情緒文無誤。
我認為Slam Dunk 電影版 與現代籃球脫節,缺少戰術佈致,白白浪費了3D 化的意義。
山王戰大量穿插宮城線的劇情,很影響整體流暢度,顧此失彼。
這種阿Q式的情緒勒索文章也能當成評論發?評論者對於作者在一部電影的時間限制內想表達的內容而做的取捨完全感受不到,只是一味地想要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到底是什麼巨嬰心態?
作者对于“未完成”的执念不过是对少年jump编辑的错付。井上自己受北条司无心之语的启发,早就下定决心在山王战后完结。《十日后》近乎行为艺术的表达,更是表明故事虽已结束,但角色的人生还在继续。如今的电影对老粉来说,更像是对TV版全国大赛“未完成”的圆梦。
我对于作者近乎发牢骚的长文本身没有太多意见,但是这种近乎发牢骚式的长文竟然也能登上“深度”专栏?对端感到失望。
估計作者是香港人(利申:我也是)我同意作者大部分的observation,例如:男兒當入樽不是中學最紅動漫,現階段的香港人喜歡消費回億和將消費作另類情感投影。
但這評論logic很混亂,將【未完成】扣在過度消費回億這話題上。其實井上雄彥停止畫入樽是跟出版社不咬弦,加上停在山王是他個人意願。
經典就是懂得完成。完全與否跟消費不消費回億是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難道像龍珠和足球小將一樣?悟空頭髮變到七彩都要繼續畫落去?
看不懂作者是想評論漫畫還是電影還是老粉。
有點不明白。作者應該是香港人,我記得當年的漫畫名稱是《男兒當入樽》,為什麼文章標題用《灌籃高手》呢?
看到《灌籃高手》電影版第一篇負評,沒想到如此淺薄!
作者寫的落落長,其實就只是糾結在「未完成」。雖然結局戛然而止令人遺憾,但正如前面 ena 網友講的,繼續畫下去就陷入另一個少年漫畫的窠臼,主角們只會越打越威能到超乎現實的境界。停留在最熱血的一刻也沒什麼不好。何況後來井上雄彥開始〈浪人劍客〉〈REAL〉,顯然對於〈灌籃高手〉也沒有更多更好的故事繼續說,何不尊重?
想對作者說:Grow up! Move on! 套句宮城良田對三井壽說的「一直沈溺在過去的,是你自己」。不是每個老粉都像你一樣要求井上雄彥畫出結局給他,也不是每個好評都只是消費熱血,更不是沒達到自己的期望就等於認真討論作品。真正討論井上雄彥如何用心的手法新的角度說老粉已經熟悉的故事,仍然重現當年熱血的文章多的是
電影中, 沢北榮治向神明祈願賜予他一樣在過往比賽還沒有得到過的, 結果落得求仁得仁
現實裏, 今天回頭再看二十七年前那一天的那一句 "...就是現在了!!", 更加感到是一語成讖
@ena 我也蠻喜歡《灌籃》漫畫的結局的。
在我看來就這樣帶點遺憾的青春定格更符合現實。
@CHOCOPAL
我想如果作者不地圖砲其他人都是跟風的無腦消費行為而只有他看到種種不足渴望會有深度討論的話,反應不會那樣。
然後無可否認,男兒當入樽再畫下去,就會變成普通的熱血王道運動漫畫,主角色群一直努力贏下去知道NBA還是奧運?(可以參考足球小將或我要高飛)那樣相信不會那麼多讀者念念不忘了。
我反而滿喜歡漫畫的結尾定格在青春的一頁,那種不圓滿成就了作品的圓滿。如果說那是因為井上和編輯有分歧而突然結束,那麼也是個很好的巧合。
所以作者入場是為了看什麼?看井上怎麼弄出一個圓滿的結尾來滿足他看漫畫的遺憾嗎?
電影的時長有限,要架構一個相對完整的故事,勢必要作出取捨,如果視角是決定要從宮城出發,作者所說的關於櫻木和流川的劇情塞了進去就會妨礙敘事的流暢性,這樣反而兩頭不討好。
這種粉絲情緒取向(作者還大量夾雜了很多電影無關的私人經歷)的評論居然會在端看到,雖然取了個高大上的標題結果說的還只是表面,對端的審稿失望了。
批评的基本都同意,评论区干嘛戾气这么重……
删掉的片段除了鱼住去会场削萝卜之外,都挺可惜的,尤其是樱木对晴子说真的喜欢打篮球。新的声优听着也很违和。为漫画的山王战流了无数次眼泪,在影院里最后也没哭出来。
或者应该说无论怎么改编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最完美的slam dunk永远在漫画里。
這篇文章不知所云,完全感覺唔到佢所謂嘅憤怒同電影有嘅問題,又唔知佢想電影要d咩,如果問題只係單純唔鍾意電影删減改篇咗,寫成大段嘢出嚟,純屬垃圾
啊就真的好看咩!我這個青春期從來不碰籃球的香gay,想起那些國中時期滿身臭汗自以為是流川仙道藤真的臭直男,我一點共感都沒有,但是這次在電影院也是看得淚流滿面。你覺得不好看,就覺得別人的稱讚淺薄,拉哩拉雜掉了一堆書袋,真是一篇彆扭又掃興的文章。
我很少這樣粗鄙地評論,不過這回我要任性一次。收皮啦,這都甚麼爛文章,寫乜春啊?
寫了大半篇,東拉西扯,不知所云。所有立論都無基礎,所有感想簡言之都只能指出“我不喜歡”而無法說明具體原因或引用其他主流意見去進行比較。
去到結論部份更慘不忍睹,為甚麼SLAM DUNK一定要寫晴子櫻木,為甚麼不能寫宮城?還有如果你10多歲你爸死了你哥死了,你哭不哭啊作者,你全家死了,你不哭?啊你可能不哭,因為你不正常。
不是其他人盲目推崇,也不是你言之無物就可以自詡獨樹一格。寫評論之前,先去唸唸書,看看人家文學批評是怎麼做的,賞析是用哪些角度做的,而不是寫些垃圾出來自鳴得意、獻世。
利申文學系畢業。
當我讀到你質問為何沒替part 1收場、為何沒著墨於櫻木v小河田、為何不呈現那些你眼中更為感動的瞬間,我只覺得你這篇文章並沒有打算以入樽/井上為文本進行討論,而是應該在個人社交平台發的牢騷文。有這樣的平台,格局不用那麼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