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麗珠以日記體書寫的《黑日》出版的時候,正是反送中運動理大一役之後。緊接而來的一場瘟疫,令原本沸沸揚揚的抗爭塵土初落。自疫期隔離營選址之爭發生,街頭抗爭就幾乎只剩下每月「831」、「721」、或與抗爭有關的逝者悼念儀式等,人們還堅持回到清冷街頭,追討未明的真相。如此疫期中讀《黑日》,見字回溯大半年來香港怎樣在一步一驚心的日子中一路走來,也是在應接不暇的戰役後,從積疊糾纏的情緒中檢視每道傷口。
疫情稍減未滅,國安法與川普決策再來,香港氣氛普遍低迷,「在這樣的時刻,整個香港的人都要去思考如何去重整自己的生活。然而,要是香港消失,其他生活都不會有,所以自然要穩住你的家,才可開始做別的事情。」比起雨傘後失敗論的衰嚎一片,香港人過去大半年的表現多處沉著勇毅, 韓麗珠也認為,包括雨傘運動後所謂希望幻滅與無助的那六年,其實都在積聚能量。「我很清楚我的行動,就是寫作」,她說。她感到自己早已比從前更加勇敢,更認真面對生命。「從前我很怕去拒絕自己不想做的事,也有不誠實的時候,有時是不再想要一些什麼,或是不想繼續一段關係,會等對方提出,我還是有些懦弱和被動的時候,但經歷這一切,我發覺不想再去浪費生命了,不能再把力量放在不妥的地方,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何時是最後一天。」6月9日以前,她開始堅定地拒絕了一些生命中不喜歡的事情。「因為我想留下一些能量去做我想做的事,自那時起,我開始去遊行,也整個人專注在這件事上,然後再寫作。所以抗爭帶給我的,在6月9日以前已經開始了,進化了許多。」
作品自去年四月始寫,韓麗珠日復一日正視那些洶湧而來的資訊與思緒,細思了身處一場翻天覆地運動中,每個行動的意味與源起,審視創傷的源頭,併發症,尋找可能的疫苗,以處理每道傷痕積累下來的糾結。「整件事廣闊得就像大海,出一本書只是其中一條船。根本不可能涵蓋。裏邊一些像黑洞的部分幾乎永遠無法平反,不公平的事已無法由書寫令正義得到伸張。透過書寫,我只想令沒有經歷過、或其他地方的人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實在太多委屈,而這些委屈實在太細微,你不身處其中根本不會知道。」

作家本來就要面對誠實
沒有暗語,沒有假借的行動代號,沒有匿名,日記體的書寫,無論內容是否與抗爭相關,都是對當下時空的一種回應,書寫的內容都因每一個日子,每天發生事情而起,也記錄了自己身處的位置和場合。日記體也意味一種赤誠的坦露。大半年以來,人們對述說自身的經驗噤若寒蟬。白色恐怖之下,不知說什麼會有怎樣的後果,身處什麼地方變成犯罪證明,什麼情況會被消失,一切已沒有邊界可循,加上稍有話語權的人,任何立場表態都有被抽秤(註:故意挑剔、指謫他人缺點)的機會。然而韓麗珠在決定出版這些日記前,並沒有太多猶豫。她認為:「寫作的人本來就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揭露和誠實的勇氣。」
白色恐怖不是出版一刻才意會。出版散文集《回家》後,裏邊有些文章談到社會運動,姐姐打電話來提醒她,寫這些東西很容易被人針對的,最好不要寫,寫些別的不好嗎?然而她想到,寫作的人,要是明知有些東西你不可以寫就不去寫,那是違背了寫作本身。「當社會上好像有自由和民主的氣氛時,作者去面對誠實勇氣的問題時,只要想到私人的事情,是否可以公諸於世這個層面。然而當寫作氣氛不是那麼濃厚,或已充滿極權滲透時,作者要思考的則是,會否因為把事情寫出來而被捕。然而誠實的勇氣由此至終是必需的,這是作者一開始就要去想的問題。」
更迫切的告誡還是有的。「2018香港藝術發展獎」頒獎禮上,韓麗珠獲文學藝術組別藝術家年獎。當時是5月尾,文化界已有不少關於反送中的聯署,那天頒獎典禮,她跟梁寶珊最後致詞,二人的致詞都為此發聲。韓麗珠也說了:「希望以後的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對於寫作的人來說,免於恐懼的創作自由,比任何獎項來得更重要。」,後來無線刪減了那一段,大公報的得獎名單中也抽走了她和梁寶珊的名字。後來有些寫作的朋友,提醒她這說明中國的言論自由再收窄了。要是你說這些,或在文章表達這些觀點,可能要被點名,往後出版可能就會有困難了。「我想他是關心我的,然而我覺得。寫作的人要是明知道一些事情發生而不說,那不如不要寫。這個關口對我而言較大。」回想起來,她當時本來並不想去,社會發生這麼多事,心情本來不太好,但想到有機會在台上,當時現場也有許多高官,或者可以為這件事說一點什麼。
有時專欄的編輯,因為出於關愛,也會指出一些字眼是否可以斟酌。她明白這是因為不想文章引來危險和爭議,但也感覺到,整體社會氣氛是非常緊張。「然而我覺得有時人在白色恐怖之下,那種監察並不是真的有一個人不准你寫,而是自身的恐懼,你內在會生出一個監察者。我也會有這個監察者,但我會盡力去跟他相處,叫佢得閒(叫他有空)就去喝喝茶,不要打擾我。」

從反抗到報仇
每個人的位置不一樣,因為各人適合做的事不一樣。有些人知道他們的行動是要在街上才能實踐,有些想不了這麼多的,會站得較前;反之有些人能力上適合站後一點。無論你做任何一個選擇都會有後果。「前線有前線的後果,和理非有和理非的後果,救護會有救護的後果,寫作有寫作的後果,畫畫也會有畫畫的後果,你就去承擔自己的後果。」
韓麗珠直言書寫是為了解決自己深層的問題,因身處的環境有激烈的轉變,由個人創傷,要走進社會的大創傷中。無論是參與運動還是反對運動的人,本來就帶住自己的情結或情緒創傷,然後走入集體創傷之中,去面對或自療。「從去年六月開始,發生了許多事情,其實我好需要寫作去幫我理清一些問題。因為每個早上都十分緊張。每早起床從夢中回到這個世界,就感到不知今天發生了什麼,要看手機,或打開收音機聽聽有沒有衝突發生才安心。然而我總是過一會就要把這些都放下。再去做日常生活要做的事情。會去寫這些日記。」當現實過份貼近。用小說去梳理,其實需要距離和時間。「正如原子彈爆炸,也需要十年時間去書寫那經驗。然而爆炸的一刻,同樣需要文字和寫作,即時也無法想得太多的文字。那種文字正是比較接近散文、日記、或隨筆。」
思考與批判在《黑日》中比記事的比例要高許多。例如早在抗爭初期,不少篇幅都反覆思考對施暴者怨恨滋長的問題,甚至嘗試梳理他們的心理。然而運動的口號,後期無可避免地演化到「報仇」,甚至不少人認為這是延續抗爭意志的力量。「經過抗爭,我們的思想不能簡單停留於,暴力就是不好。抗爭前,我們可能會這樣想,因為我們是在一個較為單純的世界。然而經過抗爭,我想大家都要對暴力有更深層的思考。」她說。
她指出「報仇」的目的終究是為了要令自己的傷口癒合,而不是要去令傷害自己的人受苦。她相信叫「黑警死全家」的人不一定會這樣做,有時是需要這樣的情緒發洩。而這些人為何會有這麼多的恨,是因為這些人很愛這個地方。「我們對愛的理解不一定全是正面的。愛裏邊同時包含很深的恨意,是因為當連結得緊密,同時對方無法做到自己的要求,或者是做了一些傷害性的事情。然而愛本來是什麼?就是當你把自己脆弱的部分打開,然後承受整個世界對你所做的事,所以生出恨意,也是自然而然,從而延伸暴力和激烈。」她覺得,當抗爭者去說「黑警死全家」或報仇,只停留在口中。「這種暴力,遠遠及不上,手上拿槍炮武器的人,或有權力去把人判監,或有權力可用任何方式去對待他人的人。」從一開始,權力和暴力都不對等。所以當我們說到暴力,對於暴力的想像,應該要因為抗爭而有所更新。究竟這種暴力,是豪無原因,是基於惡念與邪惡而衍生的暴力?還是這種暴力,是為了由極權生出來的更大的暴力?這種暴力,會不會是反抗一些更大的暴力,要取回公義的暴力?

運動激起慈悲心
藝術發展獎的致詞上也早說過這一段:「很多人說,以前的香港比較美好,我卻覺得,近年的香港愈來愈美好。近十年的香港,是許多動蕩的地方,是消失中的地方。活在一個消失中的地方,對於自己和整個世界會有更多覺察。」在經過日漸黑暗大半年,爭鬥的手段也愈趨殘暴,韓麗珠看見的卻是運動激起了人的慈悲心,原來社會上許多人是互相連結的。「有些人被捕,有些人遭遇性侵,如海上有許多浮屍,沒穿衣服的人被拋到海上。有些事情並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也會感到很痛苦,即使不是受害者,不是受害者的家人都會覺得好痛苦,於是很想幫忙這些人。不是因為你自己受苦,卻好想去救那些人,這就是慈悲心。這種感受是從前很少見的。」
她提醒發生抗爭之前,香港從來都不是一個美好的世界,要是大家有留意社會狀況,一直有許多不公義的存在。如警察去打露宿者,這種事情十數年前都一直存在。「城市中的動物,農民,經常被迫遷的農夫,一直都在承受許多的不公義。抗爭只是把承受不公義的人口,擴大至只要立場跟政府不一樣,就會成為被不公平對待的人。」歷史上由在集中營對付猶太人的所作所為,早已指出人性可以有多殘忍。日記中反複對照了了關於不同人道災難的作品,這是為何韓麗珠對事情發展日復日滋生惡意並不令人驚訝。「這正是為何我們需要建立較好的制度去防止人性去到那樣子。所以抗爭本來就是源於制度失效,提醒我們人性的惡在沒有制衡中會擴大,可以去到納粹集中營時期那麼極端。」
決定以《黑日》為書名以前,她本來想到《暗黑日光》等幾個都是四字的書名。後來一位台灣的作家朋友,想來想去,在沖咖啡的時候想到了《黑日》這名字。既指涉「日記」,好像也保留了暗黑背後那光明的意味。問過幾位作家朋友後,她把文字都寫在紙上摺起,放在她的白果跟前,像抓周一樣隨牠選,想看牠會抓哪一個。最後牠一抓,也就抓到了《黑日》這個名字。「我有好強烈的感覺,覺得事情並沒有那麼差。有時發生災難,會想到為什麼是我?然而很多時遇上些很極端的事情,會把許多內在的潛能激發了出來。香港人正是經歷了這些,一些很好的元素才走出來。那些捨己為人的行為,很多是我自己也做不來的。雖然我知道不是所有事情都那麼光明,但至少一部分是這樣的事件。只有在覺得自己生命快要失去,或是將會一無所有的時候,反而有些好事出現了。」

毋須審訊的小歷史
韓麗珠不是沒有看到,自六月以來不同機構的記者都站得很前,奮不顧身地去紀錄,公正持平的紀錄已不少,不同位置的人也不需要擔心得不到一個公正的論述。政府同樣有自己的一套論述。「所以缺少的是微觀的小歷史的敘述,而這些微小的聲音其實好重要。小歷史的敘述。即是由不同的人,由微觀的角度,去記錄這段時間的生活。」
她解釋,香港正在經歷的轉變,是因歷史發展到一個地步,中國因經濟發展在世界上演變成一種主導地位,同時它獨裁的意識形態漸漸在全球擴張,其中香港首當其衝,這是為何我們每一個人在經歷一種深層的轉變。「加上歷史元素,香港是一個不斷消失的地方,而活在此處的人,並不想去順從當權者。大部分人都想去抓住香港這個身份。因為好想抓緊一點什麼,於是想不斷去創造。」
未明的真相那麼多,文章也有提到讀者就曾質疑,一些未經法庭判案的事情,所以不應當作已有發生。然而法律從來不會是凌駕所有真相的唯一準則,在審判底下觸及不到的還有許多。從作家的所見所聞而引申的感受與聯想,並非新聞寫作,考慮的不只是公正持平。「吳傲雪是首個挺身而出的證人,但有人質疑。然而我們可以再回溯,一直以來,女性告強姦或性侵,是很少可以罪成。這是因為整個報案制度與法律制度,即使已有證人走出來,都並非去關顧受害者。日記中我寫的也是這些我看到的和我相信的事情。而微觀角度重要在於,可以補足大敘事聲音的不足。」

穿梭虛假與真實
黑日中的文章,雖然是散文,但韓麗珠覺得,那個以第一人稱去書寫的「我」,也不過是一個敘事者。「因為一直以來寫小說,觀看生命與世界,都是從小說的角度出發。所謂小說的角度是,這些事情,外在世界,最終都是虛假的。世界如何呈現,往往基於敘事者如何去形容,去投射一個怎樣的世界。那還有什麼是真?就是看事物的角度。」正如《人皮刺繡》,即使小說內容是虛假的,她同樣認為當中的世界觀對真實是重要的。真實與虛假很多時一體兩面。意思不是說這些日子以來同一件事件眾說紛紜也,只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而是什麼樣的人,接觸到怎樣的資訊,如何去辦別,引起怎樣的反應都是理解現實中很重的一部分。
「抗爭對我們而言好真實,甚至是太過真實的人道災難。然而,我知道有一天它還是會過去。就像我們現在回看文革,或猶太人種族滅絕的事件,我們這一代人已再也沒法覺得身在其中。往往是直至再有別的災難發生在身上,我們才可以透過我們身上的發生過的災難去想起這是怎樣一回事。」歷史,也只有在重覆發生的當下才變得真實。
從魔幻走向現實,以小說起家的韓麗珠2018年才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回家》,上一本短篇小說《人皮刺繡》作品用了兩三年去書寫剛好是去年四月交稿。然而到反送中運動,生活又迎來了巨大的衝擊。在《黑日》中,她不時對照過往類近的歷史中,不同時期的人如何面對每一個決擇,以及艱難的時刻。
「日常生活中我不是容易憤怒的人,然而我一旦憤怒,會憤怒好幾年。但我最容易感到的是傷心,不是怨恨。因為我知道,制度上沒有制衡時,人從來可以很恐怖。只看他做多少出來。所以我最關心的是,一個本來正正常常的,可能是我們的鄰舍,或我們認識的身邊的人,本來好像都跟我們差不多,為何突然會做一些極端的行為呢?為何會在上班時開槍打一個不認識的人呢?我比較想知道他們的心路歷程是什麼。然而要探索一個人腦中想的是什麼,就不可用散文手法,我必需要用小說的手法。」

在歷史中從不孤單
那半年間,她翻看的書單有普利摩李維《滅頂與生還》關於集中營的記憶錄,有米蘭昆德拉或村上春樹的報告文學,「因為其他國家已遇過類似的災難,如捷克的抗爭等,或多或少會有相似之處。那是因為想知道為何會發生,想得到一些支持。我們需要知道,我們在歷史上不是孤單的人。雖然不同國家遇到的景況不同。」
歷史告訴我們這些事情從前發生過,以後也會再發生。「我需要知道的,其他國家的人發生這樣的事情時,他們如何去過渡這種危機呢?而那個時候也發現,自己可以跟其他國家這些狀況連結起來,所以想再重看一遍 ,可能會因此明白更多。」運動期間,韓麗珠到了外地辦講坐,開寫作課,這樣的時刻過去,少不免被問及身份的狀況,世界其他地方對香港的關心,也與以自己國家經歷過的創傷與抗爭去跟香港作比較,或者去交換一些經驗 ,令我知道,香港人其實做了許多。「這本書跟之前的小說與散文集不一樣,之前的都是我需要出,因為小說中的世界對我是重要的。而這本書是出版社提出要出。另一個原因是,我知道其實這個世界需要這本書。這個世界需要經歷過抗爭的人,不一定是我,其他人都可以,只是去寫這段時間的生活。」
她指出,無論是惡法或瘟疫,香港都是首當其衝的正面迎擊者。瘟疫是失衡的表徵,無論是精神或身體上的疾病,都要通過地震般的衝擊,才有可能重新得到平衡。然而,另一重擊又迎面而至,多微小的生活都會再受到衝擊。再要拋出自身,去與歷史連結,這個過程會更不容易。在重組書中每個月的事件列表時,有些事不記得了,要看多次去記起,加上要對應自己寫過的事件,原來像二度傷害。本來她覺得自己沒有創傷,結果卻似是傷口未好,再打開一次,這種感覺很尖鋭。然而她始终覺得:「生命不是關於你如何刪除你不喜歡的,而是去創造空間,去安置這些你沒有很喜歡的事情。」可預見更黑暗的日子還會再來,遺忘有時比想像中的速度要快。在災難中的名字都化成數字之前,去記住不再只是一種選擇,卻是一種堅持。

歡迎光臨端傳媒小吃店!
1月5日至2月7日,《好久不見,想點什麼?——台港連結的廿道料理》於香港誠品銅鑼灣店 9F 開展。展覽期間設有限定訂閲優惠,精選了20篇台港主題文章免費開放閲讀,歡迎你閲讀、分享,來一趟台港文化深度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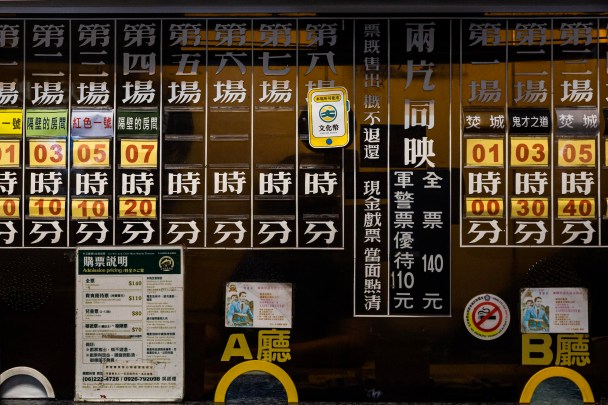
很喜歡這篇文章。
毫*無
倒数第三张图片的图例可能写错了?
謝謝讀者指正,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