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1年,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他來說「絕對會是一場災難」,隔年,他得了諾貝爾獎。2014年,漢德克(Peter Handke)指責諾貝爾文學獎是個馬戲團,早就該被廢除了,五年後他就得了諾貝爾獎。獲獎前對於諾貝爾獎持否定態度的頂尖作家不在少數,但他們後來卻還是欣然拿獎——漢德克還稱自己獲獎時有一種「怪異的自由感」(a strange kind of freedom)——那麼,這些姿態反映出了諾貝爾文學獎怎麼樣的意義?
在得獎前一年,聶魯達(Pablo Neruda)說道:「諾貝爾獎,無論它發給誰,總是一種對文學的尊敬。我不是那種會爭論某個獎有沒有頒對的人。重要的是這個獎——如果它有任何重要性的話——對作家這個身份給予某種尊重。這才是重要的事情。」尊重、榮譽、肯定、賦予怪異的自由感,這是作家們對於諾貝爾文學獎的判斷。這是他們角逐的最高殊榮。
但這些都是大作家們在煩惱的事,而諾貝爾文學獎對於我們,一般讀者,它的意義又是什麼?尤其是現在這個需要同時面對大瘟疫、新冷戰危機、社群媒體的加速與分眾、能源與氣候危機等等的時期,諾貝爾文學獎所承擔的作用就絕對不只尊重與榮譽。本文會從文學談到諾貝爾文學獎,嘗試框定出我們這些遠在東亞的讀者們,該如何看待它的意義。
諾貝爾文學獎讓我們看見的是現代世界人之間的疏離感越發強烈,疏離與孤立甚至成為一種美學。到了疫情時重讀,更是別有一番苦澀。

文學:娛樂是形式,而先知是內容
從最基本的概念開始的話,我們可以先回顧法國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的一個陳述,他說,面對各種環境時,哲學所探索的都是三種情境之間的聯繫:選擇、距離、例外。這三個情境又能理解為決定、裂縫、事件,而哲學便是「必須接受事件,必須同權力保持一定的距離,必須在你的決斷上堅定不移。」如果把以上這三組概念移植到文學上的話,無論是哪種文類,都是作家們將關於這三種情境的思考實體化,寫為文章,集結成書。
在這種思考過程裡,有人會著重內容,有人偏好形式;有人會鑽研文本本身,有人關注外部;還有階級、性別、種族、地域等等議題,共構出我們現在稱之為文學場域的地方。在這裡,就連「文學是什麼」都不會有一個固定的答案,它永遠都容許開放解讀、詮釋與辯論。然而,其中始終不離巴迪歐所認為的選擇、距離、例外,所有人都以這三者來框定他們所理解的文學究竟是什麼。
由是,可以用一個深淺的程度表來理解文學,我們會說有些文學比較高深,又有些比較淺薄,有些比較困難,又有些比較容易。這些比較可以轉譯為兩組概念,娛樂與先知,以及舉止與神秘,前者是以色列作家奧茲(Amos Oz)提出的,後者是美國作家歐康納(Mary Flannery O' Connor)定義的。奧茲這樣說:「在西方,至少在英語國家內,偉大的作家和詩人通常被視為表演者(娛樂者)。他們可以杰出、可以精湛、可以深邃,可仍然是表演者。就連莎士比亞也被視為一個高貴的、也許是最偉大的演員。與之相比,在猶太-斯拉夫傳統中,作家們被視為先知。這也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因為與先知不同,我聽不到上蒼的聲音,我認為我並不比一個美國或英國作家更能做一個先知——去預見未來,或者充當人民的良知。」
這個反思並非只存在於亞洲或非歐美文化當中,在美國本土的歐康納換個用詞,討論了相同的議題——「小說的職責是透過舉止體現神秘」——作家該研究的就是「舉止」(人類行為的具體細節)以及「神秘」(人類如何逃避或正視生命的意義)。由是,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公式:舉止/表演即形式,神秘/先知即內容,頂尖的作家通過前者表達後者,通過選擇、距離、有時遭逢例外,企圖書寫出人類史上的偉大作品。
無數文學作品都關注人際關係的過於緊密會帶來怎樣的損害。而去年我們碰上了一次例外,一個導火線,一場疫情讓所有人的距離都重新洗牌,遙距上班以及網絡購物等等現象,都讓我們必須重新把握距離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今屆的諾貝爾文學獎大熱門,也是來自以色列的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在2017年獲曼布克獎的小說《一匹馬走進酒吧》裡,便巧妙地把舉止/表演及神秘/先知這組關係寫成故事。故事講述一個蹩腳的脫口秀表演者拼命表演,無所不用其極地逗樂觀眾,但觀眾實在不太理解他在做什麼。在表演途中,過往的歷史創傷、戰爭後遺與少年陰影不住從他的笑話裡側漏出來,內容越過了形式的限制如山泥傾瀉,讓他的觀眾都走光了。沒有觀眾,但脫口秀還是要表演下去,他就說道,「有匹馬走進酒吧,跟酒保點了金星啤酒。酒保幫牠倒了一杯,馬喝完再跟他點了杯威士忌。牠喝完後再點了龍舌蘭酒。一乾而盡。點了杯伏特加,然後再點啤酒⋯⋯」故事拉扯成一千零一夜的接龍,試圖通過娛樂來續先知的命,通過舉止來接駁神秘,讓文學連上歷史的餘燼。
諾貝爾文學獎:距離讓我們提防例外
而距離是一個這兩年被燃點起來的重要議題,在整個現代進程裡,我們至少遭遇了從電話換成手機,再從手機更換成智能手機的過程,這個過程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大幅壓縮。在這數十年的過程裡,有無數文學作品都關注人際關係的過於緊密會帶來怎樣的損害。而去年我們碰上了一次例外,一個導火線,一場疫情讓所有人的距離都重新洗牌,遙距上班以及網絡購物等等現象,都讓我們必須重新把握距離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而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應當是引導我們在閱讀作家們的作品過後,在想像的世界裡遭遇過各式各樣的故事,更能充份預備好去面對且理解生命裡下一個無法預測的例外狀況。
另一位諾獎大熱門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去年參與了《紐約時報》的一個計劃,名為「大疫年代十日談」(The Decameron Project),也是以一千零一夜的方式讓文學持續下去。雜誌於七月刊出,找來了數十位作家書寫他們在疫情期間構思的故事,其中大多數都書寫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被徹底切割,居家隔離以及回老家使得城市空蕩蕩,人味都流失了。又有一部分寫由於與伴侶困在同一空間,距離感無法拿捏好,兩人每天的選擇全然相異,磨擦就少不免。
這個計劃當中一個接一個的故事接龍,展示的是這兩年間作家與讀者們對於世界的重新理解,並嘗試通過文學中想像的時空來接駁現實那凝固在家中的隔離時空。這種重新理解距離感的過程,不只是美國,遠至歐亞非都是一種共同經驗,一場疫情重新洗牌了人類對於距離的理解,而作者們捕捉這種異常,將其書寫下來。巴迪歐除了舉出距離、選擇和例外以外,他還強調,要表達哲學和以上三個情境時,都採用了故事的形式。說故事是人類的本能,而文學是把故事打磨到極致的形式之一。
在2019年獲獎的兩位作家,漢德克及朵卡萩(Olga Nawoja Tokarczuk)也是擅寫距離的說故事大師,漢德克以冷硬筆法書寫人與自然之間的距離,人與人之間彷彿永遠隔一面牆,無法理解,只能通過自然或景物來間接描述。朵卡萩把場景帶到波蘭村莊,卻以一個接一個的夢境展示出人之間的距離無法靠近,偶爾如果可以通過夢境或雲遊還能相聚,但絕大多數時間就算面對面也像是溝通不良。這些都是在疫情前的作品,而諾貝爾文學獎讓我們看見的是現代世界人之間的疏離感越發強烈,疏離與孤立甚至成為一種美學。到了疫情時重讀,更是別有一番苦澀。

如今,越顯示在地特色的作品就越是國際化;越彰顯自己是包容進步的就越是歧視。文學也沒有逃離這個困境,畢竟它所反映的仍然是當今社會的脈搏。
至於今年,在地球被疫情肆虐兩年過後,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應該座落於,它如何讓讀者在得獎文本中觀察到人與人之間被不斷劇烈改變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感與十年前、三十年前、六十年前有何不同。這種改變除了疫情以外,在整個現代進程裡從未停止地變幻,而文學作為一種路徑,除了表演與舉止以外,更重要的是神秘的先知功能。比如卡繆的《鼠疫》橫跨七十年後擊中我們如今對於封城的恐懼,薄伽丘的《十日談》穿過七百年來引導紐約時報發起《大疫時代十日談》計劃。而諾貝爾文學獎的意義應當是引導我們在閱讀作家們的作品過後,在想像的世界裡遭遇過各式各樣的故事,更能充份預備好去面對且理解生命裡下一個無法預測的例外狀況。
我們:與諾貝爾文學獎的距離
於我而言,諾貝爾文學獎從來都是一次例外,它絕大部分時間也超出我的閱讀脈絡,比如去年的露伊絲.葛綠珂(Louise Glück),我猜是北美女性會獲獎,於是我選愛特伍,結果沒想到是詩人。又或巴布.狄倫,不過這個應該沒幾個人會猜得中。漢德克得獎後引來繁體中文翻譯潮,石黑一雄也是。諾貝爾文學獎本身對於我們的意義,是突出我們與它之間的距離與選擇的差異,而我們總能從外部觀察,獲得賭博與突出肚腩曬書的短暫樂趣。

獎項本身就是瑞典學院的一次選擇,它們每年經典化一位作家,這是作家們可以獲得的最高榮譽,同時讓世界各地讀者們知悉這位作家在獎項遊戲上已經破關了。但與此同時,它有時能達到政治效果,比如莫言或亞歷塞維奇,都是對於他們批判極權社會的文學進行肯定。有時,瑞典學院又想創造些意義,結果就莫名地選出了巴布.狄倫,但至少可以看出這個獎項所反映出的價值觀與經典化效果。
大江健三郎說:「諾貝爾獎對你的文學作品幾乎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它提高你的形象,你作為社會人物的地位。你獲得某種貨幣,可以在更加廣闊的領域裡使用。但是對於作家而言,什麼都沒有變。」因為諾貝爾獎對於作家而言只是一個榮譽,它的實際作用是座落在讀者身上的。它讓文本進入一個大幅出版與外譯的管道裡,這就是經典化。而我們必須從中理解的是,我們所身處的位置與瑞典學院所選擇的價值觀,有怎麼樣的距離,我們應該收緊這個距離,維持原判,還是與其拉開?
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在自己所身處的地方,能說出自己比前一年的自己有進步了。在這個時空失序的疫情時期,我們有沒有用更好的目光來把握這年所讀的書帶給我們的選擇、距離和例外?

社會上從來不乏批判諾貝爾文學獎歐洲白人中心主義的聲音,2019年漢德克及朵卡萩雙雙獲獎更引來了大批責疑聲浪。此外,石黑一雄、奈波爾、魯西迪被稱為「移民三雄」得獎時,又不太看得見有人猛力批判這三人的歐洲中心跟戀殖傾向。如今,批判得獎作家時用種族框架與地域框架也如同隔靴搔癢,也不應該是我們用來檢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濾鏡。因為,就算如果瑞典學院每年順序沿著各大洲頒獎給各色人種,又會被批評為虛偽或形式主義。形式主義的定義是,把內容無限推後不談。相信這絕對是瑞典學院最不願意扯上邊的標籤。
如今,越顯示在地特色的作品就越是國際化;越彰顯自己是包容進步的就越是歧視。文學也沒有逃離這個困境,畢竟它所反映的仍然是當今社會的脈搏,因此,如果諾貝爾獎給我們帶來什麼啟示的話,就是別管它什麼白人中心,也先別管移民三雄這樣的標籤當中的政治正確性或權力關係,漢德克有沒有政治醜聞也沒有關係,而是遠在東亞的我們應該從他們的作品裡學習,並閱讀自己的地方,表達自己的地方,從多方閱讀裡參照出我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並作出選擇,從文學裡練習迎接例外的準備。
諾貝爾文學獎是個一年一度的鬧鐘,它遠道旅行而來,提醒我們是時候該檢視自己與瑞典學院之間的距離了。但最重要的是,無論是近、不變、還是遠,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在自己所身處的地方,能說出自己比前一年的自己有進步了。在這個時空失序的疫情時期,我們有沒有用更好的目光來把握這年所讀的書帶給我們的選擇、距離和例外?在疫情時期,當所有人的距離變得曖昧不清時,獎項提醒我們,是時候該用文學的虛構時空,為現實輕輕覆蓋一層娛樂的薄膜,並在其中期盼看見先知的靈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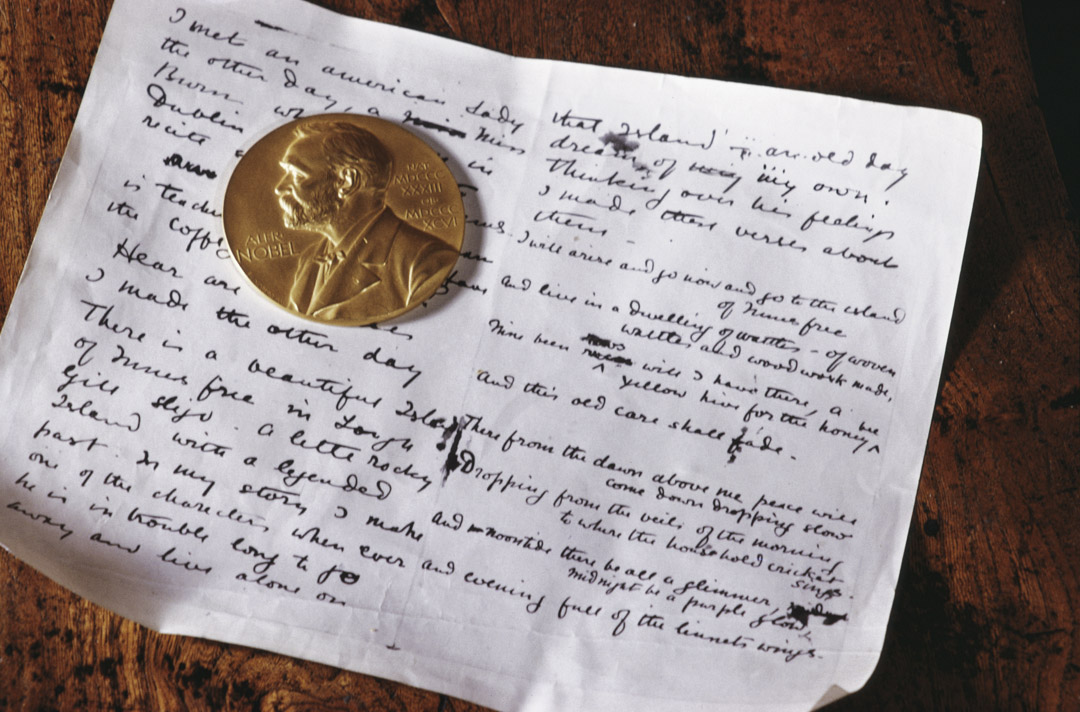




很不錯的文章,在疫情肆虐的今天,諾貝爾文學獎更多的意義在於讓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被文學消解,疫情有結束的那一天,人們也有互相擁抱的那一天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not Marc Marque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