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手指南》(Beginner's Guide)這個被很多遊戲設計師譽為經典的作品中有這樣一幕,一位應當是成功人士的講者隻身站在演講廳中心,台下坐着的觀眾是他的死忠粉絲。觀眾抬起頭,眼巴巴盯着講者,他相信講者是智慧的化身,馬上又要口吐蓮花。
這時遊戲視角反轉,我們站在講者背後,才發現他其實十分緊張,觀眾席在他眼中化為煙火重重的奇景,似乎馬上要將他吞噬——這正是我在戲院看《天能》(Tenet)時想起的第一個畫面,諾蘭也許比我們更清楚,他讓我們/自己失望了。

最近幾個月,我終於實現了自己都不曾料想到能夠擁有的夢想——製作遊戲。寫故事、買部件,同時協助搭檔——一位出色的遊戲藝術家搭景、測試程序,安排遊戲測試聚會,攝製過場動畫場景,配音,忙得不亦樂乎。在一切技術與藝術的挑戰下,我學到不少技能,對創作這件事也有了較以往完全不同的感悟。首當其衝就是,當身份從玩家、評論者轉換到產品創作者時,我忽然發現自己的產能多麼有限,發現遊戲製作(或一切工業化水準的視聽產品製作)真是一磚一瓦搭建起來的,更不必說我們的產能完全由兩個人提供。以前想當然的質問某個遊戲為什麼不加上這個功能,添上那個人物,現在明白了,很大可能設計師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一個傑出的想法從誕生於腦洞到最後落地人間,中間的旅程漫長複雜。觀眾和玩家看到的是最終結果,比較參數則是與之有關的各種文化產品與生活經驗,於是很快大家會有建設性的批評。而對創作者而言,在小樣、原型、初代問世之前,其實我們更像弗蘭肯斯坦博士,並不知道自己在有限資源內的創作最終會變成怪物還是傑作。這也許是為什麼,過去兩週,想要和我熱切討論《天能》何以成為如今面貌的設計師和電影人,無論平日裏如何挑剔自省,總是要在對話開始的時候加一句鋪墊:「我敬佩諾蘭在拍這類電影上的膽量和努力。」
基於大量的負面評論和身邊人慾言又止的萌態,我終於擺脱懶癌魔爪,去戲院第五排找座位,在久違的凍死人的冷氣中看完了這部畫面冷清的爭議之作。開場戲過去,又看了五分鐘法國口音的女科學家面無表情、演示物理定律後,我悄悄給搭檔發短信:「諾蘭需要一個對觀眾友好的教學關卡。」
高概念、玩法與教學關卡
高概念是荷里活常見的敘事工具。在我的理解中,「高概念」的「高」,部分是指一個(往往很酷的)核心概念,其地位遠遠高於劇情、人物、美術、配樂;或者說,電影的其他元素是圍繞這個概念慢慢衍生的。一般我們看到的高概念電影大多是科幻、玄幻類型,具體的概念有違我們在真實世界中體驗到的物理法則和社會法則。譬如超級英雄電影裏英雄的超能力,或時空旅行電影裡對於平行宇宙的定義。電影之外,科幻小說也是高概念的地盤,人物和故事成為測試概念的試驗場,或是展現概念運行面貌的畫布。
在高概念電影中,主角是誰其實不重要,我們看到《廿一世紀殺人網絡》(Matrix)中的尼爾,或是《天能》中的,好吧,他就叫主角,理論上可以是任何人,任何一個被更高等級智慧選擇的救世主化身。而主角的隊友們,就好像金庸筆下逍遙派的門徒,往往身懷絕技,尤其熟悉旁門左道,譬如鎖匠(程序員)、有療癒功能的法師(醫生)、恃靚行兇的致命女人(恃靚行兇的致命女人),他們負責降妖除魔,護送主角殺掉大boss,或者找到寶藏(密碼)。

聽上去是不是像你玩過的絕大部分劇情類遊戲。沒錯,高概念在遊戲領域甚至比在電影工業還要常見,只是在遊戲行業中它的名字換了,叫做「核心玩法」。譬如《刺客信條》(Assasin's Creed)中藐視重力加速度的跑酷,《騎馬與砍殺》(Mount & Blade)中的騎馬與砍殺。遊戲設計師中很多人的慣性想法是「如果玩家可以這樣殺人/潛行/對話/穿越時空」,那故事應該怎麼編比較好。這並不是說設計師不在乎情節、人物。遊戲是互動的媒介,玩法就是玩家領會設計師意圖的最主要路徑,越好的遊戲,玩法和故事結合越緊密,這是藝術創作中經典的法則:形式與內容的緊張關係。而越新鮮有趣的高概念,比如《女神異聞錄5》(Persona 5)中偷心怪盜這個設置,就需要越直觀的玩法來傳播——潛行、殺掉保護思想的守衞怪、盜取藏在心頭最深處的執念,故事與玩法一氣呵成。
大部分遊戲都有教學關卡,即是通過簡單任務讓玩家理解、學習、最後熟練掌握遊戲玩法的最初幾關,譬如李逍遙在村子裡殺蜜蜂,或是白狼在瓦倫練習追尋氣味找到吸血鬼。選擇最簡單直白的任務入手,就好像數學、物理老師在讓你大量做題之前,先告訴你勾三谷四為何就可以弦五,如果豬八戒和孫悟空在電梯裡上下跳動會不會導致大家死得更快(我的物理老師就是這樣介紹力學定理)。當你領悟了道之後,才能用道的方法帶入習題集,理解、乃至解決難題。

高概念電影也是一樣,因為劇中一切都不會完全遵守現實世界的法則,一個必要的教學關卡可以在電影最初十分鐘內,讓觀眾逐漸明白創作者所造的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除非電影同時又是驚悚懸疑類型片,高概念本身要壓軸出場讓觀眾頓悟。其實,諾蘭的前作《潛行兇間》(Inception)在這層面已經非常完美:從開場火車之夢讓人意識到夢的不同境界,到巴黎建築師看到地平線折疊醒覺,再到主角前妻不斷出現演示真假不分的害處,層層疊疊,早在影片核心部分來到之前,大部分觀眾已經明白潛行兇間是怎樣的高科技。
有評論家批評《天能》中的物理假設前後矛盾,無法站得住腳。我倒覺得其實這不重要,這部電影和遊戲一樣建造了平行世界(當然過於現實的鏡頭風格沒有幫到諾蘭營造好這一重世界),是個 make-believe的空間,如果導演 make 到位,觀眾自然會 believe。之所以有人喊出戲,又有人要看一二三四五遍覺得是自己智商不夠才看不懂,是 make 的不夠。我們第一次知道逆轉時空這件事,是法國女演員一臉「人間不值得」的現場教學,這時高能信息轟炸觀眾(以及主角),畫面就是幾個子彈來來去去,並沒有起到演示作用;下一次變成印度阿姨,她的口吻是「你不用知道,也不該知道」;然後男二號一臉瞭然「我知道呀,我是物理學碩士」,教學完全是口述,別說動畫,連 ppt 和板書都沒有。
而電影和遊戲相比,製造視覺場景有天然優勢,如果諾蘭在奧斯陸機場的第一次打鬥,或是在基輔反派大佬打傷女主角的場景中,在布景、鏡頭轉換上給多點考慮,讓觀眾一目瞭然,哦,時間倒流是這樣啊,可能大家就可以吃著爆米花欣賞高潮戲的精彩。當然了,直到高潮戲,諾蘭好像還是沒有想出更明確的視覺語言,導致我們妄圖理解誰在順行、誰在逆行時,居然要去找角色身上的小布片,看看誰是藍隊,誰是紅隊,等一下,我們還要記起來,藍隊是逆行還是紅隊是逆行⋯⋯

時間循環,英雄重新來過
也許是文科生出身的緣故,我一開始就沒花時間從理性上梳理「熵」和時間、物質、主體的關係,甚至也沒花時間琢磨,為什麼從一個槍口出來的子彈會回到另一個槍口的問題。當法國女演員說:「別想了,信就行。」我馬上言聽計從,總覺得之後諾蘭會像拍《潛行兇間》中「房間失重需要引爆炸彈引起下墜」那樣,拍一個傻瓜版本給我。
沒想到導演比我還懶,從頭到尾,諾蘭這個物理老師也沒解釋清楚他的熱力學方程,就急著拉我們做題。結果我認識的幾位科學家和工程師看電影時都被坑在原位,想不明白方程式到底是什麼,導致錯過了最後半小時最能展現諾蘭腦洞的情節——前蘇聯軍事基地的時空夾擊戰。
而我之所以覺得我懂了,還是因為我愛打遊戲。最後男二背著預示他將死在上一個輪迴的書包揮手作別,告訴主角:「你才是幕後大Boss啊,我們早就是好朋友呀。」我忽然明白,所謂時間逆轉,所謂天能,其實就是一個越挫越勇的玩家誓死不看攻略挑戰《血源詛咒》(Blood Bourne) 的過程啊 (好吧,其實我挑戰的是PS版《蜘蛛俠》)。

想像你在玩一個魂系遊戲——或者對手眼協調能力不出色的玩家來說,想像你在玩一個動作冒險遊戲。因為難度太高,玩十分鐘就會死,但你堅忍不拔,死一次長一次智慧:下次跑到這裏要停一下,下次不要用火系魔法炸身上有炸藥的 boss;下次讓法師一開始就加防衞 buff。而這個該死的動作遊戲還加上了「choice matters」的功能,不但要打得過,還要選得對,每次選錯了,你就暗暗記住,下次重新來過,相信刺客不要相信德魯伊,甚至到遊戲很深入的時候才反應過來,原來隊友是卧底,而 boss 才是真愛,所以,讀檔(或死掉),再來。一直到通關之前,你都不知道故事是怎麼回事,甚至你是誰。但一旦通關,你就開了天眼,步步為營,善始善終。
想到這裏,我就開始覆盤,如果《天能》一開始就告訴大家這是一場遊戲,就好像《飢餓遊戲》(Hunger Game) 那樣。未來人就是遊戲設計師,主角和 NPC 則是早就掛掉的當代人,然後導演就可以把預算的一小部分撥給界面設計,讓視覺更加風格化也更加易懂。那樣就不用非常俗套的把禍端推給氣候變暖,以及再次倒楣的俄國大漢,而是可以大張旗鼓地說,對未來人而言,歷史完全可以是遊戲素材,畢竟我們現在也在各種《三國》遊戲裡指導劉關張怎麼攻城掠地,不是嗎?一旦歷史架空,那反派就可以是任何人了,比如《美國賤隊》(Team America) 裡那個動不動就要核爆全球的金正恩,或者,妻子也是長腿美人的特朗普?一場遊戲一場夢,就算你在遊戲裡殺了一個歷史人物的全家,對這個人而言,他既不會知道,也不會受影響。

開著這些腦洞(以及消化著八小時前喝過的咖啡),到半夜四點,我還在覆盤,從製作者角度幻想諾蘭如何拍個更平易近人、不用看很多次就能懂的《天能》,或者別拍電影了,直接做成遊戲。開場歌劇院那部分完成度很高,事實上,這是整個電影製作水準最高的部分,但敘事角度而言其實根本可以不出現,節省預算,就剪了吧(留著出DLC),可以把軍事基地做的更加細緻——對了,省下來的錢也可以僱幾個關卡設計師,那麼酷炫的概念,值得一個更好的旋轉門,氧氣罩也稍微高級一點吧,還不如我的N95呢。那麼開場可以直接是奧斯陸機場,懸念叢生,然後倒敘。遊戲還可以轉換主角,我是說可以控制的人物,那你可以一會是女主角,一會是男二號,甚至帶著小米手環的反派大佬。事實上,我也考慮過是不是男二變成男一更加好玩,那樣主線就變成了燒腦的「他不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會死」。

想到嗨處,我又陷入疑惑:「如果我都能想到,諾蘭怎麼會想不到呢?」
作者
我不算是一個稱職的諾蘭影迷,雖然我的確在戲院看了三次《潛行兇間》,也在《蝙蝠俠》裡第一次領略克里斯蒂安貝爾的男性魅力,而且我本人對時間、記憶這些概念極度著迷,甚至自己的遊戲也設置了一個和記憶有關的高概念。但是我沒有追過他所有的產出,比如《敦克爾克》(Dunkirk)(我也不太喜歡玩《使命召喚》),所以遠稱不上諾學家。
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我還是一個熱愛故事的人。遊戲設計最終是機器的語言,是和人工智能打架,打架結果也一早被算好,總在一個平衡區間內。但我最喜歡的那些遊戲,不然就是用遊戲的語言講了極度深刻的故事(比如《Fran Bow》),不然就是用遊戲的玩法讓我浮想聯翩主動給它編故事(比如《新手指南》)。遊戲裡的故事和人物會比電影裡更碎片、更容易表面化,彌補這種缺憾的手法與其說是技術(虛幻引擎或是《最終幻想》的動畫),不如說是沈浸在遊戲時間中不斷動作的我們願意相信它們是真的,是複雜的。在遊戲動作中,我們慢慢消化這個世界,這個故事,這些人,然後感歎設計師的出色。而越出色的遊戲,設計師也就越出名,比如宮崎英高,比如 Neil Druckmann(這也許是個反向的例子)。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樣在打通遊戲後,尤其是3A遊戲,坐在電視機前花十幾分鐘看完職員表,相信光是那些奇怪的工種(聲音協調員),就會讓我們明白,所謂作者只是個幻想。
當然如同我所有自以為了不起的頓悟一樣,早有一個法國人(或是德國人)想到了這點。關於「作者」的虛幻性,福柯早就參透。「作者」,無論是王家衞還是小島秀夫都是一個想像出來的形象。福柯指出,文化產品需要一個權威作者的形象,投資人有信心,觀眾也願意埋單,當然也許最簡單的原因還是因為我們懶,記一個人的名字總是比記兩個、三個、一百個簡單(再多也記不住了)。當我們在談論某個文化產品的作者時,也許我們早就墮入陷阱——這個人根本不存在。譬如,你知道在(不是很好玩的)《哈利波特》遊戲中設計魁地奇遊戲具體玩法的那個人,並不是J K 羅琳嗎?
所以,當我要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拍出《潛行兇間》的諾蘭怎麼會拍出這樣的《天能》時,我很快意識到這個問題本身的漏洞,於是非常邪惡地谷歌了這樣幾個詞「Christopher Nolan fell out with」(諾蘭和誰漸行漸遠)。果然,我發現讓我念念不忘的鏡頭雕刻師,憑藉《潛行兇間》得到奧斯卡最佳攝影獎的 Wally Pfister,在得獎後就離開了合作七次之久的諾蘭,訪問中他說不想透露合作終止的原因——創意夥伴的背棄,這是另一個古老的故事,就不再展開。但這也許能夠解釋為什麼很多畫面雜亂無章,色調也太過陰沈。
而雖然部分音樂聽起來仍是Hans Zimmer 味道,《天能》的作曲人換成了瑞士作曲家 Ludwig Göransson,這解釋了人物對話時過於嘈雜的音軌,還有追車畫面伴隨的奇怪電子音樂。最重要的是,搭檔告訴我,《天能》也是第一部諾蘭獨立擔任編劇的電影,在那之前他很多電影的編劇名單裡都有他的弟弟 Jonathan Nolan,搭檔還加了一句:「Jonathan Nolan 也是《西部世界》的編劇和導演。」
當然更加容易看到的變化是演員,雖然影評都在讚羅伯·派汀森的演技大有提升,我每次看到他的鏡頭都告訴自己:如果是湯姆哈迪,你會更愛這個電影。女主角真的很好看,但不知是編劇還是演員本身的原因,我總覺得選她的原因,除了導演的審美品味,很可能是因為她的腿夠長,可以從後座用腳踩到前座的按鈕。而剩下所有演員,就連俄國大漢都很模糊,反正日本也有核災難,就不能找渡邊謙來演個變態嗎?

所以,和《潛行兇間》一樣,《天能》不是諾蘭一個人的電影,這個新的團隊的合作並不如他們在訪問中說的那麼默契。但,如我在開頭所說,我和我身邊投身創作的朋友一樣,也許也愛開玩笑嘲弄《天能》,但依然「敬佩諾蘭在拍這類主題電影上的膽量和努力。」如果我能明白《天能》讓人失望之處,相信諾蘭早就在過去的未來或未來的過去,明白了一百次。這一次的失敗,未免讓尚在路上的其他人心有慼慼,我們確實也可以感謝他提供了一個經典案例,讓我們看看減法怎麼做,又有什麼東西是萬萬剪不得的。。
畢竟,如同 Youtube 《天能》預告片下的一個絕妙留言所說:
《天能》很可能是諾蘭的第一部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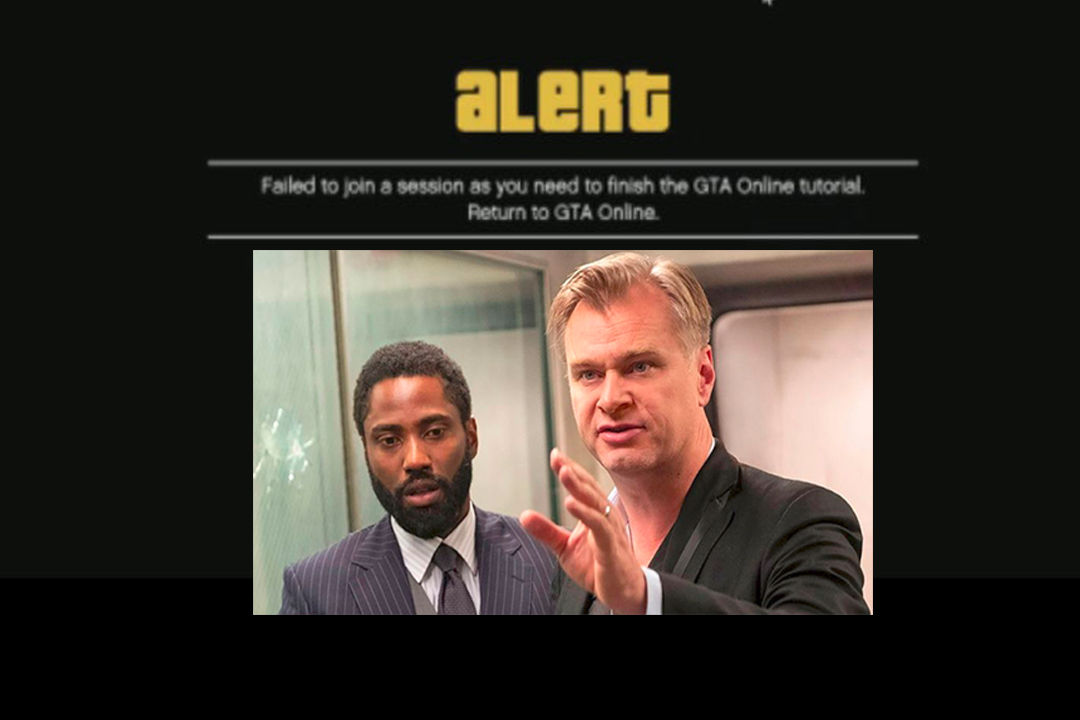




这篇影评太精彩了,完美地表述了我心中的感受,还挖掘到更多信息。我也觉得《信条》就像一个游戏,但是不怎么好玩。同是文科生,我觉得设定大概了解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太深究,我感受到的就是,故事不是很好看,情节比较混沌。就是音乐的部分不太同意,Hans Zimmer的音乐也越来越吵了,在《星际穿越》和《银翼杀手2049》里听多了都有点受不了。这一部里的配乐如果声音调低点就好。还有《哈利波特》游戏中设计魁地奇游戏具体玩法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能否请作者赐教一下。
謝謝各位費心評論,
@ArtKang 謝謝你的保留 我習慣用一件事情理解另一件事情 但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雖然是自己的理解也確實解釋的不夠清楚 謝謝你反饋
@kes 非常感謝你長久以來的支持 覺得自己作為作者很幸運
關於看懂看不懂提出意見的四位留言者,都非常謝謝你們的評價,我愈發覺得大家在評價這樣容易看不懂的電影時,其實是在defend自己的智商,但我總覺得作為創作者,愈能把自己的創意翻譯得易懂(易懂不等於弱智)愈見功夫,不然就是把自己的功課推給消費自己作品的人看,那後者願意消費與否都沒有問題,是個人意願,談不上智商高低。
最後,剛剛發現原來這套戲的剪輯師也是新加入的,更能解釋很多cutscene的問題——新加入不等於不好,可能是合作不夠默契,而這個新團隊從導、演、編、攝、音的問題我覺得爆發得很清楚,和諾蘭幾部前作比差距實在太大。
> ...配乐被编成逆曲....
还真不知道,如果逆着也好听,那我给一句卧槽。
可是如果不好听,就失去根本了。
如果連配樂被編成逆播也成曲都不知道就批評配樂的話 或許做這電影的人不像你做遊戲一樣有心無力吧
很中肯呢!看到身邊人正評滿滿,但自己看到一頭霧水,還以爲自己太蠢。作者分析過後,確實理解到電影在解釋理論跟鏡頭上都很雜亂。
我對"高概念"在這裡的解釋,還有其等同"核心玩法"的說法有點保留。
另外是勾三"股"四。
很高興再見到你的文章,雖然我不打機,但每次都能通過你的文字去遊戲世界探險。
p.s 祝你的遊戲成功
一次看不懂看兩次,還是你期待所有電影都餵到你嘴邊? 不懂的就查啊,電影入面的物理科學大部分都就套了個名詞,查完再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