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自然生態愈來愈受人欣賞,但眾生並不平等。雀鳥或蝴蝶這些野生動物備受人們喜愛,另一些野生動物卻偏偏不受人青睞,有些甚至因為到訪市區,引來人類的投訴,需要動用公共資源管理。
野豬和猴子就是這麼不受歡迎的野生動物。
我是一名行山愛好者,幾年前經朋友介紹,誤打誤撞與猴子結緣,做過年半的野猴生態調查員,成為公家野猴管理系統的一分子。我的工作分成兩部份,一部分是每年出車200多次,到香港的郊野公園點算野猴,調查野猴的數量變化,另一部分是協助獸醫進行多次猴子絕育行動,控制野猴的數量。
我原本對野猴一無所知,但那時候我幾乎每天都和猴子相處。在猴子眼中,我可能是一粒移動的大花生,出現的時候就有食物。而這份工作於我來說,則是帶給了我很多野猴的知識,同時讓我收穫了一段與猴子相處的難忘時光。

猴子從哪裡來?
香港有很多猴子,但牠們不是原居民。據説1910年代政府興建九龍水塘,發現附近生長著很多有毒植物馬錢,有人擔心馬錢的果實污染食水,因此引進數頭獼猴吃掉馬錢,自此獼猴在九龍山不斷繁衍。
現時野猴主要在金山、獅子山、城門郊野公園和大埔滘自然護理區等地活動,同時在市區也偶然發現。根據漁護署的數據,香港野生猴子總數目估計約為2000隻左右,分成約30個猴群,品種為普通獼猴、長尾獼猴及牠們的雜交種。
在香港保育猴子,實際是替牠們絕育。馬騮在香港自然界的食物鏈處於較高位置,沒有敵人,可能只有猛禽會獵殺嬰兒野猴;牠們在香港的環境太容易得到食物了,不但有非常嚴重的非法餵飼,而且有些垃圾房管理不好,牠們也會洗劫裡面的食物,食物充足,所以數目增長很快,人猴衝突也偶然發生。
為了控制野生猴子的繁殖數量,海洋公園保育基金自2009年起受漁護署委任,為野猴絕育。我的山野猴子工作記,就是始於這個野猴絕育計劃。

「正」字數猴子
我們是小團隊運作,上司是一名外籍獸醫,但平日出車的是香港人隊伍,包括一名司機,兩名野猴生態調查員。每日工作朝九晚六,上下班到海洋公園打卡,中途就出車到郊野公園的指定地點數猴子。
猴子在山林活潑亂跳,怎麼靠兩個人就能統計清楚?我們的策略是用食物引牠們出來,再按族群統計。猴子喜歡吃香蕉,但香蕉只有在特別行動才會奉上。平日我們多準備天然健康的食物,如黃豆、花生、瓜子及蘋果。蘋果因為不耐放,還要叫同事小心預備,以免帶出去的時候變壞。要到絕育行動時,我們才會預備香蕉及提子這些好一點的食物,這樣較容易抓到猴子。
我們往往把食物放進大型捕猴籠裡面,這是一個訓練,不是每一次都會抓走猴子,但能令牠們習慣進入籠中,方便絕育行動的時候捉走牠們。
「嗚——」我們大叫一聲food call,野猴聞聲看到食物,便紛紛出動,猴群之間的搶食爭鬥亦因而掀起序幕。在戰場中,猴子齜牙咧嘴、爭鋒相對,我們這些人類只被當作死物,不會被打;有些猴子追逐時,還會抓著我的腿轉彎,以為是柱子。我們只冷眼旁觀,默默地履行統計的職責。
猴子統計沒有捷徑,我們見到一隻,就用數「正」字的方法寫在記錄表上。最理想的情況是,牠們出來站在開闊的空間,我們像操場點名那樣點算。另一種情況是,整個猴群朝着某個方向走,我就定某個點集中點算牠們。點算時,我們還要分清男女和年齡,有陰莖和尖長犬齒便是雄性,有乳房或哺乳痕跡的是雌性。新生兒也是點算目標,少於一歲的猴B通常會黏著媽媽。

我們希望猴子出來越多越好,但一定不會一擊即中,所以一年數兩百多次,不停地呼喚牠們出來,不斷地數,並用最大的數字作準。把不同族群的猴子加起來,就得出香港有多少隻猴子,我們也用這個方法計算猴子的出生率。但是死亡率我們就無法統計,因為牠們的死亡未必在我們的視線範圍出現。
香港的野猴一般壽命為廿多歲,出生季節大概為每年的4月至9月,6月至7月為生育高峰期,冬季是交配期。所以在4月生育季前,整個猴群的數目最穩定,我們會進行較完整的統計,希望拿到全年最準確的紀錄。
猴族命名術
數猴子的困難之處是辨識不同的族群。猴子看起來很像,但看得多便能辨認,我花了兩個多月時間就認出大部分常見族群。技巧是認準一兩隻特徵明顯的猴子,如頭大、眼大、傷殘等,來確認是哪個族群。
為求方便認出特定族群,野猴會被人類命名。這些花名歷史久遠,很多名字的緣由和命名人都難以稽考,但我相信是香港同事所起,因為他們用中文思維命名,但用英文寫報告。有個族群叫「三腳雞」,因為有隻猴仔跛了一隻腳,英文名叫「Three legs chicken」。有個族群很喜歡打架,據說有隻猴子很喜歡舂同族的眼睛,所以那群猴子裡面很多都是盲眼,也有一些斷手斷腳。又有個猴群叫「毛女」,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有一隻猴女比較多毛。

就像人類一樣,這些猴子的族群關係是可以編寫成族譜的。有些族群壯大後分裂,有些逐漸消散,只不過沒有人寫出來,但資深的同事是心裡有數的。以前有個說法是香港野猴有四大家族:有一族叫「胡子」,可能是有鬍鬚;有個族群叫「白眼」,可能眼睛白色;有一族叫「賭神」,相傳當時的老大髮型梳起,樣子長得像周潤發;還有一族叫「孖指」,英文名叫double finger。這些族群至今還在,只不過下面發展出小族群。
身為猴子調查員,我見過猴族的離離合合。香港猴子的基本是母系社會,由媽媽維繫族群,基本上猴女一輩子待在同一族群,但猴仔長大後會出去闖蕩,加入其他族群。牠們跟不同的異性交配,豐富基因多樣性。只要猴仔在其他族群表現出色,又討到女猴歡心,就有機會在那個族群爭取到較高的地位,甚至成為猴王。
但有些已經離群但未找到其他猴群加入的雄性猴子,看起來就像一群「死飛仔」聚集一起。有時候也有孤猴隻身闖蕩江湖,更可能走出市區。新聞報道的那些到便利店偷麵包、到麥當勞搶食的猴子,就是離群的孤猴,牠們比較有膽量。
一覺醒來:還能做愛,但沒有後代
我們工作的最重要任務是絕育行動。這項行動就不止是三人小組,而是出動獸醫團隊、護士、工作人員及義工,共10至20多人候命。我們在野外設置帳篷作絕育場所,挑選年紀適合,健康狀況良好的野猴做手術。
行動那天,我們會先在捕籠裡準備食物,待平時入籠有素的猴子進入,便按下關閘按鈕。當大閘徐徐關上,猴子眾生相畢現。籠子裡的猴子意識到被困,有些會驚恐到瀨屎(失禁);也有猴子很輕鬆,依然在很chill地享受食物,因為牠們可能已經被捉過好幾次。至於外面的野猴,有些覺得我們捉了牠的朋友,不能丟下朋友不管,就在外面兇我們;也有猴子覺得不公平,不滿自己沒在裡面吃東西,就向我們咆哮。但牠們大多數都只是裝模作樣,不會真的衝過來。

為了令猴子沒那麼緊張,我們會用帆布蓋著籠子。大籠有個活門,待猴子冷靜一點,工作人員就在籠內推活門,把猴子推到另一邊,由大籠轉移至小籠,即是俗稱的『針籠』。這個籠裡面有間隔,猴子被夾扁,動不了,我們就替牠們打麻醉針。猴子秒睡,獸醫及工作人員把牠們搬到桌子,躺平度高磅重,做身體檢查,還杜蟲、打瘋狗症疫苗。
已經閹割、年紀太小、正在懷孕的猴子都不適合做絕育手術,只有適齡和身體狀況良好的猴子才會做微創的閹割手術。這個手術數分鐘就能完成,不論雄雌,都是伸入內窺鏡儀器,拿起其輸卵管或輸精管,剪走其中一部分,再在牠們的肚縫針,打止痛針。
在戶外做絕育行動並不是易事,在密封帳篷做手術十分炎熱。9月還可以很熱,獸醫出汗可流滿整個水桶,我第一次參與也差點熱到昏厥,喝了一支電解質飲品還覺不夠。我們也試過下雨繼續做手術,做到雨水滴進帳篷內,獸醫上司仍堅持做,但有時亦會放棄,改天再完成。
對猴子來說,一覺醒來,也許並不知道自己喪失生育能力,因為牠們的性器官全在,還能做愛,只不過沒有後代。閹割後,我們還會替猴子植入晶片,並為牠們紋身。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圖案,方便我們之後辨認。
紋身的過程也是要爭分奪秒,先是剃乾淨毛髮,再把墨水刺進皮膚,爭取在麻醉藥效還維持的時候完成。聽聞有同事試過在紋身的時候,猴子甦醒,突然坐在手術床上。但我們都不會害怕,只要懂得抓住馬騮腋下位置,牠們不會襲擊或咬到人;如果是十多公斤的大猴子,我們也可以叫義工幫忙,抓著牠們的四肢。
一隻完成閹割的猴子,肚子有一個紋身,兩個洞,牠們甦醒後即日就會放走。
有老人家聽到我們閹割猴子,可能覺得雄性猴子很可憐,聯想到清朝的太監,但我們已經是用最文明的方法控制猴子數量。想一下香港的野豬,以往政府的做法也是用閹,但現在已改為殺豬。

請不要對我直視5秒
絕育有沒有成效呢?根據基金網頁的資料,絕育計劃把本地野猴的出生率降低超過一半,從2009年超過六成降至近年低於三成。
但香港的野猴政策,除了絕育,還有加強公眾教育,嚴懲非法餵飼。但市民往往還是不知怎樣和猴子相處,非法餵飼問題也禁之不盡。我每天上山被幾百隻猴子圍著都沒問題,但有些市民見到猴子就鬧得很緊張,因為大家對猴子的認知程度不同。就算是人類,你都不想有人直視你超過5秒——如果不是愛上你,就是對你有敵意,所以我們也不應該跟猴子四目交投。
猴子會經常齜牙咧嘴兇人,但牠們都只是作勢,不會夠膽直接攻擊人。想像一下,牠們最重都只是十幾公斤,無論有多孔武有力,人類對牠們來說都是龐然大物。
政府當局視猴子是一個trouble maker(麻煩製造者),那麻煩的嚴重性怎麼衡量,就是看投訴數字,數字越少越好。但我覺得投訴多少不一定跟猴子族群的大小有關,反而是跟人類是否認識猴子,是否懂得和猴子相處有關。某種程度上,公眾對猴子這個物種很陌生,很好奇,但又很害怕,不了解。牠們沒攻擊你,但你覺得牠們在攻擊你,甚至還挑釁猴子,所以才有投訴案例。
比如說,我經常看到有家長帶小朋友去看猴子,喜歡在兒女面前做英雄,用棍挑釁野猴。正是有這些奇怪的相處,襲擊事件和投訴才會發生。
每逢漁護署收到市民被野猴滋擾的投訴,我們就需替投訴人捉猴子。我任野猴生態調查員時,城門郊野公園常常發生猴子襲擊人類的事件,我們便要安裝大籠嘗試捕捉猴子,再把牠們放回山上。但我懷疑,即使捕捉猴子,也治標不治本,只是暫時讓猴子遠離此地,根本的原因是猴子越來越多、越來越頑皮呢?還是人類對猴子的忍耐力降低,增加了人猴衝突?
在公眾教育上,香港可以做得更多,不單是呼籲公眾不要餵猴,而是可以仿效台灣獼猴協會那樣出版繪本,到學校舉辦講座,向公眾講解猴子的某個表情,不是代表生氣,而是害怕,減低因了解不足而造成的誤解和衝突。

不愁食物,飽食終日
香港管理猴子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野猴不愁食物。有「熱心」市民上山餵猴,也有行山人士經過會餵猴,實際上他們已觸犯了非法餵飼條例,我們會當面阻止。
野猴在大自然界有食物可吃。牠們是雜食性動物,會吃昆蟲,我們見過猴子捉毛毛蟲、竹節蟲來吃,但牠們主要吃素,花、果、葉都會吃,牠們有時嘴巴變黃,就是吃了大頭茶。如果大自然真的沒有足夠食物,牠們的族群就會變少,維持平衡,那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有「熱心」市民幾乎每天都駕車前往金山郊野公園餵猴,有些揹著一袋食物,有些揹著一個小腰包,前輩同事跟這些熱心市民搏鬥了十多年。他們認得我們車牌,我們也認得他們的車牌,但我們跟他們的關係只有「眼超超」。他們不怕我們,清楚知道我們沒有權利拘捕,即使我們報案,待執法人員到達,他們已經遠去。當然,大部人未至於猖狂到在我們面前餵飼,但我們遠處會見到他們餵飼。
我們也見過一位九十多歲婆婆,每天拉著一架小車上山餵猴,有位漁護署人員決定拘捕她,她說自己沒有身份證,只有老人院會員卡,漁護署人員無奈口頭警告了事。到2024年修例加重罰則,漁護署人員決定行動,她重施故技不果,工作人員便跟她回家拿身份證。即使最後署方發告票,她還是沒交五千元罰款,至於後續發展我就沒再跟進。就好像放生其實是破壞環境一樣,我們改變不了這群人的行為。
在一些鄰近山邊的屋苑,猴子也常常容易大快朵頤。比如在慈雲山那裡有個斜坡,很多街坊在那裡餵飼野狗,食物包括燒肉、乳鴿、臘味,雖然猴子不是餵飼對象,但牠們也會照樣過來吃。
除了明目張膽的非法餵飼,猴子也很容易在垃圾站找到食物,垃圾站常常被猴群洗劫一空。比起自然界的食物,人類濃味的食物對猴子來說吸引很多,牠們很喜歡吃零食和甜食,我就看到猴子吃巧克力棒,拿著雪糕在舔。即使牠們不懂開瓶蓋或用飲筒,也會咬爆塑膠瓶和檸檬茶盒,總之想盡一切辦法,品嚐想吃的食物。
垃圾站是人類興建的,我認為即使要興建,都要有特別設計,比如大型垃圾桶應該有緊閉的上蓋,令野猴難以直接打開垃圾桶取得食物。

在猴子身上看到人性
每天和猴子相處,我常常在牠們身上看到人類的原始性。
猴子是族群動物,很喜歡同伴相殘,不單對另一個族群會打,對自己人也會打,每日上班就像看古惑仔那樣。我們長期觀察,就知道誰是老大、老二及老三,老大的地位最高,有優先享有食物的權力,進入籠子的時候,其他猴子會散開,讓他先吃。
猴老大是經常欺負小朋友的。就算猴老弟沒有得罪老大,也會無緣無故吃猴老大一拳。為什麼?因為老大要樹立權威——我十天不打你,那你豈不是忘記我是老大?
但別以為當老大很容易,牠的地位並非無堅不摧,隨時隨地都會遇到挑戰。族群的大哥也會隨時被打,因此每天的老大都可以不同。有些被趕的,又會可以變成另一族群的老大;有些老大變老,則變得沒權沒勢被趕走。
雌猴也打得厲害,即使抱著子女在胸口,依然能來去自如,打得眉飛色舞。媽媽不會理兒子, 因為兒子有能力捉緊媽媽,所以媽媽會如常跑來跑去,跳來跳去,打來打去。
除了競爭,猴子之間也有合作的關係。食物面前,野猴傾向自私,但牠們也會「吹雞」叫同伴過來吃東西。每個猴群都有不同的聲音,有時候牠們叫同伴來吃東西,有時候則是召集同伴打架。
牠們會合作打另一群猴子,也會合作照顧同族的猴孩。除了親生媽媽,小猴也會有其他母猴照顧。有些樹有一堆小猴子,由一兩隻媽媽照顧,就像是託兒所一樣。

人類要解決自己製造出來的猴子問題
無論猴子如何顯露近似人性的特質,但人猴終究有別。這份工作讓我每天與猴為伴,我肯定對猴子有感情,想牠們好,有時亦欣賞牠們的可愛,但我們畢竟太不一樣。
我不認為自己與猴子的關係是「朋友」,我們難以建立真正的溝通。我會跟牠們說「別頑皮,別跳上來」,但牠們聽不懂,需要直接用動作表達,比如用手擋住,牠們才會明白。牠們認得我,親近我,但可能只是當我是一粒移動的大花生,出現的時候總伴隨一桶食物,而不是因為我這個人本身。大自然充滿不確定性,有一次我也不明所以被猴子攻擊,當時那隻猴子十分躁動,幸好我雖受傷流血,但傷口不深,我打了瘋狗症及破傷風針,就當是普通刮傷。
人類是要和猴子共存,但人也要解決猴子製造的麻煩,而這個麻煩的根源也是源自人類——那些亂餵猴子的行爲是人為的,所以就有絕育計劃,就有我從事這個工作。
我認為政府是不想猴子滅絕的,香港人亦不會接受。雖然公眾不那麼關注猴子,不像野豬那樣有關注組,但不至於想牠死。殺豬已經很多人罵,如果你殺的動物那麼像人類,又有完整的族群,我覺得社會是不能接受的。大自然總有漏閹之猴,所以這個計劃應該長做長有,可以穩定地做下去,但自覺未必有太大發展空間,後來我就離職了。
從行業的角度説,投身生態保育的人士中,很少人了解猴子,遠不及觀鳥或研究蝴蝶那麼普及和賺錢,所以我也很容易跟別人打開話匣子,算是某種優勢。回想起來,雖然在山上做野猴生態調查員很炎熱,但我享受在大自然工作,上班亦十分自由,時間彈性,大部分日子都能準時下班。
山野間的野猴,往往也比人類更容易相處和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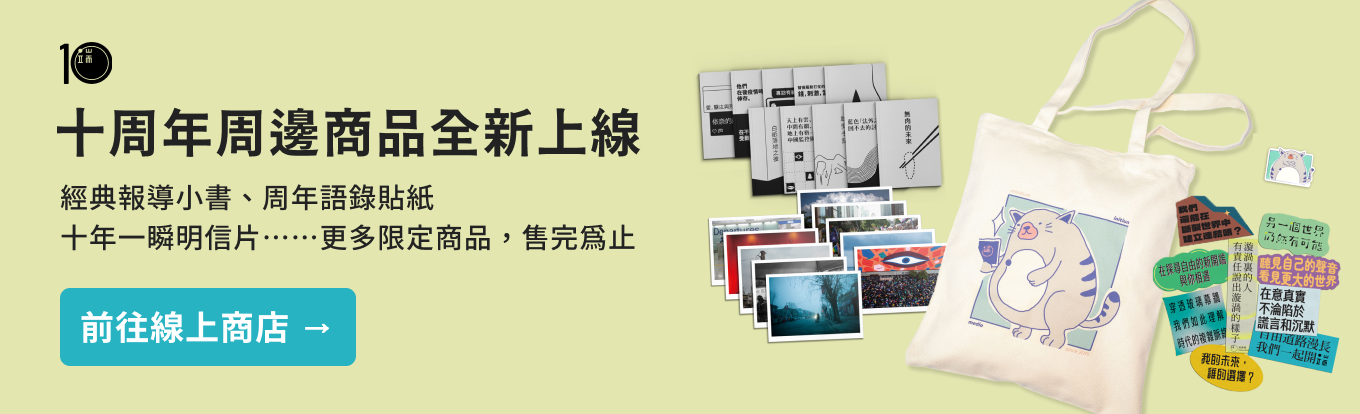



老人家聽到閹割猴子只心疼公猴不心疼母猴是甚麼跨物種厭女情意結?
照片拍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