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忠實觀眾們而言,屬於彼思Pixar的第一個影像,不來自任何一部正片,而是它的開場動畫:一盞金屬小台燈跳入空間中,踩扁了「PIXAR」字樣中的「I」(「我」),取代了它的位置,再一頓左顧右盼。許多年後,網絡上的創作者受此啓發,創作了這個鏡頭的反打:「我」看著小台燈一步一步地走來,接受自己的命運。這是彼思Pixar給我們的第一組難忘形象,並且已然在人類視角的邊界打轉:本該不動的物體擁有生命和律動,令字母變成一種物質,語言成為一種表演,一個狂喜的形象。彼思Pixar的故事正是由此開始:三十餘年的旅程,近三十部長片,我們見證了這間擅長無中生有的工作室迸發出各種想象,到近年,它的創造力卻在續集產出和原創作品中逐漸喪失,這是隨著時代走向的必然憂鬱,還是有什麼其它緣由?讓我們從頭說起。
這是彼思Pixar給我們的第一組難忘形象,並且已然在人類視角的邊界打轉:本該不動的物體擁有生命和律動,令字母變成一種物質,語言成為一種表演,一個狂喜的形象。
尊·賴斯達導演的《反斗奇兵》是第一部電腦渲染的三維動畫長片,上映於1995年,此時正值電影誕生百年。而30年後,無盡的虛擬影像正在世界中飄蕩,在此刻回望這一原點,一切都如此純真:彼思Pixar的初代創作者們攜帶著建造和破壞的雙重慾望,在電影中切割出兩個世界。所謂的「現實」維持著某種扁平的狀態,與此同時,電影深化出一個內部的宇宙,其中形象憑借自身存在的差異來創造社群和法則,也是這家工作室最完美的原型機:從玩耍出發,一位孩子立刻掌握了場面調度的基本形式,在臥室創造屬於他的類型電影(西部片、科幻片……),那麼,讓玩具們活過來則再「現實主義」不過。在《反斗奇兵》中,安迪一家是一個沒有全貌的畫外空間,人類如巨物一般存在,與此同時,作為表演者的玩具帶領我們重寫觀看的角度。彼思Pixar的機器是一個外世界和一個里世界的博弈,分別呈現為看似自動運轉的龐大體系,及其內部由人物團體組成的破壞力量,總是巧妙地在完成自己的遊戲後,又悄然回歸到體系中…… 一種家長與孩子般的關係?不止如此。

對於那一代受啓蒙的孩子們——如今或已接近而立——而言,彼思Pixar的影片最早地展示了關於物質的觀念,儘管它們的本質是虛擬的,但其中無疑存在一個電影的範本:如何將事物放大、放映出來。但是,若要追溯對影片感受的源頭,除了驚嘆外,或許更有這種放大帶來的原初恐怖。我們見證了巨大的皮球砸向塑料軍人、一盞台燈旋轉著將一台高科技玩偶踢落、被斬斷的頭顱或被錯誤拼接的身體、玩具城中無限陳列的巴斯光年複製品。被損毀、遺棄和取代的恐懼統治著電影——彼思Pixar作品的經典形式,是棄兒、怪物和收養家庭的故事。電腦動畫的不成熟帶來了充滿樂趣的矛盾體,因為電影人必須遠離對真實經驗的重現,而去製造滑稽的摹仿,如同孩子模仿家長的口頭禪,或是自己在電視上看過的圖像,這種輕快的非寫實性允許彼思Pixar將兩個世界,並將動畫形象一律當作「怪物」對待,通過一種倒置:當非人類的身體充滿情感的眼睛或尖端科技渲染的柔軟毛髮,人類也不介意帶上塑料的肢體及浮誇的五官。

所有的形象與其說是普遍印象中的「擬人」,不如說首先需要一種「擬真」,為了讓觀眾感受到材質。彼思Pixar因此創造了它們最精彩的矛盾:作為一件商品或附庸的悲哀,和作為一位朋友或陪伴者的快樂。真實永遠被放置在細微末節處,只是為了創造形象,而世界不過是各種形象的弗蘭肯斯坦式拼貼。繼安迪的玩耍啓發了玩具們的自主表演之後,《怪獸公司》比《反斗奇兵》更進一步地成為了一種場面調度的教學,正如法國《電影手冊》在當年的評論中精准地提到,怪物公司的發電術不外乎是一個電影院的比喻:「孩子——即觀眾——所發出的尖叫,由怪獸—演員的表演所激發,這種尖叫成為一種「收益」,支撐著這家工廠兼工作室的運轉,也養活了那些依賴它的經濟和藝術群體…… 從未有一部電影如此清晰地揭示:激發觀眾情感的慾望,以及這種慾望的異化(將觀眾視為一種可盈利的資源,是某種工業化情感剝削的核心),竟是電影作為藝術與工業的整個體系經濟存續的保障。」 從本片到《玩轉腦朋友》和《靈魂奇遇記》,創造「體系」是導演彼得·道格特的長處。然而,如果這一解讀將影片的外世界進一步刻畫為一個反烏托邦,影片卻從未陷入到負面情感的泥潭中,恐懼立刻化為了探索的力量,因為里世界早已從不同岔路中找到替代恐懼的方式,即笑聲,並從各種災禍喜劇式的表演中綻放出來。
被損毀、遺棄和取代的恐懼統治著電影——彼思Pixar作品的經典形式,是棄兒、怪物和收養家庭的故事。電腦動畫的不成熟帶來了充滿樂趣的矛盾體,因為電影人必須遠離對真實經驗的重現,而去製造滑稽的摹仿,如同孩子模仿家長的口頭禪,或是自己在電視上看過的圖像。
《怪獸公司》的瘋狂在於它不僅創造了一個自給自足的政治和經濟體系,也不斷書寫著各種即興式的大小形象,一些「只是怪物」的存在。它們的外表並無任何所指,不追求效率或效果,只會突然闖入來呈現差異,或是從速度和調性上改變影片的節奏,為此蘭迪·紐曼的爵士配樂如同電影的靈魂。彼思Pixar繼承了經典好萊塢的傳統,去拍攝工作中的人物的瑣碎流程,它對一項職業的樂感保持痴迷——身形修長、天生迅捷的反派蘭道,被「毛怪—大眼仔」團隊一大一小的組合速度擊敗。「怪物公司」的大樓儘管是積累資本的恐怖之地,卻意外滿足了我們遊蕩探索的夢想,它比我們認知中的更加龐大。無論是公司明面上的工位,還是老闆實施綁架的「管道間」,都只是待探索的一角。其真正的臟腑是「門廊」機器,那既是個密閉空間,也是連接著無限世界與深淵的大型樞紐。「門」是彼思Pixar作品中最出彩的概念,它恰如其分地成為了剪輯自身,那令人眩暈的通道系統集結了所有的速度。

因為「門」的存在,這裡永遠發生著對另一端的想象——人類世界再一次被扁平化,被壓縮在一位小女孩「Boo」身上(我們見過她的家長嗎?),我們會記得她門上的粉色花朵。由於「Boo」的闖入,已有的工作制就被換了個玩法,成為一片由隔板、槓桿和各種拐角所組成的汪洋——總帶著虛驚一場與真正的生命危險——廁所的抽水馬桶成了捉迷藏的開關,小怪物們排隊經過走廊,傳頌著「麥可·華斯基」這個名字,似乎只需要喊出其名,通過直覺的重復,她便承載了這個獨眼綠色球體的喜劇天才,而之後的《太空奇兵·威E》中,角色的名字也是情感的咒語,一種愛情的即視感。事實上,無論是瓦力豐富的機器聲,還是「Boo」的咿咿呀呀,它們都無需被翻譯,正如怪物的形象無需被解釋。但恰恰在這個集合了妙語與呢喃的差異地帶,「毛怪—大眼仔—Boo」的臨時家庭才顯得如此溫暖,這同樣也是玩具家族和《超人特攻隊》中家族的秘密,亦是《五星級大鼠》中老鼠對人類不可思議的「駕駛」之源。在彼思Pixar最好的作品中,怪物總是那個粘人精,但它從不自我投射,它需要的是同行人在其身上進行放映,這便是拍攝電影。
另一場「大與小的轉換」發生在《海底奇兵》中,它同樣用簡潔的線條勾勒了一個藍色世界,在此我們同樣遭遇到來自畫外的危險,捕撈船的底部在水下看似黑色的巨獸,隨之則是潛水員佔滿銀幕的巨大面孔。牙醫診所的水族箱和大堡礁似乎一樣大,馬林和多莉尋找尼莫的路線則猶如一本海底生物譜,冒險者要經過哪些海域、得到什麼生物的幫助,都有明確的軌跡,正如尼莫關停淨水器的步驟,在劇作和情感強度上都十分瞭然。然而,也正是這兩條被規劃好、並終將匯聚的命運之流,卻時不時從敘事任務上脫節,開始原地追逃、繞圈,得到短暫的遺忘和開小差式的快樂,這都得益於那條叫多莉的藍唐王魚。她的「短期失憶症」改寫了我們對魚類神秘記憶力的想象,多莉的記憶沒有固定標尺,它極具選擇性,和穿梭的節奏、情感的壓力有關,甚至直接反應為運動方向的轉換,而非心理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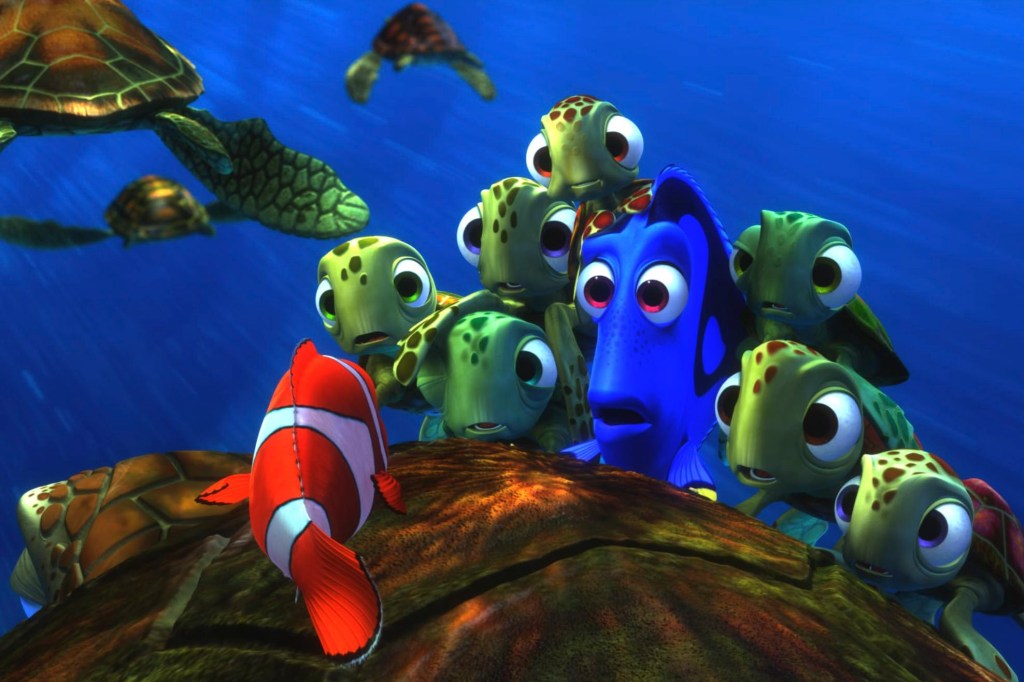
在無形的水中,多莉是一位不規則的舞蹈家,會創造出多餘的冒險,或加速故事的線性。和很多確保孩子或家長「不會跑出視線區域」的兒童電影相反,《海底奇兵》最迷人的時刻,是一片黑暗。透視消失了,看不見馬林的多莉給了對方一個新角色:「你是我的良知嗎?」 於是,它們帶著縹緲的快樂,游弋於死亡的領地並追逐它白色的小光點——在父母們緊張的頭腦里,身體下沈到一大片黑色中,將被視作「死亡」——又躲過鮟鱇魚的追殺,逃出此地。是的,彼思Pixar的角色雖然向觀眾保證了自身的不滅,但它們總是會超越警告,在龐然大物的跟前轉圈,或者誤入黑魔法:海淵、水母群、乃至一場即興的勇氣,它們都會導致目光的斷裂。
彼思Pixar的角色雖然向觀眾保證了自身的不滅,但它們總是會超越警告,在龐然大物的跟前轉圈,或者誤入黑魔法:海淵、水母群、乃至一場即興的勇氣,它們都會導致目光的斷裂。
生命的持續不在於角色的肉身是否頑固,而在於這些身體所承載的理念,以及推動虛構的信念。憑借它,多莉可以和鯨魚實現「溝通」,下水道將直通大海;而剪輯重置了角色面對距離時的潛能:「小丑魚爸爸尋子記」的故事通過生態圈傳播,成為民間傳說,從馬林講給小海龜們的趣事,一路演變成了帶給尼莫的童話。這是一股強大的洋流,而受其鼓勵的尼莫,立刻以自身的冒險接力了父親的傳奇,又一次咬著石子游向飛速旋轉的過濾口——甚至連成功的瞬間都未曾展現,因為速度在這之前已然成為了決心。

這場二十年多前的接龍,或許演變成了彼思Pixar近作《外星奇遇記》中的全球播報:為了拯救他們的外星朋友,一個男孩和他的阿姨乘坐飛船逃離地球上方的太空垃圾,全世界的天文愛好者都在幫助他們。這兩種烏托邦的建構都過分天真,但處理方式天差地別:《海底奇兵》用形象間的跳躍,壓縮了海域上下不可能的距離,小海龜到處溜達,兩條劍魚一邊擊劍,一邊將故事娓娓道來,形象的組合里,總是有很多莫名其妙、又理所當然的滑稽;《外星奇遇記》則在主角之死的威脅下,對坐標進行了無限度的膨脹,支援的聲音來自北歐還是來自亞洲,都沒有區別,語言失去了神態,孩子們復讀著統一的目標,組成一片迅速推升、迅速燃盡的網絡。當劇作向自動化投降,彼思Pixar也創造了一部刻板印象里的「生成AI電影」。
《外星奇遇記》則在主角之死的威脅下,對坐標進行了無限度的膨脹,支援的聲音來自北歐還是來自亞洲,都沒有區別,語言失去了神態,孩子們復讀著統一的目標,組成一片迅速推升、迅速燃盡的網絡。當劇作向自動化投降,彼思Pixar也創造了一部刻板印象里的「生成AI電影」。
《外星奇遇記》「與時俱進」地給予了我們幾種AI模型:「全能語言翻譯機」、克隆體、窺視鏡…… 但形象已然消亡,無論是外星種群的形態,還是這些全能機器的本體,都呈現為史萊姆狀的粘土團,而其終極形態則是家長眼中的「完美孩子」。它們是最完美的功能性角色,既能抹除所有差異,又能讓人於瞬間發現問題,甚至還會表演身體恐怖;一旦問題解決,這些複製品就可以毫無眷戀地揮別、死去。早期彼思Pixar堅持著一個原則:如果你不把一塊史萊姆看作朋友,你就不會有任何朋友。因此,你必須創造出這位朋友獨立的生活方式,而不只是將其視為現實存在的變體;那麼在此時,這家工作室已陷入了情感危機,它認為,史萊姆是該被捏回去的。和輕易死亡的克隆體同理,當艾力歐邁出星際聯盟、回歸地球的那一刻,那一大堆「外星小生物」作為創傷替代品,也都會在頃刻間失去意義,因為在這裡,地球和外星共用一套劇作經驗,一切怪物,都可以被主角的心理機制所消化。

這種心理機制的出現,顯然要追溯到《玩轉腦朋友》的成功,這個在當時或許顯得激進的靈感,改寫了彼思Pixar的方程。從這個時刻開始,彼思Pixar電影中的怪物無一例外成為了一些具體形態的替代品:人類的情感、生老病死(《玩轉極樂園》)、文化和種族(《熊抱青春記》、《元素大都會》)、身份政治(《反斗奇兵4》、《超人特攻隊2》)、靈魂以及創造力本身(《靈魂奇遇記》)——電影熟練地為這些事物創造了對應的機制,然而當我們一眼便識破背後的主題,形象似乎也一並消失了;與之對應的是,技術愈發強大的彼思Pixar難以抵擋還原真實世界的誘惑,也就意味著去講有「現實感」的人類經驗,而沒有誰比彼思Pixar更明白如何操控情感。
因此,《玩轉腦朋友》是它最恐怖的自畫像。儘管它保持著喜劇的表面,影片的憂鬱氣息仍然無法阻擋,形象因此也成為了某種急救者,在一個情感愈加混沌的時代中艱難地為觀眾指引方向,將其簡化為五顏六色的球體投影和腦內的小精靈。事實上,觀看這部電影的治癒效果,或許是在離開影廳後,觀眾能自己在腦內想象它們,恢復擁有「想象朋友」的感覺。這裡依舊存在一些關於電影本身的思想,但一個愈加深重的危機也隨之而來,當電影淪為一種偽裝的心理療癒,而抵達它的方法則是拋棄人與怪物分離卻陪伴的關係,並將一位小女孩變為實驗品和提線木偶,儘管它真誠地告訴我們要讓悲傷和喜悅同行。「怪物公司」從未如此高效,而製造「電力」的力量不再是笑聲,而是憂鬱與鄉愁的眼淚。

這些近作無疑都更深層次地被裹在家庭關係中,但留下來的不會是馬林與多莉的長途跋涉,更像是一群完美家長的焦慮,正如《超人特攻隊2》中超能先生令人哭笑不得的帶娃時間,這些場面的真實反而強化了面對真實的疲態,將節奏和速度從影片中抽走。彼思Pixar的「中年危機」,如同將想象力黏成一灘漿糊,它們不再被列舉:《外星奇遇記》中有太多含混不清的可愛事物,除了艾力歐那些高度無害、且沒有自保能力的「想象朋友」們,還有那艘飛船,它的按鈕錯亂紛雜,但除了駕駛鍵和定位鍵,其餘的娛樂項目都一閃而過,彷彿掉進了一片散髮甜味的亂碼,就算是完成了對瘋狂的理解;而在駕駛飛船的途中,由於宏大使命的壓迫,連玩耍的機會都被壓抑了,所有的飛船都只留下了單一的功能。
當我們一眼便識破背後的主題,形象似乎也一並消失了;與之對應的是,技術愈發強大的彼思Pixar難以抵擋還原真實世界的誘惑,也就意味著去講有「現實感」的人類經驗,而沒有誰比彼思Pixar更明白如何操控情感。
與此同時,隨著這些虛擬理想國的功能化,「現實感」在銀幕上充分地展示技術的權威:《靈魂奇遇記》中驚人的紐約市風光,讓人難以想象作者花了整部影片的力氣(以及一整個反面的抽象宇宙),去說服人們生命的美麗;《玩轉腦朋友2》則在萊利的臉上畫出「精准的演技」,它像是一台偽科學機器,會自我解剖,分析每個局部微表情,而任何腦內世界的異動,都將帶來面部的調節,內外世界由此高度同頻;《外星奇遇記》則強調了大人臥室與孩子臥室的隔絕,但,隔絕必須被抹除,艾力歐的床頭擺著一張他和「理想父母」的合影,他的披風、孤獨的海灘、他的專屬語言,都反射著這份現實陰影的面積。所以,語言不僅要被翻譯,還要被家長學習,他的沙灘、星際通訊器也必須被體驗。
回想一下馬林和尼莫的分頭冒險,以及安迪媽媽清理玩具的習慣吧,在那些由更簡陋動畫所製造的小房間里,每個人的習慣都得到了保持。有時,學習是一種遙遠的同步,也有時,理解從未真正發生。《海底奇兵》交織著兩段歷險,卻從未讓它們相互注視,對方的處境是無法想象的:馬林面前只有大海;尼莫所面對的是一片玻璃和一座假山。但這對父子各自結識了新朋友,奇異的友誼與自身使命共存,促使它們學習到玩耍和獨立的方法、放鬆的方法。本片之所以能成為一部理想的公路片,就是因為馬林不得不放下已有的經驗,去接受原創經驗的挑戰。友情和孩子氣是無根的東西,它牽著失憶而狂喜的多莉,在魔法陣中跋涉。

再次贊美《海底奇兵》,它先於那些「寫實主義之作」,探討出了應對創傷的方法,從一位父親的恐懼,到集體魚類對船隻的恐懼,給出的啓發卻很簡單:去學習交朋友。以此為例,我們會發現早期彼思Pixar的故事,總是以朋友為單位,一對截然不同的朋友、一群搭檔,組成了家庭最深層的形態,真實是個摸不著邊的混沌體,在我們看不見的角落,無機物也散髮著存在的靈暈,而兩個形象的第一次相觸,就形成了友情。有個普遍的認知可以證明《反斗奇兵》與我們的友誼形式,即所有的形象都是演員,「草莓熊」只是上演了一出復仇故事,巴斯光年只是被切出了一個西班牙浪子的版本。一位演員是可持續的,在電影故事之外,ta還有更神秘的生活態度,我們無法想象這份神秘,就像演員會為了觀眾的愉悅,一次次裝扮自己、走進類型,演員絕不可能被用完即棄。《反斗奇兵3》第一次讓彼思Pixar意識到了童年的逝去,但它不僅給予觀眾這些人物在面臨死亡時奇跡還生的可能,還有另一種「不死」的思想:「土豆先生」與「土豆太太」是這個家庭最傑出的性格演員,他們的五官被無數次拆出,錯放在不可能的身軀中,卻依舊是他們本身:當「土豆先生」被安置在玉米餅上,他的特技超越虛擬的肉身,透過徹底的形式達到頂峰。
永生是對形象的詛咒嗎?在《反斗奇兵3》的結尾,安迪把他的玩具朋友們交給邦妮,並向她一一介紹了它們,在經歷了一整部電影的類型穿梭之後,我們又回歸情節劇的院落,認識每個人的肖像,這幕戲是整個短暫童年的縮影。玩具的交接發生在十五年前,在我們與彼思Pixar相識三十年的中間點,角色們不說話,用眼睛創造著規則。十五年後,當彼思Pixar試圖自我庇護,艱難地追趕著一個偽造的現實,唯一戴著永生枷鎖的,就是那盞小台燈,它是一個被流放的演員,對面沒有銀幕,只剩下對記憶的誤解。




寫得很好 文筆也無問題 是我們看慣了某種語言方式? 還是對外行人來說較難理解當中概念?
确实小小辛苦
作者嘅文字令人睇到好辛苦
這篇文章我需要餵給AI才能理解作者在寫什麼。表達太混亂了,像夢囈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