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1941-2025)先生数日前于香港养和医院逝世,在众多纪念他的评论中,都绕不开连他自己都不承认的“才子”称号,以及因他自身经历和言论的种种矛盾而引起的不同误解。
更遑论从香港本身的文化记录角度出发,据笔者回忆,四人走红的时期及晚至九十年代,在社会普遍层面,其实并不存在把蔡澜、金庸、倪匡和黄沾并列为“香港四大才子”的说法。作家沈西城曾指出,由金庸、倪匡、蔡澜“三大才子”发展到包括黄沾的“四大才子”说法可能产生于2008年以后,而也是在此前数年,笔者在中国内地便听说有此讲法,故此个人结论这称号的源头极可能是源于中国大陆,并于0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 。
但这“四大才子”的说法在后来乃至当下如此普及,以至香港民众也普遍接受,如理解它是作为一个“外来”的概括称号,则能以他者观点,从旁看出了一点香港流行文化和广义上的香港文人的特色——这个界定“香港式才子”的过程,某程度上,也同时是在界定香港流行文化之本色。
蔡澜(1941年—2025),香港美食评论家、作家、电影制片人,及饮食节目主持人。籍贯广东潮州,生于新加坡,大学于日本留学,毕业后定居香港。其于文化界交游甚广,与金庸、倪匡、黄沾三人相熟,且并列为“香港四大才子”。1989年至1990年间,蔡澜又因与倪匡及黄沾一同主持亚洲电视经典成人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广受观众欢迎,三人被传媒并称为“香港三大名嘴”。
“香港四大才子”是一个反过来由中国灌输进香港的称号,它产生的背景有独特的香港文化与其时中国大陆文化发展的辩证性质。
风花雪月的背后
围绕蔡澜的最后话题,之所以能引起关注,也引起更新一轮悼念期过后的批判(如批判他的通俗浅浮、渣男逻辑,及曾监制多部带剥削性的三级艳情片等),而又跟纪念倪匡及黄沾之笔墨如此不同,原因是蔡澜并不以经典传颂作品传世,反而是他那种闲云野鹤的任性及一直输出的“我活过”人生观,最能打动人心引发共鸣。
显然,普通人不可能像倪匡、黄沾那样,高产出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但如果真的能放得开,却勉强能成为蔡澜。表面上他是几位“才子”之中最贴地的,身上包罗的并非宏大的家国情怀两岸潮或异星奇想,而是活生生的饮食男女享乐主义。
然而这个由风花月雪组成的蔡澜宇宙,其内核又不止这些。在淡然嬉笑,颂扬躺平的表象背后,公众看不出他的真假。他享乐的背后是对世界不满作出抗衡?还是在嬉笑天下之间若有所指?前半生活得风流,婚后真可从一而终?这种种矛盾与模糊,使他充满魅力,对男女关系以至酒色的沉溺热爱,若放于今天更是不合时宜。
他发表的偏见,既有文化又够市井;爱得丰富,又情感专一;试图从传统中挣脱,但又保有高度老派风范。一切都只能出现于其赖以成名的年代,那种香港著名的混杂文化精髓,也是最后的风流一代。
他发表的偏见,既有文化又够市井;试图从传统中挣脱,但又保有高度老派风范。一切都只能出现于其赖以成名的年代,那种香港著名的混杂文化精髓,也是最后的风流一代。

占据大陆“才子”称号想像
我们从蔡澜那些不分真伪的生命哲学与男女八卦中,也许满足了一种旧时代对“才子佳人”的想像。这得从“才子”与“佳人”的角度讲起。就如先前所说,“香港四大才子”是一个反过来由中国灌输进香港的称号,它产生的背景有独特的香港文化与其时中国大陆文化发展的辩证性质。不要忘记,九十年代是港式流行文化大举“北伐”的黄金年代,因港式作品的通俗性,同时也惹来不少批判,由金庸到四大天王都成了一时的评击对象。
但无可否认,香港出现的这批正值影响力盛年的创作人才,真情流露又充满跨界特色,和中国大陆地区其时的文化名人形成巨大落差,适时“占用”并重新定义了中国传统中对于“才子”的想像。在其时中国的语境中,当代“才子”缺失,要不,就要上溯至民国时期如梁思成徐志摩一代,故而其时出现的受欢迎的香港男性创作人,即暂时占据了“才子”的位置。
这同时也解释了四大才子名单中,是如此不恰当地把金庸也并列进来的原因:那其实就是一个当其时,中国内地对他们认知中稍知名的“香港文坛名家”的集体名命。
“才子”在传统文化想像中,没大师、名家那么严肃,而是更多生活化和情感牵动,甚至常常和“风流”这形容一并使用,这使得它在当代理解中,有了一种多才多艺而入世的文化身份特色,也像今天的著名斜杠创作人。
这种入世在蔡澜身上,通过各种传闻渲染,形成神话。除了多姿多彩的情史,也包括他的仗义——例如有说当年香港办日本电影展,早年没互联网资料,寄来的物料都只有日文。策划人急找翻译,有人提议找蔡澜,可那是个没有手机的年代,如何最快找到?于是江湖传说就是他们到尖沙咀据闻是蔡澜爱泡的酒吧碰运气,终于真的在其中一家找着正喝得半醉的蔡澜,而他真可以一边继续喝一边把文字译出。蔡澜的传说常带这种场景感。
既然其时这些香港名家在大陆来势汹汹,当人们要找到标签香港流行文化人的符号时,没有什么比改一个近似“四大天王”的称号更为方便。这解释了在电视节目《今夜不设防》最为走红的九十年代初(1989-1990播出),香港整体上对“四大才子”之称号闻所未闻,反而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到千禧年香港文化大幅进入中国大陆之后,才慢慢流行起这一称号。
这同时也解释了四大才子名单中,是如此不恰当地把金庸也并列进来的原因:那其实就是一个当其时,中国内地对他们认知中稍知名的“香港文坛名家”的集体名命。这四位才子,分别创作了中国大陆其时没有充份发展的文类,分别是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粤语流行歌词和饮食文章。

可以大展拳脚的香港
这四位香港才子毕竟有共通点,也呈现了一些香港地道的文化名人特色,就是他们都通过媒体曝光达致高知名度,作品跨界,身份众多,“杂家”是其中的共通特质。所以金庸和倪匡已可能是当中身份最单纯的,金庸最重要当然是创办《明报》的报人和武侠小说作家(也一度是电影编剧),倪匡是科幻小说作家、编剧、专栏作家,两人主要还是以文字创作为主;但黄沾和蔡澜就跨界得多,蔡澜更是身份最多变复杂,由作家到美食评论、饮食顾问和企业创始人、电视电台节目主持、社交平台内容生产、电影监制、翻译,不一而足。这些都是我梳理香港流行文化赖以成功之要素时,归纳过的几项特质使然:
七十至九十年代,香港社会具有极强的流动性,适逢文化媒体广告产业初代发展盛世,产出天马行空不受限的想法和表达,表现在香港影视创作上则是一种“咁都得”(这样都可以?!)的精神。时机上,这时期香港流行文化身为强势,客观条件是建基于对比同期大陆和台湾,香港乃最自由开放之地,兼具市场输出力,处于地理文化位置上的总枢纽。香港像块极具诱力的磁石,把各方人才和资本吸引到来。
他由新加坡到日本,而后主要定居香港,就更是香港一度作为华人人才流动中心点的典范。在此大背景下,才把握得到蔡澜的流动性所带来的,局外人笑看人生宇宙的哲学。
来了香港,在此大展拳脚,就是香港人,就是香港才子。金庸、倪匡皆非广东人,到香港后才学粤语,黄沾和蔡澜倒是广东文化背景,但四人都不是香港出生,黄沾在广州,蔡澜在新加坡。若集中讨论蔡澜的话,他由新加坡到日本,而后主要定居香港,就更是香港一度作为华人人才流动中心点的典范。
在此大背景下,才把握得到蔡澜的流动性所带来的,局外人笑看人生宇宙的哲学,他强调的半生追寻人生意义,最终相信吃吃喝喝,对酒色财气风花雪月毫不遮掩的赞颂,说实在也是一个香港时代的普遍价值。这种特质,后来再为香港壹传媒的媒体出品放大,形成一种港人普遍对“不扮高深”、要活得自在真诚的人生观的夸赞。

生活艺术指南?
李渔的《肉蒲团》中,读者可能难以分清作者是在享受书写欢愉,还是真有影射社会的志趣。这形成了拆解蔡澜宇宙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只不过蔡澜这种可能源于中国传统中才子形象的云淡风轻,为这份逍遥更添了一种传统的文化衬托。电影制作上,蔡澜作为监制不算十分有成就,有段时间在邵氏较清闲,制作成龙电影的成功可能只因顺着了成龙其时的风头。若论较为代表性的创举,则是在三级片当道的九十年代,开拍古装艳情片。他是曾以《肉蒲团》作灵感,制作艳情电影的跨界者,尽管结果是,蔡澜并没有拍成改编自《肉蒲团》的作品,把“肉”改成“玉”的《玉蒲团》系列制作者另有其人,蔡澜作为监制并取得成功的,是另行开发的《聊斋艳谭》系列。
这样一位跨界者,不会奇怪坊间会将明末清初的才子李渔跟他类比。似乎李渔笔下的“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我忧”在蔡澜的文字宇宙中,确实有点当代回响。他不同系列的小品,由讲饮食旅游到电影幕后与明星秘史,确不乏《闲情偶寄》的风范,如果林语堂称李渔此作为“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那么起码三十年来,华人读者圈也有不少把蔡澜的文字当作“当代中国人生活艺术指南”来仿效。
李渔的《肉蒲团》中,读者可能难以分清作者是在享受书写欢愉,还是真有影射社会的志趣。这形成了拆解蔡澜宇宙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一个声称“草草不工”的文人,而他练字其实又如此勤奋,他的人生是真的“草草”吗?
在眯著眼含蓄微笑的背后,他四十年前于中年时就表达出自己向来是feel sad的矛盾。就连在他潇洒的言语和表述之间,在一些足够长时间、以致可以终于捕捉到他某些短暂情绪瞬间的访问中,还能看到他对于个别问题的不置可否,或避而不谈。而也有不少文章,过多强调了他那些爱情经历的传奇性,略少提及个人的反思和内心处境。

久美子的中国想像
例如提到年少在新加坡时期,他搞大了女孩的肚子,这在当年或者不算小事,但他只以“后来不了了之”带过。到日本时期,最传奇的、也由他自己写过的,是跟比他年长五年(蔡澜本人也记错为八年)的日本女诗人村冈久美子的关系。这段往事过去因只得他文章记述,单方之言未免惹人疑问,但刚好最近法国《PURPLE》杂志由久美子女儿Anna Dubosc出土的故事和图片却为此补上一笔。
杂志刊出的照片,拍照人是蔡澜留日时好友黄森(Richard Wong),证实了那是蔡澜所说的1964-1966年间的东京,他曾在给亦舒的文字中写道:“一天,久美子忽然向我说要到她一生向往的法国去了,我当然祝福她,并支持她。我送她到横滨码头,她上了船到西伯利亚,乘火车到莫斯科,再飞巴黎。记得当年送船,还抛出银带,一圈圈地结成一张网,互相道别。”
蔡澜文章中提及的去横滨送船时的银带,今次有了《PURPLE》照片实证更令人难忘,还有二十多岁时青葱的蔡澜那表情,侧面令读者某程度上相信了他的记述并非夸大。但一生人能有一段这种深情已看来值得,而蔡澜怎么就像经历了几十段这样的深情?他是如何可以在几十年的经历中,每一段都看来付出那么深?(他还有其他如把另一女友的骨灰撒到世界不同嘉年华会的故事)。这个,单单用他回亦舒的一句:“我不轻易爱一个人,但只要爱上一个人,会爱很久很久。”就可解释?
这种既多情又长情的矛盾,本质上仍有念旧的老派,可能在这时代确已不合时宜。倒是那种极力追求一种亲身体验的实证精神,令蔡澜的文字虽距离经典创作很远,却不乏独一无二的“过来人”神采。
而说他那些年来交过的从南洋日本韩国到拉美的女友,若说他是以此作为一种对不同生活可能的探寻,尽管跟他向来强调通过走天下来认识及选择合自己生活方式的说法吻合,但今天看来,也正回响着是男性将女性个体身份族群化、面谱化及物化的批判。
事实上,这论点也是研究身份界定时恒常出现的角度:就如杜哈丝(Marguerite Duras)小说中爱上的,往往是“中国北方情人”,也就是一个中国情人形象,而非那个个体本身。讽刺的在于,在蔡澜和日本女友久美子的关系中,蔡澜也可能变成一个出生在中国哈尔滨的久美子,对中国的想像 。
这种既多情又长情的矛盾,本质上仍有念旧的老派(久美子的故事,结局是过了近四十年,他从黄森口中得悉久美子已住进巴黎近郊安老院,于是前往探望,此时床上的久美子已认不出他),可能此刻确已不合时宜。倒是那种极力追求一种亲身体验的实证精神,令蔡澜的文字虽然距离经典创作很远,却不乏独一无二的“过来人”神采。

我活过
这神采在他更被传颂的饮食文字方面尤显特色,这也是单从文字创作而言,蔡澜还能占一席位的原因。一方面,他以日本经验、对日语熟悉及日本人处事方式的了解切入,既带知识又具趣味,不仅在尤其是日本菜的介绍和评价上作出了华语世界的新突破,更创新了美食书写的关注点,由单从对食材和厨艺的评介,演进成一场带故事性的文化冲突,和对何谓“美食”的价值新评估。
在蔡澜饮食文字风格之前,再上一代的香港饮食文字倾向食物和掌故,要不就是文笔古雅,要么就是个别“鳝稿”(软文宣传稿)充斥,欠缺蔡澜笔下的爽快与喜恶分明,也较少对中国菜以外的引介 。蔡澜对食的追求,是近似武侠小说中“手中无剑”的境界。问他自己做晚饭要准备什么食材?他说,不需预备,那天早上到街市看,看到什么自己喜欢的就要什么。
在一片关注食材营养价值的潮流中,他独排众议,推荐充满罪恶感的猪油饭。在一篇被不少美食爱好者奉为经典的小文中,他把顾客和板前师傅的相逢比喻成一场决斗:
“寿司绝对坐在柜台前吃才过瘾,眼看玻璃长柜,选新鲜和合自己胃口的东西吃。
切生鱼的人叫板前样,外号快刀二郎,客人的生死,掌握在他手中,算账没有一定的规格,全凭他的喜怒哀乐。通常是叫埋单的时候,他的庖丁尖刀在砧板上轻轻划几下,叫出个夸大的价目,要是他看你不顺眼,使用刀大力地割,就变成天文数字了。
当然,你可以说老子有钱,管他娘的。不过这种待刳的态度太消极,我们一定要将二郎打倒才爽快。从门口走入,直闯柜台。忽然背景昏暗,雷电大作,抛起巨浪,快刀二郎的眼中闪出凶光,我们面对著他,眼看就是一场生死的大决斗⋯⋯接著由我们出拳:指著鸡蛋块,叫:‘撮’TSUMAMI。寿司的做法不外两类, 一种只是切片,用手抓来下酒,便叫‘撮’;另一种是肉片下加了饭团,叫‘握’NIGIRI。这是基本招,一定要学会发音⋯⋯不管你多么喜吃寿司店中较高贵的食品,如鲍鱼和云丹等,你一定得先尝一客‘金鎗’MAGURO,它是最普遍的生鱼片,客人以此为基石。
快刀二郎可逮到机会了,他拿出一大块金鎗鱼,切那黔黑的次等部份回敬你一记。我们也只好吃下这一棍,但即叫甜酸姜片来涮口,表示反抗。姜日语叫‘SHIYOGA’,却千万不能直言,而须用寿司密笈的口诀‘我利’GARI。到了这个阶段,快刀二郎已经知道你的段数不小,不敢再出阴招。”
短短板前的接触,既有实用日语调教,又有应有态度的输出,复见对好坏的判断,而且现场感十足,也就是美食书写后来崛起的体验加知识性文笔的典范。这是“我活过”精神的一种体现,其另一个意思就是我经历过。

若说金庸后期立场转化,黄沾败于晚期放弃坚持,惟倪匡一如既往,蔡澜就始终是游于各种力量和价值之间的局外人。这令他能一边在大陆发展餐饮和社交平台,又同时和香港一度风光的广义民主派,其时仍存在的自由媒体,及政界人士,打成一片。
“他们香港人”
所以放到由倪匡、黄沾和蔡澜主持的传奇电视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中,三位历炼和人脉那么广的名人,所卖的就是任何一位当红明星,上到节目皆得尽情分享,哪怕是被视为敏感的题目,因为他们三位过来人会给到这些独特经验以智慧唱和。张国荣在节目上谈初夜,记未红时的遗憾与介怀。许冠文分析无厘头的由来。在1989年开季不久的五、六月一辑中,所有主持穿上黑衣服一改谈笑风生,转而说到家国情怀,彼此过去的相关经历。
解读蔡澜,另一好奇点正是在几位才子之中,他在广义上的政治立场最为回避不明。可能是他的容量和坚持不取态都比别人强,足够令他可以避开选择(新加坡社会政治和李光耀看来是他另一个想少提的话题)。如果说金庸后期可能毁于过度关注历史留名而有立场转化,黄沾也败在晚期放弃过往的坚持,只有倪匡一如既往,那蔡澜就始终是那位游于各种力量和价值之间的局外人,这让他可以在中国大陆发展他的餐饮业务和社交平台,但同时仍能跟香港一度风光的广义民主派,无论是其时仍存在的自由媒体,还是政界人士,都打成一片。相信是他非常晚期的墨宝写着“风骚老板娘”,悬挂在台北刚开业不久的“红棉”私房菜餐馆。
到最后,有限生命中在香港生活得最长久的蔡澜,他虽以“香港才子”见称,但他又属于哪里?他口中仍会以“他们香港人”作形容。他最后一篇见报的专栏文章,在公布死讯后两天于香港的报章刊出,题为〈香港最适合我 让美好留在回忆〉,内容主要写义大利美食之行,不知是否有心作出此时此刻此城比喻,文章这样结尾:
“旅游的意义,在于比较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然后挑选自己最合适的。到最后,我还是觉得香港最适合我,西西里再好,去过一次,让一切美好留在回忆里,足矣。”
就如电视荧幕上的清谈节目,今天再不可能出现边喝酒边抽烟及随之而来的爆料与任性。一位一线明星如果在节目中爆出各种过界猛料,翌日就可能面对人设死亡。也许更重要是,今天在这城市中,再说风流才真的是不合时宜。这也使蔡澜及所属那风流一代更成绝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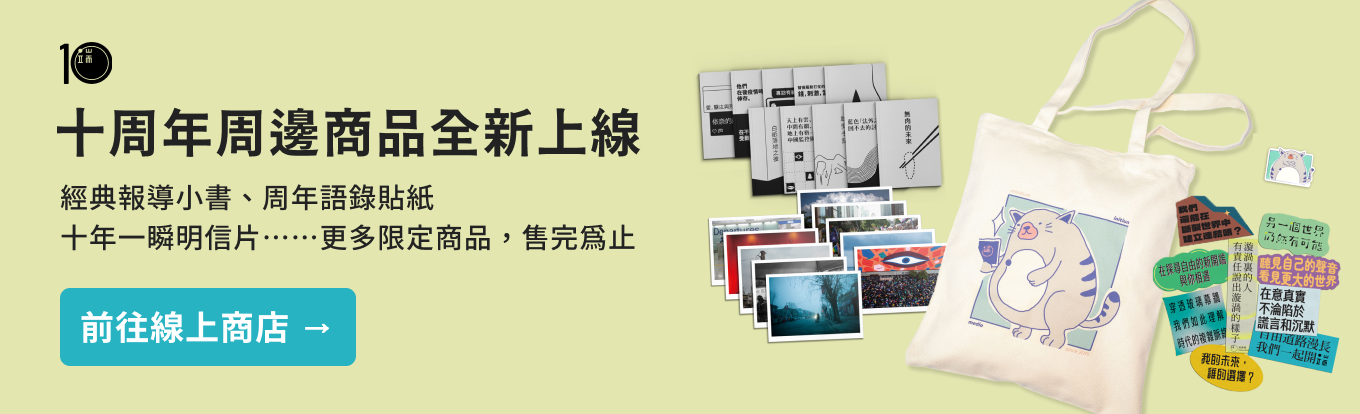



“也許更重要是,今天在這城市中,再說風流才真的是不合時宜。這也使蔡瀾及所屬那風流一代更成絕响。”Well said.
蔡瀾其中一個願望,是開辦妓院。
讀過蔡瀾早期文章,文字很多沙石,句字不通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