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是一个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诞生的政治共同体概念。不过,从这个时代开始,人们就有着“五服制”、“九州”和“四海之内”等多种不同的“天下想像”。“五服制”更多地被使用于说明天下的政治秩序,在涉及统治关系时,无疑更多使用的是“九州”和“四海之内”;而在“九州”和“四海之内”二者之间,又更多是使用后者。出现这种异同的原因,就在于天下思想原本是一种关于统治正统性的理论。或者说,天下思想就是先秦时期各个王朝,尤其是周王朝时期,为了说明统治正统性而制造出来的理论。
“五服制”、“九州”和“四海之内”三者之不同,表面上看来似乎在于对天下结构理解之不同,但其实质却是对需要接受统治正统性的对象范围理解之不同。“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论礼》)既然是“天下”,就必然要包罗万物万民,这里就不可能只生活着一个血缘民族集团,或数个彼此之间具有血缘关系的民族集团。因此,主张统治正统性的理论根据,最终必须是地缘主义而不是血缘主义的;既然是“天下”,那就不可能只有王公侯伯子男等统治阶层而没有万民,周天子也就不可能只考虑统治阶层的利益,而无视作为被统治者的民心。
因此,作为统治正统性理论的天下思想,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其实就已决定了它必须是以追求最大公共性和普世的价值为最终理论根据的。迈过血缘主义走向地缘主义,不是重视统治阶层利益而是以民为本的“四海之内”的天下想像,无疑比五服制和九州的天下想像更能体现这种精神。换言之,“四海之内”的天下想像之所以出现和被广泛使用,说明当时的人们理解到“天子”的统治正统性应该得到天下一切民众的认同。
人类不可能赋予自己绝对权力:“天子”与“天命”
因为天命说的诞生,统治者事实上自己拒绝将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当成是一种不受任何制约的、至上的绝对权力。
一般认为,“天子”一词诞生于周代。虽然《孟子》和《史记》都称尧、舜为天子(注一),但都属后人追记。在《尚书.夏书.胤征》、《商书.说命.上》和《诗经.商颂.长发》中也可以看到“天子”一词(注二),但是因为夏代尚无文字,《夏书》肯定也为后人所追记;《商书.说命》也被指属于后人伪造的“伪古文尚书”类;而关于《商颂》成文于商代还是春秋甚或战国年代,也是众说纷纭。
也就是说,即使将人间最高统治者看作“天”的代理人的意识产生在商代(注三),根据对现存文献的考证,明确提出王是天之子嗣的“天子”一词,应该始于周代。故日本学者贝冢茂树指出:“到了周王朝时,王是天帝之子即‘天子’,是一个将天上‘帝’的意志传达给地上人间的仲介,这样的观念巳很明确。《尚书.召诰》篇中的‘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一文,是说殷作为皇天的元子即嫡子的命令被天帝取消,才是殷亡国的理由。这种认识,应该是在殷人原有的观念的基础上,被周人更加明确地意识到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天子”一词不论是出现在哪种场合,它被提出来时,总是与天命和天下联系在一起的。如《尚书.周书.洪范》中:“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周书.康王之诰》亦记载:“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
“天子”一词的出现,意味着天下思想在理论上的成型。在各种周代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天、天命、天子、天下”四者既构成了人类社会与天神之间关系的自上而下的四个层次,也是构成天下思想中四个最基本的要素;而这四个基本要素,又围绕着德的思想互相作用,从而编织出一套解释王朝之更替、统治者为什么上台和为什么下台,即说明统治者为什么能够得到或失去统治正统性的理论。
简而言之,按照“天下思想”的说法,王朝之更替、统治者的上台和下台,都是依照天命而行的。也就是说,统治正统性的直接来源就是天命,而天命即“天”的意志。因此,要想真正理解天下思想的构造,必须从理解天与其他三者(天命、天子、天下)之间的关系开始。
从《尚书》中可以看出,先秦时期文献所记载的由“天”发出的“天命”,都是与王朝交替有关的。例如成汤(商汤)在讨伐夏桀的出征式上宣誓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书.汤誓》)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66年)在伐殷前所作的《泰誓》中亦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
值得注意的是,《泰誓》记载周武王不仅说周伐商是因为接到了天命,并且认为当年商汤伐夏的起因亦是接到了天命。“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尚书.周书.泰誓中》)也就是说,至少在周武王时,历代王朝交替的原因已经与“天改变了意志(天命)”连在了一起。
值得强调的是,在先秦时期中,“天命”的话语只是出现在最高统治者的王以及王朝更替的层次,换言之,“天命说”只是一种针对最高统治者即王朝和天子更替而诞生的话语。例如“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史记.五帝本纪》);“文王,克明德慎罚……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尚书.周书.康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尚书.康王之诰》)
可是,商纣王也主张自己是“吾有民有命”(《尚书.周书.泰誓上》),当年“剥丧元良,贼虐谏辅”的夏桀亦是“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尚书.周书.泰誓中》)那么究竟天命站在哪一边呢?那就只能在战场上见分晓。前朝庞大的政权机器顷刻土崩瓦解,证明失去了天命;新朝的正义之师所向披靡,说明它有了天命:“(商纣)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戎商必克。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尚书.周书.泰誓中》)可以看到的是,胜利者并不愿意将胜利归因于兵强马壮,反而更愿意强调他能够以少胜多。因为这样他才能证明自己“以尔有众,厎天之罚”,他是在替天行道。
将王和王朝的更替说成是来自于天的意志即天命,无疑首先是出于强调其统治正统性的目的。但是许倬云先生曾经就“天命说”诞生的意义,做过更加令人深思的分析:“西周早期曾有过辩论,究竟天命是降于周人还是降于周王?如果降于周人,这一天命观念就不过是将周人看作选民,正如犹太人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一样,不容易发展为一个普世的观念。然而西周的选择则是天命降于周王,王者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能实现这个盼望,王者就会失去天命,这是一个道德的理念,将政治的权利和普世性的道德有了必然的关联性。”(注四)
因为天命说的诞生,统治者事实上自己拒绝将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当成是一种不受任何制约的、至上的绝对权力。因为这种约束是一种对其道德的约束,所以通过王命说而产生的制衡权力机制具有普世性的价值。
是“同心同德”还是“离心离德”:“天命”与民意
因为“天命”源于人民之所视、之所听、之所欲,堵住了民众的嘴的统治者,绝对不是一个真命天子,因为他的做法直接破坏了天命的源泉,在他的身上当然不会出现天降大任的天命。
从天命说中可以看到,天下思想的发明者同时给“天”赋予了两种性质。第一是天圆地方的“物质的天”,因而能够涵盖天下万民万物;第二是神格化人格化的“天”,先秦时期亦称之为“帝”。它不但具有绝对强大的力量,同时毫无私利私欲、不偏不党,因此具有判断是非的思维能力和意志。周文王甚至能够通过做梦和占卜得到天命,说明当统治者用天命来说明自己的统治正统性时,并不是将天子作为一种冥冥之中的抽象物质,而是将天解释为是一种实际的存在。因此,天子必须敬重上天,其实就是要时刻意识到:“天子”,不过是一个由“天”选定的“天下”管理人而已。
《尚书.周书.泰誓中》中有记载:“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注五)天子不仅要绝对聪明,被天选为“天子”的最重要条件是道德的条件。“德为圣人,尊为天子。”(《中庸》);“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圣人?《诗》曰:‘文王受命。’非圣不能受命。《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汤武与文王比方。”(《白虎通德论.卷六.圣人》)天子非圣人莫属,这一思想被后人所继承,如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亦说:“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汉书.董仲舒传》)
《荀子.正论》更直接指出成为天子的道德标准:“天子者,埶位至尊,无敌于天下……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震动从服以化顺之。……故天子生,则天下一隆,致顺而治,论德而定次。”在荀子的眼中,“德”成为了一个社会确立秩序的根据,而在庄子的眼里,“道德”又是一切社会良知循环生成的基本元素:“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庄子.外篇.缮性》)
只有具有高度道德意识,做为道德楷模的人才能够接到天命,与“天”之间建立起一种如同父子般的信赖关系。天命说之所以重视德的问题,目的在于使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统治的正统性,手段却是把德解释为来自于天的一种属性,“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尚书.酒诰》)。至于统治者的工作仅仅就是替天行道,替天行德而已:“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尚书.周书.泰誓下》);“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尚书.周书.梓材》)
后人将德解释为王道,也就是作为统治者要遵守的根本原理。“德之有也,以道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新书》卷八,道德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天命说的思想,不是统治者因为接到了“天命”所以要实行德治,而是一个统治者是否实行“德治”,是他有无接到天命,即是否真正是一位被天选中的天子的证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夫是之谓天德,是王者之政也”(《荀子.王制》)
。
因为目的在于向天下万民说明统治的正统性,所以在天命说中,“德”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具有非常具体的行为标准。这一点从《泰誓》中就可以看到,周文王在当时已经把“德”具体为重“民欲”、“民视”、“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泰誓上》)这句话清楚地点明了“天”与民,即“天下”之间的关系:天最重的不是天子而是民。如果要想接到天命,就必须秉承天意,仁人惠民:“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尚书.周书.泰誓中》)
周文王甚至提出一个是要“同心同德”还是要“离心离德”的命题,其实质就是要强调,作为一个统治者必须明白天命来自民意、民心的道理。因此,表达民意的渠道必须畅通;一个统治者要想证明自己的统治具有正统性,即接到了天命,就要尊重和满足民众之所视、之所听、之所欲,而不是蒙住民众的眼,不是蒙住民众的耳,不是让民众没有一点思想。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因为“天命”源于人民之所视、之所听、之所欲,堵住了民众的嘴的统治者,绝对不是一个真命天子,因为他的做法直接破坏了天命的源泉,在他的身上当然不会出现天降大任的天命。这是一个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被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普遍理解和广泛接受的公理。
“革命”的理论:民主主义之前的统治正统性装置
作为制造统治正统性装置的革命思想却并不一定要求发生暴力行为,它更像是一把永远悬在统治者头上、让他时刻警醒的正义之剑。
毫无疑问,“天命说”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天命”源自于民意,因为天之最爱是民而不是天子。因此孟子才列出了这样一个至今都为民众所深深向往的政治秩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
东汉王符更是明确提出,天为民而立天子,天子为民而生:“太古之时,烝黎初载,未有上下,而自顺序,天未事焉,君未设焉。后稍矫虔,或相陵虐,侵渔不止,为萌巨害。于是天命圣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佥共奉戴,谓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潜夫论.班禄》)统治者之所以称自己为天子,也就是说他们承认自己的统治只是替天帮助天下黎民百姓不受暴政侵害的一种形式,因此,一个统治者要想取得统治的正统性,也就是天命,就必须时刻站在保护民众及其利益的立场上,注意民心民意。
“革命”的思想是构成天命说的一个有机而重要的成分,因为革命的思想是一个要求统治者时刻不忘尊重民意的装置。按照天命说,改朝换代就是“革命”,即天改变了衪原有的意志,而决定另外寻找新的、能够执行衪的思想之人,为新的天子。由夏到商的“成汤革命”如此,由商到周的“殷周革命”也是如此。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革》)《逸周书.月解》称:“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易民之视,若天时大变,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注六)
但从以上也可以看出,天意变来自于民心变。按照“天命说”,“革命”的发生既是一种天意,更是一种民意,或者说,天的“革命”意志的产生,其实就是对民众意志的反映。因此,所有的新统治者也都愿意将自己的“顺天革命”说成是顺应民意:“周将伐商,顺天革命,申谕武义,以训乎民,作武顺、武穆二篇。武王将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于众,作和寤、武寤二篇。”(《逸周书.周书序》)
也就是说,从“天命”到“革命”,“天命说”的思想本身就是以“民”为本展开的,这一点不仅从“天命”源于“民欲”、“民视”、“民听”的思想中看出,还可以从“革命”同样源于民意的思想中得到反映。正因为如此,革命都会被强调为发生在统治者践踏民意、实行暴政之时,目的都是为了“除民之灾”,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尚书.多士》)
源于失去民意、起于暴政之时、追求救民保民的这一“革命”思想,也为后世所继承。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是在哪个时代,“革命”多是与“德”,即统治者的素质问题一起被提出来的。
“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尚书.多方》)“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寔始,斯乃虙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龚行天罚,应天顺民,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后汉书.列传.班彪列传.下》)“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保此怀民。”(《汉书.转.叙传.下》)
统治者之所以失去民心,就是因为失“德”,而统治者失“德”就必然会失去民心,已经失去替天行德能力的现任统治者必然遭到民众抛弃。“天命说”告诉世人,“革命”的行为虽然是由“天”实施的,但是“革命”的真正源头却是民心。而“天命说”中关于“革命”的思想进一步强调:对“民”实行的“德治”才是一个统治者取得正统性的最终根据,因此也是天下思想理论构造的核心。
革命的思想让民众有了对幸福生活的幻想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动机,因为它告诉他们民众自己永远有可以要求公平公正待己的权利。“天命”源自于民意这一深刻的思想,让先秦时代发明出来的“革命”思想,事实上成为了中国自古至今一个制造统治正统性的装置和再装置。
不过,作为制造统治正统性装置的革命思想却并不一定要求发生暴力行为,它更像是一把永远悬在统治者头上、让他时刻警醒的正义之剑。正是因为革命思想的存在,才能够促使或逼迫统治者对自己的行为反省,对自己违反民意,即人性和人权的行为有所收敛。
天命说针对的是最高统治者而不是针对人民,革命的思想其实是一种让人民可以监督最高权力、让最高统治者受到道德制衡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思想不仅不是造成社会混乱的因素,反而恰恰是一种让社会保持稳定的动力。无疑,“革命”的行为可能会伴随着社会的动乱和暴力,但它只会发生在最高统治者失去民意、实行暴政之时;而从天命说的观点来看,这种革命的过程又是一个统治正统性再装置的过程。
许倬云先生对“天命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西周发展的天命观念,在当时是一个超越性的突破。”因为西周的选择了天命降于周王,让王的责任显得清晰,让“政治的权利和普世性的道德有了必然的关联性。”(注七)正像韦伯所分析的那样,任何时代的任何政权都必须具备某种统治的正统性,否则它最终难逃崩溃的命运,这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规律。
因此,在实现民主主义的选举、保证民众意志可以自由表达,从而使民意得到普遍反映的政治体制出现之前,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否定革命思想对统治者的监督和道德制衡价值。因为即使在非民主主义的社会中,统治者也需要找到统治正统性以维稳自己的统治,而要让民众真正接受其统治正统性,通过高压和镇压的手段是绝对做不到的。但要让统治者意识到实行仁政的意义,除了让他们对革命保持畏惧之外,民众还能有其他什么手段呢?
(王柯,日本神户大学教授)
注一: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史记.五帝本纪》)“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孟子.万章上》
注二: “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尚书.夏书.胤征》)“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商书.说命.上》)“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诗经.商颂.长发》)
注三: 在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上建树颇多的贝冢茂树,认为这种意识始于商代的占卜:“用卜询问天帝意志是殷王的特权,它意味著殷王就是天帝在地上的代理者”。同贝冢茂树前书,145页。
注四: 许倬云《王道,仁道,人道》,《王道文化与公义社会》,台北:中央大学出版中心,远流2012年9月,30页。
注五:亶,实在,诚然,信然。
注六:《逸周书》初写作于春秋,但是其中亦可看出后人加工的痕迹,如改正朔,易服色,三统循环说等,应是来自于西汉董仲舒的思想。
注七:许倬云《王道,仁道,人道》,《王道文化与公义社会》,台北:中央大学出版中心,远流2012年9月,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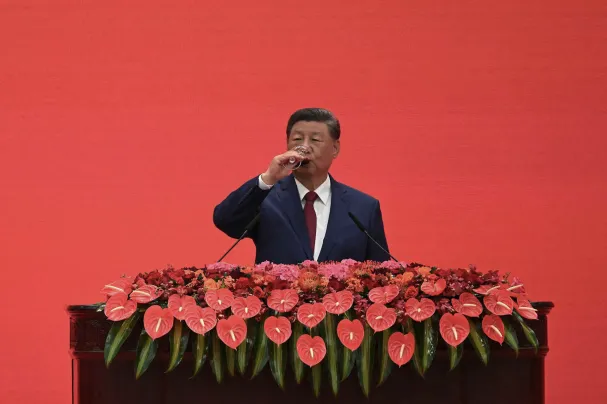
這裏的上古當然是指,夏啓之前的部落聯盟時代。而聖人就是聯盟的首領。已有的文獻肯定都是後人所著,但這並不意味着後人就是僅憑自己的腦洞瞎編的。
打漏字了,補回:
上古聖人又是怎樣的上古?記載的文獻到底都屬後人追記還是真的能證明是上古傳統?
什麼叫「華夏傳統」?是說夏朝嗎?作者不是解釋了嗎?
//一般認為,「天子」一詞誕生於周代。雖然《孟子》和《史記》都稱堯、舜為天子(註一),但都屬後人追記。在《尚書.夏書.胤征》、《商書.說命.上》和《詩經.商頌.長發》中也可以看到「天子」一詞(註二),但是因為夏代尚無文字,《夏書》肯定也為後人所追記;《商書.說命》也被指屬於後人偽造的「偽古文尚書」類;而關於《商頌》成文於商代還是春秋甚或戰國年代,也是眾說紛紜。//
上古聖人又是怎樣的上古?記載的文獻到底都屬後人追記?
民本思想,本就是自遠古以來的華夏傳統,並非周朝的發明。而「天子」則是由上古的聖人制度演變而來的,也不是周朝的發明。另外,「天命」是儒家的概念,墨家提倡「天志」,道家講「天道」,三者並不是一回事。對歷史的研究,僅靠看得見的文字和文物是行不通的,還要對看不見的文化傳承有所把握才是。
簡單來說,當今中國既沒有民主的制衡力量,也失去了這種自古有之的「天命說」思想的道德和革命制衡力量,幾乎只能靠統治者自行良心發現。
即便是现在,祖先的智慧与道理依然无人能比。而现在的中国,离下次革命的时间正越来越近
此文值得收藏细读。
没有经学功底,不敢贸然评价。不过如果作者对“天命说”的阐释是可靠的话,那真不啻为在中华帝国意识形态的后院里掘出了一方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