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学家Michael Mann的《民主的阴暗面》是影响我最深的其中一本书。我和很多有理想主义底色,自认关心社会正义的人一样,自小相信民主虽非万能,但也是最能确保人类幸福的政治制度。但可恶的Mann在我青春年少时,把我的信条一条一条撕个粉碎:他说服了我,现代民主一天走不出国家的框架,demos(公民共同体)与ethnos(族裔共同体)就永远都分不开,意味著国族主义既能催生民治理想,但对于公民身份的限制又会带来对少数的压迫,以至清洗。
打开各种媒体,巴勒斯坦的新闻好像证明了这一点。吴海伦在端十周年系列“人类命运不共同?”的开篇中讲了一个故事:美国犹太学者、记者Peter Beinart一直都是自由派锡安主义者,支持两国方案、提倡在作为犹太国家的以色列国旁边,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作为历史巴勒斯坦地区内的阿拉伯人的家园。但在Beinart亲自前往西岸、见证了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基础设施后,他在2020年在《纽时》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不再相信一个犹太国家”的评论,公开与锡安主义运动决裂。他终于发现,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民主国家”两者可能是矛盾的,一个又自由又民主又是犹太国家又不压逼少数的以色列,只能存在他的幻想之中。他的结论是,一国方案是唯一的解法:“我们是时候去想像一个犹太人的家园,而不是一个犹太国家。”
这就是Mann说的,公民共同体和族裔共同体的矛盾。但这却又是现代民主的本质。人们总是说,“以色列是中东唯一一个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tic)国家”。这话现在说来颇为讽刺,内塔尼亚胡身上背负几宗贪腐案,而打仗转移国内视线,简直是威权国家巩固政权的playbook 101。但以色列的确普遍被各种民主指数列为“民主”,长年的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隔离和压迫,并没有让以色列的民主考核不合格,因为公民权利﹑人权﹑法治﹑安家乐业的可能性,的确给到了那些拥有犹太血统的“公民”--即便他们可能来自美国﹑俄罗斯﹑欧洲,别说自己,连祖上不知几多辈都没踏足过这块土地。

现在加沙已两年战祸,连月饥荒,而且以色列自战争之始已杀害超过270名记者。为甚么没人出手阻止?我读过一篇曾参与调停1994年卢旺达屠杀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军官的回忆,他指西方国家当时拒绝出兵阻止屠杀,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关心非洲人的生命:“我们只需要静观其变,让他们彼此厮杀几个星期,然后再进场收拾残局。”结果屠杀“果然”只维持了100天,期间卢旺达死了近一百万人。这个军官讽刺说,如果是卢旺达境内的350只大猩猩被杀戮,他们还更有可能出手介入。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有“共同体”出现,同时出现的,就是被排除在共同体以外的人。《美国独立宣言》起草时高喊“人人生而平等”,但平等的只有白人有产男性而不是女性和非洲奴隶;今日欧盟的盟歌是高举博爱和人类团结理想的Ode to Joy,但仍然容许逃离叙利亚战争的难民溺毙地中海。
我常常在想,对远方的“观众”而言,那些戴著头巾,肤色黝黑的巴勒斯坦人,可能跟游戏里的NPC差不多,更别说是甚么人类共同体的一员了。这些都是打开Netflix见不到的人:我们见不到他们牙牙学语﹑读书考试﹑暗恋同学﹑谈恋爱﹑初吻﹑初恋,和朋友闹翻,为读医还是读文学而跟父母抬杠﹑毕业﹑失恋﹑结婚﹑中年危机﹑婚姻失败﹑生大病……我们见到的永远只是被“误炸”而奄奄一息的记者的尸体,或者在拿救援物资时被开枪射穿头的青年,或被断水断粮饿得面黄肌瘦的小女孩。同是人类,我却无法说我们和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人的条件”(human condition)。学者Judith Butler提出过“可哀悼性” (grievability)的概念:不是所有生命在全球媒体语境中都被视为同等“值得哀悼”的。有些生命因为不被叙述、不被视为“完整的人生”,从而变成“ungrievable”。在我们的时代,巴勒斯坦人就是被排除在共同体外的人,而这不单是政治权力的结果,当中还有媒体人﹑说故事的人的一份。

“人类命运不共同?”系列的作者们聚在一起聊天时,都忍不住说:“天天都想世界毁灭,怎么想像共同体?”“每篇文章都好难以比较积极的方式收尾。”我第一次读吴海伦的初稿时跟他说:“你最后有很努力end on a high note, good effort。”他说:“很可能失败了,但总要试一下。”我说:“由它失败吧。”我想大家心底里都明白,作为一个对于他人的痛苦有基本同理与感知的人,要去认真地探究这些问题而不陷入虚无犬儒,都只好学会自嘲和为自己解套。而失败是必然的。难道要一个人去平反世界的忧郁?
而我也已经很久没有去过西亚了。几年后不知还会不会有“巴勒斯坦”。在设计“人类命运不共同?”系列时,我们的评论编辑雨欣问过我,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是共同体的一部分。是她问了我才想起,在我一个人走过西亚的土地的时候,那些戴著头巾,穿著长袍,肤色黝黑的人,是如何跟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分享他们仅有的一切。在一无所有处,当人撕下所有标签﹑面具﹑身份地位后,我们才最能窥见彼此的人性。
这些偶尔的,无心而短暂的交会,比一切又伟大又光明又正确的,被正经八百地印在某些镶著金箔边的文件里的政治语言,给过我更多的希望。正是因为知道那些希望在人世最低处,我不崇拜盛大辉煌的阅兵仪式,也不像领导人们一样渴望长生不老,我想这也算是普通人的道德勇气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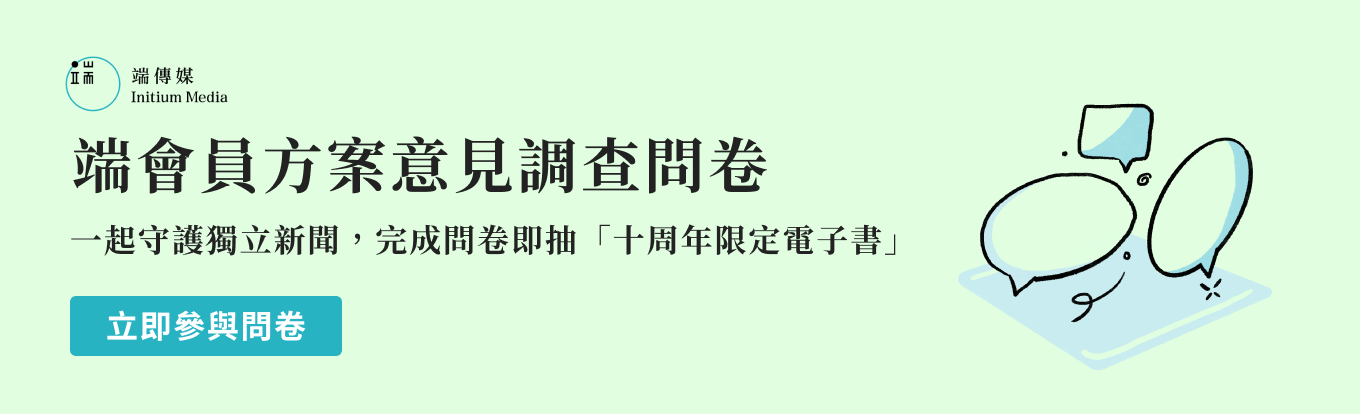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