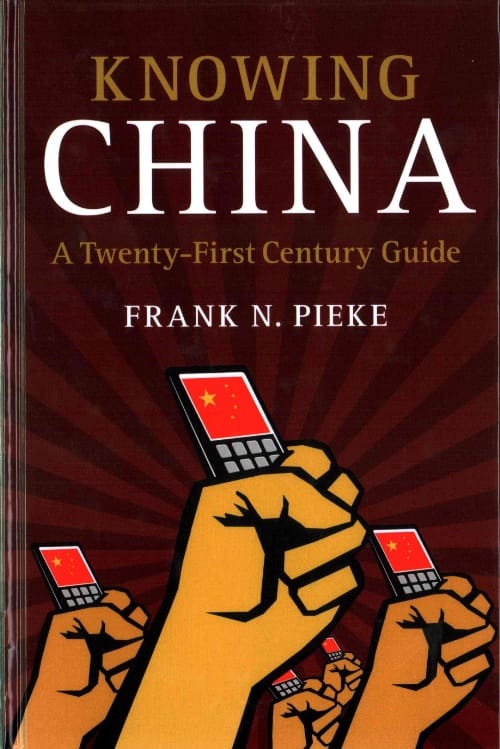
1957年出生的彭轲,早年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曾长期任职于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现任荷兰莱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当代中国教授。主要学术方向包括中国共产党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等。在新书《Knowing China》里,他希望跳出学术圈,对更多读者讲述他几十年来观察的中国社会变迁。
端传媒近期专访了彭轲,探讨了“新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执政目标和管理手段的变化,以及它未来可能面临的最大危机。

Frank N. Pieke指出,为了存续而奋斗是共产党的基础,但它也一直有“比自己还大”的目标,以前是阶级斗争、共产革命,今天则变成古老的“救国”。为达到这种目标,共产党正在走向精英化与官僚技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