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中风景]如果把我的浮光掠影中国大陆记行,当作一本小集邮册……
有一次我到杭州,他们安排我在一艘船上演讲,那艘船是在京杭大运河上的两个码头跑,可能是想重演当年宋代大运河上航行的情景。我当时缺乏这一趟航行的思古幽情预设的想像,胡里胡涂想像那就像在我这十几年“打书生涯”,在各种小书店里谈创作的小景框小讲区,只是它(这个想像的小咖啡屋、小书店)是在河流上跑罢了。
这个设计,我觉得挺有些马奎斯长篇《爱在瘟疫蔓延时》的结尾,阿里萨和费娥米纳这对睽违了五十年的老情人,在那条内陆河上跑着,过去的一生皆历历如绘在这样的航行中,像透明薄光的幻灯片,在流动中被召唤、重叠、百感交集。我觉得这特浪漫。
那主办人前一天,提示我,因为这是在杭州,看我的演讲能否围绕着“白娘子和雷峰塔的故事”,和这个景致有关联。
“谁?”我一时没弄明白。
“白娘子啊,白素贞啊,我们中间有一段,经过的河道,会眺望到雷峰塔啊。看您能不能说些有关的典故。”
“好,没问题。”我说。
湖光山色在我们四周,像电影播放着。来宾们也不是我习惯的小书店文青,是一些年纪和我相近或较我年长的大叔大婶。他们脸上都带着悠闲、明亮的郊游流光。
那晚我在旅馆里,脑中约略跑了一轮可能的题材。我是这么想的:白蛇传基本上是个人妖恋、变形记、动物变态成人形而无法得到人间情爱的忧郁故事。于是我想了几个和这“变形记”相关的桥段,遂安心睡去。
但第二天上船后,我发现我的想像和眼前那空间的气氛,好像有误差。它不是个我习惯的“咖啡屋或小书店空间”,船舱内座位的排置,有点像电视剧中战国主公和群臣的酒宴,我坐前方主桌,来宾们分据两侧的桌位,我们的桌上都放着一杯精致青花瓷盖碗茶的西湖龙井,一些果脯和小甜点碟。游船的引擎声和舷侧被水波拍击的响声极大,舷窗外是河岸风光,我们看去可能是天际线被各大楼楼盘切断,间错一些淡灰的小山,但主办的那位女士会不断的提点,在古代这里是什么所在,是什么历史景点。湖光山色在我们四周,像电影播放着。来宾们也不是我习惯的小书店文青,是一些年纪和我相近或较我年长的大叔大婶。他们脸上都带着悠闲、明亮的郊游流光。我应该不是拉住大家专注力的进行一场,关于“变形记或人兽恋”的演讲;应该在这轻轻晃动的明亮河上空间,说些历史掌故、穿插一些短笑话、思古之幽情的说说白蛇传。
但我当时脑袋没转过来,就切进了原本准备的讲稿之中。
他的父母在寻回失去的爱子之后,发现他们面对一更无能为力处理的“失去”:他们的孩子已长成一青少年的外形,但内在是一头北极熊。
我先讲了小说中,一些关于“动物变形成人类,或人类变形成动物”,那个移形过渡的换日线,半人半兽的暧昧状态(其实这是我喜欢的题材,想想火影忍者的漩涡鸣人,那恐怖巨大的查克拉,源自被他父亲封印在他腔腹里的九尾妖狐啊)。我讲起一部爱斯基摩人的动画片《男孩变成熊》。一个小男孩在婴儿襁褓时,被一只母北极熊闯入他们的冰屋抱走。他的人类母亲悲痛欲绝,陷入忧郁。另一边,那头母熊把他当一只小熊那样照顾,同时训练他“如何成为一只成熊”:如何捕捞冰下的鱼、如何猎杀海豹、如何孤独在雪原上生存、如何躲避人类猎枪的搜捕。他把北极熊的母熊当自己的妈妈,把另一只小熊当自己妹妹。有一天,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他的人类父亲(骑着一台雪地摩托车)终于找到了他,而且射杀了那头母熊。把他带回家。那之后是个悲惨的认知混乱的过程:这男孩认为自己是头熊,无法重新融回人类的生活,他的父母在寻回失去的爱子之后,发现他们面对一更无能为力处理的“失去”:他们的孩子已长成一青少年的外形,但内在是一头北极熊,最后他们怕他跑掉,还用铁链拴着他。而在另外的场合,男孩遭遇人类青少年同伴的霸凌羞辱、在混乱中他意识进入“北极熊模式”,把那些青少年全重创痛击。然后他奔跑回空旷的雪原,他向一洞窟里的山神祈求,想变成真正的熊。那神祇说出一古老的,人类男孩变成熊的考验:一,你要承受海洋里最残酷的激流。二,你要承受雪原上毁灭一切的暴风。第三个最难,你要忍受最痛苦的,天地之间无可依凭的孤独。如果能通过这三个考验而还活着,那就可以蜕变成一头熊。第一关男孩差点被溺死,是海中的鲸因古老的传统,救了他。第二关,男还差点被那飓风扯碎,是雪原上的牦牛,因古老的祖先训示,而排列成墙,护挡住他。最后一关,是这种“变形记”最美,也最让人虚无畏惧的一段,在那巨大的孤独里,属于人类的最后一点灵光,分崩离析,像穿过死荫之境,男孩终于变成一头北极熊了。
当代所谓中国人,其实灵魂的内在,早经过了过去一百年来,那整个西方,或“现代”,像钻地机穿凿、炸开里头难辨其原貌的,各种羞辱、伤害、要让自己变成不是自己,或有一天发现想变回自己……
我发觉船上的听众们,在这样原本预设进入“古代中国时光河流”的船舱内,被我讲的内容,弄得颇困惑。我又讲了墨西哥小说家富恩特斯。卡洛斯的《奥拉》,极美的一篇穿梭那移形换影之缝的小说。透过历史素材,死去老将军的札记、日记、信件,这个年轻历史学家困在一幢殖民时期的颓圮老豪宅中,发现那个精灵般的美人儿奥拉,其实是那委托他写亡夫老将军传记的老太婆,那关于她自己青春美丽时期的执念,最后非常魔幻的发生的时光吊诡的“变形记”(我努力拉回:那在中国,就是白蛇传的欲力啊)……
我隐约发现我串连这几个“变形记”,其实后面有一个“当代所谓中国人,其实灵魂的内在,早经过了过去一百年来,那整个西方,或‘现代」,像钻地机穿凿、炸开里头难辨其原貌的,各种羞辱、伤害、要让自己变成不是自己,或有一天发现想变回自己……,那一切的镶嵌、碎片插在我们的内在各处。我们现在的船是机械动力,我们看到的河岸风景其实已是全球化所有城市的楼盘地产商的地貌,我们口袋有手机、我们喝着这盖碗茶,但真实的感性,想像,其实是已经变形了的这个现代的时间分格、商品环伺、移动的便利、所有媒体的讯息残影闪烁在我们脑前额。我们可能更接近能体悟白娘子的困苦,而非许仙或法海的稳定自我感吧……
我感到气氛变得僵固,一种说不出的迷惑与尴尬。船这时到了回返点的一处码头,暂停泊让大家下去拍照。我自己站在船尾抽烟,为自己说不出的将这一航程,带进一稠状昏暗的叙事情境而生闷气。但那些大叔大婶是些非常好的人,他们先三三两两在我身边拍照,然后和我攀谈。跟我聊这杭州种种个人的经历,打烟给我,说我怎么这么年轻,原本听名字以为是个老头。还抓小孩来和我合照……
(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为《有一次我到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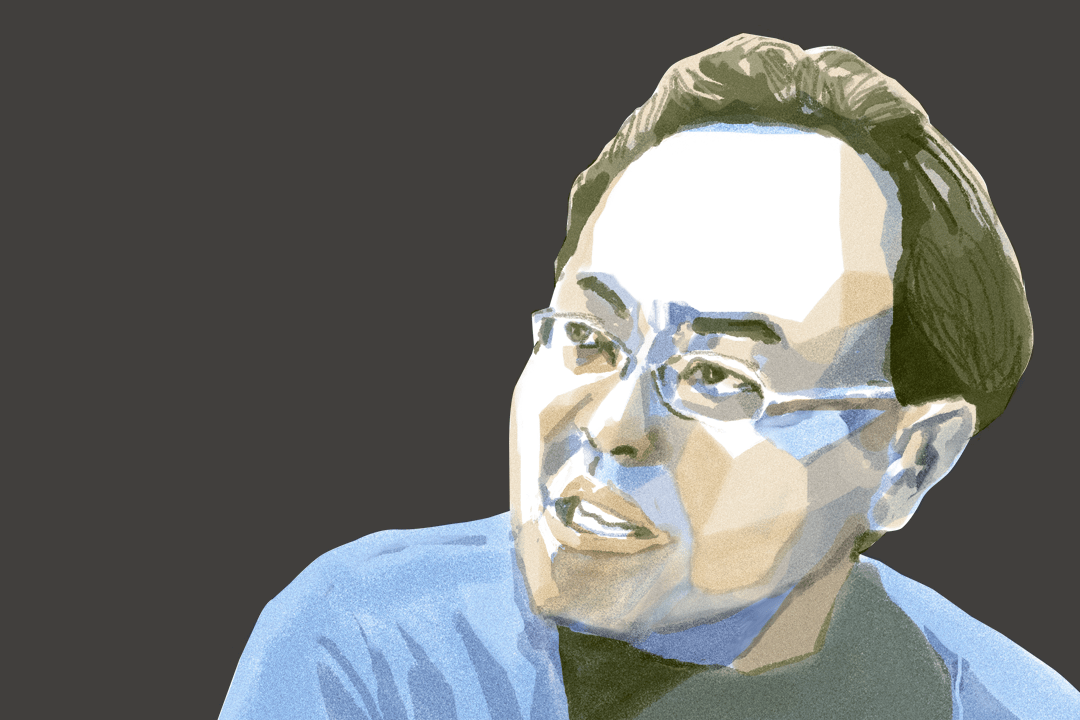




好文章。我們於是必須在這一場又一場的變形記之中,重新尋找並辨認自己身上真正屬於中國的那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