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玉玲,人类学硕士。曾任职编辑,业余参与文艺活动策划。现为人类学研究员,研究时代变动下的日常生活方式。
疾病,在身体里发芽,却在社会和文化中开花,盘根错节,形成一张巨大的意义之网。尽管它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但自诞生之日开始就无可避免地附带上丰富的隐喻。或与一切阴森恐怖的想像联系,对身体的折磨,对精神的摧残,它打破了生命美好的虚构、让死亡恣意亵渎高贵的灵魂,它身体和精神关在一个绝望的孤岛上,自生自灭;但它也可以是罗曼蒂克的、富有诗意的,可以将人的生命得到升华。启蒙时期,卢梭(Rousseau)超脱了前人把疾病视为惩罚的宗教意义,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自我激情的展现,肯定疾病与过度激情紧密相连的积极因素。
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也曾详细地论述了欧洲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短短的几十年间,结核病是如何逐步在浪漫主义文学的推动下走上诗意化、浪漫化的神台。疾病一跃成为一种代表个性的审美符号。
被称为“白色瘟疫”的结核病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慢性传染病。早在西元前几千年,人类已经有感染结核病的记录。中国湖南长沙马王堆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挖掘出的女尸的左肺有结核病的钙化灶。埃及也曾经发现过脊椎感染了结核病的木乃伊。然而,结核的病征却使病人的外表呈现出致命的诱惑。苍白的脸色,发热使得面颊潮红,更显风韵;虚弱的身体,咳出的血在手帕上变成一朵朵优雅的红花,渐渐消瘦的神态形成了一种如花般凋谢的病态美。死亡的虚空和健康的平庸与之相较显得不值一提。
当时有许多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都沉醉在这样的病态当中,并获得了巨大的精神愉悦,并认为这样的死法可以消解死亡的乏味和身体的庸俗。自恋的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曾对友人表示,宁愿死于结核病,因为这是一种凄美的死法,可以赚取女性同情的眼泪。到了二十世纪初,汤玛斯·曼(Thomas Mann)在《魔山》(Der Zauberberg)中甚至提出,“笨人必定健康而平凡,而疾病则能使人变得高雅、聪明、才智,超脱不群”。后来被确诊患有结核病的卡夫卡(Franz Kafka)也认为,这是一种带有哀伤的幸福疾病。在桑塔格的笔下,疾病的浪漫化,并非仅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精神转向,而是已经从文字走向了美学化的巅峰。当时社会大众也搭上这辆快车,把疾病包装成为一个可口的甜品,自己品尝之余还能馈赠亲友。这股浪漫化的风气甚至吹到了日本,从而影响了一批当时在日本求学的中国作家。郁达夫等中国作家创作了许多涉及结核病的小说。
灵魂病与天才病
假使正如桑格塔所说,结核病是一种“灵魂病”,那么,还有一种被披上罗曼蒂克的外衣的“天才病”,便是梅毒。在欧洲,患有梅毒甚至致死的名人多得吓人,上至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下至臭名远播的希特勒;从文学家福楼拜、莫泊桑、波特赖尔到画家梵古、哲学家尼采、航海家哥伦布、音乐家贝多芬、舒伯特。由于梅毒螺旋体会侵害神经中枢,从而使人出现狂喜、精神亢奋、幻觉甚至偏执的人格,使得福楼拜坚决认为梅毒是与高智慧的大脑活动有密切相关。这种以性行为为主要传播途径的疾病,在亢奋的性欲和虚幻的爱情之双重作用下,成为一种获得艺术创作原动力的最佳方法。正如二十世纪初欧洲一片繁荣景象下埋藏的杀戮,梅毒的浪漫外衣正是当时社会城市化生活种下畸形果实。
这个罗曼蒂克的绮丽幻想并不能维持下去,并最终被科学所击碎。1882年,德国著名医学家、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最早发现结核分枝杆菌,并论断出了结核分枝杆菌的致病机理,后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1928年亚历山大·弗赖尔(Alexander Fleming)发明了青霉素,到了1945年,链霉素等抗生素的问世,其他药物也陆续出现,治疗结核病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身上附带的浪漫主义神话宣告破灭。
然而,进入了新世纪,疾病的隐喻并未消失。在亚洲,正有另一种疾病的浪漫化现象出现。有别于肺结核或梅毒,这种疾病的浪漫化并非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而是架空在人的大脑中。其病毒原产于韩国,她比先辈更具群众基础,更受不同女性群体的青睐,藏匿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察觉,并以长时间、小剂量的特点,随着韩剧的播出,逐渐横扫中国。她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其并发症。这种并发症不是对患者千般折磨以至于药石无效,而是通过虚拟世界的传播到现实世界中,让荧幕前的女性无力招架。她便是白血病,又称为“爱情幻想综合症”。
一旦患上这种疾病,就会让患者的中枢神经瘫痪,大脑的语言功能萎缩,无法正常思考,只能随着剧情的发展作出悲喜无常的表情。这种疾病也无法根治,只能间歇性缓解。如果说她的先辈是建立在浪漫主义的肥沃土地上,白血病的浪漫化,就是在大众消费文化中生根发芽。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韩剧逐渐引进中国市场,这股浪漫爱情的异国风潮就迅速虏获大部分女性观众的心,让她们沉浸在爱情的感动与忧伤中久久不能自拔。这些韩剧之所以能有如此威力,除了云集众多外表靓丽的男女演员、尽情展现了韩国美丽的风光之外,更重要的是,她们都有一个让人相似的老套剧情,剧中美丽善良的女主角大多会因身患绝症而死。
根据一些骨灰级网友的统计,韩国影视作品中七成与死亡相关,但其中八成却是剧中主角身患不治之症。《蓝色生死恋》、《美丽的日子》、《泡沫爱情》等高收视率的剧集无一不是出于这个经典的韩剧套路。爱与死作为艺术创作的经典命题,韩剧选择了用死亡的永恒来衬托爱情的精美,实在是无可厚非,但让人惊讶的是,编剧大多都偏爱同一种疾病:白血病。韩剧初入中国,肆虐萤屏之时我才是中学生,但和几位姐姐剧迷追了几部之后,我不禁想问,为何韩剧女主角都死于白血病呢?
白血病,俗称“血癌”,是一种造血组织的恶性疾病。由于某一白细胞系列的前提细胞失去分化成熟能力,而在骨髓中和其他造血组织中呈恶性增生,侵犯身体器官,最终破坏全身组织、器官,抑制造血功能的正常运作。可见,白血病,一种不具传染性的难治之症。然而,白血病之所以被浪漫化,并不在于疾病的本身,而在于她使得病人以何种面目置于他人的目光之下。
韩剧女主角的最理想疾病
这让我想起曾经在覆诊时遇到的一名女病友,她直言,宁愿自己患上的是白血病,因为它不会引发任何让他人感觉不适的外表变化,反之,甚至会让患者更具病态美,惹人怜惜。有别于其他实体肿瘤,白血病并不会造成局部的赘生物生长,而是全身扩散的恶性血液病。主要的病征是发热、贫血、出血等。尽管同样是疾病,但白血病不会如器质性疾病般给身体带来器官损害从而导致外表发生变化;也不如皮肤疾病般,给完美的女性形象带来丝毫的毁坏;更不如致命的流行病般分散了人的注意力去关注更为广大的社会性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白血病,是韩剧女主角能患有的最理想之一种疾病。
在韩剧中,女主角经常会出现皮肤苍白、流鼻血、突然晕倒、腹部剧烈疼痛等症状。这些疾病的特质一旦遇上温柔的女性,便顺理成章地更显出一种让人怜惜的女性柔弱美态。这种模式不得不令人想起中国文人对女性“病西施”式的审美观,四大名著《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便是“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时如弱柳扶风”,宝玉甚至借用《西厢记》中的“多愁多病身,倾国倾城貌”来形容她。女性、柔弱、病态,组成了一种中国传统的病态审美。
在这样的文化根基之下,韩剧自然能迅速风靡中国,一边用白血病来增加女性的柔美,一边有疾病的残酷来诘问爱情的意义,配上优美的风景、动听的乐曲,将两者结合为一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从而,中国女性观众在长久以来被观看的压抑,瞬间爆发被转换成观看者,带著内化的病态审美观使得白血病被浪漫化。
曾经触目惊心的疾病和死亡,在韩剧中被浪漫化为一种展现女性柔美和爱情永恒的一剂良方。如烟花般短暂、灿烂的爱情,在必死的疾病面前被凝固为一个不朽的化石,没有肢体残缺、没有血肉模糊,白血病,更加增添了女性的绝美,在残酷的疾病和死亡面前显得楚楚动人;男女主角以刻骨的爱情来企图抵御死亡,尽管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正是这种徒劳的努力,让女性观众深陷其中,在叹息悲痛之时享受着这病态的审美。相比于先辈,白血病的浪漫化则显然更具杀伤力,它让人在视觉愉悦中消费虚妄的爱情,嫁接到现实生活之中,从而对疾病和死亡产生了一种妄想的态度。
这其中巨大的心理落差必然使得人们再次逃离,以一种漠然的态度旁观现实中的徘徊于生死边缘的白血病患者,却为电视荧幕幕背后的影像倾注最大的关注和爱意。现实和虚构的混乱和背离,只是加强白血病的浪漫化。即使等到治疗白血病的万灵药发明出来,还是会出现新一代的疾病浪漫化。在最新的一些韩剧中已经出现更为多元化的奇难杂症,如《秘密花园》中的幽闭恐惧症,《匹诺曹》中的匹诺曹症候群以及《没关系,是爱情啊》中的图雷特氏综合症等。也许,当疾病成为一种生存的形态和艺术的表现,要治疗疾病浪漫化,就只能通过书写来解放人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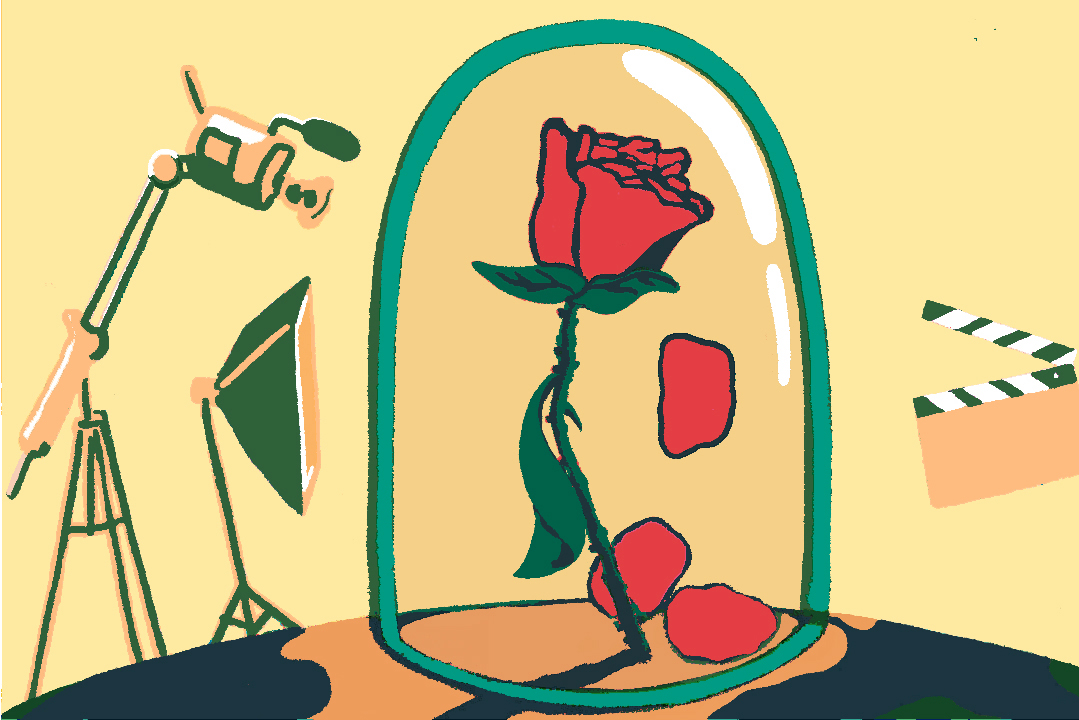




这个观点很新鲜,没怎么看过韩剧的我从没想到白血病的浪漫化过程
曾经的韩剧的确是这样的,柔弱的女主角需要强力的男主角来扶助,极端表现就是得白血病,凄美死去。想想很多言情小说也是这样的啊,柔弱的女主角加上强悍的男主角。但今天的韩剧已经不是这样的,女主角们更独立更自由,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爱情,而是可以去选择,去追寻。而今天的言情小说也相应地有了这些变化。期待作者写出更多的韩剧观察文章。
「相比于先辈,白血病的浪漫化则显然更具杀伤力,它让人在视觉愉悦中消费虚妄的爱情,嫁接到现实生活之中,从而对疾病和死亡产生了一种妄想的态度。」
用幻化疾病的角度试图去解释「韩流」得以流行的原因,很特别。
其实并非生理上的病态才算是疾病,更让人生畏的恐怕是心智上的残缺或认知方面的缺陷,这比眼见的所谓「疾病」,更流行,因为患者通常觉得自己没有这个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