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及美國政府對以色列的政策時,所謂「美國猶太社群遊說組織」(例如AIPAC)的影響力向來引發許多爭辯以及想像。但晚近半世紀以來,形塑政策、左右大眾論述的主要力量其實不是美國猶太社群整體的意向,而是極少數擁有美國猶太社群「代表權」的頭人。
這個觀點來自史丹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新聞學教授和資深媒體人Eric Alterman。身為美國猶太裔的Alterman在2022年底出版《We Are Not One: A History of America’s Fight Over Israel》一書,廣泛引用不同組織的檔案紀錄、不同人物的傳記資料,以及新聞報導、民調數據、其他歷史學者的研究,分析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社會、特別是美國猶太社群如何討論以色列。他的結論是:一群極少數人綁架了整個美國猶太社群,進而綁架整個美國社會談論以色列的方式。這些極少數的猶太裔菁英與以色列右翼政治人物亦步亦趨,而且近半世紀以來,美國猶太社群的組織「徹底不是民主產生:其效忠的對象是保守派金主,而非組織領導人宣稱自己所能代表的人群」。
這些少數金主不只有錢,更知道如何運用金錢影響政治,積極讓自己的聲音成為主流社會的主要參考對象,同時利用各種方法壓制社群內外反對的聲音。雖然以色列的猶太人遠比美國的猶太人更右翼,但多數時間,美國主流社會關於巴勒斯坦、關於美以兩國關係的辯論,卻反而比在以色列更受到壓縮,即使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美國自由派媒體上,對於巴勒斯坦觀點的陳述,甚至還比以色列的自由派大報《國土報》(Haaretz)來得更加單薄。原因正是這些寡頭金主的影響力。
在《We Are Not One》裡,我們見到的故事是:一小撮人善於利用其他人的沉默,積極搶占論述的空缺,並且打壓其他人的聲音,讓自己能夠持續獨佔發言權。但就是這一群極少數的人,改變了美國猶太社群,甚至美國對以色列的態度。

「替代的上帝」:當以色列成為美國猶太人的主要身份
在2013年的一個民調發現,僅有38%的美國猶太人表示相信以色列政府「真心尋求和平」,在年輕世代當中更只有四分之一這麼認為,而支持以色列屯墾政策的美國猶太人更僅有13%。當時以「對抗反猶主義歧視」為宗旨的知名組織Anti-Defamation League(簡稱ADL)領導人Abraham Foxman輕蔑地回應:「聽好了,猶太世界組織多得是,這些組織者才是真正付帳單的人」。Foxman 時常接受主流媒體採訪,「代表」猶太社群抗議各種反猶主義的表現,而且經常指控批評以色列政府的人「反猶」:曾中箭的包括各大國際人權組織﹑美國公共電視資深記者﹑甚至卡特總統本人。
Foxman的底氣,來自ADL的金主,猶太裔的右翼賭場大亨Sheldon Adelson。在基層猶太裔選民壓倒性支持奧巴馬的2012年,這位金主在初選期間以超過9,200萬美元支持共和黨。這也反映了近四十年來美國猶太社群領導人的趨勢:即使基層猶太選民高比率支持自由派,但領導人們卻頻繁和右翼結盟,尤其是最右翼的福音派基督教民族主義者──他們其實對猶太人充滿偏見,但認為支持以色列能「加速上帝的再臨」。在Adelson的支持下,ADL財力雄厚,聘請的全職員工就超過三百名,在美國多個州都能建立區域辦公室,有助遊說選區國會議員。這位金主相當慷慨,甚至讓Foxman本人更可以隨時調用他的一架私人飛機。
既然有Adelson這樣的金主「付帳單」,也難怪在面對對美國廣大猶太社群內的不同意見時,Foxman自認有本錢嗤之以鼻。
而像ADL﹑AIPAC這類的組織是怎麼變成美國猶太人的「代言人」的?根據Alterman,轉捩點出現於1967年:那年埃及等國聯軍對以色列發動攻擊,卻在六日之內被以色列徹底擊潰,反倒讓以色列佔領更多土地。這場「六日戰爭」,直接令美國猶太裔社群的面貌翻天覆地。

在1967年前,多數美國猶太人都沒有「以色列情結」:主要猶太組織的刊物的關注重點是美國國內種族平等議題,或是其他社群工作,而以色列議題經常位置靠後、篇幅偏少,甚至只是被放在「海外議題」的大標題下。當時已有幾位知名菁英是以色列建國的熱切支持者,但一般猶太社群成員、特別是中上階級猶太人普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興趣有限,《紐約時報》當時的猶太裔老闆甚至公開反對猶太復國主義。這些菁英高度認同美國,不覺得自己需要建立一個所謂「真正的家」,遑論接受「真正的祖國」保護。許多美國猶太人的政治傾向也更「普世價值」,猶太人所建立的公民組織的關懷,和其他自由派組織其實相差無幾。
但六日戰爭讓猶太身份認同變得極其重要。當時美國猶太社群先集體經歷以色列可能滅國的恐慌與無力,但在一週之內又迅速感受到大獲全勝的驕傲和勝利:在戰爭之後,猶太社群的報紙裡大幅報導各地美國白人的讚嘆,猶太人迅速感受到「書呆子」之類的刻板印象被顛覆的自豪:「雖說猶太人很會拿鋼筆、提手提箱,但如果有必要,猶太人也很能操作來福槍和坦克車。」那時美國媒體刊登的以色列士兵照片魁梧瀟灑,被專研美國文化的權威猶太裔學者Amy Kaplan形容成「兼具軍事勝利和陽剛性魅力的圖像」。
那時美國猶太組織開始主打為以色列募捐,捐款爆增四倍以上,許多美國猶太人開始以捐款、以支持以色列為展現自己猶太認同的手段。50年代的美國猶太組織其實山頭林立,但在1967年的分水嶺之後,以「為以色列政府行動」為職志的金主開始取得領導地位,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各種社區動員、國會遊說、政策智庫、媒體論述的組織。而美國的政治制度也尤其獎勵這種大型的組織,既可以在各州、各地區發展,又可以在聯邦層級一致統籌,運用金錢和人脈發揮影響力,AIPAC以及「美國主要猶太組織主席會議」(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通常簡稱CoP)皆是在此一背景下,逐漸在政壇、在主流視野中躍升為猶太社群的「代言人」。

這些組織與以色列政府密切合作,而由於自1977年之後、亦即在這些組織茁壯的同一時期,右翼的以色列聯合黨(Likud)多次勝選,連續長期執政十餘年,更確保了這群頭人又與這些組織頭人建立起緊密的關係,讓這些組織的議程已經遠遠不只是「親以色列」,而是和以色列當中的右翼亦步亦趨。
影響所及,書中提到當工黨籍的拉賓(Yitzhak Rabin)於1992年重新當選以色列總理時,其實明確向AIPAC表示希望他們撤手,讓工黨新政府自己決定協商的進程。他的財政部長也表達,以色列已經足夠富裕,並不需要這些美國金主的捐贈。新任外交部副部長更是在會議中直接向CoP成員呼籲:拜託不要再打壓美國猶太社群內的不同意見了。但在這個時候,AIPAC根本無心住手,反而與以色列的右翼合流,包含在破壞奧斯陸協議的階段性成果之後,選擇在此時於美國國會運作立法,要求克林頓政府將大使館遷移至耶路撒冷。
如同書中引述的一位資深記者所說,這揭穿了AIPAC的謊言:他們甚至根本不是無條件支持以色列政府,而是支持以色列內部的右翼政黨。
誰敢批評以色列?
「只要報紙裡出現看似對以色列有任何一絲批評的東西,我的編輯從一早就會有接不完的電話。」
這一群右翼鷹派的頭人們,挾著巨大的資源,以猶太社群的代表自居,搶占各種政策制定和公眾論述的空隙。社群內固然有不同的聲音,但他們在一波波鬥爭中敗下陣來:早在1972年、也就是六日戰爭的五年之後,就有一群自由派的拉比和知識分子組織倡議組織Breira(意指「選擇」),呼籲以色列必須「在領土問題上做出讓步」,並「承認巴勒斯坦人對國家的渴望具有正當性」。其中一位共同創辦人解釋,他認為進步派猶太人「有責任」另起爐灶,不能把所有捐款都給予傳統的猶太社群組織,因為這些組織才是真正「盲目讓以色列自取滅亡」。

一開始,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都發表肯定該組織的社論。但組織頭人們立刻予以反擊,比如在給基層會員的新聞信中汙衊他們是在提倡投降,或者杯葛與任何同時邀請Breira成員的活動;尤其在Breira的幾位創辦人和一位被認為與巴解組織關係密切的阿拉伯裔作家密會之後,CoP公開譴責這樣的會面是巴解組織宣傳戰的一環(即使他們的會談原先是秘密),美國猶太社群內的主流刊物更攻訐Breira證明敵人意圖消滅以色列的策略已經取得成功,並且特別點名其中特定幾位領導人在先前曾參與社會主義團體,將他們「抹紅」。很快地,原先加入的成員陸續在壓力下退出,捐款人也陸續撤回捐款,Breira在五年內就徹底銷聲匿跡。
書中提到,在Breira事件之後,猶太裔大導演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歷史學家賈德(Tony Judt)等也都曾在社群內被點名批判。時至今日,寒蟬效應依然存在:作者引述一份2013年的猶太教內部調查,顯示在認同自己是「鴿派」的拉比當中,有高達四分之三表示害怕表達自己對以色列的看法。作者引述一個代表近兩千名自由派拉比的組織領導人的解釋:鴿派的拉比們「非常害怕,原因是他們會被右翼的教眾攻擊,而他們經常控制財源。」
當然,比起在美國猶太社群內部打壓異己,這些組織更為人所知的是對「外人」的攻擊。書中提及其中一個經典案例:AIPAC自1973年起組織了專門反及媒體中「假訊息」的部門。《洛杉磯時報》負責報導埃及的記者David Lamb回憶,「只要報紙裡出現看似對以色列有任何一絲批評的東西,我的編輯從一早就會有接不完的電話」;而以色列政府駐紐約辦事處的發言人自己也向記者炫耀:「不論是記者、編輯還是政治人物,只要知道他們在幾個小時內就會接到幾千通憤怒的電話,要批評以色列之前也會考慮再三。」獲獎無數的《紐約時報》國際記者Thomas Friedman在1982年到以色列、黎巴嫩實地採訪,在報導中寫下「今日在西貝魯特全境,以色列戰機、炮艦和砲兵無差別(indiscriminate)發射彈藥」--這句看似平凡,但編輯仍不顧Friedman反對,強行刪去「無差別」字眼,以免讀者反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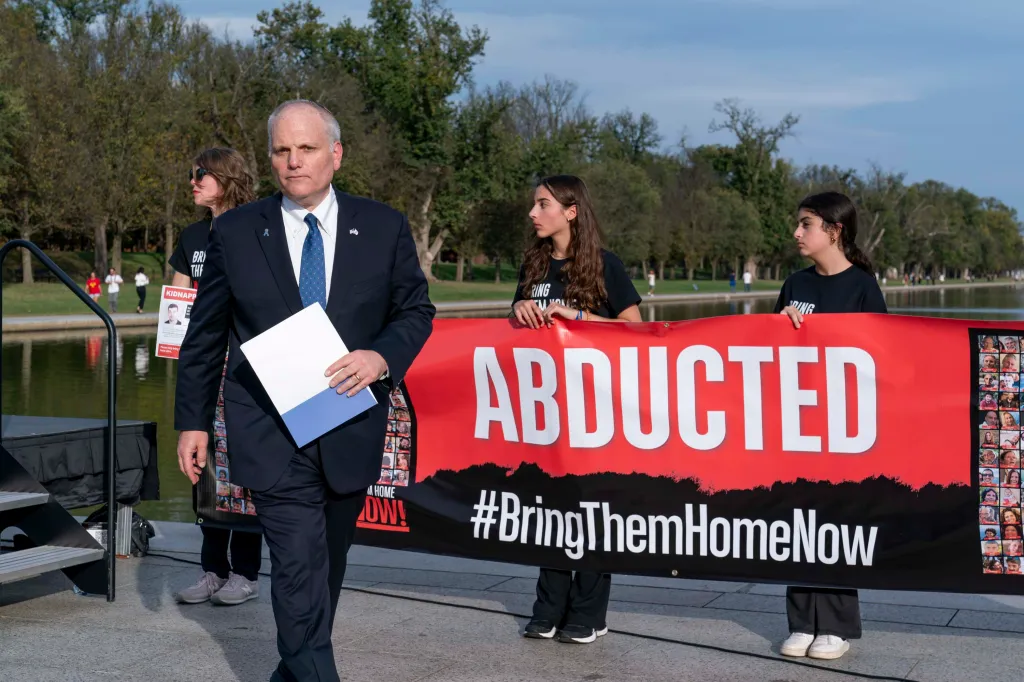
這些組織不只盲目攻擊敵人,同時也搭配著積極搶占陣地,讓自己的聲音更容易成為主流社會的「預設立場」。比如在政壇上,AIPAC等組織的強項在於有龐大的研究與幕僚人力,能夠迅速提供政治人物各種法律草案、談話重點、智庫研究報告,並且能以巨額政治捐助吸引政治人物予以採納。在2016年,美國知名女性主義政治行動委員會EMILY’s List的主席Stephanie Schriock分享她過去擔任幕僚時的經驗:
「在你和猶太社群會面募款之前,你就必須先和你州裡的AIPAC領導人會面,此時,他們會清楚要求你必須先提出你關於以色列的書面政見。所以你就開始打電話,去找你那些已經提出書面政見的朋友,用他們的政見當成你的政見,而你朋友的書面政見則是AIPAC設計好的。」
媒體上的道理也相仿:「攻擊對手」本身不是目的,讓自己的論點成為社會預設的正當論述才是。比如在2000年以巴又一波談判破裂之後,由於談判秘密進行,一度存在資訊的真空,人們並不知道實際上發生的情形。這些少數菁英在媒體上所散播的論述,是強調以色列政府如何做出史無前例的讓步,但巴勒斯坦代表依然錯失機會、貪得無厭,大幅形塑了美國社會對此波談判的觀點。
其實,《紐約時報》駐耶路薩冷的記者隔年即出版調查報導,克林頓的國安顧問Rob Malley也投書媒體,雙雙抵觸了此一主流敘事。兩篇文章都相對持平,提到以、巴、美三方都各有誤判,也都各有無法接受的條件。然而,這樣的文章不但為時已晚、大眾已經有既定印象,而且他們又再度受到頭人們針對性的攻擊。Rob Malley當時就被CoP的領導人公開指控為「最親近阿拉伯的國安團隊成員」,CoP又重申「事實只有一個,不容爭辯:巴勒斯坦人導致大衛營談判崩解」。名義上專注於對抗反猶主義的ADL的領導人Foxman,亦同樣指控Malley是「依照『某些人』的議程行事」。

正是因為這樣的策略奏效,使得這些寡頭菁英在主流論述中的地位屹立不搖。雪上加霜的是,美國媒體經常根本不覺得自己能找到代表其他觀點的正當發言者。作者提到,知名的巴勒斯坦裔教授薩依德(Edward Said)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是唯一例外,是少數美國媒體和觀眾所能接受的發言者;否則在太多時候,代表巴勒斯坦觀點的人除了美國人眼中張牙舞爪的「恐怖分子」阿拉法特之外,就只有在大學校園上「搗亂」、滿口學院理論術語、終究也說不清楚該怎麼改變的大學生。
改變的可能:打破組織頭人的壟斷
這樣牢不可破的壟斷,真的能夠打破嗎?Alterman卻認為一切仍大有可為。近年在美國猶太社群內部,如J Street、T’ruah等新組織的出現,雖然遊說、選戰資源遠遠無法和AIPAC競爭,但在論述、在政策上有提供有意義的「替代方案」,協助不同立場的政治人物更知道可以怎麼做,也有了合作的對象。近年來,更多的美國猶太作家、宗教領袖也都開始講述不同的故事,逐漸撐開論述的空間。
而既有組織頭人至今仍持續運用相同的鬥爭策略,半世紀來始終如一。舉例而言,ADL執行長在2022年指這些新興猶太組織「嘗試以自己的猶太身分當成盾牌」,窩藏「反猶主義」的敵人。就此而言,建立發言的正當性依然是一條主要的戰線。Alterman舉例,面對如國際特赦組織等團體提出研究報告,具體指證以色列的種種人權侵害和戰爭罪行時,與其爭論以色列「是否可以跟南非相提並論」、接著深陷「這個指控是否構成反猶主義」的既有泥淖,更好的策略應是努力嘗試,促使人們嚴肅看待報告中對於以色列現狀的種種具體批評。
而若要削弱這些頭人的影響力,則必須注意這些既有組織頭人最大的弱點,其實也正在於他們和基層社群成員脫節。其中最明顯也最重要的現象,莫過於美國猶太人選民依然多半屬於自由派,但組織頭人卻在近四十年來集體右傾,尤其不斷與福音教派的代表人物過從甚密。發展至今,AIPAC甚至於2022年宣布成立行動委員會,與MAGA派金主一同資助上百位共和黨候選人。除此之外,美國猶太社群的青壯世代根本並未親身經歷六日戰爭,反而更熟悉各種近期戰爭慘況的報導,他們所認識的以色列總是由內坦雅胡這樣的強硬派所代表,這些矛盾都是挑戰頭人們壟斷地位的重要利基點。

這也扣合了本書的書名:We Are Not One,「我們並非一體」。數十年來,以色列右翼偕同美國猶太社群頭人們,不僅獨佔代表猶太社群的正當性,更讓他們的觀點成為主流政壇和輿論所預設的唯一正確答案。然而,美國猶太社群和既有組織的寡頭金主們不是同一群人,和以色列民眾、特別是其中的極右翼更不是同一群人。這樣的矛盾是當下困局的歷史起因,而在作者Eric Alterman看來,這也應該是衝破既有限制的最佳起點。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