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髒話(又稱粗口)經常被文化論者視為突破社會禁忌的良性文化現象,但我們仍不能一概而論,而忽略個別與髒話有關事件中的語境分析。中國羽毛球手陳清晨在奧運比賽期間「爆粗」,不只是關於運動場上的不君子行為,更是中國民族主義與舉國體制折射到國際體育賽事中的典範性事例。
事緣7月27日,陳清晨在一場跟韓國選手進行的奧運羽毛球女雙賽事中,頻繁地高聲喊出擬似「我操」、「牛逼」等粗言,引起網民議論紛紛。港台網民多數認為,比賽中「爆粗」是不尊重對手、有違體育精神的行為,應予以譴責;但當中亦包含了嘲笑成份,部份人認為中國運動員文化質素低下,不懂國際體育禮儀。然而中國網民的反應則相當正面,不少人認為陳清晨的舉動旨在激勵士氣,同時也表現她率性一面。當然,在奧運賽事中聽到熟悉的漢語髒話,也挑起了中國網民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掀起了一輪以「國罵」作為「國粹」的議論。
遇到灰色地帶:小粉紅與國際的落差
「國罵」一語出自魯迅在1925年的文章〈論「他媽的!」〉。網上不少想當然的言論都引述這個典故,並聲稱在情緒高漲時爆出一句「他媽的」,是民族性的表現,有正面意義。但魯迅原文的意思是說,當時中國仍有士大夫跟「下等人」的階級之分,士大夫「口上仁義禮智,心裡男盜女娼」,低下階層要在嘴裡反抗,就發明了一句「他媽的」,魯迅看來,這「也還是卑劣之事」。因此,魯迅論「國罵」,其實是迂迴地批評社會的階級不平等,而沒有為髒話說項之意,我們亦難以將他的說法套用在現代語境裡。
反而是,以「國罵」形容髒話,既有批判民族性,亦有民族自嘲成份。在現今網絡世界裡,髒話愈發擺脫了其作為禁忌語的性質,而晉身成網絡日常語,不論在內地還是港台網絡上亦然。2009年,中國政府發起「整治網際網路低俗之風專項行動」,封鎖網絡上的髒話,網民因此發明了「草泥馬」(操你媽)、「卧槽」(我操)等髒話諧音,以避過官方網絡審查(即「河蟹」(和諧))。類似的髒話諧音在港台網民之間亦相當盛行,例如香港網民已習慣以「撚」(𨶙)、「膠」(𨳊)入文,或台灣網民以台語諧音講「趕羚羊」(幹你娘)、「機車」(欠姦)等。
在一般網絡發言或現實中的日常談話中,這類扭曲髒話(minced oath)往往被視作無傷大雅,也不常被看成是低俗、無禮或沒文化的表現,不過在正式或官方場合中,例如政治人物發言、傳媒廣播等,不論是正式的髒話還是其諧音,則仍是禁忌。
網民對這個灰色地帶的理解和反應,更反映了中國的小粉紅民族主義,跟台港、周邊國家、以至國際文化政治之間的落差。

陳清晨在運動場上的「率性」表現,正是觸碰了髒話作為「日常用語」,跟作為「禁忌語」之間的灰色地帶,而網民對這個灰色地帶的理解和反應,更反映了中國的小粉紅民族主義,跟台港、周邊國家、以至國際文化政治之間的落差。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國際奧委會雖沒對比賽中的語言禮儀進行個別規定,但世界羽毛球聯合會則訂明禁止運動員「用清晰且洪亮到讓裁判或觀眾聽到的聲音使用在任何語言中被普遍知道且理解的詞語進行褻瀆或表現不雅」。另一邊廂,中國女子單車選手鮑珊菊和鍾天使在頒獎台上領取女子單車團體賽金牌時,被發現佩戴毛澤東像章,明顯有違《奧林匹克憲章》中禁止在運動場上進行政治宣傳的規定。一如「陳清晨事件」,此事同樣引起了中國網民喝彩。
表面上看,這兩件事只屬個別例子,反映了某些中國運動員對國際體育規例的敏感度不足,因而才犯下這類與比賽勝負和獎項無直接關係的錯誤,然而在事件背後,卻說明了一種看待國際體育活動的中國民族主義心態:以爭勝,而不是體育精神,為運動員的最高價值。
要體育精神,還是致勝策略?
體育精神(sportsmanship),有人會稱為公平競技(fair-play),是現代體育領域中最廣為認同的最高價值。民國時期的教育家羅家倫曾把fair-play譯作「運動家的風度」,並強調「寧可有光明的失敗,決不要不榮譽的成功」。但今天我們理解的sportsmanship,意涵遠比fair-play豐富,據《奧林匹克憲章》訂明,「體育運動是每個人的權利。每個人都有能力在沒有任何歧視的環境下進行體育運動,在體育運動的交流中追求友誼、團結和公平競爭進而更加深入的體會奧林匹克精神。」
背後的理論基礎則是來自「人權」的觀念。奧運作為國際最重要的體育比賽,也理應被視作現代體育精神的最高體現,當中涉及的不只是運動選手不可以為爭勝而違反比賽規則,如偷步、使用不合規格的比賽用具和衣飾、或服用禁藥等,亦關係到運動員、有關國家的體育組織、以至觀眾對「奧林匹克精神」的充分尊重。換言之,「不犯規」只是運動員應有的行為表現,更應深究的,是行為背後的運動員心態。
除了sportsmanship,還有一個相關的概念是gamesmanship。跟sportsmanship不同,gamesmanship重視比賽中的致勝策略,尤其是如何在整體佈陣、心理戰和臨場發揮的事情上下功夫,力圖在不違反規則的前提下,盡可能尋求「擊敗對手」的方法——要注意的是,這裡講的是「擊敗對手」,而不是「爭取勝利」。運動項目中,如球類、搏擊等,均以「擊敗對手」為獲勝指標(這類姑且稱為「第一類」),而像田徑、游泳等項目,則沒有對打成份,運動員主要是專注於自己的表現,最後以時間、距離等客觀標準評定勝負。(姑且稱為「第二類」)。 另外還有一類,如跳水、體操等項目,也沒對打成份,但評定勝負方法則由評判團的評分決定。(姑且稱為「第三類」)。Gamesmanship在「第一類」項目中對運動員表現的影響較大,在其餘兩類中則較小。
一種看待國際體育活動的中國民族主義心態:以爭勝,而不是體育精神,為運動員的最高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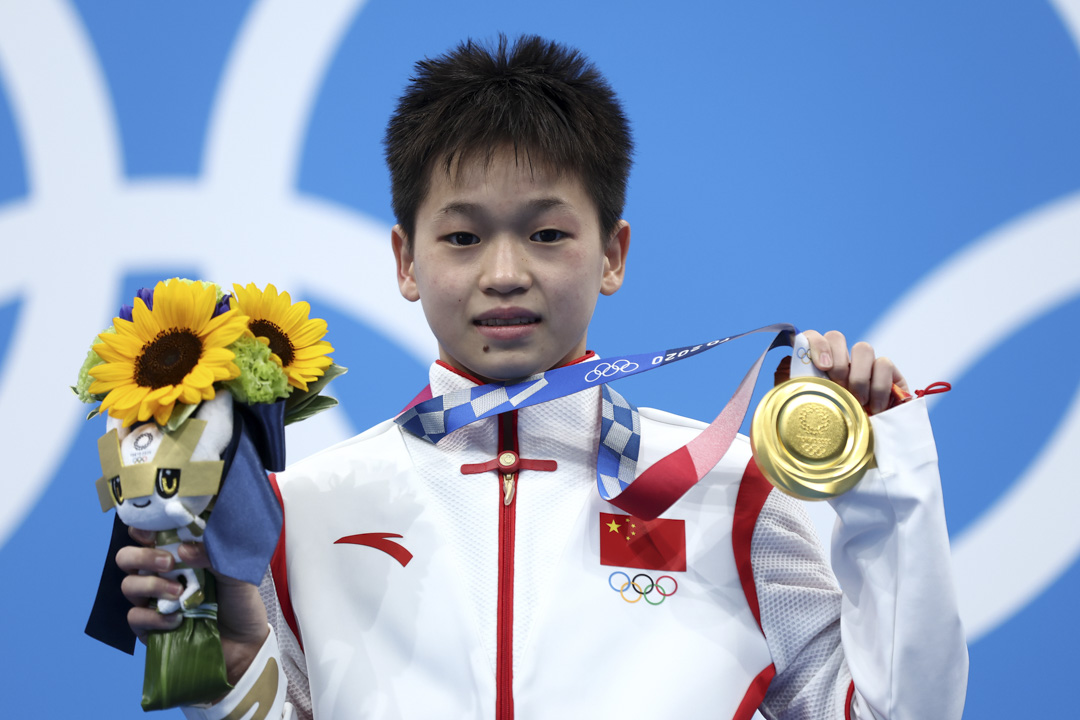
中國舉國體育體制,策略與僭越
據美國《紐約時報》分析,中國自1984年以來所獲的奧運金牌中,有近75%集中在六個項目上:乒乓球、射擊、跳水、羽毛球、體操和舉重,原因是中國體育體制承襲自蘇聯模式,由國家在全國各地物色有潛質的兒童,再送到官方體育學校進行全日制訓練,而為了爭取更多金牌,政府會把資料投放於西方國家較不重視的項目上。
《紐約時報》的報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體育體制的一些冷戰背景,即以「舉國體制」發展國家體育,而影響所及,中國運動員在國際上表現較出色的,一般都是個人項目,例如「第二類」和「第三類」,運動員可以透過重複性和高強度的訓練來提升水平。相反,像「第一類」項目,除「 乒乓球」和「羽毛球」等個別項目外,中國運動員表現相對較差。據《紐約時報》統計,除女子排球外,中國從未在奧運中得過任何集體項目的金牌。(至於今屆東京奧運中國女排表現不濟,以及過去曾有「鏗鏘玫瑰」之稱的中國女足亦不復當年勇,似乎進一步反映了這個狀況的激化。)
這種中國體育的「舉國體制」,令中國運動員專注於個人重複性的訓練,以保證在國際比賽中有穩定的良好表現,因此對於有大量臨場不確定因素的「第一類」集體項目,如足球、籃球等,單純的重複性訓練是無法得到好成績的,這似乎說明了中國體育體制不擅於在gamesmanship上鑽營比賽策略。
但弔詭的是,若將視野放到比賽規則以外,中國其實是十分重視gamesmanship的。事實上,陳清晨「爆粗」似乎也可視是gamesmanship的策略之一,即以心理戰方式打擊對手士氣,即使我們並不知道,這是否有意為之。可是,問題卻出在這一「策略」僭越了sportsmanship。
對於中國運動員來說,由舉國體制承襲下來、以爭取金牌(甚至連得銀牌或銅牌也被視作失敗)為最主要(即使不是唯一)目標的集體思維,令體育精神變成了一件相對次要的事。在比賽中不犯規,主要是避免被取消資格,而非真切地認同並尊重體育精神。於是,對於一些沒明顯犯規的舉動,不少中國運動員都相當不敏感。
一個著名例子是中國泳手孫揚。今年他因禁藥問題被禁止參加東京奧運,不過在網絡上,他最廣為知的事件,則是2019年世界游泳錦標賽中,在鏡頭前向英國選手史葛(Duncan Scott)說:「You loser, I’m win, yes!」,表現極為挑釁。至於鮑珊菊和鍾天使佩戴毛澤東像章,似乎也不像是一種有意挑戰奧運文化的政治行為,而只是無心之失。
對於中國運動員來說,由舉國體制承襲下來、以爭取金牌(甚至連得銀牌或銅牌也被視作失敗)為最主要目標的集體思維,令體育精神變成了一件相對次要的事。

「戰狼」引發的正反效應
回說陳清晨事件,事後陳清晨在其個人微博中說,她只是「對自己一個赢球氣勢上的鼓勵」,又指自己「可能是發音不太好」,「讓大家誤會了」。可是,她並未清楚說明她那句話是否髒話,而在稍後的比賽中,則已未再聽她發出類以的聲音。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爆粗」確是她自我激勵的方法,然而她並未注意到,這種方法有違國際間對體育精神的理解,更有違反跟判定勝負無關的體育規例的風險。
陳清晨事件不只清楚說明了,在現存中國體育體制下,運動員欠缼關於體育精神的良好觀念,由此也牽動了中國民族主義跟國際政治輿論之間的矛盾。習近平曾表示,要求中共各級領導「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既開放自信也謙遜謙和」。這當然是一套大外宣辭令,卻因為與過去的「戰狼外交」大相逕庭而為國際注意。不過,中國在國際間的「戰狼」形象深入民心,在奧運中,中國運動員任何出位舉動,都很容易被解讀為符合中國官方外交形象的表現。
這種解讀可從正反兩方面談,一方面,中國網絡小粉紅總是喜歡把這些事件解讀成民族主義的體現,例如讚揚陳清晨「爆粗」為「國罵」, 甚至故意將這些違反國際禮儀的行為,硬說成是一種民族復興的表現。另一方面,小粉紅的煽風點火,旋即引起台港網民的反彈,他們既對中國運動員有違體育精神反感,也燃起了跟中國內地在政治上的對立情緒,並將這情緒重新投射到運動場上。
事件很多,不勝枚舉。例如在羽毛球男雙決賽,台灣的李洋和王齊麟擊敗中國的李俊慧和劉雨辰奪金,台灣網民歡喜若狂,更有人將羽毛球場地的綠地白界設計成「新國旗」,以宣示跟中國劃清界線的國族思想。相反,中國內地網民則咒罵連天,他們不只批評李劉表現不濟,更譏諷李王是「台獨選手」。中國網民的反台情緒,更引發台灣藝徐熙娣(小S)被小粉紅「出征」,中國網民指她在台灣羽毛球手戴資穎敗給中國的陳雨菲後,以「國手」形容台灣運動員,是「台獨」的表現,更指罵她不要再至大陸撈錢。
小粉紅的煽風點火,旋即引起台港網民的反彈,他們既對中國運動員有違體育精神反感,也燃起了跟中國內地在政治上的對立情緒,並將這情緒重新投射到運動場上。

需要注意的,即使中台網民雖有互相蔑視的集體情緒,但表達方式卻各有不同。更重要的,是面對自家運動員的落敗,態度也迥然不同。內地網民幾乎一面倒地對落敗(哪怕只是失落金牌而得到銀牌)予以譴責指罵,連帶運動員自己對也幾近條件反射地為自己未能奪金而道歉。相反,台灣網民則多對運動員的付出表達謝意和鼓勵,即使在戴資穎敗給陳雨菲這類涉及鮮明政治情緒的賽事裡,戴資穎雖敗,卻赢盡了民心。這種情況同樣在香港發生,不只張家朗奪得劍擊金牌,而令香港人欣喜若狂,即連游泳選手何詩蓓兩奪銀牌(不是兩度失落金牌),或羽毛球伍家朗因「球衣風波」而表現失準,香港網民都給予充份支持,全無罵難之聲。
一種解釋當然是,台灣跟香港向來不是國際體壇上的勁旅,今屆東京奧運的成績已是超額完成,而中國則是體壇強國,故要求不同,也有沉重得多的歷史包袱。可是,中台港民眾看待奧運的迥然態度,同樣反映了gamesmanship跟sportsmanship的對立。中國的小粉紅民族主義崇尚優勝劣汰,純以勝負論英雄,對體育精神也缺乏細緻的體會。而不少台港民網民討厭中國,政治因素只是較闊而空泛的時代背景,真正令他們反感的,是那種無視體育精神的集體性格。
奧運發展到今,國家勝負(或僅僅是獎牌榜排名)已不再是現代體育的唯一價值,國際間愈來愈關注運動員在比賽中表現以外的各種議題:體制問題如日本奧委會的賄賂醜聞、操守問題如俄羅斯因為禁藥被罰不能以國家隊名義參加、政治問題如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賽,有難民代表隊參加奧運、或文化政治問題像睪酮濃度影響女性運動員參賽資格的爭議等,凡此種種,皆指向一個關於乎現代體育精神的思潮演進:
我們的世界愈來愈重視如何更精準而完善地達成奧林匹克精神,也就是對個人權利的悍衛、排除歧視、弘揚友誼、團結和公平。任何對成績和勝利的追求,我們都只能以上述基礎上進行,而不能繞過它。
中國的小粉紅民族主義崇尚優勝劣汰,純以勝負論英雄,對體育精神也缺乏細緻的體會。而不少台港民網民討厭中國,政治因素只是較闊而空泛的時代背景,真正令他們反感的,是那種無視體育精神的集體性格。




「内地网民几乎一面倒地对落败(哪怕只是失落金牌而得到银牌)予以谴责指骂」这一句实在过于偏颇,我认为评论区中@Detective 说的更为全面和公允。这一届奥运会中,对于运动员的评价饭圈化才更接近真实舆论风向。
这篇文章有失偏颇吧,中国对于金牌的狂热在2008年及以前要比现在更狂热,这两届反而得银牌赞许也逐渐多了起来,包括重新看待刘翔。
而且,也不用太苛责运动员(当然违反条例那就是另一回事),这个事情反应的是举国体制背后对运动员素质教育的问题,是个结构性问题,不要对着个体过多的责难,你能要求一个连9年义务教育都没正经上完的人有什么更好的激励自己的方式吗?
其实不是很认同把这种狂热归结于“小”粉红的问题,这种金牌狂热早在小粉红之前就有了
现实中看奥运然后骂骂咧咧的也很多中老年大爷
有时候网上评论大家都默认是年轻人写的,但是中老年人也上网的,而且现实中年轻人并不一定比中老年人更金牌崇拜
想解释一下,女乒团体赛里面顶替刘诗雯的选手叫王曼昱,她得分以后喊的似乎不是脏话,乒乓球选手很多得分以后会喊类似“troy”这样的话,用来为自己加油打气,所以也谈不上是受陈清晨事件的影响。
就我在微博觀察而言,絕大多數大陸網民對落敗選手表達的是支持和維護的態度,比如混雙時落敗時我見到的聲音都是「不要將選手贏乒乓球視為理所當然,其實每一塊獎牌都獲之不易,輸了也不應該譴責選手」諸此之類。而在港台的社交圈總能看到「港台維護而中國謾罵落敗選手」這樣的言論,不知道是怎麼有這個結論的。作者也是沒有調查的情況下就預設立場。不應該投在深度文章。
中国国内的舆论风向已经接近纳粹时期了,理性的声音能听到但绝对不会被自然放大。
文章里反复提到的奥运会精神其实因为奥组委的腐败和不透明早就沦为笑柄,奥运会无论是从赛事观赏性和专业性,都无法与其他专业赛事比拟,赛事本身成了可有可无鸡肋。
而个人金牌以国家归属分类则成就了民族主义温床。开明一点的社会完全不可能说服纳税人承办赛事,而举国体制的国家与奥委会媾合,各取所需而让奥组委更加腐败和不透明。
这样也好,很快这个垃圾赛事要自绝于文明世界了。
我對國內愈演愈烈、犬吠般的民族主義非常厭惡和悲觀,但這篇文章確實過於不公允,先竪一個靶子然後削足適履地把奧運賽事硬往上面套,落了下乘。
Watchout大媽是特例吧,她根本就是有事在喊,沒事也在喊,還要把人家喊在口邊的在喊,抄了米元的Lucky,對A國人喊B國語,與其說是話術,不如當成背景噪音就好
评论区比文章本身更有意思😁
……不應放入深度文章吧。
大家評論比文章好看
一开始看没啥信息量只是在炒冷饭,以为这是一篇发表观点的评论,后来才发现是一篇深度。原来深度不是深度调查的意思了啊。。。
“内地网民几乎一面倒地对落败(哪怕只是失落金牌而得到银牌)予以谴责指骂”——这句话也太不符合事实了。确实有一些对运动员的指责,比如女排自由人,羽球男双,但绝大部份情况对落败运动员都非常友好宽容,刘诗雯在败给伊藤后几乎被全网安慰。作者是没有近距离观察中国互联网吗?写出这样的文字,对整篇文章的可信度都要打上折扣。
当然这些对落败运动员的友好确实不能证明“唯金牌论”不再起效,相反,互联网呈现的对体育项目的兴趣是彻头彻底以国家划分,完全落在民族主义叙事的框架中。
這篇文章也太過度主觀了
預設立場好鮮明,鮮明到晃眼
感想
早在08年,國內就已經有這種主義抬頭了,但是當時還是很理性的,起碼能有討論空間,而不是一言堂,我姑且區分開來稱之為愛國主義。具體像是一直都有的保釣行動和當年的京奧世博。
直到我1516左右在大陸讀書的時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並且在跟朋友討論的時候提到。這種極端民族主義,雖然是政府自上而下有意烘托的,但是他們根本控制不住這種熱潮,只不過他自以為能自己有能力操控。這可能在短時間內可以轉移注意力,問題是他帶來的後果是很嚴重而且深遠的。
陳清晨這事是最典型的例證,她第一次可能沒有注意,看韓國隊喊了,自己也喊了。我不知道韓國隊究竟喊了什麼,我只能說這是陳清揚自己的個人風格和行為,最多只能說她個人質素有限。一直到賽後,她在微博上的回應也能看到她其實是覺得自己不妥的,後來輿論出來一面倒都支持國罵,於是就更加肆無忌憚了。
陳清揚本人是什麼樣我其實不太介意,關鍵是國內輿論,以及輿論行成後其他中國選手的反應才是最讓人擔心的地方。包括女乒乓球團體賽決賽中頂替劉詩雯的選手,以及男雙羽毛球中的中國選手。這兩位我不知道名字,也不想去瞭解他究竟是什麼名字,我只是看了部分比賽直播,已經能聽到這兩位模仿陳清揚的所謂打氣鼓勁方法。
這才是最惡劣和嚴重的地方,渾然形成一種惡性循環,而循環內所有人都不以為然,依然沾沾自喜,怡然自得。以管窺豹,可見這種風氣多麼普遍。
中國的民族主義只不過是鍵盤戰士,在講求風向的今天,不會有理性討論同分析,我愛國所以我是對的,我愛國其他國家是敵人。讓有識之士退出,無知=中國,可以怪誰?
看到评论区有人提到小粉红不能代表中国,可是现实是小粉红真的就代表了中国,不仅在墙内占据了主要舆论场(微博),而且在墙外强势输出,造成中文世界里的港台网民产生了小粉红=大陆人的印象。不过,我也觉得用唯金牌论来切入中国大陆沸腾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太合适,但是民族主义泛滥确实是事实,而且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庄生小梦
完全赞同
唯金牌论或不唯金牌论其实都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这次有日本当肉便器,所以吃相相对好看点
@holo哟
按總獎牌數排名是美國的慣例,可以從歷年美國媒體報導奧運會的網頁歷史紀錄就可以看出來了。這點黎蝸藤在上報有撰文提及
黎蝸藤專欄:奧運會 美中兩國誰更輸不起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20807
不存在刘诗雯没有被骂,女排没有被骂,女足没有被骂的情况。只是在于你身处的同温层是在哪里而已。中国的互联网社会已经比过去更加撕裂了,不同的人所处的社交圈子老死不相往来而已。
我倒觉得唯金牌论的态度不再如之前那么强烈了,女排失利,混乒丢金,不再有那么多骂声,但丢了金牌,心里还是会不平衡。陈梦夺金后,大伙感觉非常爽,似乎对日本报了混乒丢金之仇一般。。。中国的举国体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林丹对做饭缺乏最基本常识,何雯娜连煤气灶怎么用都不懂。。。很难想象这些专为奥运而训练的运动员,是不是平常除了吃喝拉撒睡加训练外,就没干过别的了。。。其实我都不知道运动员如何做才不会被攻击,如这次刘诗雯,女排没有被骂,但为何之前周琦失误,男篮输给波兰,就被“尊”为波兰名宿了。。。
赞同一些评论的观点。这次奥运会的确充分表现了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并不是通过“唯金牌论”来体现的,其实现在不管是民间舆论还是官方,都一直在呼吁不要唯金牌论。在绝大多数中国选手没有拿到金牌或者没有奖牌的情况下,我看到网络上基本都是鼓励、肯定的声音,最多是感到遗憾(比如男子跳水因为失误输给了英国选手)。真正批评没有拿到金牌的运动员的,是很少很少的。
我能想到的被网民批评的,是男子羽毛球双打决赛的输球。但网民之所以批评主要不是因为他们输了,而是因为觉得他们在比赛中完全没有斗志,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拼劲。网民批评射击选手王璐瑶,主要也不是因为她没有进入决赛(其他项目没进决赛的中国射击运动员还有很多),而是因为觉得她输了之后在微博上发自拍说“我怂了”,网民觉得她缺少斗志。当然我是不认可网民这种上纲上线的。但是总的来说,这届奥运会,我很少很少看到因输了比赛而批评运动员的声音。
倒是有一种相反的极端现象,就是体育“饭圈化”。因为过度呼吁不要唯金牌论,导致有时候运动员都批评不得,一堆网友像是粉丝支持娱乐偶像一样,不管运动员成绩如何都一昧吹捧,还不允许别人有任何批评意见。有的比赛运动员确实发挥的有问题,底下评论却还是一堆“辛苦了抱抱”之类的话。我倒觉得这也是过犹不及,因为竞技体育说到底还是要追求胜利、追求出色的场上表现的,运动员哪里表现不好也应该可以自由讨论,只要不上升到人身攻击、辱骂这种程度即可。
最后我认为,这届奥运会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主要体现在对待外国选手(特别是日本选手,也有美国选手)的态度上。网民因为混双输球,对日本运动员水谷隼、伊藤美诚的辱骂真的让人不堪入目,体操全能比赛输掉之后,对桥本选手的辱骂、对裁判、国际体联和奥委会的辱骂也是达到了一种无视规则和事实的非理性高潮,此外同样是打分类的男子蹦床比赛,只是因为中国选手最后时刻被逆转,凭借自己不了解规则的“朴素审美认知”,就认为裁判又“收钱了”(实际上造成差距的打分都是机器打分)。谈到美国选手常常称之为“药罐子”、“持证吃药”、“输了不怕,永远都有重赛的机会”之类的。我认为,这些对于国外选手的超出道德层面的言论,总是觉得自己被裁判黑了的“受害妄想”,才是中国民族主义最鲜明的体现。
这篇未免有点立场先行了。大陆互联网确实民族主义盛行,所以乒乓球混双失金以后很多人网暴伊藤美诚,但对于许昕刘诗雯并没有很多指责的声音,因为大家也越来越明白运动员自己是最想赢的,对他们也大都是安慰鼓励。
@KatieFish 笑死,你可真是标准的双标,我建议你可以和奥委会 battle 一下,把基督教开除出宗教籍再来评论
对于最近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现象我也是目瞪口呆,仿佛奥运会已经完全失去了奥林匹克精神,变成抗击外敌的战场了;再加上最近出征小s的事件更让我对这种气氛感到无比恶心。可话说回来倒也不必含沙射影表达港台比中国优越的观点。就几个简单例子反驳,戴资颖败给陈雨菲,宣泄口在陈雨菲身上罢了,ig上诅咒谩骂就这么选择性无视了吗?如果这是所谓体育精神我真的无话可说;球衣事件也是这样,某些走狗承担了这种愤怒罢了。如果说中国网友倾向于你如果输了你就是罪人的论调,港台网友不过是倾向于我输了我是受害者的论调罢了--只是宣泄口不同,却有着同样的核心罢了。真的,都是粪坑就别比个高下了,中文世界越发极端无法沟通是公认的事实,但是端能否不要再添把柴了?
一派胡言,先做有罪推论,然后再误导无关系的事件为因果关系!动不动就说大陆民族主义,台湾那群绿们敢谈民族主义吗?因为他们是什么种他们很清楚,不能敢谈吗?美国敢谈吗?撇开美国制度因素,美国不敢谈民族主义,因为盎格鲁撒克逊虽为政治第一阶层,但是人口不占优,他敢谈吗?老特一唤起民族主义就被卡卡的大脸,是盎格鲁撒克逊不想民族主义吗?是不敢😀😀😀
好无聊的文章。
毛教是邪教。基督教不是。毛澤東政治含義遠超十字架,不信教的人也能戴十字架頸鍊做裝飾品。
怪了,难道我玩的新浪微博和楼下某几位玩的不是一个?从奥运会开始直到今天结束,我可以算是全程在微博目睹了各种受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挑唆的网暴,从一开始在奥运第一天网暴第一位金牌获得者杨倩开始,就越发离谱可笑,大批网友去扒杨倩的微博,看到她曾经发过一条关于耐克的微博,就大肆辱骂她是跪族女孩还要她滚出中国,同时接着网暴另一个射击比赛女孩王璐瑶,因为她没得奖反而在微博发了张(看起来有点拽的)自拍,对自己水平不行的认怂自嘲也被网友曲解,一时间什么“你花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居然这么大言不惭”的骂声此起彼伏。
奥运持续的这么些天,我对以微博为首的大陆社交媒体越发鄙夷嫌恶,他们完全把奥运会变成了政治运动,变成了另一种“抗日”宣传。几乎所有官媒和网络大v大肆宣扬日本的各种“问题”,甚至宣扬极端民族主义仇恨,比如现在大家人人都会说的那句“仇恨日本人是所有中国人的出场设置”就是在奥运会期间被散布开来的,而我也恰好目睹了这张图片的发布瞬间,发布者是某(据说是)外交部工作人员(绰号小明,微博:禾几日月,他的账号一共有至少4、5个,这个号是他其中一个小号),这张图片发布不久就全网传地到处都是。
实际上一些媒体、大v早在奥运艺术节上的人头热气球就开始了嘲讽,后续接着嘲讽开幕式森山未来表演的对新冠死难者默哀的舞蹈(而且大量营销号故意拼接了原本并不属于开幕式的wassai节目中的一些片段,甚至还找出n年前的“舞踏”表演视频,张冠李戴地咒骂日本开幕式“阴间”,炫耀08年奥运会多么辉煌。实际上如果自己去油管看看wassai的节目,会发现表演极有意思,很有创意,没有丝毫所谓“阴间”元素)。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因为作为一个艺术系的学生,我从去年年底网民对钢琴家傅聪去世时连续几天咒骂他“叛徒”的事件已经看出了这种极端民粹之可怖,类似文革中的那种“人民/精英”对立的论调再起,不是人民大众喜欢的艺术就要被打倒,精英的艺术是资产阶级的荼毒。真是疯狂。哀叹人文精神没落和道德滑坡,哀叹艺术将死。大陆的艺术人文教育迫切需要改革,特别是需要提高审美教育(但是在那种党化教育的环境下,我不抱什么期待)。如果说,普通民众和艺术有距离有隔阂,难以接受现当代艺术,因为审美上的许多理解感知都需要积累(时间上的,知识上的,体验上的),需要大环境,这些都可以慢慢来,但是,那种对一切不理解的事物持排斥乃至仇视的态度实在令人忧心忡忡,如此下去将不再有艺术尤其是现当代艺术生存的空间。
除了艺术方面,这种以仇恨为依托的风气也无处不在,从奥运会尚未开始时就全面展开了,一些媒体、大v集体造势:什么奥运村的床是纸做的一坐就坏啦(俄罗斯运动员专门发了短视频辟谣),什么奥运比赛的水是辐射水,铁人三项比完运动员集体呕吐啦(国内铁人三项运动员专门发了辟谣博,澄清了水质达标和集体呕吐是因为剧烈运动的缘故)……类似的造谣不可胜数,转发量巨大,却不见辟谣贴有多少转发。进入比赛日之后,那种无尽无休的“敌对”又无数次显现。伊藤美诚水谷隼战胜刘诗雯组合,网民开始咒骂伊藤“表情欠揍”,水谷“吹球了”(其实中国队也吹了几次),咒骂日本裁判眼瞎,跑去外网“出征”轮番轰炸伊藤的推特等社交软件,挖出伊藤妈妈曾经对伊藤“只有你才能战胜中国队”的教诲是“变态教育”,曲解她访谈中的各种表达,着意塑造她仇中的形象等等。甚至我亲眼见到更恶毒的评论,比如“要找人轮奸她”。这阵仇恨旋风直到桥本大辉和肖若腾跳马比赛时桥本一条腿出界发酵到了顶点,无数网民涌入桥本的Instagram做表情包辱骂他、辱骂裁判,刷爆了Instagram,导致fig隔一天后出台了一份桥本扣分项的书面证明,旨在说明一切判分都符合规章制度中,没有问题。有个别理智的了解比赛规则的网友在微博科普了体操项目的扣分准则,依旧被网民网暴辱骂他们是“二鬼子”、“精日”、“我们恨日本需要理由吗”,甚至连退役体操队员李小鹏都出来带节奏证明“判分有误”(实际上他一句“起评分”就暴露了他根本不了解现在的评分规则)。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按照规则来扣分,肖若腾不仅该被扣掉0.3(未向裁判致意),而且该被再扣0.3、甚至0.6(重新上台致意,还穿着拖鞋)。
这一切我都亲眼目睹了,尤其目睹了大v甚至一些官媒是如何煽动民意、营造对立的,无耻之尤。我说的这些事情都不仅有个别网友参与,不是零星的、无足轻重的、可谈可不谈的事情,而都是几万评几万转这样大量网民参与其间的微博主流事件或现象,反应的是主流民意。在此期间的那种令正常人无法忍受的“双标”可谓被演绎地淋漓尽致:陈清晨骂脏话就是“爽、牛逼、提气”,日本选手表情傲慢点就是“恶心、不要脸”;戴毛徽章不是违反政治姿态规则,而是“我们的信仰”,外国人戴十字架项链才该被制止;台北选手赢了,“丢脸,居然输给台独”,大陆选手赢了,“搞死台毒,太牛逼了”,香港选手赢了,“港独滚,其他不管,只要放我们的国歌就行”……等等等等。这一切对比官媒宣扬的“我们强大了,不再唯金牌论”是多么滑稽又可悲。
这几天又在微博看到了吹捧体育举国体制的文章,宣扬“没有中国就没有这些运动员的成功”“没有国家哪有我们”“没有党就没有现在的一切”类似的话术。加上这几天打压各行业的种种政策,恐怕所有的一切都说明了目前中国已经面临国内外压力极大的险境,必须疏导、化解一部分社会矛盾冲突,防止在高压状态下压力锅聚积到某一零界时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但是我看到的是民众被两种极端情绪拉扯的惶恐无力和矛盾心态,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疑惑,不敢往根源去思考,党化教育阻拦了独立人格的塑造,被宏大民族主义叙事被想象的共同体被虚无主义狂热捆绑,也逐渐形成道德化的反多元主义潮流。民粹在一般意义上就是各种矛盾日益累积激化、民众危机意识和不满情绪不断上升导致的产物,而且和政治人物在选举中反复煽动民粹的策略有关。 一旦合法性建立于民族主义叙事,晚期癌变后容易面临被反噬的风险。赵鼎新有个准确的观察:“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与当政者统治意识形态谱系接近的极端思想对政治稳定性的挑战往往会更大”,最近在微博有人重新发布余英时2013年那篇《警惕文革借民族主义还魂》也很快被删帖。
奥运会总算是过去了,但被煽动起来的越发极端的民粹浪潮、这股泛道德泛政治化的风向不知道何时能了?媒体们职业素养集体丧失的混乱局面(包括从郑州大雨事件中看出的深度新闻已死通稿就是一切的现象)何时解决?。。。
说真的在端看了这么多文章,这是我第一次写评论,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事实错误,这些事实错误导致了一个不完全正确的结论。
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此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人关注的热度特别高,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是在日本,日本在中国本身就带有话题度,第二是最近几年中国的民族情绪确实空前高涨,需要一个出口。
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就不太可能出现因为中国运动员没拿金牌就责骂之的情况。因为民族主义情绪是不允许任何人说本民族不好的,本民族自己人也是一样。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会让网民把运动员当成“自家孩子”,也就出现了“打不得骂不得”的情况。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你很难在网上看到如当年谴责刘翔的情况。从奥运会开始到现在,我一直高强度关注相关信息,像关注度最高的伊藤美诚水谷隼那场比赛,中国输给了日本,然而中国选手的负面评价几乎绝迹,几乎没有人责怪二位中国运动员。
但是大部分人也确实在心里认为金牌最重要,爱国主义热情不让他们责怪本国运动员,这种情绪总得有个宣泄口吧?是谁呢,那就是奥运会的裁判,是对方的运动员。也就会出现诸如恶搞辱骂伊藤美诚水谷隼的情况,体操比赛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百度体操吧早有爱好者分析过此次比赛并没有什么太大误差,但是各种各样的玩笑已经砸到了那个一条腿迈出去的运动员身上。这才是此次奥运会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真正的体现。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文笔不错,但切入点找得不好,再加上缺少调查,有一些很容易让人反驳的事实错误,所以显得不够客观。
要讲民族主义的话,大陆网民持续认为中国选手在东京奥运被不公正对待(外加国内媒体刻意选取部分事实煽动)这个角度更合适吧……这比只论胜负普遍多了也民族主义多了
@利欧塔
你这样跳脚的样子真的很公知很没偏差,你经历的是文革2.0腰斩你的是审查部门,干嘛要怼小粉红?
还要煽动网民来对付他们?
要区分小粉红导致的取样偏差很难吗?这对媒体而言是最基本的调查和平衡。
我已经搞不清楚反智的是谁了?
骂了脏话,国内舆论还乐于大肆宣传,活该被投诉,搞不好人家原来都没意识到(在比赛过程中有喊叫行为本来就是正常,各国选手都有类似的行为),还是看了国内的舆论才发现可以投诉。
但是毛泽东头像我则认为有有失偏颇,因为如果这要算是一个涉及政治和宗教宣传的话,认为应该把所有政治宗教宣扬相关行为也一并检讨。
例如随手一搜便不乏带着十字架上场的报道
https://chinese.christianpost.com/news/olympian-proclaims-the-glory-goes-to-god-after-silver-medal-win.html
其次说到外国人的体育精神更佳,不在意金牌得失我也要打个问号?
不说上面这个什么基督报只言奖牌总数,不言金牌数的春秋笔法
下面这个前几天纽约时报的金牌统计表的推特也特别有意思,不知是不是中国的金牌特别小气一些,才作此设计
https://twitter.com/nytimes/status/1422507555616665611
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其实早都有预设立场了,没啥水平这篇文章
@EricChan
道理是这个道理,不过北京奥运会那时看比赛,其实管不了那么多,所有运动员都是全村人的希望。
现在看起来那时候的中国人既自豪又自卑可能也是最可爱的中国人吧
其他不谈,但作者真的了解大陆网友对奥运参赛运动员的态度了吗?若真的了解,就不会有“纯以胜负论英雄”这个观点…
文章和很多討論僅討論了「是否尊重對手」。一場比賽能辦起來不只需要對手,還有裁判、場地裡的技術人員、工作人員、服務人員,還有無數的志願者⋯他們把場地弄得那麼整潔、燈光那麼明亮、冷氣那麼適宜⋯不是拿給地痞撒潑的⋯這些尊重在討論的時候也不應忽視。
补充:发现了此文前后矛盾之处:您自己都说(骂脏话、佩戴毛徽章)“與比賽勝負和獎項無直接關係”,后半句为何又批判“中國民族主義心態:以爭勝,而不是體育精神,為運動員的最高價值。”我想请问作者,您举例的几位中国运动员的行为,和您所强调的他们”争胜“以及您提到的体育精神,有什么关联?骂脏话、戴毛徽章就能赢奥运,那也太简单了,所有人都可以去奥运比赛了。
仅凭自己的臆测就推断出中国体育“纯以胜负论英雄”……举个小例子,苏炳添100米决赛跑第6、中国男子女子4×100均没拿到奖牌,按作者的逻辑他们应该被中国人骂死了,事实又如何呢?还有作者多次举例的《纽约时报》,以“奖牌总数”作为奖牌榜,因此美国可以领先中国,又是不是一种“以胜负论英雄”?再说骂脏话,君不见韩国队员在某些比赛中也骂脏话?偏偏他们骂得中国人骂不得?从一句我操就可以洋洋洒洒发挥出一大篇连质疑都算不上、而是立场鲜明的所谓“评论”,看似理性思考,实际上,有点坐井观天了。
好文,细致的观察👍
@zxm1030 我覺得是隨著中國人民和官僚對於體育的認識增加以及教育水平的提升,對於勝利的定義更加多元以及豐富。過去大眾對於運動項目了解不深的時候,只是知道金牌是最好的,銀牌是第二,銅牌就是第三,贏就是贏,輸就是輸。但是現在觀眾對於運動員的發揮會受哪些因素影響會有更深的認識,對於選手表現的評價也不會再囿於最後拿到什麼獎牌。典型的例子是蘇炳添雖然在決賽其實是最後一名,但是觀眾能看到/被引導看到其他選手搶跑對他引以為傲的起跑速度反應時間的影響,以及他在半決賽中打破亞洲紀錄背後的意義。相反地,羽毛球男雙組合儘管取得銀牌,但是因為在決賽中以一種很不體面的方式輸給中華台北對手,所以還是會招致大量批評。這些例子以及劉翔被平反的事例背後都有國內民族主義以及愛國主義思潮的推動。
@saltyd 我認同你的看法,其實不論是陳清晨講粗口 又或是鐘天使戴毛主席像我覺得都無傷大雅,特別是運動員在比賽中的巨大心理壓力,粗口是一個有效的發洩途徑。但是我反感的是內地輿情明顯的雙種標準,包括是對於中國游泳隊過去服用禁藥黑歷史的無視與對外國選手的偏見;對於獎牌榜應該是金牌排序還是獎牌排序的著緊;一面在嘲諷美國運動員桑德斯的抗議是在搞白左的政治正確,一面又在讚揚運動員領獎時戴的毛主席像;前一天還在批評日本混雙乒乓組合的叫聲影響比賽,第二天又跑出來為陳清晨講粗口辯護。這種雙重標準才是令人鄙夷的。
@EricChan
也许是可以用全村人的希望来解释额外的好胜心,但条件改善后稀释的好胜心并没有影响民粹对于中国no1的渴望,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苏炳添可以作为闭幕式旗手,和为什么我们会欠刘翔一个道歉。
很简单,中国人想赢,而且想一直赢下去,所以不再“唯金牌论”会更合理些
咁點解作者唔引用舉重隊石智勇個句‘I want the whole world to hear my WO CAO’不但只冇受到國際輿論‘審判’「比如話呢篇文章」反而成為外國健身愛好者崇拜對象,並將距嘅‘臥槽’作為meme甚至印係件衫度作為文化衫出售作為例子呢? 我承認中國大陸呢次有好多反奧林匹克精神嘅輿情,我都好憎,但同時我唔見得港台民族主義者對大陸選手嘅惡意中傷同嘲諷好似作者描寫咁比中國大陸高級。maybe that's prejudice?
@Lchen195 女足有幾位簽約了外國豪門/過去有優秀表現的球員沒有入選。其中李影被質疑是因為她公開出櫃而導致落選。
又是一位香港作者,這篇文章對中國舉國體制的了解,還沒網友Lchen195短短幾行說的清,連基本功都不扎實,就忙於用表層的現象來支持自己的既定立場,也罷,這文章歸根結底也不是寫給大陸人看的,為了迎合港台讀者罷了
@EricChan 你说的女足的事我还真不知道呢!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何女排,女足等中国团体性体育项目一蹶不振了,本来想是不是人才断代了……你提到的这个因素好像也挺有道理。
例子來源:
【拿干净金牌!张雨霏霸气回应美国媒体兴奋剂质疑-哔哩哔哩】https://b23.tv/gpiPPe
@利欧塔 中國嚴格限制境外媒體在中國內地的宣傳採訪,自家媒體又不吝於展現自己愛國愛黨,聽黨指揮的報道立場。這也不能怪境外人士對中國產生偏見了。
最簡單的例子,用這次奧運會的新聞來說,當游泳選手張雨霏被外國媒體問到興奮劑問題時,有哪一個中國主流媒體會提到1994年廣島亞運會中國游泳代表隊大量使用興奮劑的醜聞?1990年至1998年之間,有28名中國游泳運動員的禁藥檢測呈陽性,幾乎占當時使用禁藥的世界運動員總數的一半的過去有提及嗎?2016年里約奧運陳欣怡尿檢呈陽性,孫楊在2018年拒絕飛檢,還砸毀樣本的故事呢?還有幾年前被剝奪的2008年北京奧運的3枚舉重金牌?
如果我們再看評論區里的發言,大多只是各種歐美運動員以患病為名服藥的陰謀論,又或是歐美各國藥物水平領先,所以藥檢檢查不出來的陰謀論(諷刺的是2008年北京奧運被褫奪的3枚奧運金牌正是新科技檢驗封存樣本而發現的)。連中國自己都對自己國家和外國有偏見,又有什麼底氣去批評外國人對中國有偏見?
@利欧塔 非常赞同你最后关于反思的话。其实任何新闻报道都做不到绝对客观中立,因为报道是人写的,每个人都受困于信息茧房。观点越鲜明越容易引起正反争论,所以我对很多批判类文章点评时会告诫自己尽量不要先入为主,说别人屁股坐歪很简单,但怎么能肯定自己的屁股就坐对了位置呢?我近年一直在关注知乎,发现很多热门提问都来自官媒“观察者网”,说实话它的提问方式本身就很容易令回答者带上情绪,我内心是很不喜欢这种做法的,它是在以一种隐形方式来操控舆论,还是比较喜欢端这里的理性讨论,不同意见更有利于了解不同地域的视角和价值观。
@利欧塔 你可以找到有哪几篇报导陈清晨事件的新闻里留言区高赞评论是批评陈清晨的吗?我找到的b站几篇热门视频都没有怎么找到批评的言论?这也许是不同人互联网同温层的差距,但我不认为作者在这篇文章里的观点是少数。
@lchan195 這個才是真的,金牌和銀牌的差別不僅在於運動員手上的獎牌和他們獲得的獎金,更重要的是他們退役以後的待遇,這個才是真的。過去中國運動員退役以後,獲得金牌還是銀牌,不論是他們自己還是背後的團隊獲得的待遇天差地別,這才是中國體育體制唯金牌論的背後動力。這幾年不再那麼強調金牌,背後也是有運動員出路增加,以及部分運動員的家庭變得富裕,不太擔心出路,以及各地政府修改運動員退役後待遇安排的背景在。而這種體育舉國體制其實影響最大的,我認為反倒不是在這屆奧運會上拿了多少獎牌,金牌。而是在本屆奧運女足選人,戰法排兵佈陣上的荒腔走板,以及背後關於各省政府為了在今年全運會上的成績而犧牲奧運的陰謀論:
“本期中国女足大名单中的队员在结束奥运会比赛后,还将以“奥运组合队”的形势参加全运会比赛,一旦“奥运组合队”在全运会上夺冠,那么进入东京奥运会名单的球员注册地的省市将分享这些金牌。一个球员算一枚金牌,但每个省市不超过两块金牌。”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75423188/answer/2024015439
顺带一提,Lchen195的评论值得参考。
有几点想告诉跨墙来看端传媒的中国人:
1.不管是欧美的媒体,还是台港的媒体,我们假设,或许他们常常在各种时事评论和观察上有着严重的取样偏差(比如有人说,实际上很多中国网友认为爆粗口很不礼貌,文章却认为很多人对爆粗口很满意),但是你们有无注意到:为什么对于中国的时事评论观察,取样多关注、偏差以所谓“粉红”(我们需要为此下个简便的定义,粉红之意为:不对中国的任何大型社会结构的事件作出有意义的批判者,可能辩护、可能赞扬,不包含冷漠以待与反思者)为主?
你们有无想过,不管粉红是多是少,粉红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公共话语(日常还是网络)?我前些日子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批评中国政府对香港地区的文化审查过度,连学术节目都被迫腰斩,直骂“白痴”。我情绪很激动,但是这不至于我被人举报,说我有反华倾向。
是的,如果该文章真的和很多其他文章一样,有严重的取样偏差之嫌(即为挑樱桃之意),同时也没有合理的理由解释为何如此,我们应该怀疑这篇文章的作者在观察上是否严谨。
但是,中国人因此必须思考的事情是:为何他人对中国的观察,常常有偏见呢?偏见在哪?“偏见”是否是“事实”或“大比例”?偏见的影响力大吗?偏见是否对真实世界产生实际作用?
你们一天不反思这个问题,你们永远不可能真的想到办法,和别的国家的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和对话,进行澄清——永远不可能。
2.就算我们假设是全世界所有媒体的偏见好了,完全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请问:为什么全世界所有媒体都会产生这种偏见?怎么产生的?该偏见如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偏见?
在没有基础认知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偏见。一偏见被检验为假,除了多次的实际观察与分析得出的结果,还有几个条件,就是:作为基础认知的偏见没有大范围被人传播过(不考虑传播的量,只针对传播的范围),并且基础认知的取样极少,并且该传播没有产生实质影响力(影响政策、企业决策…),并且该传播没有影响大部分人的判断,并且大部分人有严谨调查。
我们可以假设大部分人没有严谨调查,但是达成这一条件不代表偏见自动产生,好一些前提条件如果存在(大范围被传播,基础认知取样多,产生影响力,影响判断),请不要仅仅就怪外国人充满歧视与偏见。他们可能是被误导了,而不是有意为之;也很有可能这个偏见折射了中国的部分现况,并且该现况相当显著,以至于全世界无法忽视——最好的案例,就是粉红言论与审查体系的结合(导致我被举报),使得主流媒体的反驳、反对声浪被迫减少(这种情况只能让观察者产生取样偏差、挑樱桃的行为,而非观察者自身有问题在先),让大部分人转换至非主流媒体(或者审查体系作用不大的地方)大量讨论,形成有些人所谓的“不理解中国网络媒体的生态”。
中国人,不是全世界都坏心眼。全世界都有自身的问题,但是你们也必须反思自身的问题。
@半熱 大家的社交媒體的同溫層而已。我在b站搜‘陳清晨’,相關的視頻評論區可沒看到有太多批評的言論。不要用你的同溫層以偏概全了。
【输急眼了?国羽2-0暴虐韩国队,韩羽协却要求严厉处罚陈清晨-哔哩哔哩】https://b23.tv/Ujs2eK
【国羽女将爆粗口为自己鼓劲事后道歉:发音不好,网友:别改好听-哔哩哔哩】https://b23.tv/vT32JL
【what's up!🐮啊你-哔哩哔哩】https://b23.tv/aoFDRQ
@第十一个观察者 我的對這句的解讀是:重點不在於成為最好,而是比別人都要好。如果用一個故事去做解釋,就像是兩個人被熊追,爭得第一就是「要跑得快」,比別人優勝就是跑得比零一人快。後者暗示的是影響別人比賽成績也是勝利的一部分。
我就看到很多内地网民对这种行为的反对和批评,我怎么就没感觉到有很多人支持,很多人甚至觉得尴尬和丢脸,为此讨论的也不少。作者真的很会为了观点而预设角度,这样也是很不客观的表现。中国更加看重礼仪之邦,不管表面功夫还是内里底蕴,真不至于遍地小粉红
这篇文章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基调大致一样,我并不反对其中观点,但想谈一下自己对举国体制的想法。与欧美和港台不同的是,中国在人均GDP等层面仍是欠发达国家,如果查一下能在奥运赛场出现的中国运动员履历,会发现许多人出自三四线,五六线城市的乡镇,如果没有国家支持,他们自己的家庭根本无力让他们发挥这种运动天分,的确训练很艰苦,而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也的确是这些有天分孩子改变人生的一条途径,国家级运动员退役以后再次也能做教练,总比哭哈哈种地,流水线打工强吧。如果能进奥运前三,北大清华等学校都可以自己挑,对于运动员来说,比赛获胜就是改变自己甚至家族的命运,得失心重,拿不到牌就掉泪太正常了。
的确如文章所言,中国有夺金实力的多是小项目,比如跳水,体操等偏技巧型的,运动员都是很小就训练,文化课基本没好好上,所以我小时候一直听说一句话“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基于这个理由,陈清晨激动时爆粗口我能理解(邓亚萍以前也是打个比赛哇啦哇啦乱叫型),但是我不赞同说什么发音有误,还有网民把听脏话称为“极致享受”更是可笑,错了就错了,道歉就是了,欲盖弥彰比讲脏话更丢脸。
@Flyfish123
你居然还尝试跟这篇文章的作者讲道理...真是难为你了
别的基本上是符合事实。但是“内地网民几乎一面倒地对落败(哪怕只是失落金牌而得到银牌)予以谴责指骂”,不太赞同。至少这届奥运会我看到很多的声音都是对运动员成绩的肯定,哪怕铜牌都没有,也为运动员成绩的突破感到高兴,而且最重要的是希望不感染疫情平安回来
这篇文章的cherry picking用的真是炉火纯青
“要注意的是,這裡講的是「擊敗對手」,而不是「爭取勝利」。”
请问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跳水冠军的名字是全红婵,不是“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