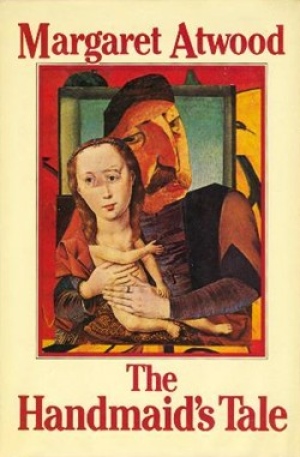
表面來看,本書同時批判了極權主義、男權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然而,儘管全書中與《聖經》相關的符號、儀式與引語無處不在,宗教卻只是極權統治的工具罷了。基於美國的宗教土壤,極權統治者勢必會利用對《聖經》的解讀來奪取權力和維護統治合法性,正如女主角也曾引用《聖經》作為反抗;在現實中,儘管宗教團體是反對女性墮胎權和阻礙性少數群體爭取平等權益的大本營,但支持女性權益與接納性少數者的進步教會也並不鮮見。事實上,在基列國對《聖經》的極端詮釋下,天主教與基督教也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可見宗教本身並不是恐懼的來源,極權與男權的制度結構才是一切的根基。
正如女主角瓊所指出的,權利遭到侵蝕如同溫水煮青蛙,若平日不夠警惕敏感,等醒覺之時早已天地巨變。水晶之夜前,許多生活在納粹德國的猶太人仍心存僥倖;冷戰期間,大部分德國人也不曾預料到柏林牆會在一夜之間竪起;建國前夜,躊躇滿志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曾想到自己即將面對的苦難;特朗普上台之前,許多美國人做夢也沒想到會再次看到3K 黨和納粹旗招搖過市;而九七年的香港,又有多少人敢預言有朝一日連《中英聯合聲明》也只剩「歷史意義」?
更值得警醒的是,基列國雖有鋪天蓋地的「眼目」,但仍然留有地下聯合抵抗的可能,這也許是因為其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意識形態阻礙了對技術的運用,也許是因為小說創作之時的科技局限;而在現實中,面對熱心的朝陽群眾、無孔不入的監控監聽、靠不住的隱私條款和全景監獄式的技術窺探,當微信聊天記錄和臉書言論皆可用來羅織罪名,我們又比基列國國民自由幾分?在基列國的法庭審判中,被告被堵住嘴巴,法官只是聽取政府指控之後就宣判有罪;而在現實中,李明哲等人甚至被迫自證其罪,這種對人格的徹底毀滅比起基列國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生育變成任務
令極權主義更加可怖的,則是將女性徹底物化為生育機器的男權主義。在基列國,由於環境污染而導致生育率下降、嬰兒畸形率和死亡率上升,結果嬰兒的生命被視為最珍貴的財產,而能夠生育的女性成為「兩條腿的子宮」,生命的意義只剩下生育一項任務。在這裏,任何傷害嬰兒的行為都會被處以極刑,墮胎權益支持者自不必說;第一集被懸掛在牆上示眾的屍體中,就有一具是幫助施行墮胎手術的醫生。這一切看似極端,但又再熟悉不過:劇集中,使女們在教導嬤嬤的逼迫下對遭到性侵的同伴進行蕩婦羞辱,類似的情景難道不是每天都發生在現實中與網絡上嗎?
《使女的故事》
劇名:The Handmaid's Tale
播映:Hulu
放送日期:2017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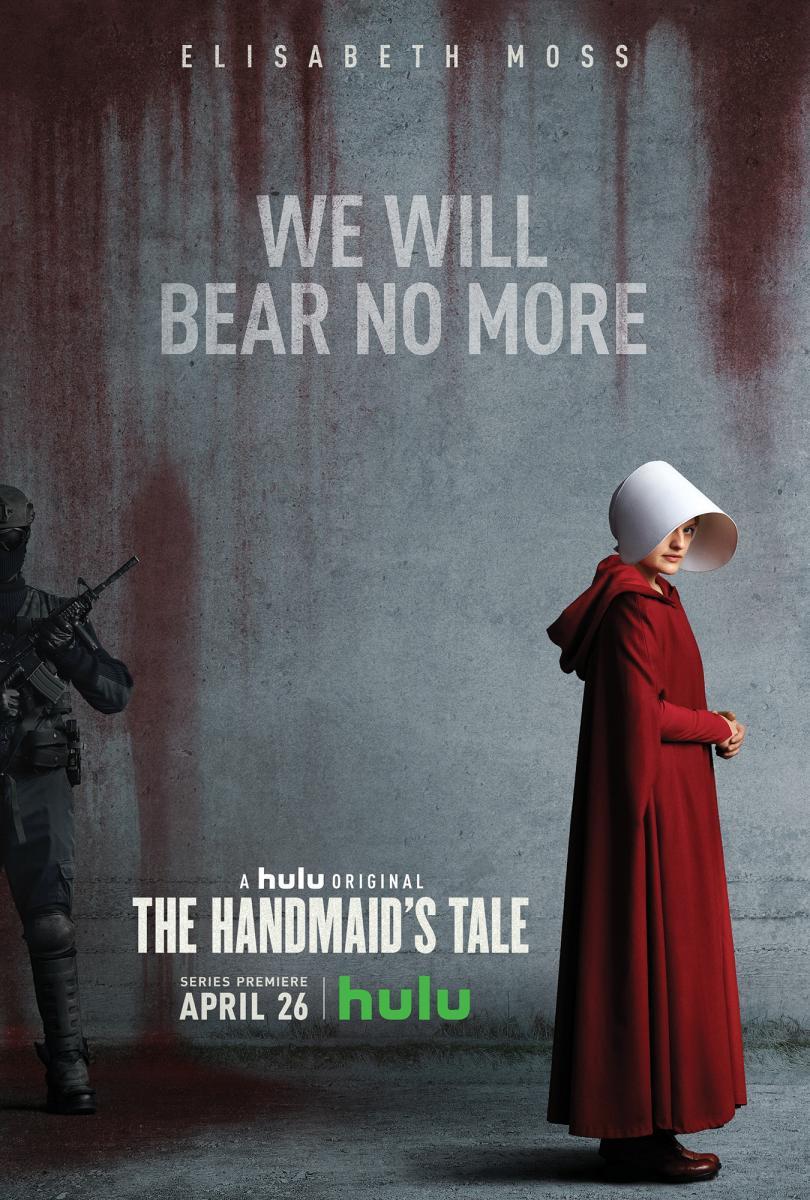
使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只能用男主人的名字加上前綴作為稱呼,這又與許多社會中女性婚後須冠夫姓的傳統甚至法律有什麼本質區別呢?就連希拉蕊這般抱負的女性,也不得不為丈夫的仕途而改冠夫姓,這又何其荒謬?只不過後者早已成為一種以「文化習俗」為名的常態,也就鮮有人質疑了。
至於基列國對生育的執著與迷戀,更是對當今社會現實的白描。在中國,從計劃生育的強制墮胎到全面二胎的社會壓力,如此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也不過是當權者的一拍腦袋,女性自己的聲音從未真正被聽到過;甚至連分娩之時該順產、剖腹產還是無痛分娩,女性也被制度性地剝奪自主選擇權。在美國,當公然為性騷擾張目的厭女者特朗普被毫不在乎的選民選為總統,女性權益面臨的威脅同樣前所未有。上任首日,特朗普就簽署行政令,禁止對提供墮胎服務與信息的國際組織提供聯邦撥款,致使 Planned Parenthood 等非營利組織遭受重創,更有可能影響到無數低收入女性的人生;最諷刺的是,在他簽署命令時,象徵最高權力的白宮橢圓辦公室中所有在場者都是白人男性。這充滿戲劇性反諷的一幕,哪怕出現在劇集中,恐怕也不會有任何違和感。
生育是對女性生活影響最大的因素之一。避孕藥的發明曾被認為是美國女權主義思潮興起的重要契機,也被《經濟學人》雜誌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科學進步。生育率的降低讓女性得以從繁重的生養任務中解脫出來,獲得更高的教育和經濟獨立的機會,也獲得了追尋自己人生的可能。但時至今日,無處不在的教育與就業歧視、同工不同酬的男女工資差異和難以打破的玻璃天花板背後,仍然飄蕩着生育綁架的陰影。許多人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地相信:不生育的女性是不完整的。《使女的故事》在這一方面甚至算不上極端。
《使女的故事》固然已經是一劑喚醒沈睡者的猛藥,卻依然有其保守之處。即使在如此壓抑的故事裏,片中仍處處流露着對母愛的強調;支持女主角瓊活下去的主要是她的女兒,瓊自己的自由與人生則似乎位居其後。更令人驚訝的是,在一次電影節放映後的討論中,劇集創作團隊竟紛紛否認作品的女權主義主題。其中,扮演珍妮的 Madeline Brewer 認為它「只不過是一個女人的故事」,而不是「女權主義宣傳品」;主演 Elisabeth Moss 雖然強調了「女權即人權」--女權主義最基本的訴求之一--卻也堅持認為它「不是一個女權主義故事」。就連愛特伍自己也頗為謹慎地申明,她對「女權主義小說」的定義僅僅是「將女性當作人一樣去描寫」,且「女性對故事的主題與結構十分重要」,而不曾強調其反抗與運動意義。由此可見,儘管這部劇集從內容到影響都毫無疑問是女權主義的,但就算在參與創作的女性眼中,「女權主義」依然是一個被高度污名化的概念;每當提及它,她們都不得不先主動自我澄清,與女權主義運動劃清界限。女性最重要的武器之一--語言--仍然被男權社會牢牢束縛,這也是《使女的故事》在劇集之外帶給我們的警示。




"「女權主義」依然是一個被高度污名化的概念;每當提及它,她們都不得不先主動自我澄清,與女權主義運動劃清界限。女性最重要的武器之一--語言--仍然被男權社會牢牢束縛,這也是《使女的故事》在劇集之外帶給我們的警示。" 說到我心坎裡,身為女性主義者的無奈,同時也是為什麼我堅持使用女性主義/女權主義一詞,而不是改用較不引起爭議的“平權”,為了捍衛這話語權。
非常喜欢Hulu 好剧特别多~ 说Hulu一生黑的,Hulu本来就不是服务大陆用户的,你自己要搞假IP这种钻空子的事,还要怪别人没有空子给你钻?别丢人了
其實當我看過Vanity Fair的文後,我覺得《使女的故事》是在重視男女平等而不是真的在忽視女權主義。
Link:
https://www.vanityfair.com/hollywood/2017/04/handmaids-tale-hulu-feminist-elisabeth-moss
作者最后“儘管這部劇集從內容到影響都毫無疑問是女權主義”的结论有点武断。确实剧集涉及女性各种权益被剥夺,但那样的极权社会背景下,除了少数权贵阶级,平民(包括男性女性)都是被奴役的受害者。小说我没看过,仅谈剧集,June第一次在城墙上看到的三具蒙面尸体,都是男性(一个是同性恋, 一个是支持堕胎的医生),还有后来与某使女发生性关系被定罪为强奸犯,最后被众使女活活打死的那个男人。使女成为“两条腿的子宫”固然令人发指,但在每个月履行一次的压抑的“受精”仪式里,男性指挥官不也是生育的工具吗?
既然「女權主義」被污名化了,那“劇集創作團隊竟紛紛否認作品的女權主義主題”反而显得合理。对Margaret Atwood来说,她要说的都已经在她的作品里了(怎么诠释是读者的自由),为什么她要用“这是一个女权主义故事”去给作品定义、给作品的丰富性打折呢。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它不是什么”往往比“它是什么”,能留给观众/读者更多的理解、诠释和想象的空间吧。
Hulu一生黑,就那么喜欢折腾非美国用户
好不容易绕过IP封锁,你还要开启位置定我位?
"權利遭到侵蝕如同溫水煮青蛙,若平日不夠警惕敏感,等醒覺之時早已天地巨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