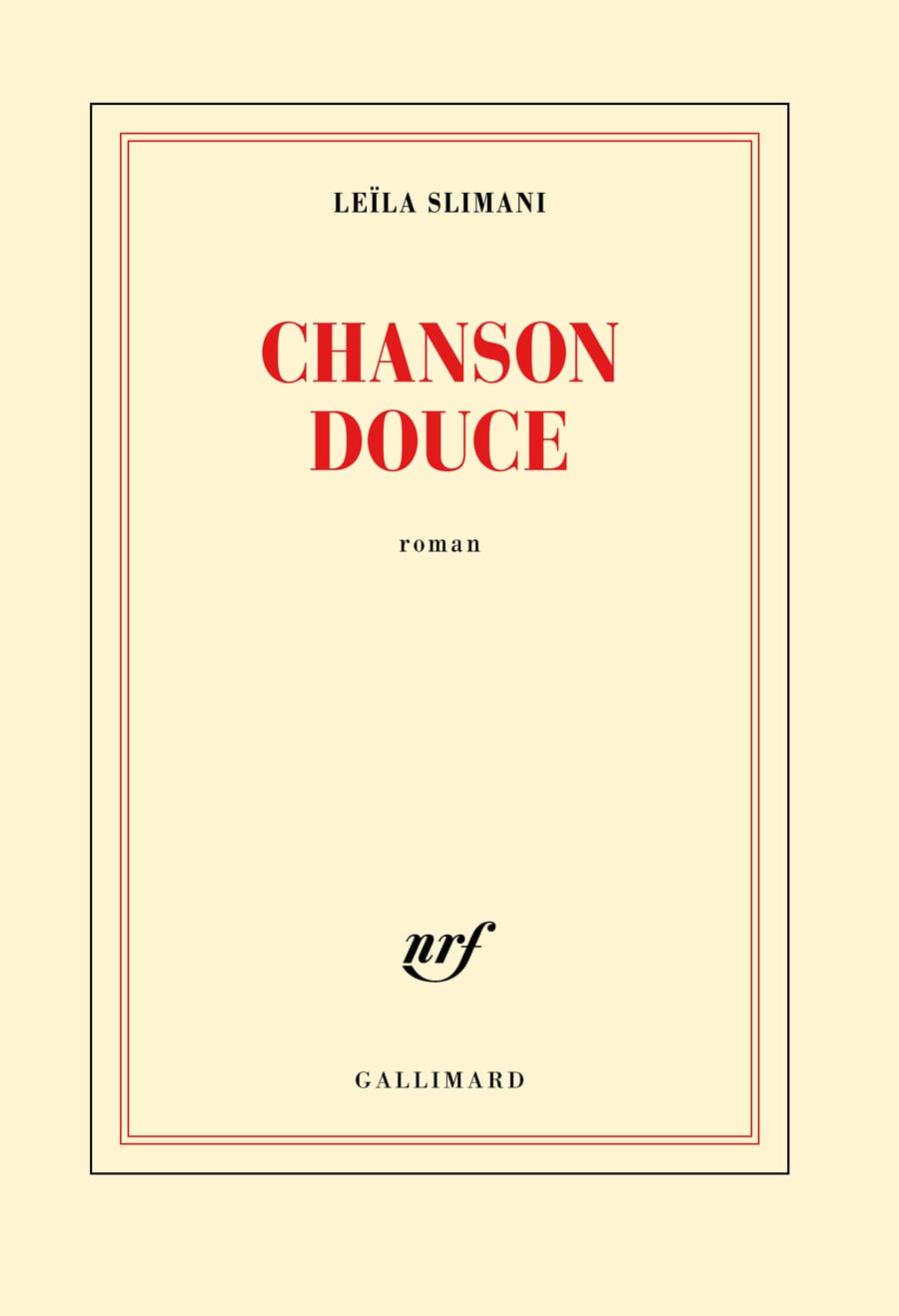
自始至終,作者都帶着記者的冷靜,用疏離和乾澀的口吻說故事,在不同的人物間轉換,記錄下巴黎社會秩序背後的種種陰暗。蕾拉說,她最愛的作家是契訶夫(A. Chekhov),因為他的沉靜,因為他從不評斷筆下的人物。她自己亦是如此。
「嬰兒已經死了。只需幾秒鐘。醫生確認他沒有受苦。[…] 小女孩,在救援到達時依舊活着。她掙紮着,像個野獸。」小說的開頭便把讀者猛然拉進殘酷的結局之中。作者透過旁觀者角度細細描繪了案發現場的情形,那位一直出於驚嚇狀態的母親,以及一旁的兇手——孩子們的保母,她把刀插入自己的喉嚨,卻仍活了下來: 「她不知道如何死亡。她只知道如何給予死亡。」
然後,小說以回溯的方式講述了慘劇的起因。米利暗(Myriam)和保爾(Paul)是巴黎一對平凡的中產階級夫婦,育有一子一女。米利暗無法忍受平庸的家庭主婦生活,於是決定復出當律師,她聘請了保母露易絲(Louise)來代替她照顧家庭。露易絲彷若從童話書裏走出來的瑪麗·包萍(編注︰Mary Poppins,出自迪士尼電影《歡樂滿人間》,原型為P. L. Travers的魔法保母《瑪麗·包萍》小說系列)。她把家裏照管得井井有條,和孩子打成一片,很快便成為家庭不可或缺的存在。可是隨着故事的逐步推進,讀者便會察覺到這位恬靜的保母的古怪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