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中風景]如果把我的浮光掠影中國大陸記行,當作一本小集郵冊⋯⋯
有一次我到杭州,他們安排我在一艘船上演講,那艘船是在京杭大運河上的兩個碼頭跑,可能是想重演當年宋代大運河上航行的情景。我當時缺乏這一趟航行的思古幽情預設的想像,胡裏胡塗想像那就像在我這十幾年「打書生涯」,在各種小書店裏談創作的小景框小講區,只是它(這個想像的小咖啡屋、小書店)是在河流上跑罷了。
這個設計,我覺得挺有些馬奎斯長篇《愛在瘟疫蔓延時》的結尾,阿里薩和費娥米納這對睽違了五十年的老情人,在那條內陸河上跑着,過去的一生皆歷歷如繪在這樣的航行中,像透明薄光的幻燈片,在流動中被召喚、重疊、百感交集。我覺得這特浪漫。
那主辦人前一天,提示我,因為這是在杭州,看我的演講能否圍繞着「白娘子和雷峰塔的故事」,和這個景緻有關聯。
「誰?」我一時沒弄明白。
「白娘子啊,白素貞啊,我們中間有一段,經過的河道,會眺望到雷峰塔啊。看您能不能說些有關的典故。」
「好,沒問題。」我說。
湖光山色在我們四周,像電影播放着。來賓們也不是我習慣的小書店文青,是一些年紀和我相近或較我年長的大叔大嬸。他們臉上都帶着悠閒、明亮的郊遊流光。
那晚我在旅館裏,腦中約略跑了一輪可能的題材。我是這麼想的:白蛇傳基本上是個人妖戀、變形記、動物變態成人形而無法得到人間情愛的憂鬱故事。於是我想了幾個和這「變形記」相關的橋段,遂安心睡去。
但第二天上船後,我發現我的想像和眼前那空間的氣氛,好像有誤差。它不是個我習慣的「咖啡屋或小書店空間」,船艙內座位的排置,有點像電視劇中戰國主公和群臣的酒宴,我坐前方主桌,來賓們分據兩側的桌位,我們的桌上都放着一杯精緻青花瓷蓋碗茶的西湖龍井,一些果脯和小甜點碟。遊船的引擎聲和舷側被水波拍擊的響聲極大,舷窗外是河岸風光,我們看去可能是天際線被各大樓樓盤切斷,間錯一些淡灰的小山,但主辦的那位女士會不斷的提點,在古代這裏是什麼所在,是什麼歷史景點。湖光山色在我們四周,像電影播放着。來賓們也不是我習慣的小書店文青,是一些年紀和我相近或較我年長的大叔大嬸。他們臉上都帶着悠閒、明亮的郊遊流光。我應該不是拉住大家專注力的進行一場,關於「變形記或人獸戀」的演講;應該在這輕輕晃動的明亮河上空間,說些歷史掌故、穿插一些短笑話、思古之幽情的說說白蛇傳。
但我當時腦袋沒轉過來,就切進了原本準備的講稿之中。
他的父母在尋回失去的愛子之後,發現他們面對一更無能為力處理的「失去」:他們的孩子已長成一青少年的外形,但內在是一頭北極熊。
我先講了小說中,一些關於「動物變形成人類,或人類變形成動物」,那個移形過渡的換日線,半人半獸的曖昧狀態(其實這是我喜歡的題材,想想火影忍者的漩渦鳴人,那恐怖巨大的查克拉,源自被他父親封印在他腔腹裏的九尾妖狐啊)。我講起一部愛斯基摩人的動畫片《男孩變成熊》。一個小男孩在嬰兒襁褓時,被一隻母北極熊闖入他們的冰屋抱走。他的人類母親悲痛欲絕,陷入憂鬱。另一邊,那頭母熊把他當一隻小熊那樣照顧,同時訓練他「如何成為一隻成熊」:如何捕撈冰下的魚、如何獵殺海豹、如何孤獨在雪原上生存、如何躲避人類獵槍的搜捕。他把北極熊的母熊當自己的媽媽,把另一隻小熊當自己妹妹。有一天,恐怖的事情發生了,他的人類父親(騎着一台雪地摩托車)終於找到了他,而且射殺了那頭母熊。把他帶回家。那之後是個悲慘的認知混亂的過程:這男孩認為自己是頭熊,無法重新融回人類的生活,他的父母在尋回失去的愛子之後,發現他們面對一更無能為力處理的「失去」:他們的孩子已長成一青少年的外形,但內在是一頭北極熊,最後他們怕他跑掉,還用鐵鍊拴着他。而在另外的場合,男孩遭遇人類青少年同伴的霸凌羞辱、在混亂中他意識進入「北極熊模式」,把那些青少年全重創痛擊。然後他奔跑回空曠的雪原,他向一洞窟裏的山神祈求,想變成真正的熊。那神祇說出一古老的,人類男孩變成熊的考驗:一,你要承受海洋裏最殘酷的激流。二,你要承受雪原上毀滅一切的暴風。第三個最難,你要忍受最痛苦的,天地之間無可依憑的孤獨。如果能通過這三個考驗而還活着,那就可以蛻變成一頭熊。第一關男孩差點被溺死,是海中的鯨因古老的傳統,救了他。第二關,男還差點被那颶風扯碎,是雪原上的氂牛,因古老的祖先訓示,而排列成牆,護擋住他。最後一關,是這種「變形記」最美,也最讓人虛無畏懼的一段,在那巨大的孤獨裏,屬於人類的最後一點靈光,分崩離析,像穿過死蔭之境,男孩終於變成一頭北極熊了。
當代所謂中國人,其實靈魂的內在,早經過了過去一百年來,那整個西方,或「現代」,像鑽地機穿鑿、炸開裏頭難辨其原貌的,各種羞辱、傷害、要讓自己變成不是自己,或有一天發現想變回自己……
我發覺船上的聽眾們,在這樣原本預設進入「古代中國時光河流」的船艙內,被我講的內容,弄得頗困惑。我又講了墨西哥小說家富恩特斯。卡洛斯的《奧拉》,極美的一篇穿梭那移形換影之縫的小說。透過歷史素材,死去老將軍的札記、日記、信件,這個年輕歷史學家困在一幢殖民時期的頹圮老豪宅中,發現那個精靈般的美人兒奧拉,其實是那委託他寫亡夫老將軍傳記的老太婆,那關於她自己青春美麗時期的執念,最後非常魔幻的發生的時光弔詭的「變形記」(我努力拉回:那在中國,就是白蛇傳的慾力啊)……
我隱約發現我串連這幾個「變形記」,其實後面有一個「當代所謂中國人,其實靈魂的內在,早經過了過去一百年來,那整個西方,或『現代』,像鑽地機穿鑿、炸開裏頭難辨其原貌的,各種羞辱、傷害、要讓自己變成不是自己,或有一天發現想變回自己……,那一切的鑲嵌、碎片插在我們的內在各處。」我們現在的船是機械動力,我們看到的河岸風景其實已是全球化所有城市的樓盤地產商的地貌,我們口袋有手機、我們喝着這蓋碗茶,但真實的感性,想像,其實是已經變形了的這個現代的時間分格、商品環伺、移動的便利、所有媒體的訊息殘影閃爍在我們腦前額。我們可能更接近能體悟白娘子的困苦,而非許仙或法海的穩定自我感吧……
我感到氣氛變得僵固,一種說不出的迷惑與尷尬。船這時到了回返點的一處碼頭,暫停泊讓大家下去拍照。我自己站在船尾抽煙,為自己說不出的將這一航程,帶進一稠狀昏暗的敘事情境而生悶氣。但那些大叔大嬸是些非常好的人,他們先三三兩兩在我身邊拍照,然後和我攀談。跟我聊這杭州種種個人的經歷,打煙給我,說我怎麼這麼年輕,原本聽名字以為是個老頭。還抓小孩來和我合照……
(標題為編者所擬,原題為《有一次我到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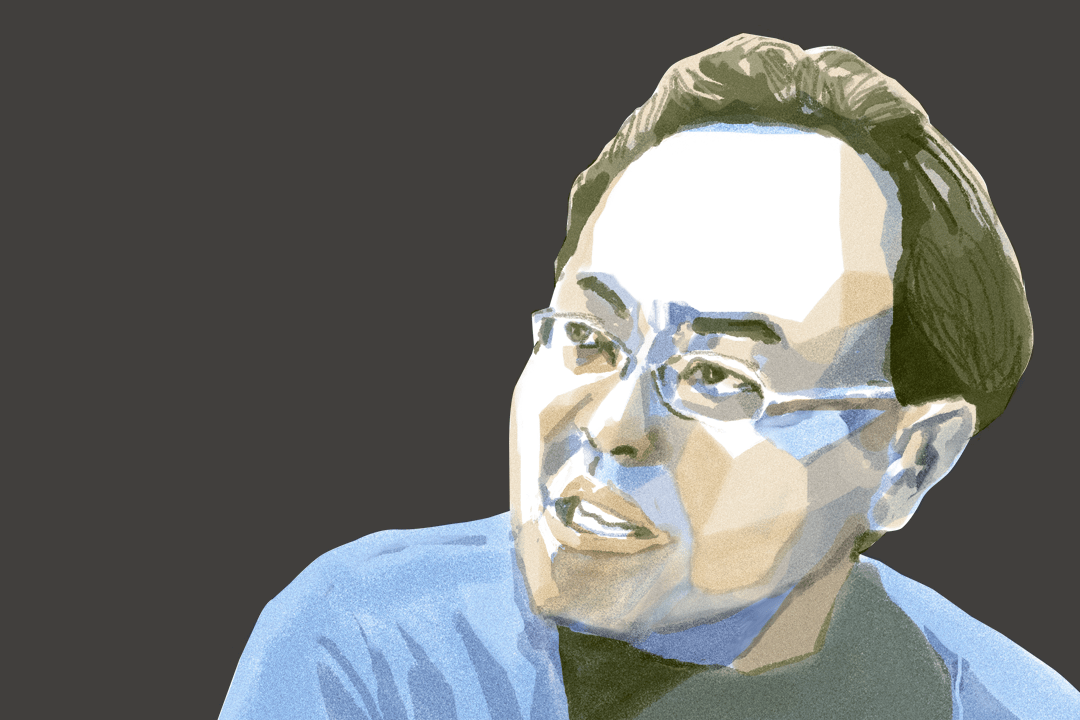




好文章。我們於是必須在這一場又一場的變形記之中,重新尋找並辨認自己身上真正屬於中國的那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