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不要在這裏了,不讓在這裏集結。」
「可是我們就兩三個人誒,我們就是過來玩的。」
「不要跟我說這些,現在這裏臨時管控。」
「管控?有文件嗎?」
「我們管控還需要文件嗎?為什麼要給你看文件啊?下文件,那我現在口頭跟你說了,行不行?」
11月27日晚,寶榮與廣州海珠廣場中布控警察爭執時,錄下了這段讓他哭笑不得的片段。
當晚,廣州與北京、上海、成都等多個城市,同時發生對防疫封控的群體抗議行動,以年輕人為主的市民們走上城市的街頭,喊口號,唱歌,舉起白紙與悼念烏魯木齊慘劇的鮮花,這不僅是他們很多人生命歷程中的第一次街頭經歷,也是中國大陸高壓政治環境中,數十年少有的抗爭場景。
參與其中的人,或許訴求與站出來的原因不盡相同,但抗議愈發荒謬甚至不斷造出人禍的防疫封控政策,是「最大公約數」。11月30日,含廣州在內,多個城市放鬆防控,分管防疫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也首次在座談會中提及防疫面臨「新形勢新任務」。
這似乎是抗議帶來的些許迴音,但警方的盤查與騷擾也接踵而至,寶榮的朋友就曾被警方以防疫調查為名,在清晨重重敲響房門。而與此同時,那些夜晚的共同經歷,也在每個參與者心裏種下了不同的種子。

周旋
廣州的示威從一開始,就註定伴隨着與警方的斡旋與纏鬥。
11月27日下午,寶榮看到社交媒體中流傳着一張海報,約定晚8時在廣州人民橋底共同紀念因過度防疫而死去的同胞。前一日,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抗議與南京傳媒學院等高校學生的白紙抗議,在中國大陸社交媒體的重重審查中仍被不斷傳播。27日當天,除廣州外,北京、成都等其他城市也發出相應號召。「要跟大家站在一起」的念頭下,寶榮沒有多想,就叫了朋友一同前往。
然而,當他抵達人民橋底時,已有大量警力部署在周邊。寶榮與朋友只好一圈圈地在附近遊蕩。
八點半左右,人民橋底部署的警察越來越多,他們甚至開始隨機翻路人的包,幾乎每20米就有兩位警察,安靜的街道上沒有任何示威的痕跡,只有一些如寶榮一樣不願離開、四處走動的「路人」,與越來越多的警察和警車。
「當時還在封控,人不多,但有一些行人,從他們尋找的眼神裏,能看得出來其實是同路人。」林樂回憶,他也是當時在現場走動的人之一。不久,一些路過的朋友開始小聲提醒:你們快走,這邊要抓人了。於是寶榮、林樂等人便動身到海珠廣場,去參與十點半的活動。
原定地點是海珠廣場標誌性的雕像前,然而那裏同樣布滿了警察。據寶榮回憶,當時廣場上有近五十位警察,他與朋友站在雕像下聊天,試圖等待更多人加入。警察留意到他們的停留,便不斷要求他們離開,於是就有了本文開頭的對話。
緊接着,寶榮手機上開始不斷收到 Airdrop 傳來的一些圖片,有的是傳播地點時間信息,有的是提醒注意安全。約十點多,兩三位年輕人走到寶榮身邊低聲問:「你們是嗎?」
「是。」
「可以跟我走,在小花園裏。」

「不要圍觀要加入!」
約10點半,悼念活動在海珠廣場的小公園深處開始。有人打開藍牙音箱,在現場放起了音樂。第一首是葉倩文的《秋來秋去》。
「秋來也秋去,秋風教人掉眼淚,何時才跟你可重聚。」寶榮說,念着歌詞,不知為何,覺得竟也很符合當時的心境。
人們隨着音樂聲逐漸靠近彼此,有人互相打招呼說好久不見,有人派發白紙,有人只是安靜地站在原地哼唱。歌聲也吸引了不遠處的警察,一首歌還未放完,警察們已逐漸逼近。不知是誰喊了一聲:「大家都站在一起吧!」最早到場的幾十人便伴着音樂,手舉白紙,沉默地站在一起,面向警察。
「其實看到警察越逼越近我很害怕,」寶榮說,「我甚至下意識將手上的A4紙團了起來,但看到身邊人都紛紛舉起手裏的白紙,我便也展開,加入了他們。」
幾首歌放完,示威者對面的警察開始結成人牆,並拉起警戒線,將人群分割成線內的示威者與線外的圍觀者,拉線的同時不斷驅趕周圍人群,試圖引導人群至靠近馬路的部分。這時,有人忽然喊了一聲:「不要圍觀要加入!」
「不要圍觀要加入!」其他示威者也跟着喊起來,寶榮說,那是那晚喊得最多、時間最久的口號。期間,一些圍觀者漸漸走入警戒線內,加入示威的核心區域。領頭口號的聲音也開始多元起來:「逝者安息,人民萬歲!」「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還有粵語的聲音:「廣州人,企起身!」
除口號外,示威者們與北京、上海等地一樣合唱起《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國際歌》等,而Beyond樂隊的《海闊天空》、《光輝歲月》更合唱了不止一遍,寶榮還聽到身旁有人用手機播放了謝安琪的《家明》。
唱累了、喊累了,一些示威者開始嘗試與圍堵在面前的警察溝通。有人用普通話問:「你們是誰的父親,又是誰的兒子?你們最開始考入警校,就是為了站在這裏封住你們所服務的人民嗎?」有人用粵語苦口婆心:「三年啦,過夠啦,飯都冇的食,你哋都系人,都知而家工好難搵,你哋咁樣,翻屋企瞓唔瞓得着啊?」(注:三年了,過夠了,飯都沒得吃,你們也是人,也知道現在工作不好做啊,你們這樣,回家睡不睡得着啊?)
沒有人給出回應。

核心示威者之外:對罵聲、便衣與污名
「廢青返屋企!(注:廢青回家!)」圍觀者中,有人喊到。
海珠廣場上的核心示威者喊口號期間,外面也聚集了越來越多的圍觀群衆,有人拍照,有人發布抖音、快手等視頻網站直播,有人在觀望,有人在猶豫,有人認為示威者在「搞搞震(搗亂)」,喊着「返屋企!返屋企!」,有人回擊:「收皮!收皮!」
在廣場的另一個角落,幾位示威者被圍困在警戒線和圍觀人群的包圍裏,其中一位女性與圍觀的大叔對罵起來,大叔指示威者是「廣州曱甴」,外地人收了錢搞亂廣州,女性則回問:「你可以代表廣州人嗎?」
一直在警戒線外各處拍照記錄的伯謀回憶,雖然白紙是代表對審查的抗議,但當時很多圍觀的尤其年長者,對此一無所知。抗議結束後,一些民族主義公衆號甚至造謠污名稱,白紙是為了方便外媒記者重新合成照片,換上需要的口號。更有人在白紙上後期加入繁體字標語的照片,在社群網絡裏傳播,稱此為香港行動者煽動的證據。
「可能與廣東文化也有關吧,廣東人普遍是務實的、遠離政治的、生活安定的、政治冷感的,」46歲的丹尼說,他是11月27日晚廣州示威者中極少數的中年人,在他對身邊人的觀察裏,很多上了年紀的圍觀者並不知道這場抗議的訴求是什麼,只是通過意識形態過去對他們的灌輸,下意識想到「顏色革命、境外勢力」,再加上疫情期間海珠區城中村廣州人與湖北人的矛盾,便會認為「外地人代表不了本地訴求」。
「在我的觀察裏,示威者中其實很多廣東人,很多講粵語的,」林樂回憶,「但領頭喊口號的女生多是普通話,聽不出廣東口音,因此圍觀者可能會產生『外地人在搞亂廣州』」的認知。」
同樣身在覈心示威者人群中的阿偉,也聽到了「返屋企」等聲音,身邊一些廣東人還回嗆:「要返自己返啦!」由於有一定距離,他無法分辨「返屋企」等噓聲的來源,「我不確定是故意搗亂的便衣,還是外面的圍觀者。」
阿偉是從周圍的人群漸漸走入示威核心區的,他此前在警戒線外發現現場除警察外,還有很多易於辨認的便衣警察,他們往往都是一些精壯的中年男人,黑色衣服和鞋子,戴着N95口罩,會拿着手機靠近示威者的臉進行拍攝。
「但如果是故意搗亂的,廣州疫情期間本地外地矛盾,的確是一個容易被挑起矛頭的焦點。」阿偉補充。

「一起走!」
晚上11時30分至12時之間,警察組成人牆將核心圈內的人圍了起來了,看着警察漸漸逼近和圍困的行動,站在外圈的聲援者開始喊:「放人!」
阿偉跟着人流漸漸走入核心示威者的地帶時,並沒有留意身邊情況,查看完信息一抬頭,才發現自己已被困在了警察的包圍圈中。此前在國外讀書時,阿偉時不時會去圍觀當地的遊行、罷工等,遇到感興趣的活動,也會跟着走一段,那時只覺得一切稀鬆平常。11月27日是他第一次在中國大陸參加聲援,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兩種情景的壓抑,第一次覺得自己距離即將被鎮壓的運動,如此近。
當晚,核心區域的示威者被圍困了近1小時,期間有人想離開,但走不出去便只好折返、繞圈,還有人想要衝破警察的阻攔人牆,未免引發衝突,被其他示威者拉了回來。用丹尼的話說,警方和示威者兩邊,當晚都保持着剋制。
直到一位年輕男性向警方表示,自己想回家、不鬧事,其他人便也圍了上來。警方派出一位自稱廣州越秀區分局的領導與示威者談判,最初要求示威者3至5人一組走出,由警方送回住所,並登記身份證。在場示威者表示不滿,認為只要警方開路,大家就可以很快離開。
據阿偉回憶,警方與示威者的談判來回進行了幾次,每次否決都因示威者「如何保證安全」的問題無法得到滿意回答,大家擔心打散分組後可能有人會被要求做筆錄,甚至遭遇暴力對待。忽然,人群中傳來一聲「一起走!」,其他人便也跟着大聲喊起來。
阿偉說,那一刻忽然很想哭,也想起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衝入立法會時,大家強調一起走的場景。雖然原因不盡相同,但那種團體感是一致的。
1點左右,雙方達成「白紙不再舉着、離開後不再聚集」的協定,阿偉、寶榮等在海珠廣場被圍困的示威者安全離開。離開時,寶榮給此前在人民橋偶遇的陌生朋友發信息報平安,並詢問他們在哪裏、是否安全,很可惜,他們因落單被帶入警察局做筆錄。
寶榮問,需要幫忙嗎?
朋友說,沒事啦,就是頭髮被揪掉很多。

種子
「有開酒吧的大哥說,以後去他酒吧隨便喝,但我不記得名字了......還有一個女孩生日,我們很多人給她唱生日歌。」距離11月27日已過去3日,寶榮回憶起那時的心境和偶遇,仍然有鮮活的溫馨感。
這幾天,寶榮時不時還會拿手機小聲公放着「禁曲」隨處走動,希望通過黃耀明、謝安琪等歌手的聲音,讓同伴得以辨認彼此,他很懷念在現場產生的那份聯結感。
同樣懷念的還有林樂,他說,其實內心裏知道去到現場的人,訴求未必是相同的,有的人是宣泄,有的人是維權,有的則是想到更深的東西,但那一晚大家能真實地聚在一起,好像平日裏累積的孤獨感忽然得到了釋放,「原來有同樣想法的人可以有這麼多,原來我們可以這樣看見彼此。」
「很多人反覆問我,是不是人頭200快,白紙什麼意思,具體發生了什麼,」伯謀將拍攝的部分照片發布在社交媒體後,收到了很多詢問,這讓他覺得自己有義務將更多真相記錄下來,「無論相機還是手機,其實每個人都有義務去記錄、去傳遞、去發聲,否則我們就只能接收那些被篡改的信息。」
抗議過後,不少參與者遭遇了警察的騷擾。據寶榮了解,此前被帶去做筆錄的朋友回家後仍要不時被上門的警察以「流調」為由要求「談談」。凌晨,朋友家忽然響起重而急促的敲門聲,「流調不是防疫辦的事嗎?」朋友如此拒絕後,上門的警察不多久便離開了。
「我們這一代是對89有一些印象的,」丹尼說到,「會對這個體制的冷漠有一個認知,所以看到小朋友們願意出來,覺得很難得。雖然他們未必有公共行動更深的政治意識,但走出來就很難得。」
提及33年前的天安門運動,阿偉認為,兩次大型示威未必有可比性,「89是高度政治化的運動,而這次幾個城市的示威主要還是針對防疫政策,」他覺得,目前示威停留在沒有非常政治化的狀態未嘗不是件好事,「就如今中國大陸的環境而言,能有這樣的一次行動已經很難得,已經是89後再未有過的了。」
阿偉說,兩三年前在國外時,從來不會有所謂「愛國主義」的心態,對由黨國建立起來的「愛國主義」很排斥,回來後也一直想着如何再離開。但11月27日那晚過後,「就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行動者們似乎在現場共同建構起了新的身份認同。「我們意識到可以為自己的生活站出來的時候,變革就已經在發生了,不一定要一些很明確的政治口號。」阿偉說。
「每個人心裏的種子都種下了,我相信有一天有機會的話,我們都會抓住的,都會想表達自己的。」林樂說。
文中姓名均為化名。文中人稱代詞「他」均無關性別。

2017年7月,端傳媒啓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但本文因關乎重大公共利益,我們特別設置全文免費閱讀,歡迎你轉發、參與討論,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瀏覽更多深度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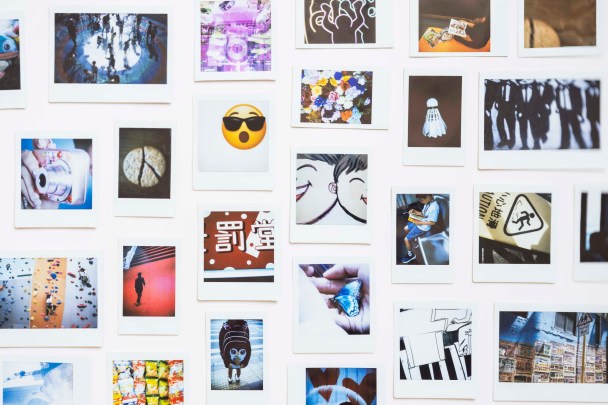
那天去晚了只能在警戒线外围,看到了一直在拍照的长发小哥,也看到了出面谈判的政府官员,但警戒线里面的抗议者一张面孔都没能看清,只是远远依稀听到他们在喊口号,后来就听说有些人还是被事后算帐带去调查,非常担心。感谢端传媒,让我们看到了更详细的报道。
BBC記者訪問烏魯木齊火災死難者家屬(第3條影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3883937
祝平安
谢谢
好。我與你們同在。
可惜種子落在石地裡,怕是發不了芽的。
多谢,平安。
「我們意識到可以為自己的生活站出來的時候,變革就已經在發生了,不一定要一些很明確的政治口號。」阿偉說。
「每個人心裏的種子都種下了,我相信有一天有機會的話,我們都會抓住的,都會想表達自己的。」林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