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詩人楊牧(1940-2020)病逝。報紙上稱他是「距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台灣詩人」,從國際聲名切入,算是方便的標籤,讓對文學不熟悉者立即讀取座標。而另一種觀察我以為更為貼切,消息傳出不久後,台灣小說家朱宥勳在facebook上提出觀察:這位詩人的逝世,除了像過往其他重要詩人逝世那樣立刻湧現大量訊息與哀悼貼文外,幾乎每則貼文都附上了發表者自己喜愛的楊牧詩作,非常多樣,不是只有那一兩首經典,而是涵蓋不同時期、不同主題、不同風格。這樣的致意與引用持續累積,甚至還包含了散文、文論、編輯事業、為故鄉花蓮擘劃大學之理想等方面,顯示出楊牧其作其人其生涯的豐沛、廣闊與吸引力。
此刻我在柏林,手邊沒有任何楊牧集子。就憑綠水洋黑水洋中伶仃浮起的暗影,岩壁上鑿過的線條,記敘一些因緣與體悟。
我的第一部詩集《屏息的文明》由楊牧寫序,那年我二十四歲。願提攜他根本不大認得的新手,我終生感激。該篇序文也刊登於報紙副刊,不久後在某個聚會裡遇見周夢蝶,我自報姓名,老人家面容肌肉牽動,嶙峋大手緊緊一握,我竟聽懂了河南腔國語:「楊牧寫的序,我在副刊上看見了,我就想,要讀讀你的詩。」這是楊牧序的威力。
當年我心頭年輕的神是駱以軍,詩集就想找駱寫序。讀完了詩稿,駱苦口婆心喳喳呼呼勸告:「這個,我不能寫欸,你的詩很名門正派啊,不是我人渣風格,你要不要找同樣名門正派寫啊?」在駱鼓勵之下,厚著臉皮,寫信寄稿子到中研院向楊牧自薦。過了四、五天吧,楊牧竟然親自打電話到我台大宿舍裡,很親切,表示看過了詩,想跟我談一談。
這是我與楊牧頭一次見面。他約在臺北仁愛路上的福華大飯店地下一樓「蓬萊邨」,台菜餐廳。記得他問了:「怕不怕吃肥肉?」其實怕,可是總覺得說怕,太普通人了。這問話是不是一種考驗?肯定得放出一股子瀟灑來。於是大聲說:「不怕!」楊牧笑了,就點了一碟白切肉。後來才聽說,詩人愛吃肥肉,而且切肉刀工不賴。
那天肯定也討論了詩,我卻一點也不記得了。只記得啖了不少肥肉來表示肥肉於我如浮雲。肯定也喝了台灣啤酒吧,楊牧曾寫過一篇極富情味的散文叫〈六朝之後酒中仙〉,歷數詩人酒癖與酒詩,能醉與不醉,能醉的人包括他自己,確實喝了酒以後,他也放鬆許多,能開文壇中人無傷大雅的玩笑。雖然得到楊牧正面回應,那時候不大願意當名門正派。童年時代讀武俠小說,嚮往楊過、金毛獅王或金蛇郎君之類,不受名門正派肯定才酷啊。十餘年下來,我已經明白了我的性情確實不酷,不必妄想。
後來幾回見到,幾次在陳黎辦的花蓮太平洋詩歌節,以及東華大學舉辦的楊牧相關活動。有回在花蓮。與楊牧夫婦同車。車過某處,楊牧立刻提高聲音指給其他人看:「花蓮中學!我的母校!我認為它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學!」我早在楊牧散文中讀過他的中學時期以及青春萌動時的詩啟蒙,當面聽他率直地讚美花蓮中學,還是覺得可愛。
另有一次,陳黎交代我一項任務,要我主持兼與楊牧對談,還要讓楊牧朗讀自己的作品。上場了,楊牧不大願意,只讀了一首,其餘都叫我念。沒練習,現場硬著頭皮朗誦,咦,這典故!這字不認識,怎麼辦,難道「有邊讀邊,沒邊讀中間」?萬一讀錯,豈不讓楊牧看不起?我決定直接求救,把麥克風拿遠,湊近詩人,小聲問:「這字怎麼讀?」楊牧神祕一笑,更小聲地答:「我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比這更不負責任的事情嗎!以上過程不過幾秒內,我只好挪回麥克風,有邊讀邊,沒邊讀中間,咕嚕嚕亂念混過去。可惡,我是不是被整了!
從楊牧那裏我學到,正派或酷派都行,學院內或學院外不會造成任何方面絕對的阻礙。〈《柏克萊精神》自序〉中說:「我又發現有人動輒即稱在學校教書而又弄文學的人為『學院派』,而且好像學院派是很菜的一派。我剛開始被人家稱為學院派,也莫名其妙地恐懼起來了,好像犯罪的感覺。後來我想,學院派有什麼不好呢?一邊看書教書一邊從事文學創作有什麼不好呢?學院派的人可能比較喜歡掉書袋,用典故;然而適量的掉掉書袋,技巧地用用典故,也不是文學的弊病,更可能是文學的拓寬。」不過,流連於書與知識,也可能閉塞,救濟之道在於:「應該常常伸手摩摩自己的胸口,看看他的心在哪裡跳,或者看看他的心還跳不跳。」時時開窗看看活生生的世界,且誠實,敏銳,開放。
奚密教授認定,楊牧扮演台灣現代詩場域中GAME-CHANGER的角色,建立一套新的習尚,改寫價值,影響生態。然而,楊牧詩以困難著稱,望之儼然,中西典故無數,難以親近,就像《紅樓夢》在讀者中的尷尬位置,常常看到「我試著讀過可是──」之類有點不好意思的「懺悔」。但是,無論教學或演講,我從來不會忽略他的詩。不僅僅談台灣現代詩或現代漢語詩歌歷史,他的名字不可能繞過,針對詩的技術或主題的單場講座,也多半能從他詩集中找到合適例子。我從來不認為必須把楊牧每一首詩每一個典故都搞懂才有資格談他的詩,傑出的詩作從來不只一層意思,深層淺層相互映照,偏光或正光,都成風景。

既然認識了楊牧作品的價值,又時時從中得益,難免也醞釀著一股想把那份喜悅與震動傳遞出去的渴望。當我們面對年輕讀者,一方面對於文學懷抱好奇,另一方面,又已習慣手機閱讀情境下欠缺風格的免洗截句,如何使他們能調整目光,也試著走入經典詩人的世界?一味強調其高其偉岸,恐怕不能奏效,反而得從彰顯柔情與徘徊、傳遞鮮明聲響、浸潤生活美趣的詩作為起點。從大詩人的「小」作出發,漸進漸悟,也有其樂趣。
作為大學裡的文學教師,我的方式是這樣:先從〈蘆葦地帶〉、〈聲音〉、〈情詩〉、〈貓住在開滿荼蘼花的巷子裡〉講起。
〈蘆葦地帶〉裡雖隱隱浮出故事形狀,重點不在敘事,是隨著「我」的視線與心情表現出某種猶豫,猶豫背後又存在著更為巨大的情感力量,一點一點逼迫著,逼迫人把手探進自己心裡,安撫那未熄的炭火。教楊牧的詩,一定得讀出聲音來,用自身情感體會讀給學生聽,講解之前就要先讀。聲音本身已提供暗示,像雲凹陷,柔軟的陰影發出呼召。尤其我喜歡讀這段──
那是一個寒冷的上午
我們假裝快樂,傳遞著
微熱的茶杯。我假裝
不知道茶涼的時候
正是彩鳳冷卻的時候
假裝那悲哀是未來的世界
不是現在此刻,雖然
日頭越升越高,在離開
城市不遠的蘆葦地帶
我們對彼此承諾著
不著邊際的夢
在比較廣大的快樂的
世界,在未來的
遙遠的世界
逼迫般的情感就藏在三個「假裝」裡。事實上早明白「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那點熱將要失去,證實那悲哀就是現在此刻。全詩從故作趑趄冷淡,到情感表現漸強,一點一點揭示脆弱,以承認假裝來帶出不再假裝,結尾的「我愛你」才能水到渠成,不顯庸俗。
與〈蘆葦地帶〉可以併讀的,還有〈水田地帶〉,鋪陳以分離為前提的相聚,畫餅充饑似的約定春夏秋冬,顧左右而言他,最後才痛下決心,寫出「為了證明這是幻想不是愛」,如同上一首詩的「假裝」,正言若反,努力想證明一切是幻想,正反襯出愛的呼之欲出與無可奈何。〈不尋常的浪〉也表現了類似心境,「在追憶裡/否認我曾經否認,或者後悔/你以為將來你可能後悔」,究竟是雙重否認還是負負得正?此刻何以否認?過去否認了什麼?將來何必後悔?此刻又如何後悔未來的事物?這句子刻意曲折,所展示無異於〈蘆葦地帶〉裡的「假裝」,愛情最扭曲也最真實的形式。
至於教學生讀〈聲音〉,主要看重單純卻深具微控功力的旋律與節奏:
而世界好像也是很小的了
就像在一把雨傘下了——
只有那麼大。而我也知道
那是心跳了,不是雨點
不是雨點的,因為夜
已經太深了,已經太深
雀鳥都在休息
樹也在休息
雨也休息
只有心他不休息
「不是雨點」和「不是雨點的」,加了個「的」產生什麼效果?兩個「了」,作用是什麼?「休息」三句,「都在」、「也在」、「也」的變化,又能帶來怎樣的聲音變化?情感與聲響又如何配襯?這首詩是最好的示範。
〈情詩〉在聲響表現上也極為傑出,文白混紡本身就能調節節奏,再藉著斷句來讓普通敘述句子也成為節奏的一部分,楊牧最為拿手。同時,以由衷讚嘆的兩次「真好」,和難以自制的兩次「坐在燈前吃金橘」,來營造出俏皮感。那麼,這情詩寫給誰呢?既給「你」,也給屈原(個體化詩人的始祖),更是給詩人所生長的土地,表面看起來謙虛,說自己沒有芸香科那麼美,不過是台灣米仔蘭,「土土的名字/樹皮剝落不好看/生長沿海雜木林中/也沒有好聽的故事」,可是呢:
木質還可以,供支柱
作船舵,也常用來作
木錘。憑良心講
真是土
本地生長,用途多樣化,可支撐可引領可施力,「真是土」,看似自抑,實則自高。我一直把這首詩看作楊牧台灣本土主體的迂迴展現,兼顧複雜詩藝與本土認同。想以詩表現鄉土之情?不是只能直白乾澀或重複那些老掉牙譬喻。
至於教〈貓住在開滿荼蘼花的巷子裡〉,就想讓學生們感受經典詩人也能萌力大開。這首詩不只充滿了浪漫寧馨生活小物件,「光陰很長/很溫柔,像貓貓的鬍子/比吉他的調子更悠遠」──貓貓,天呀,這是楊牧的詩嗎!是那個隨時可以拋出典故如翻天印的楊牧的詩嗎!詩人持續跟隨著貓貓腳步:
是疑似的薯葉,黃昏有雨
打過夢幻芭蕉;貓貓跑進
院子淋雨,麻雀驚飛上屋頂
這貓的面目和名字都好記
她住在開滿荼蘼花的巷子裏
夢幻芭蕉,細雨貓貓,花影下時隱時現。從讀到這首詩開始,我就決定,人生的願望清單要加上一筆:聽楊牧親口說出「貓貓」。(可惜並未實現)
從上述這幾首不同類型、技術、題材的詩,引進楊牧詩藝的小門,就發現裡頭森羅萬象,禁得起長時間探索。耐讀,無窮,因此他是詩人中的詩人,詩人們的老師。
比起多次譜成歌曲的鄭愁予余光中、常被廣告文案化用的夏宇、非文學讀者也聽過的席慕蓉,楊牧的詩從未躋身暢銷行列,也因為不容易摘句與簡化,不那麼「日常化」。最著名的句子,恐怕非「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莫屬,常常在各式社會抗議場合與論述出現,作為起手式,頗具力量,彷彿接下來就要給出答案。事實上,這首詩針對籍貫/省籍問題在台灣社會造成的繩結,設事設景,丟出更多困惑與思考,而非答案。再者,楊牧詩以聲響和曖昧取勝,不像余光中的作品那麼容易擬為中學考題,而主要作為文學學習過程中的高標來被認識,或許也算一種幸運。

最後想提一筆:台灣詩人沈嘉悅曾寫過一首詩,就叫〈我不喜歡楊牧〉,我喜歡楊牧,可我也挺喜歡這首詩。它描述讀不懂楊牧就像「進了停車場/停了車/要出來卻沒有零錢/一樣尷尬」,「你可以開車/但不要停進收費停車場/你可以讀詩/但不要跟人說你不懂楊牧」,「楊牧」被當作「名門正派」、仰之彌高的符號,一道權威的門鎖。但是,讀詩寫詩應該更自由,標準應當更多樣。可不可以不懂楊牧?當然沒問題。不過,假設那一扇小門開了,也不妨走進去看看,裡頭絕無惡犬,但有貓貓,有台灣米仔蘭,有靈妙的聲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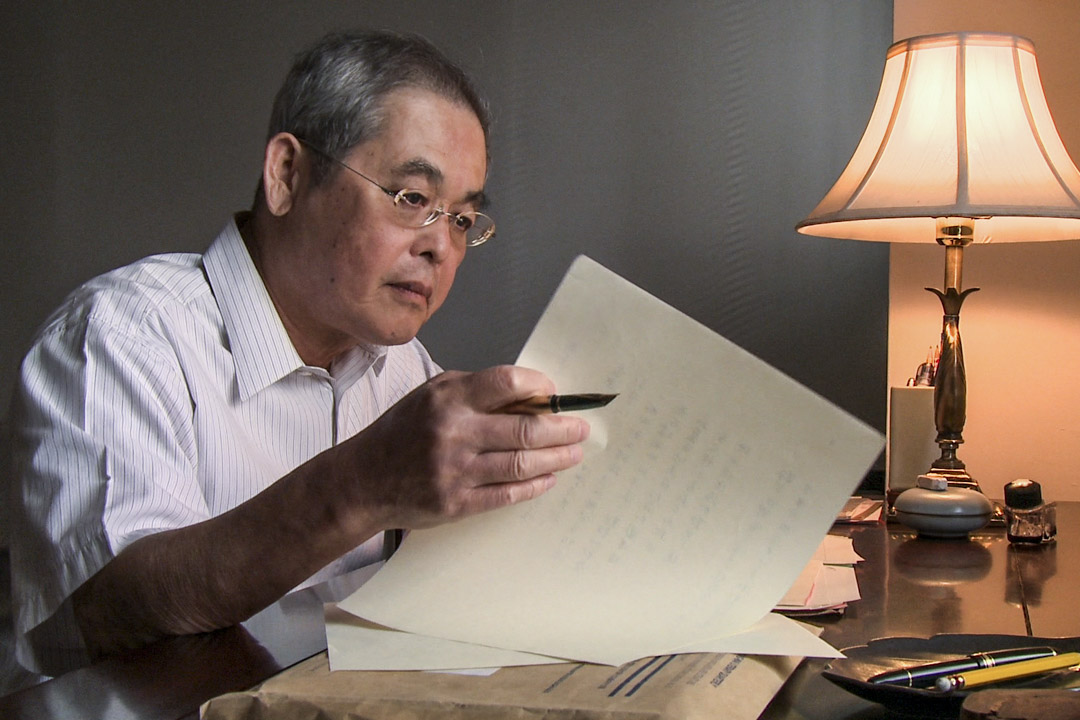




我觉得诗词贴近生活才是诗词的存在
這一篇又不是新詩讀者養成計畫==
還是欣賞 不了
新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