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诗人杨牧(1940-2020)病逝。报纸上称他是“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台湾诗人”,从国际声名切入,算是方便的标签,让对文学不熟悉者立即读取座标。而另一种观察我以为更为贴切,消息传出不久后,台湾小说家朱宥勋在facebook上提出观察:这位诗人的逝世,除了像过往其他重要诗人逝世那样立刻涌现大量信息与哀悼贴文外,几乎每则贴文都附上了发表者自己喜爱的杨牧诗作,非常多样,不是只有那一两首经典,而是涵盖不同时期、不同主题、不同风格。这样的致意与引用持续累积,甚至还包含了散文、文论、编辑事业、为故乡花莲擘划大学之理想等方面,显示出杨牧其作其人其生涯的丰沛、广阔与吸引力。
此刻我在柏林,手边没有任何杨牧集子。就凭绿水洋黑水洋中伶仃浮起的暗影,岩壁上凿过的线条,记叙一些因缘与体悟。
我的第一部诗集《屏息的文明》由杨牧写序,那年我二十四岁。愿提携他根本不大认得的新手,我终生感激。该篇序文也刊登于报纸副刊,不久后在某个聚会里遇见周梦蝶,我自报姓名,老人家面容肌肉牵动,嶙峋大手紧紧一握,我竟听懂了河南腔国语:“杨牧写的序,我在副刊上看见了,我就想,要读读你的诗。”这是杨牧序的威力。
当年我心头年轻的神是骆以军,诗集就想找骆写序。读完了诗稿,骆苦口婆心喳喳呼呼劝告:“这个,我不能写欸,你的诗很名门正派啊,不是我人渣风格,你要不要找同样名门正派写啊?”在骆鼓励之下,厚著脸皮,写信寄稿子到中研院向杨牧自荐。过了四、五天吧,杨牧竟然亲自打电话到我台大宿舍里,很亲切,表示看过了诗,想跟我谈一谈。
这是我与杨牧头一次见面。他约在台北仁爱路上的福华大饭店地下一楼“蓬莱邨”,台菜餐厅。记得他问了:“怕不怕吃肥肉?”其实怕,可是总觉得说怕,太普通人了。这问话是不是一种考验?肯定得放出一股子潇洒来。于是大声说:“不怕!”杨牧笑了,就点了一碟白切肉。后来才听说,诗人爱吃肥肉,而且切肉刀工不赖。
那天肯定也讨论了诗,我却一点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啖了不少肥肉来表示肥肉于我如浮云。肯定也喝了台湾啤酒吧,杨牧曾写过一篇极富情味的散文叫〈六朝之后酒中仙〉,历数诗人酒癖与酒诗,能醉与不醉,能醉的人包括他自己,确实喝了酒以后,他也放松许多,能开文坛中人无伤大雅的玩笑。虽然得到杨牧正面回应,那时候不大愿意当名门正派。童年时代读武侠小说,向往杨过、金毛狮王或金蛇郎君之类,不受名门正派肯定才酷啊。十余年下来,我已经明白了我的性情确实不酷,不必妄想。
后来几回见到,几次在陈黎办的花莲太平洋诗歌节,以及东华大学举办的杨牧相关活动。有回在花莲。与杨牧夫妇同车。车过某处,杨牧立刻提高声音指给其他人看:“花莲中学!我的母校!我认为它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学!”我早在杨牧散文中读过他的中学时期以及青春萌动时的诗启蒙,当面听他率直地赞美花莲中学,还是觉得可爱。
另有一次,陈黎交代我一项任务,要我主持兼与杨牧对谈,还要让杨牧朗读自己的作品。上场了,杨牧不大愿意,只读了一首,其余都叫我念。没练习,现场硬著头皮朗诵,咦,这典故!这字不认识,怎么办,难道“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万一读错,岂不让杨牧看不起?我决定直接求救,把麦克风拿远,凑近诗人,小声问:“这字怎么读?”杨牧神秘一笑,更小声地答:“我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负责任的事情吗!以上过程不过几秒内,我只好挪回麦克风,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咕噜噜乱念混过去。可恶,我是不是被整了!
从杨牧那里我学到,正派或酷派都行,学院内或学院外不会造成任何方面绝对的阻碍。〈《柏克莱精神》自序〉中说:“我又发现有人动辄即称在学校教书而又弄文学的人为‘学院派’,而且好像学院派是很菜的一派。我刚开始被人家称为学院派,也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了,好像犯罪的感觉。后来我想,学院派有什么不好呢?一边看书教书一边从事文学创作有什么不好呢?学院派的人可能比较喜欢掉书袋,用典故;然而适量的掉掉书袋,技巧地用用典故,也不是文学的弊病,更可能是文学的拓宽。”不过,流连于书与知识,也可能闭塞,救济之道在于:“应该常常伸手摩摩自己的胸口,看看他的心在哪里跳,或者看看他的心还跳不跳。”时时开窗看看活生生的世界,且诚实,敏锐,开放。
奚密教授认定,杨牧扮演台湾现代诗场域中GAME-CHANGER的角色,建立一套新的习尚,改写价值,影响生态。然而,杨牧诗以困难著称,望之俨然,中西典故无数,难以亲近,就像《红楼梦》在读者中的尴尬位置,常常看到“我试著读过可是──”之类有点不好意思的“忏悔”。但是,无论教学或演讲,我从来不会忽略他的诗。不仅仅谈台湾现代诗或现代汉语诗歌历史,他的名字不可能绕过,针对诗的技术或主题的单场讲座,也多半能从他诗集中找到合适例子。我从来不认为必须把杨牧每一首诗每一个典故都搞懂才有资格谈他的诗,杰出的诗作从来不只一层意思,深层浅层相互映照,偏光或正光,都成风景。

既然认识了杨牧作品的价值,又时时从中得益,难免也酝酿著一股想把那份喜悦与震动传递出去的渴望。当我们面对年轻读者,一方面对于文学怀抱好奇,另一方面,又已习惯手机阅读情境下欠缺风格的免洗截句,如何使他们能调整目光,也试著走入经典诗人的世界?一味强调其高其伟岸,恐怕不能奏效,反而得从彰显柔情与徘徊、传递鲜明声响、浸润生活美趣的诗作为起点。从大诗人的“小”作出发,渐进渐悟,也有其乐趣。
作为大学里的文学教师,我的方式是这样:先从〈芦苇地带〉、〈声音〉、〈情诗〉、〈猫住在开满荼蘼花的巷子里〉讲起。
〈芦苇地带〉里虽隐隐浮出故事形状,重点不在叙事,是随著“我”的视线与心情表现出某种犹豫,犹豫背后又存在著更为巨大的情感力量,一点一点逼迫著,逼迫人把手探进自己心里,安抚那未熄的炭火。教杨牧的诗,一定得读出声音来,用自身情感体会读给学生听,讲解之前就要先读。声音本身已提供暗示,像云凹陷,柔软的阴影发出呼召。尤其我喜欢读这段──
那是一个寒冷的上午
我们假装快乐,传递著
微热的茶杯。我假装
不知道茶凉的时候
正是彩凤冷却的时候
假装那悲哀是未来的世界
不是现在此刻,虽然
日头越升越高,在离开
城市不远的芦苇地带
我们对彼此承诺著
不著边际的梦
在比较广大的快乐的
世界,在未来的
遥远的世界
逼迫般的情感就藏在三个“假装”里。事实上早明白“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点热将要失去,证实那悲哀就是现在此刻。全诗从故作趑趄冷淡,到情感表现渐强,一点一点揭示脆弱,以承认假装来带出不再假装,结尾的“我爱你”才能水到渠成,不显庸俗。
与〈芦苇地带〉可以并读的,还有〈水田地带〉,铺陈以分离为前提的相聚,画饼充饥似的约定春夏秋冬,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才痛下决心,写出“为了证明这是幻想不是爱”,如同上一首诗的“假装”,正言若反,努力想证明一切是幻想,正反衬出爱的呼之欲出与无可奈何。〈不寻常的浪〉也表现了类似心境,“在追忆里/否认我曾经否认,或者后悔/你以为将来你可能后悔”,究竟是双重否认还是负负得正?此刻何以否认?过去否认了什么?将来何必后悔?此刻又如何后悔未来的事物?这句子刻意曲折,所展示无异于〈芦苇地带〉里的“假装”,爱情最扭曲也最真实的形式。
至于教学生读〈声音〉,主要看重单纯却深具微控功力的旋律与节奏:
而世界好像也是很小的了
就像在一把雨伞下了——
只有那么大。而我也知道
那是心跳了,不是雨点
不是雨点的,因为夜
已经太深了,已经太深
雀鸟都在休息
树也在休息
雨也休息
只有心他不休息
“不是雨点”和“不是雨点的”,加了个“的”产生什么效果?两个“了”,作用是什么?“休息”三句,“都在”、“也在”、“也”的变化,又能带来怎样的声音变化?情感与声响又如何配衬?这首诗是最好的示范。
〈情诗〉在声响表现上也极为杰出,文白混纺本身就能调节节奏,再藉著断句来让普通叙述句子也成为节奏的一部分,杨牧最为拿手。同时,以由衷赞叹的两次“真好”,和难以自制的两次“坐在灯前吃金橘”,来营造出俏皮感。那么,这情诗写给谁呢?既给“你”,也给屈原(个体化诗人的始祖),更是给诗人所生长的土地,表面看起来谦虚,说自己没有芸香科那么美,不过是台湾米仔兰,“土土的名字/树皮剥落不好看/生长沿海杂木林中/也没有好听的故事”,可是呢:
木质还可以,供支柱
作船舵,也常用来作
木锤。凭良心讲
真是土
本地生长,用途多样化,可支撑可引领可施力,“真是土”,看似自抑,实则自高。我一直把这首诗看作杨牧台湾本土主体的迂回展现,兼顾复杂诗艺与本土认同。想以诗表现乡土之情?不是只能直白干涩或重复那些老掉牙譬喻。
至于教〈猫住在开满荼蘼花的巷子里〉,就想让学生们感受经典诗人也能萌力大开。这首诗不只充满了浪漫宁馨生活小物件,“光阴很长/很温柔,像猫猫的胡子/比吉他的调子更悠远”──猫猫,天呀,这是杨牧的诗吗!是那个随时可以抛出典故如翻天印的杨牧的诗吗!诗人持续跟随著猫猫脚步:
是疑似的薯叶,黄昏有雨
打过梦幻芭蕉;猫猫跑进
院子淋雨,麻雀惊飞上屋顶
这猫的面目和名字都好记
她住在开满荼蘼花的巷子里
梦幻芭蕉,细雨猫猫,花影下时隐时现。从读到这首诗开始,我就决定,人生的愿望清单要加上一笔:听杨牧亲口说出“猫猫”。(可惜并未实现)
从上述这几首不同类型、技术、题材的诗,引进杨牧诗艺的小门,就发现里头森罗万象,禁得起长时间探索。耐读,无穷,因此他是诗人中的诗人,诗人们的老师。
比起多次谱成歌曲的郑愁予余光中、常被广告文案化用的夏宇、非文学读者也听过的席慕蓉,杨牧的诗从未跻身畅销行列,也因为不容易摘句与简化,不那么“日常化”。最著名的句子,恐怕非“有人问我公理与正义的问题”莫属,常常在各式社会抗议场合与论述出现,作为起手式,颇具力量,仿佛接下来就要给出答案。事实上,这首诗针对籍贯/省籍问题在台湾社会造成的绳结,设事设景,丢出更多困惑与思考,而非答案。再者,杨牧诗以声响和暧昧取胜,不像余光中的作品那么容易拟为中学考题,而主要作为文学学习过程中的高标来被认识,或许也算一种幸运。

最后想提一笔:台湾诗人沈嘉悦曾写过一首诗,就叫〈我不喜欢杨牧〉,我喜欢杨牧,可我也挺喜欢这首诗。它描述读不懂杨牧就像“进了停车场/停了车/要出来却没有零钱/一样尴尬”,“你可以开车/但不要停进收费停车场/你可以读诗/但不要跟人说你不懂杨牧”,“杨牧”被当作“名门正派”、仰之弥高的符号,一道权威的门锁。但是,读诗写诗应该更自由,标准应当更多样。可不可以不懂杨牧?当然没问题。不过,假设那一扇小门开了,也不妨走进去看看,里头绝无恶犬,但有猫猫,有台湾米仔兰,有灵妙的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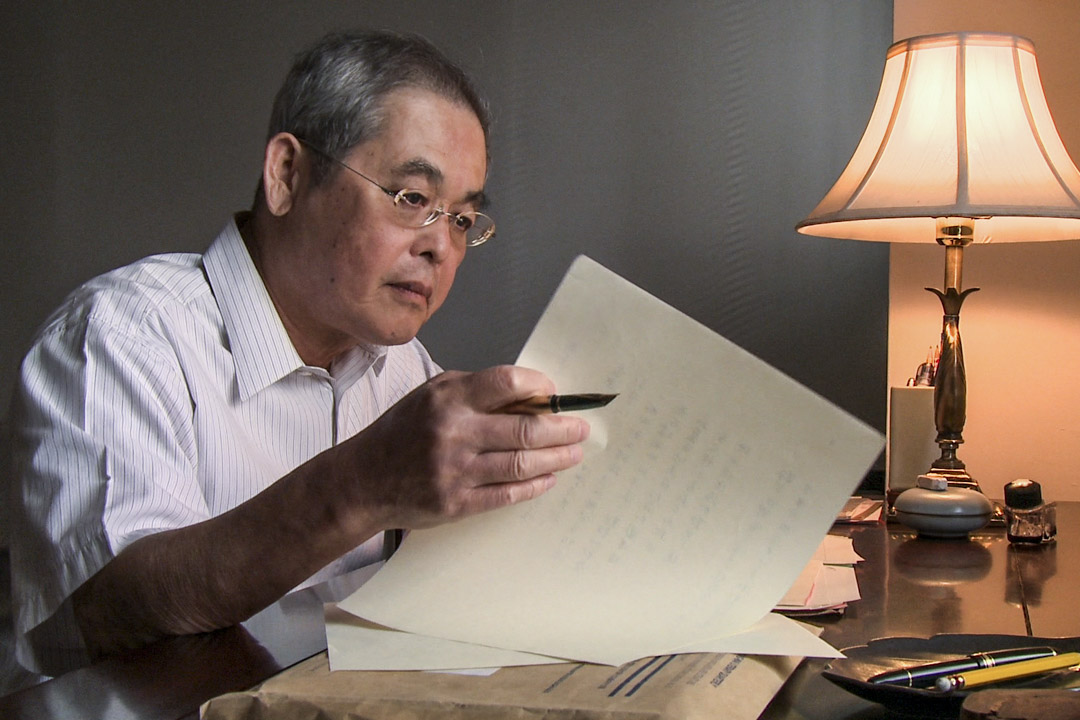




我觉得诗词贴近生活才是诗词的存在
這一篇又不是新詩讀者養成計畫==
還是欣賞 不了
新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