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賴恩(Brayan Rupe)看着我,一時說不出話, 下意識地把手指指着自己。「第一次見屍體?」他說,「四歲的時候。」
這是2019年3月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們在卡利(Santiago de Cali),南美國家哥倫比亞的第三大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兇殘的地方之一。 謀殺率以每10萬居民為單位,在全球絕大多數國家或城市,這個數字都是個位數,在住有240萬人的卡利,每年每10萬人中就大約有40人被殺。
23歲的布賴恩在卡利土生土長,我長這麼大都還沒見過兇殺屍體,這讓他很是驚訝。他決定分享一下孩童時的經歷。他說,他生活的那一片,被卡利人稱為「白水」(Aguablanco),是這座城市暴力和兇殺案最為集中的地方。在那兒,每當發現屍體,大家都會聚到現場。第一次聚過去的時候,布賴恩記得很清楚,他才四歲。 「一天早上,每個人都在喊:殺人了、殺人了、殺人了!然後我叔叔把我抱在肩上……帶我去看看。」
「屍體被扔進了一個裝滿混凝土的滾桶裏,這樣,就沒人可以把他帶走」,布賴恩回憶道。他戴着一副有塗層的眼鏡,我很難看清他的眼睛。停了停,他又補充說:「我回家害怕了好幾天,被那具屍體的樣子嚇壞了。」
兇殺傳染病學
在卡利,兇殺是一個公共衞生問題。
1992年,一名傳染病學家格雷羅(Rodrigo Guerrero)被選為卡利市市長。作為醫生,格雷羅習慣性地翻開了公共衞生報告,他發現,遠超其他疾病,兇殺才是這座城市的頭號死因——1993年,卡利的兇殺率是十萬分之124(作為對比,智利那個年份前後的凶殺率為十萬分之2.9)。格雷羅提議,既然是公共衞生問題,就可以用傳染病學(epidemiology)的方法來控制謀殺。
格雷羅現年81歲,帶着友好的微笑,顫抖的聲音和沉重的眼鏡,他笑着說:「當時,我把它稱之為『傳染病學方法』,因為沒人聽過這個詞,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傳染病學通過對疾病傳播模式的研究來控制疾病。將兇殺與原因不明的疾病進行比較,聽起來很創新,其實本質就是數據收集和分析,更好地了解問題,然後對症下藥。只是,要把兇殺問題管起來,在格雷羅前,卡利還沒有哪位市長願意去嘗試過。

半個多世紀以來,哥倫比亞一直在與自己作戰。早有1940年代到50年代被稱為「The Violence」(“暴力”)的、造成20萬人死亡的內戰。之後有左翼游擊隊運動,反叛亂的準軍事組織和該國武裝部隊相互作戰,在各地襲擊、爆炸、綁架和暗殺。儘管有意識形態起源,但時間一久,這些武裝力量開始越來越多地圍繞着可卡因的生產和出口而鬥爭,游擊隊和準軍事組織都依賴毒品獲得資金。
源自哥倫比亞共產黨的游擊隊組織FARC(哥倫比亞革命武裝組織)就是如此,他們在某個時刻控制了哥倫比亞60%的可卡因生產;而最初為了打擊游擊隊而建立的準軍事組織,也最終成為哥倫比亞的主要販毒網絡。在這一過程中,包括軍隊和警察在內的國家機構也嚴重腐敗。
因此,剛開始把卡利的兇殺當做傳染病來研究的時候,格雷羅覺得,要對卡利謀殺負責的「罪魁禍首」,定是那些強大而殘暴的毒販集團。但當格雷羅好不容易集合警局、醫院、法庭等等機構的數據後,他發現,若是排除事故或政治暴力,這座城市三分之二的兇殺案都是出於個人動機,而且很多都是在發工資的那個週末,或是新年夜、母親節這樣的假日,因酗酒、爭吵和氾濫的槍械而發生,並非因為毒販。
「毒販就像是艾滋病毒,襲擊防禦機制,讓身體在面臨其他病毒時變得脆弱。」多年後,格雷羅在一篇題為《謀殺解藥》的文章中寫道,毒販讓這座城市的警力和法治極為脆弱,因而無法應對其他造成兇殺的因素。當時,卡利警方每年僅能指認8%的謀殺嫌疑人。
格雷羅打算對症下藥,即便治不了艾滋病毒,但能清掃一下其他的症狀。他要求酒吧實行宵禁,並限制攜帶槍支,這些措施很快就產生了效果。一年後,兇殺率從1993年的每10萬人124例,降到了1994年的86例。
這一傳染病學方法,很快成了包括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Bogota)和很多拉美國家城市的「範例」。若能尋得控制謀殺的「解藥」,很多拉美城市都會心動——全世界超過三分之一的兇殺,都發生在只佔全球人口8%的拉美國家。
不過,當格雷羅在20年後,也就是2012年到2015年期間,再次當選為卡利市長,並再次梳理這座城市的謀殺數據時,他發現,如今,有組織的犯罪行為構成了卡利2/3的兇殺案。此時,卡利正在急速擴張,人口從1993年的180萬增加到了240萬,失業和經濟不平等也隨之激增。
哥倫比亞正經歷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期」。主要的游擊隊和準軍事組織與政府達成了和平協議,開始解除武裝。最近的一次大型和解,便是2016年的和平協議。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Dos Santos)因此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仍有一些武裝力量拒絕投降,並繼續毒品業務。生意很好。哥倫比亞的可卡因生產,在過去5年中增長了兩倍,2017年和2018年都創收穫紀錄,再次成為世界第一的可卡因生產國,主要出口到美國。
夾雜着政治、毒品的內戰和衝突,常常將平民作為籌碼和掠奪對象,造成了極多難民。如今,哥倫比亞有770萬在國內流離失所者(IDP),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多,包括敘利亞在內。卡利便是很多流離失所者的逃亡目的地。在過去的15年中,超過20萬前戰鬥人員和受害者來到卡利。而且,這一負擔在城市內部分布不均。這些戰爭受害者和前戰鬥人員幾乎沒有經濟手段,常常落入一些充斥着暴力和貧困的社區,也很可能加入這些社區的犯罪團伙。

大幫派消失了,城市更暴力了
在一條平靜、綠樹成蔭的街道上,端傳媒記者見到了莫斯克拉(Yesid Perlaza Mosquera),一個健壯、帶着微笑的中年男子。乍見到他,你絕對猜不到莫斯克拉曾是一位著名的販毒集團成員。而且據他說,他是一個「傳說」級別的人物。
莫斯克拉堅持說完自己的人生故事。20世紀90年代,他14歲的時候,因為足球踢得好,他加入了當時哥倫比亞最大的毒販集團:「北谷」(Norte de Valle)。足球是這個國家最為重要的運動,而毒販則是這項運動的主要投資者之一。
「小時候我一直想要阿迪達斯的鞋子,」莫斯克拉解釋他加入毒販集團的原因。 「我父親買不起,有一次他把所有的生活費都花了,給我買了雙冒牌鞋子,但不到兩個星期就穿壞了。」加入了販毒集團,就會有收入,他逐漸可以買下大把大把的阿迪達斯,裝滿整個屋子。毒販們都喊他叫「阿迪達斯男孩」。
莫斯克拉一直往上爬,成了一個頗重要的頭目。直到2004年,莫斯克拉所在的團伙與同一個毒販集團的對手開始了激戰。殘酷的毒品戰爭下,莫斯克拉不得不離開這座城市。 帶着大筆錢財,在哥倫比亞另一個大城市麥德林(Medellin)狂歡了多年之後,莫斯克拉兒子的母親在一次搶劫中喪生。這件事,莫斯克拉說,說服了他重新開始。回到卡利,莫斯克拉開始在教堂幫忙。「這個時候,我已經沒有任何從毒販時期留下的東西了。」
卡利天主教會得知了他的歷史,在2015年要求莫斯克拉去幫助卡利最糟糕的街區,尤其是幫派成員。莫斯克拉覺得他可以用自己的經歷向今天在卡利活躍的幫派成員證明,「你可以離開那樣的生活。」
「可是,現在的卡利,比以前更暴力了」,莫斯克拉說。
可以主導整個哥倫比亞的販毒集團,像莫斯克拉所在的「北谷」毒販集團,或同期的「卡利」集團,在1990年代解體,接替他們的中小型販毒組織也陷入流血衝突。今天,卡利市的政府官員認為,卡利已經沒有一個整體的犯罪結構。毒品販賣並沒有消失,但被一些小型的犯罪組織控制,這些組織給鄰里幫派提供毒品,槍支和摩托車。

這些「中小型毒販」會僱傭幫派成員殺人或搶劫,曾經「壟斷」一座城市的毒販某種意義上也維持着社區的秩序,但中小型毒販不會這樣。小幫派可以不受控制地互相爭鬥領地至死,這可能是卡利市的暴力程度仍然很高的原因。
卡利有僱傭殺手的傳統,提供有償的謀殺服務。為了協助這些殺戮,卡利提供穩定的武器供應——除了由軍隊發放的近70萬件「合法」武器以外,該市還有自制槍支武器的工廠。實在手頭緊的話,你甚至可以以小時為單位租到槍,買幾發子彈就行。
儘管極難準確統計,但據市政官員的說法,約有600個幫派團夥(西語稱為Pandilla,也即英語的Gang,港譯古惑仔、台譯流氓,大陸常稱地痞,本文統一稱作幫派成員)在卡利活躍,每個團伙通常都有6到8名年輕人,佔據各自所在街區的角落。他們大多13-14歲就離開學校了,有的因為要幫襯家人,有的因為無聊,無論如何,沒有背景沒有參考,他們都看不到人生什麼前途。他們沾染上各種毒品:可卡因,大麻,或是「basuco」,一種廉價、類似冰毒的可卡因衍生物;接着,他們就開始通過出售毒品,來購買毒品供自己使用。街頭幫派的上頭,還有被稱作「Bands」的毒販和犯罪團夥,提供毒品和武器。
這正是布賴恩加入幫派的路子。
黑洞
布賴恩是12歲的時候加入了街頭幫派。他說,那個幫派的領頭人送給他少量的毒品,「那就是我幫派生活開始的時候」。接受了這些毒品,便讓布賴恩成為該團伙的一部分。除了幫派生活以外,他一無所知,「為了金錢和毒品,我做了很多『壞事』。」
從4歲開始,死亡就不再是一件遙遠的事情。看著幫派裏的槍戰和殺戮,看著周圍發生的一切,布賴恩說,「我可能在25歲前就死了。」
當布賴恩聊着生死,聊着第一次看到屍體的經歷時,他的朋友維克多(Victor Rataria),一個20歲的年輕人,一直看着別處。他的頭有些緊張地抽搐着。 維克多的父親在他還是一個嬰孩時就被殺了;他五歲時,他的叔叔站在他身邊被射殺。
他剛從少年監獄出來。「長大後,我充滿了憤怒並被謀殺所吸引,」他平靜地說,他也像布賴恩那樣,做很多「壞事」。「十歲的時候,我很已經擅長這些事情了,我做得非常好。毫無憐憫。」
這不是誇大其詞。當曾經的毒販頭目莫斯克拉帶着他的新角色——幫助像布賴恩和維克多這樣的孩子們走出幫派生活——走進卡利最貧窮的幾個社區時,這位深諳世事的黑幫老大也被震驚了。

他說,在第一次去某個社區探訪的時候,他看到有一條街道的電線上掛滿了鞋子。「滿滿的,根本數不過來,」莫斯克拉回憶那個景象,「我就問這些掛着的鞋子是什麼?」
一旁的年青幫派成員說,那是他們殺掉的人的鞋子——戰利品。附近的人們每日必須在這些鞋子底下通過,這條街便是一條「無形邊界」(invisible borders)。
「無形邊界」這一說法反覆出現。它們標誌出幫派的「領地」,在這條分界線上,敵對團伙激烈而持續地打鬥。當一個團伙控制着某個邊界內的販毒活時,來自另一個幫派的人一旦越過這條邊界,就會被殺死。更多的人是在幫派火併時喪生。
古斯塔沃(Gustavo Andres Gutierrez)把我們領到了6號社區一條曾經的「無形邊界」邊上。
6號社區裏頭有一片街區叫做Petecuy,這是16世紀曾組織土著軍隊抵禦西班牙殖民者的一個當地領袖的名字,也曾是卡利最致命的街區,緊鄰着緩慢流淌的Cauca河。以前,屍體會被丟到河裏,因此這條河也被稱為「死亡之河」。
古斯塔沃來自這個社區,他帶着我們走到一條狹長的街道的末端,兩邊都是小小的磚房,門窗裝著欄杆。「以前,我們管這兒叫做『洞』(the hole),所有的壞事最終都被丟到這裏——贓物,屍體,你知道的,就像一個黑洞。」古斯塔沃停下腳步,轉過頭,檢查着我們的表情,「有人來這兒拍一部叫《Petecuy, the movie》的黑幫電影,演員都是在當地選的。但花了十年才拍完。」
古斯塔沃慢慢地解釋:「因為他們換了五個主角,因為這五個主角都在片子沒拍完的時候,就陸續被殺了。」連接着「洞」的那條街道,也是一條「無形的邊界」,兩邊的團伙在邊界的兩端爭搶領地。
在走進 Petecuy 前,卡利的保安部秘書長 Andres Villamizar 將我們帶到他辦公室的大地圖前,展示了這座城市兇殺最為集中的地方,他指着環繞着城市東邊的幾個街區,這便是「白水」。布賴恩來自那裏,莫斯克拉也來自那裏。
止暴有效,可選民在意嗎?
在2012年再次回到市政廳的格雷羅決定雙管齊下:一邊打擊有組織犯罪,一邊針對很多幫派群體改善社區,並稱之為「社區包容和機會」項目(Territories of Inclusion and Opportunities)。這也是現任市長阿米蒂奇(Norman Maurice Armitage)延續下來的政策,在市政廳,我拿到一張傳單:「防止暴力的綜合模型」。這個模型下有許多項目,大多可以在今天的 Petecuy 找到。
古斯塔沃在 Petecuy 出生並長大,街坊鄰里都認識他。正在鋪設道路的三名工人走來跟我們聊了一會兒。他們二十多歲,穿着卡其布工裝,看起來很專業,但都忙不迭地承認,他們要向「真正的」工人學習:三位都是前幫派成員。
古斯塔沃帶着我們參觀社區裏為了防止暴力而設置的計劃:一個提供免費午餐的公共活動室,一個全新的游泳池,有漂亮的灌木和草坪。那條「隱形邊界」現在也有了新的面貌:巨大的塗鴉鋪滿了街道兩邊的牆面,巨大的動物、和平的鄰里、為未來而奮鬥的口號。街道中間,還有一間小小的「貧民窟圖書館」,一旁寫着:「五顏六色的街道是和平的街道。」

類似的項目也出現在其他「白水」社區裏頭。
那天早些時候,我們站在13號社區的一個「公園」裏:一塊有着幾片草叢和一些散落着的樹木的空地。很多人來慶祝這兒重新開放的一間圖書館,並且種下樹苗,綠化公園。一旁,十多個十來歲的男孩在一塊混凝土球場上踢足球。
社區領袖米里亞姆(Miriam)個子矮矮的,模樣堅毅。她說,幾年前,這個公園被新來的幫派「入侵」了,公園一角成了「隱形邊界」。父母不再讓他們的孩子來這兒的舊圖書館玩,因為這邊變得太危險。最終,米里亞姆說他們去請市政廳介入,投資給圖書館建新樓。
有趣的是,這樣的項目也吸引了那些幫派小年輕。這天,好些以前的幫派成員也來幫忙種樹,有些敦實的查臘(Clever Chala)就是其中一員。他戴着眼鏡,笑容滿面,衣服已經沾滿了泥土,T恤上寫着:「愛麗絲夢遊仙境」。他說,這塊地以前只是一片泥地,不同社區的孩子們聚在一起踢球也是極為難得。只因為水泥球場少見,大家為了能夠踢球,決定和平共處。
在附近長大,查臘很熟悉街頭幫派的模樣,小時候總是害怕,想躲着走;但長大一些,幫派生活變得有吸引力,「他們看起來很酷,能買得起漂亮的衣服。」
光鮮有代價,加入幫派,就要打架。查臘指着公園的一角——「總是要在這兒跟其他幫派打架。如果有其他幫派的人闖過來,那麼他一定會被我們用槍或用刀襲擊。」
當市政廳在公園裏的圖書館還在建的時候,查臘和同夥們還佔據着公園另一邊。一天,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拿着一項提議過來跟查臘打招呼。簡單的舉動,改變了查臘的生活。如今,他已經不再混幫派了,甚至還唸完了高中。
同一個提議,也讓布賴恩和維克多擺脱了幫派生活。
他們三人都參與了卡利市政廳推行的「和平促進者」(Peace Promoters)項目。目前,已有750位年輕人蔘加了這個項目,為了讓幫派成員們更好地融入社會,市政廳給他們提供教育、諮詢和不同工作的機會,並會給他們付18個月的收入。
離開幫派生活,穿上市政廳派發的藍色T恤,布賴恩開始有夢想了。「我想成為一名心理學家,」他說,過了一會,又補充說:「我還在學彈吉他。以前,我爺爺總是試着教我吉他,但我當時並不感興趣。」我才注意到,他脖子上紋有一個音符。
穩定的工作和一個未來的可能性是這些孩子們的希望。格雷羅和現任市長的措施看起來很有效果,卡利的謀殺率在下降。2018年,卡利發生了1154起兇殺案,這比2013年的1959起,下降了41%。2019年1月到5月,卡利僅有375例兇殺,比2018年同期又有下降。
對於一個長期因毒品戰爭和持久武裝衝突而聞名的國家而言,卡利的兇殺率正在講述一個成功的故事,並且受到國際媒體的關注。
不過,有些諷刺的是,卡利市民可能並不在意。

四年一任的卡利市長要在2019年年底換人了。如果這些針對街頭幫派和暴力行為的項目無法得到選民的支持,下一任市長可能不會把這些項目堅持下去。
對於普通卡利市民而言,兇殺案只集中在城鎮的幾個地方,那些「壞」社區,人們平時壓根不會涉足。而且,卡利市安全秘書長告訴我,發生在那兒的謀殺總被視作是「罪犯相殺」。很多普通市民可能不會贊成市政廳把預算投資在貧困的社區。
這樣的項目還有「道德風險」,卡利市政府負責人權和建設和平的副秘書長博特羅(Felipe Botero)說:「想像一下,在市民眼裏,那些曾經在當地幫派中販毒、搶劫的年輕人,怎麼現在就穿上了市政廳派發的衣服?」給混跡在毒品和殺戮中的幫派成員工作機會,很多人會視其為不正當的激勵。
包括「和平促進者」在內的項目,並沒有耗掉市政廳太多預算。博特羅說,他們像是一個協調員,遊走在市政廳各種基建、教育、醫保項目裏,試着加入一層「防止暴力」的視角,譬如建設育嬰所或開展課後的體育活動,讓單親媽媽們不必把孩子丟在危險的社區裏。又或是邀請像莫斯克拉這樣的「前幫派成員」介入當下的小幫派,言傳身教,給這些還是青少年的孩子們一個離開的動力。
很難給出直接證據,到底是怎樣的措施在讓卡利的謀殺率下降?單個項目給人積極的印象,但效果難免有限:免費育兒所接納了少數單親孩子;一個公共圖書館,改變了一個幫派和一個公園;幾個插畫家,讓一條「隱形邊界」變了模樣,但不遠的下一個街區,就會出現下一條「邊界」……市政官員告訴端傳媒,這些項目能夠進入「白水」社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市長的執政意願。若下一位市長不再緊抓,脆弱的貧窮社區將很難抵制暴力文化的衝擊。

後記
在 Petecuy 見到的最後一個人是威爾遜(Wilson),外號「殭屍」,戴着一副反光太陽鏡,骨瘦如柴。他是這個社區幫派生活的老手,經歷過很多幫派的來來往往。如今他參與了市政廳針對幫派的援助計劃,對自家社區年輕人進行「干預」,也穿着一件市政派發的T恤。
快下午5點了,威爾遜身邊圍着一些人,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孩,她跟著威爾遜,因為有些害怕如今的小幫派,還有一個社區警察。道路另一頭,一對情侶模樣的年輕人捕捉到我的眼神,狠狠地盯了回來。很快,市政廳的博特羅連番打電話過來,語氣擔心:「你們真的得離開了。」
古斯塔沃說,Petecuy 的安全問題已經有所改善,2015年的時候,一個月至少有一起謀殺,如今,頂多每年出現兩到三次。然而,作為一個長着外國臉孔的陌生人,在夜幕降臨後還在附近閒逛,顯然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主意。我沒有聽完威爾遜的故事,但只得說再見——他說他的兒子還年少就失蹤了,說他依然擔心街區的安全問題,一切只是在慢慢復甦。
車子慢慢開出白水社區,同行的翻譯和司機都鬆了口氣。街邊模樣也有變化,早前的6號或13號社區,家家戶戶都在門窗上裝了嚴實的防盜柵欄。小賣鋪也不例外,只留下小小一個口子收錢。到了市中心,當代大都市的標準配置,從酒吧、高檔社區到藝術中心、咖啡館、精緻的西餐廳、日料店,一一出現。或許這才是最堅不可摧的「無形邊界」。暴力、兇殺、毒品、幫派……好似留在了另一個宇宙。日落前,我們與一些路人搭訕,大家都紛紛表示心知肚明哪裏是安全、哪裏是危險,買車也會裝上深色玻璃。
白水那邊,他們幾十年都不曾去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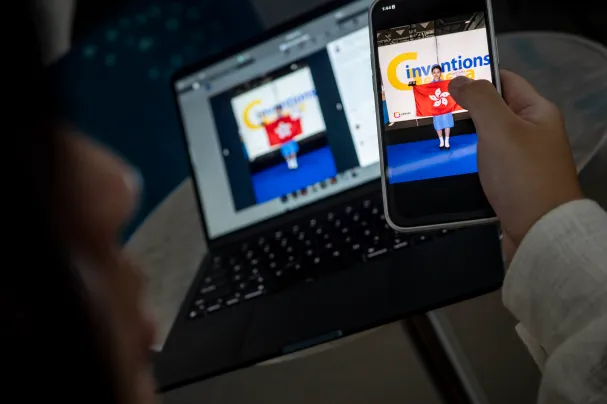

多謝作者。
额,毒品泛滥暴力肆虐是民主造成的吗,不太理解楼下说民主的另一面究竟意指什么🤔
很棒的文章,謝謝!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Netflix的narco,拍得很好,可以见识到90年代初,哥伦比亚毒贩的嚣张跋扈
好文
民主的另一面
我对哥伦比亚的了解更多地来自于影视作品,为了戏剧效果大多是直接和暴力犯罪相关的。这样的好文章毫无疑问地丰富了知识的维度,让我知道了卡利除了贩毒集团之外还有各种其他角色。
好看!
很棒的文章
好棒的一篇深度文!希望能看到更多這類的文章,華語界中有來自中南美洲的第一手報導真的很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