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只是一場夢,只有死亡才是醒來。——Gerd Leins
在傳統的藝術圈,德國藝術家 Gerd Leins 是個異數,作品獨一無二,完全隨心所欲,從不用擔心別人的目光,亦不考慮生計;在傳統的商人圈,他又是一個另類,從不將藝術品商業化,不以藝術牟利。
藝術家和商人兩個身份,像是平行空間裡的另一個自己,完全獨立。
作客 Leins 工作室,隨處可見他從沙灘上撿來各種裂開的石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不可複製的偶然,這是他追求的殘缺美 。三十年前自製的桌椅,由幾何圖形拼成,後來被爭相模仿。現在用起來仍有樂趣。屋內衣櫃、書架都是歪牙裂爪,不規則造型 。「太規範的一切,令人感到無趣。」對他來說,不怕死,只怕悶死。
他有一手好廚藝,經常呼朋喚友,不醉無歸。切洋蔥時他流著淚說:「 太好了,順便可以洗一洗眼睛,再洗一洗心靈。」屋外下雨了,他說:「 現在跑步正好!」他總是令人出其不意。
老師說他是「失敗者」
數年前Leins被邀請到德國北部小城 Buxtehude 做展覽。他大刀闊斧做了一個重口味的作品:金魚缸裡裝著死刺猬和死兔子。此舉引起軒然大波,甚至是一場騷動。當地流傳一個刺猬用計謀叫兔子跑死的民間故事。而兔子和刺猬都是城市的「 吉祥物」。
Leins 對自己的惡作劇津津樂道,原來,他甫抵當地便撿到一隻被車撞死的刺猬,又見到一隻兔子在屠宰店被殺,這些偶然的見聞令他靈感大發,他收起兩具尸體裝進金魚缸,用福爾馬林浸泡并放置在城市廣場展出。
當地人強烈抗議他的作品,最後醉酒的保安更戲劇化地砸了他的大作。Leins 卻漁人得利,意外得到一大筆保險賠償。
他一臉坏笑地說:「作品是為了諷刺人們的虛偽。童話裏的狡猾的刺猬怎麼快也快不過現在的汽車,最後刺猬是被人駕駛的車撞死的。你們既然尊重兔子為何又吃兔子,卻看不得兔子的死尸?」
相信他身上的黑色幽默和批判性是與生俱來的。
年幼的他天生有種超然的叛逆,是學校最令老師頭痛的小魔鬼。有次,他上課時在課堂搗蛋講笑話,逗得全班捧腹大笑。老師盛怒之中打了他一巴掌,他卻笑得更大聲。老師拎著他去找校長,結果校長不在,他更是像被點穴一樣大笑不止。那瘋狂的笑聲一語道破了當年教育的弊端:「他們要求人人似啞巴不要說話,實在太滑稽了!」
後來,因為他成績差,他又被老師批判為「失敗者」。他當然又是仰天大笑:「將我教成這樣子,你才是失敗者吧!」老師氣哭了。
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頭腦裏就已裝著一個老靈魂。他年幼時便思考「 意識」這個問題:「 個體的意識到底是個什麼東西?他們跟其它的事物有什麼樣的關聯?時間是什麼?對於開始與結束、生與死的疑問隨之而來。」
十多歲的時候,他在病理學專科實習,出於好奇悄悄溜進去解剖室,看到各樣的尸體、各種的器官,還有一個較為完整的「 睡著了女人」,「 人死時原來那麼安靜。」這是他第一次看到死人留下的印象。
收集訃告
每天,58歲的他從自己經營的連鎖店下班時,便回到作為藝術家的「平行空間」創作「訃告藝術」。
他的兩間工作室,一間白屋,一間黑屋。在這兩極的視覺衝擊中,他日復一日地剪報收集德國報紙上的訃告,作品命題是「 死亡」,牆上的畫布貼滿了德國各地的死亡消息。
「死亡是世界上唯一公平的事情。一張張的訃告,是人生最後的‘證書’。」
Leins拿起一張訃告仔細地看,每個故事都耐人尋味:這個孩子十年前已經去世,今天家人依然掛念他;這位先生1942年在二戰中陣亡,今天後人依然紀念他;一位女士的家人、公司、好友同時都為她刊登了訃告……「在這些死亡消息中,我讀到很多愛與思念。」
有一次,Leins讀到了一位老人的死訊。幾天後,老太太的訃告也出現在報紙上了,失去了老伴的人實在已經生無可戀了;另一則訃告透露,男人失去了太太和兩個孩子。Leins陷入沉思:他到底會憑藉什麼信念繼續活下去呢?或許是只能代替所愛的人走完他們沒有走完的人生路。
「一個人死了,依然會存在於別人的記憶中,直到這些記住他的人也都死去。當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遺忘了他,這才是一個人真正的死亡。」他說,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注重思考及關注過程中的感覺。死亡是一種感受,愛也是。人大多數時間都是孤獨的,唯有愛讓我們好受一些。
死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一百年前,你有足夠時間經歷死亡。現在,你只是醫院的行政編號,因為大多數人,最後一程是在醫院度過的。「現代社會的日常,我們對於死亡最直觀的接觸,也許就是報紙的訃告。」
Leins通常在酒後開始創作,像讀詩一樣讀出每一個生者對逝者的描繪。有的人在病魔手中做了很持久的戰鬥,有的人英年早逝,有的人活到一百歲,有的人意外突然身故……他觀察到,一個人離去時,往往被華麗的語句措辭為他們人生作結,「 即使發佈者與死者有過節,也不會說出半句壞話。」
他總是一邊讀,一邊將訃告粘在畫布上。讀完手頭的訃告,他整體構思已經完成了。訃告的版面大小,透視出其社會地位。他特意將地位顯赫的知名人士和無名小卒貼在一起,安排的一視同仁的「 墓碑」次序,疏密有序。
畫布很快被訃告鋪滿了。他用油灰刀全神貫注地將黑色顏料「批」上訃告,黑色顏料將亡者的個人信息抹去了,下手十分用勁,鏗鏘清脆,「這是一場搏鬥。」不一會兒他已汗流浹背了。在黑色乾掉之前,他又塗上一層白色,而黑色與白色混合,出現的是灰色,每一個細節都有自己的格局,單獨成為一個舞台,給人無限的想像。
漸漸地,整個畫布處於混沌中,報紙的墨色印記從在這片混沌中滲透出來。
當白色疊加在黑色之上撲朔迷離地覆蓋了整個畫布,他以黑色畫上無數個十字架,訃告已經在黑與白亂中有序的交融中消失了。
他說,最後一步是用X光一照,訃告全部信息又重現了。「只有意識到自己的生存,你才是活著。活著只是一場夢,只有死亡才是醒來。」
我們從未為自己存在過
Leins習慣將對於死亡的思考寫進詩裡。詩和訃告都是由文字組成的。他通過符號來表達自己,而用來表達一個人死亡、意識消失的符號是訃告。黑色是代表結束,象征空無(nothing)的符號;白色是代表開始,象征所有(all)的符號
。「我將這些符號轉化成一種視覺感應。從遠處看,大家只看到圖象;走近了,會在一些圖象裡看到一部分訃告,原有的信息。然後,一些跟第一感覺毫不相干的問題突然出現了。這是什麼?人們開始反思死亡。他們通過這種方式回歸自己。」
Leins的巨幅作品,大片的黑色與大片的白色背後,覆蓋著人生光怪陸離的真相。
「在社會裡的我們,通常都離我們自己很遠。消費是生活的目標。手機已經成為我們意識的一部分。死亡這個話題被壓抑住了,它只存在於電腦遊戲和電視裡。我們思考,如何通過自我意識的電子化,得到永生。這也是一種轉化,人們由此忘記了現實,無論現實是什麼樣子的。」
從黑到白的過渡中,彷若完成了一個人生命的轉化,這近乎一種儀式。而轉化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我們的一生是從開始到結束的區間,在這一區間裡,時間就是我們每個人的意識。也就是說,時間轉化成了意識。我們死去之後,我們便失去了這個意識,也失去了我們對自己的回憶。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從未為自己存在過。在我看來,灰色意味著我們的意識,也就是時間。白與黑,即開始與結束,是永恆的統一。
你害怕死亡嗎?
「我並不害怕死亡,也許有點害怕死的方式。我不知道什麼是人生,我也不能信仰什麼。我們的個體意識消失的同時,我們將失去所有關於自己的回憶。仿佛在宇宙的終點,時間與空間的盡頭,我們從未存在過。但這並沒有什麼不好,我們只是不能夠理解。所以只有過程才是目標。現在,也就是此時,即是永遠。」說完,他畫上了最後一個十字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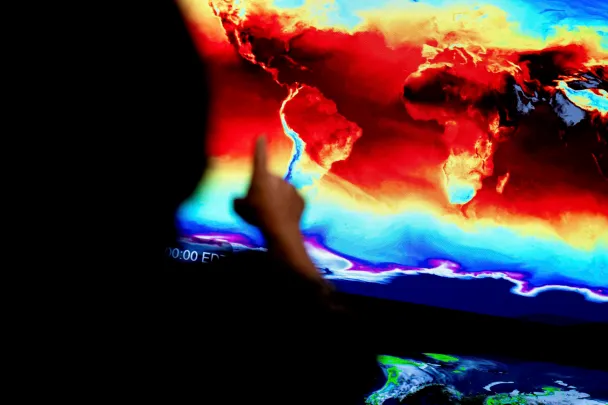

我家是祖传“糊纸”的,从汉代开始传下来的手艺,就是给死人“盖房子”,到我这就要失传了。不过我打算利用每次回家的机会,采访我爸爸(他还在做这个),写本关于死亡的书。他每一年接触到数十个人的逝世,爸爸很喜欢去了解死者的故事,有钱的没钱的,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很好的题材,我觉得。
怎么只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