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4日,上海女子沙白在瑞士通過輔助自殺手段離世,並留下一系列視頻解釋自己的生死觀和價值觀,在中文互聯網上先是引發眾多惋惜和讚歎之聲,隨後又引發一波口誅筆伐。斯人已逝,音容杳然,但安樂死、輔助死亡、輔助自殺等話題由此再度進入公眾視野(三者在倫理和法律後果上有區別,但鑒於在「尊重當事人求死意願」這一本質上沒有根本差異,本文不作詳細辨析)。
沙白之死不僅讓人回想起2018年罹患胰腺癌而求死的台灣著名體育主播傅達仁的先例,而且就在近一年來,法國和英國都曾出現過類似的著名人物尋求輔助自殺的事例。但相關人物並不滿足於「一死了之」,而是在生命最後時刻向主政者喊話,努力讓自己的死亡成為推動公眾進一步正視、社會心態進一步開放的契機;公共輿論也沒有淪為一場失焦的混戰,並且得益於政治上吐故納新的契機,在制度層面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就。
在英國,罹患晚期腸癌的53歲女子寶拉·馬拉(Paola Marra),今年3月20日在瑞士通過輔助自殺結束生命。在臨終之前,她留下一段視頻,批評英國在有關安樂死法律上的保守態度導致「不公且殘忍」的局面,並給英國各政黨領導人發出一封公開信,呼籲他們儘快在議會中推進安樂死和輔助自殺合法化進程。在法國,著名歌手弗朗索瓦絲·哈蒂(Francoise Hardy,亦譯阿迪)因喉癌於6月11日去世,享年80歲。哈蒂之死並不是安樂死或者輔助自殺造成的(因為她的身體狀況已經無法支撐出國旅行),但她本人在生前曾多次表達相關願望,尤其是2023年12月17日曾公開致信法國總統馬克龍(馬克宏),要求能儘快讓安樂死在法國合法化。
隨著現代醫學和科技的進步,億萬富翁斥重金推動生物技術突破、甚至親自上陣通過「換血」和基因改造等方式延緩乃至逆轉衰老的新聞屢屢見諸報端,「不死」似乎正在成為富人所竭力追求的一種特權(儘管眼下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而在生命的另一端,雖說「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但一個平靜的、有尊嚴的、免於極度痛苦的死法,同樣是可遇而不可求。「安樂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種「特權」,與經濟實力、法權身份、輿論關注、社會觀念等高度相關,而非人人可以獲得的「權利」。正是在這一點上,寶拉·馬拉和哈蒂都意識到自己的「特權」。她們尋求的不僅僅個人的解脫,同時也是「為民請命」,呼籲當局重視和自己一樣飽受疾病摧殘、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可憐人。但在華人世界,這一話題還遠遠沒有得到相應重視,甚至受到刻意壓制。

寶拉·馬拉:「拒絕讓絕症支配我的餘生」
在近期所有事例中,英國的寶拉·馬拉或許和中國的沙白最有相似之處:和眾多垂垂老矣的臨終者相比,她們辭世時都還正值中年;而且在生命的最後關頭,都留下視頻作為此生的印記。只不過和快意恩仇的沙白相比,寶拉·馬拉用溫和鎮定的口氣,留下了一篇檄文、一聲號角。
年僅53歲的寶拉·馬拉,生前備受晚期腸癌困擾,這種疾病持續下去,將會導致腸破裂和敗血症,而她偏偏又對大多數用於鎮痛的阿片類藥物過敏,因此在生命末期將註定會承受難以想像的痛苦。於是她萌生了前往瑞士尋死的念頭,並得到了著名安樂死機構「尊嚴」(Dignitas)的接納。在準備後事的過程中,她前往倫敦一家工作室拍攝肖像遺照,攝影師得知真相後倍感震驚,但看到她已經下定決心,於是提議拍攝一部視頻,作為對這個世界的遺言。
在這部名為「最後的要求」的視頻開頭,寶拉·馬拉開宗明義地告訴觀眾:「當你看到這個(視頻)時,我已經死了。」她解釋說,之所以選擇輔助死亡,是因為「拒絕讓絕症支配我的餘生」——痛苦會變得越來越無法忍受,尊嚴也會被緩慢地侵蝕,她將失去自理能力,「所有讓生命值得經歷的東西,都會被剝奪殆盡」,在這種困境下,「輔助死亡不是要放棄,而是要重新獲得掌控;它並非事關死亡,而是事關尊嚴,是給予人們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帶著同情和尊重來結束痛苦的權利」。
這份遺言的目的,不是為了自辯,而是為了呼籲公眾推動改變英國有關輔助死亡的法律。在同時致英國各政黨領導人的一封公開信中,寶拉·馬拉悲歎,鑒於英國法律對安樂死的嚴厲態度(1961年的《自殺法》禁止「鼓勵」和「協助」自殺行為,違者最高可能被判14 年監禁),她不僅無法在英國得到相應服務,而且不得不孤身一人飛往國外,以免給親友惹上麻煩。在她看來,現狀既不公平,又很殘忍。因為對於許多無法拿出15000英鎊前往瑞士結束生命的垂死之人來說,他們只能被迫在痛苦中死去,或者選擇自殺。她希望在自己離世一周年之際(2025年3月),英國的安樂死合法化進程能夠取得真正的進展,給垂死之人提供選擇的權利。

希克曼:人生跑道的終點是海灘
在寶拉·馬拉辭世兩個月後,另一位英國女性特拉西·希克曼(Tracy Hickman)於2024年5月也通過輔助自殺離世。希克曼此前罹患乳腺癌,病情在一度穩定之後,於2023年2月復發,並迅猛擴散到骨骼和大腦。她在治療過程中備受煎熬,日夜依靠嗎啡來鎮痛。相比充滿不確定性地痛苦多活兩三個月,她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死亡。
作為長跑愛好者,希克曼在短短57年的人生中曾經充分燃燒了自己的生命。她在全世界參加了30多場馬拉松比賽和8場超級馬拉松比賽,甚至2023年癌症復發之後,她仍然完成了波士頓馬拉松。5月22日,在這條人生跑道的終點,希克曼在伴侶和家人的陪伴下,躺在紐西蘭一處陽光明媚的海灘上接受醫療團隊的注射,平靜地告別了這個世界。
相比孤身淒涼上路的寶拉·馬拉,希克曼幸運地同時擁有紐西蘭國籍,這使得她能夠滿足紐西蘭相關法律的要求。即便如此,她在臨終前也向英國政界呼籲:「看看紐西蘭所做的一切吧,然後做得更好。 對生命權已經有很多關注了,但人們也應該有平靜、安詳地死去的權利。「而她生活在英國、同樣患有乳腺癌(此外還有帕金森症)的妹妹,眼下只能悲涼地面對自己的命運。
在2024年7月的英國大選中,此前一直敵視安樂死立法的保守黨遭遇歷史性慘敗,寶拉·馬拉和希克曼的遺願,迎來前所未有的實現機會。工黨政府上台後推出了法案,給予生命只剩六個月的成年絕症患者結束生命的權利。目前法案正處於議會辯論階段,如果最終通過,將改寫英格蘭和威爾斯的現行規則。而在單獨立法的蘇格蘭,2024年3月提交的一份法案建議給予罹患絕症晚期的蘇格蘭成年居民結束生命的權利,目前該法案仍處於早期階段,預計於2025年提交投票。在北愛爾蘭,雖然相關立法進程尚未啟動,但目前第一大黨新芬黨(Sinn Féin)、第三大黨聯盟黨(Alliance)、第五大黨社民工黨(SDLP)都表達了積極態度。與此同時,英屬澤西島和馬恩島議會的相關立法進程,也都在2024年取得了重大進展。在社會觀念和政治格局的共同推動下,整個英國的堅冰正在鬆動。

哈蒂:殘生看到了開頭,卻沒能等來結果
在法國,近年來最為矚目的輔助自殺事例,是「新浪潮」電影奠基人之一、導演戈達爾(Jean-Luc Godard)於2022年9月13日在瑞士離世,享年91歲。而2024年去世的著名影星阿蘭·德龍(Alain Delon),儘管擁有瑞士國籍和長期生活經歷,生前也曾表達過安樂死願望,但未及實現就病逝於法國的家中(一個插曲是:阿蘭·德龍的遺願之一是讓他的愛犬安樂死陪葬,但由於動物保護組織的反對而未能實現)。
就在戈達爾去世的同一天,法國國家倫理諮詢委員會(CCNE)作出一項表態,認為在「嚴格條件」下,「積極」協助死亡可以合法化。這標誌著該委員會態度的重大轉向,同時意味著給下一步的立法行動亮出綠燈,此前它曾拒絕修改2016年的「克萊埃-利奧內蒂法」(Loi Claeys-Leonetti)。該法律禁止安樂死和輔助自殺,只允許醫生為極其痛苦、預期壽命即將結束的絕症晚期患者實施「深度而持久的鎮靜措施,直到死亡」。在該委員會的表態之後,馬克龍發起的「公民大會」(Convention citoyenne)也在辯論後於2023年4月公佈了相同的立場。
在這兩起引人矚目的表態後,法國殿堂級歌手法蘭索瓦絲·哈蒂投書媒體,發表致總統馬克龍的公開信,呼籲在法國推進安樂死合法化。哈蒂在18歲時曾以一首《所有的男孩和女孩》聲名鵲起、並成為此後幾代法國人的偶像。但進入老年後,她罹患淋巴癌和喉癌,飽受病魔和放射治療副作用的折磨:劇痛、耳聾、呼吸困難、無法分泌唾液導致進食困難......她形容自己的生活已經完全淪為「一場噩夢」,「當一個人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並且無法治癒時,不結束他們的痛苦是不人道的。」
耐人尋味的是,哈蒂在致馬克龍的公開信中,通篇都沒有抱怨自己的痛楚,而是以平淡語氣講述了所見所聞的三件事:一是法國著名電影導演和編劇弗洛倫斯·瑪律羅(Florence Maltaux)罹患肌萎縮側索硬化的悲慘境遇;二是自己的母親同樣罹患肌萎縮側索硬化之後,在兩位「富有同情心和勇氣」的醫生的説明下,事實上採取安樂死方式離世(她自己也在這一過程中成了規避法律的「同謀」);三是自己在治療癌症期間遇到的其他絕望病人期盼安樂死的心聲。哈蒂沒有懇求總統對她個人的同情,而是呼籲後者能對沒有治癒希望的重病患者感同身受,儘快將安樂死合法化。
在殘生的最後六個月時間裏,哈蒂等來了法國政府提交包含解禁輔助自殺的「生命臨終法案」,卻來不及看到這一法案走完冗長的立法日程。「生命臨終法案」原本是馬克龍總統第二任期的重頭戲,但在即將完成一讀審議之前,馬克龍於6月8日解散議會,三天之後哈蒂在病痛中離世。而此後的議會選舉導致右派和極右派勢力崛起,再加上財政危機的衝擊,這一法案面臨著更加不確定的未來。

「膠囊自殺艙」:激進創新的「民主化」思路
在受基督教文化影響深厚的歐洲,自殺長期以來被視為一種罪孽,直到19世紀之後才逐漸被看作是相對正常的社會現象。早在1942年,瑞士率先將輔助自殺(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安樂死)予以合法化;進入21世紀後,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國跟進。而自2020年代以來,隨著戰後「嬰兒潮」一代老去,人口老齡化和臨終關懷壓力加大,德國、西班牙、奧地利等國陸續將輔助自殺合法化,這一潮流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擴展。
在天主教傳統深厚的意大利,儘管還沒有相應立法,但憲法法院廢除了起到直接阻礙作用的刑法條文,首例輔助自殺於2022年6月得以實施,44歲的男子卡博尼(Federico Carboni)在遭遇車禍導致癱瘓多年後,「我終於可以自由地飛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了」。
在同樣深受天主教影響的葡萄牙,議會三年來四度通過輔助自殺法案,但均被保守派總統德索薩(Marcelo de Sousa)駁回,最終經議會於2023年5月按照原文再度投票通過後,總統被迫按照憲法規定簽字放行,最終完成了立法進程。
迄今為止,幾乎所有允許安樂死或輔助自殺的國家,都將精神疾病排除在外,換句話說,只有難以忍受的肉體痛苦,才能成為結束生命的正當理由。但一個顯著例外是荷蘭,不僅明確將(嚴格意義上的)安樂死合法化,並為精神疾病患者為保留了通道,而且相關數量逐年遞增。2024年5月,有抑鬱、焦慮、創傷、人格障礙和自閉症等多重精神疾病,但沒有任何嚴重身體疾病的29歲荷蘭女子佐拉亞·特·比克(Zoraya ter Beek),經過長達10年的失敗治療和3年半的評估之後,成功獲得審批,並於5月22日通過輔助自殺離世,成為相關領域新趨向當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案例。
在這股潮流衝擊下,在運作歷史最悠久、也是迄今為止唯一允許外國人在境內實施輔助自殺的瑞士,倫理和制度堤壩也持續面臨著壓力。正是在這裡,出現了迄今為止最為激進、也最令人不安的「創新」。
根據瑞士現行法律規定,患者只有在不治之症並且承受難以忍受的疼痛、同時具有健全判斷力,才能尋求輔助自殺。但2022年5月,瑞士醫學科學院(SAMS)修訂了相關條例,要求醫生在出具診斷書之前,必須和患者進行至少兩次深入談話,而且間隔至少兩周,並且重申不能接受為非絕症患者實施輔助自殺。這一條例本身沒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但作為瑞士醫生協會的基本職業守則,對醫生有職業道德上的約束力。條例的修訂,不僅意味著確認對非絕症患者關上了大門,而且適格人群也面臨著更高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對外國人來說尤其如此。
但與此同時,另一個方向上出現了規避管制、實現「自助式自殺」的新趨向:早在2019年就已經面世的「自殺膠囊艙」,在飽受爭議之後首次正式投入使用。
2024年9月23日,在瑞士沙夫豪森州Merishausen鎮附近的森林中,來自美國的一位64歲匿名女性躺進名為Sarco(意為石棺)的「自殺膠囊艙」。 艙蓋關閉後,她親手按下釋放氮氣的按鈕,艙內氧氣濃度在30秒內急劇降低,她無痛苦地陷入昏睡,大約五分鐘後因缺氧而死亡。
這位美國女性平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但送她踏上最後一程的人,卻面臨著司法上的大麻煩。瑞士警方當天在現場拘捕了四人,其中包括專門為推廣該儀器而成立的安樂死協會The Last Resort的主席和律師,設備也被沒收,自殺者遺體送交法醫進行屍檢。這一設備的發明者、澳洲人菲力浦·尼奇克(Philip Nitschke)在德國遠端監控膠囊艙的運作,免於當場被捉。儘管被拘捕者兩天後獲釋,但檢方已經宣佈針對「誘導、協助和教唆自殺」的罪名提起刑事訴訟,一場漫長的法律戰才剛剛開始。

不僅瑞士當局對「自殺膠囊艙」持否定態度,當地幾乎所有的安樂死機構也對該設備並不認可,最主要的質疑來自兩方面:一是瑞士目前的主流模式是「醫療輔助自殺」,即必須有醫務人員介入,但在Sacro目前的運作模式下,病人只需提交精神狀態證明、確認有正常認知和判斷能力即可,醫生作為最後一道「防火牆」的作用無從發揮(更不必說「兩次談話、間隔兩周」 等技術性要求);二是這種模式讓人處在完全孤獨的密閉空間裏離世,缺少親人送別和祝福,彷彿一個「微型毒氣室」,在本質上是不人道的。
但發明人和推廣者的思路則完全反其道而行之,認為有些人就是希望用最少束縛的方式,獨自度過生命的最後一刻,既不需要「白大褂」,也不需要「親友團」,而醫生也可以由此免除職業倫理困境——此前瑞士已經出現過醫生因為給非絕症患者(自願陪同患有絕症的丈夫離世)實施輔助自殺、而遭遇司法追訴的例子。
「自殺膠囊艙」並不是高科技精密設備,運作機制非常簡單,此外,氮氣成本低廉,通常不是管制物資,許多國家並不需要醫生處方就可以獲取(甚至瑞士主流的「醫療輔助自殺」模式下也偶爾使用)。據Sarco的推廣者稱,為了實現「人人用得起」的理念,「自殺膠囊艙」基本上是免費使用的,用戶僅僅需要為氮氣支付18瑞士法郎。而在現有輔助自殺機構中、通過醫生處方獲得致死劑量的安樂死用藥戊巴比妥,要收費1萬到1.5萬瑞郎。按照推廣者的說法,相比花掉最後一點積蓄來尋求死亡,「這要平等得多」,「你不必很有錢也可以有一個體面的死亡」。
耐人尋味的是,Sarco一度被稱為「安樂死特斯拉」,其發明人尼奇克也被稱為「輔助自殺界的馬斯克」,但實際上,穿透工具性的器物層面,它更接近於馬斯克的另一樁生意——腦機接口所提出的挑戰:即技術進步有可能重塑倫理的邊界,它隱隱暗示了某種「安樂死民主化」的趨向。在尼奇克看來,死亡權是一項人權(更確切地說,「平靜的死亡是理性成年人的權利」),而不是一種醫療或法律特權,任何人都不應該被「是否病得足夠重才有資格死」的規則所束縛,只要年滿70歲的人都應當有選擇死亡的權利。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激進創新」一旦遭遇人性「滑坡」,其負面後果也完全不難想像。現有膠囊艙可以通過3D列印製造,這就意味著,一旦模型檔開源,或者有其他類似更簡易模型出現(例如刪減遠端監控生命體徵的功能),這一產品的製造技術壁壘很容易被突破。此外,如果推廣者無意或無力對申請者的材料進行嚴密確鑿的審核,這輛「安樂死特斯拉」不僅難以實現「自動駕駛」,更可能遭遇濫用,成為一輛「死亡列車」。

談或者不談,問題都在那裏
在歐洲,對安樂死或者輔助自殺的討論,基本上限定在一個高度「情境化」的語境裏,即主要針對在生命晚期康復無望、又無法維持最基本的體面生存的人群。此外,整個收入分配製度和社會福利保障可以提到某種「托底」作用,這個話題不容易逸出它原本所在的領域,演變成「羡慕你可以如此不顧死活」、或者「人生的路怎麼越走越窄」的大範圍共鳴,而一旦逸出這一領域,則折射出某種整體性的社會心態危機、一種「人礦」隱隱枯竭、「說明大家都不想活了」的危機。
沙白面對生死的態度無論多麼動人,這一故事很大程度仍然是個人化的。不管這種生命體驗多麼熱烈而絢爛,如果無法從個人經歷上升到集體觀念水位提升、並進而凝聚成為制度共識,那麼終將是曇花一現。
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弔詭現象:在一個據說是「集體本位」的社會中,客觀上享有「特權」的先行者(用沙白自己的話說,她「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得到了很多一般人都得不到的東西」),高揚「個人價值」的旗號、無意對整體福祉負責、甚至有意識地與之劃清界限;而在一個據說是「個人本位」的社會中,在安樂死道路上先行一步的寶拉·馬拉、希克曼和哈蒂,對自身在無形中所享有的「特權」不乏認知,並且在相當程度上擺脫了對「我」的執念,從個人命運推而廣之到公民同胞的福祉,展現出一種「社會有機連帶」。而在傅達仁及其家人對安樂死理念的推廣上(儘管不乏爭議),則可以看到「集體本位」的社會中,這種連帶關係是如何展現的。
這種反差,固然有「刻板印象」造成的認知偏移,但同時也體現了不同政治體的價值偏好。從特權到權利,其中關鍵一環是立法確定普遍規則、適格標準和防範濫用機制,但這已經遠遠不是輿論口水戰能夠解決的,而是留給政治與政制的考題。
讓生命之火已接近熄滅的公民,從人生體面退場,借用寶拉·馬拉的話說,這「不是要放棄,而是要重新掌控」,是讓尚未走到這一步的公民意識到尊嚴、解脫、出路的存在,從而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命運,而不是在「未富先老」的下行洪流中,在對人兼對己的絕望中滑向失控。安樂死或輔助自殺議題本身,固然只涉及社會邊緣的一小部分人(隨著人口規模的遞增,這「一小部分人」的絕對數量也極為可觀);但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方式——或者索性拒絕討論——則折射出社會對於生命本身的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纏綿病榻的癌症晚期患者,和戾氣橫生的街頭戮童兇手,雖然在現實中罕有重合,但面對的是同構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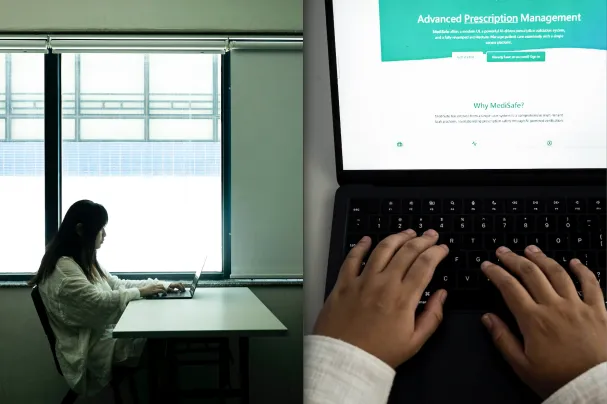

評論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