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有個叫“D-EVIL”的南京 RAP 團體在國內走紅,他們的成名曲目叫做《喝餛飩》,裏面有很著名的一句念白:「阿要辣油啊?」
隨着這首Rap的盛行,全國人民對南京話的印象都是這一句。即使在香港,碰到新知舊雨,知道我原籍金陵,都會很熱情地調侃,阿要辣油啊?
這短短的一句,要念出韻味,殊非易事,要帶着「蘿蔔味兒」來,節奏感很重要。「阿」是短促的入聲,「油」則要念得回味綿長。這一抹鄉音,猶在耳畔,其中的冷暖,聞者自知。
說起南京這座城市,浸染千百年的歷史煙雨,是公認的風雅。吳敬梓先生在《儒林外史》裏頭說,「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即使下里巴人,收了工都要跑去雨花台看落日,這城市可算文藝到了極點。可是南京話卻常常叫人笑話,大約聽起來語調莽直,又帶着一點顢頇,和風雅多少有點不襯。聽過人投訴張藝謀導的《金陵十三釵》,裏頭的名妓說城南的老南京話。秦淮脂粉,衣香鬢影,顧盼生姿。一開了口,乖乖隆地冬,一下子都變成了市井大妞,也是無奈得很。每每外地朋友說起南京話的「土」,我便很想為其正名。依現代的語言審美,南京話也曾悅耳過。往遠裏說,六朝以前,南京本地通行的是吳地方言,近乎於「蘇白」。五胡亂華、衣冠南渡後,東晉定都南京。南北朝漢人口大批南遷,帶來中原洛陽雅言。洛陽雅言流行於上層社會和知識階層,又稱「士音」 ;而並存的金陵本地居民語言吳語則稱「庶音」。這一來在南京,語言就成為劃分階層的標誌,前者有點類似英國的 RP 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很貴族高冷。頗有家世的當朝首相卡梅倫都不敢說,怕在民間丟了選票,不得不對自己的上層口音作出改良。好了,語言分化的確不利於團結,雅言和吳語逐漸融合成為一種新的口音,叫「金陵雅言」。這就十分接近現在的南京話了。由此,金陵雅言以古中原雅言正統嫡傳的身份被確立為中國漢語的標準音,就此成為中國的官方語言。明代及清代中葉之前歷朝的中國官方標準語均以南京官話為標準。從聲韻學的角度,南京官話有入聲、分尖團、分平翹,是傳承中古音最完美的官話,其影響之深遠,遠至海外。幾百年來周邊國家如日本、朝鮮所傳授、使用的中國語皆是南京官話。明清時期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所流行的也是以南京官話為標準的中國話,傳教士麥嘉湖稱官話以「南京腔為各腔主腦」。及至民國初年西方傳教士主持的「華語正音會」,也以南京音為標準。甚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時美國最初的漢語教學也是基於南京語音。清末編審國語及民國確定新國音以後,北京官話成為中國官方的標準語,南京話作為「國語」才漸漸退出歷史舞台。
「難得南京話裏的罵人話﹐句句都是擲地有聲。含義裏是透徹骨髓的怨與怒。說多了﹐融到了說話人的字裏行間去﹐也融到了這個城市的血脈裏去。這些骯髒的字眼﹐就好像這種方言裏的『之乎者也』,鑲嵌進去,倒是成就了一番韻味。沒了它們的南京話,是不地道的南京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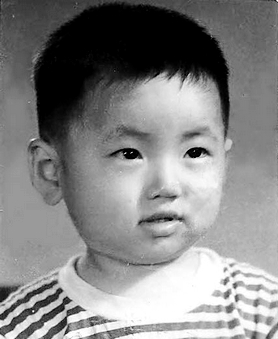
經歷這一番「必也正名乎」。有朋友就要說,當年是國語如何,做過普通話又如何,南京話還是「土」。在我看來「土」與「雅」實在也是見仁見智。《紅樓夢》雅不雅?可是裏頭的南京話,據金正謙的考辨,八十回裏有一千兩百多處,且用得絲絲入扣,毫無違和感,盡顯鮮活與淋灕。少年遷京,南京話仍是曹雪芹的母語。關於《紅樓夢》與南京的關係,葉靈鳳寫過專文,在這裏就不說了。就只說南京話,精彩已不勝枚舉。舉個例子,第二十四回裏便出現了這麼一段:「賈芸聽他韶刀(叨)得不堪,便起身告辭」。南京話說囉嗦嘮叨,只一個字,叫「韶」,精當之至。要說《紅樓夢》裏頭的老南京,皆出身金陵世家史侯,一是傻白甜史湘雲,「愛哥哥」叫得一個熱鬧。一便是女王範兒的老賈母。以賈母在這家裏的地位,向來不怒而威。可真要動了怒,罵起人來,便活脫就是個嘴尖舌利的南京老太太。第四十四回王熙鳳因吃醋和賈璉鬧糾紛,向賈母投訴。賈璉負荊請罪,賈母罵起孫子來是絲毫不口軟,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守己的挺屍去,倒打起老婆來了!」南京人常把喝酒戲稱為「灌黃湯」,罵人時把睡覺說成「挺屍」。這個鄉俗口氣,頓時讓賈母的形象大大地接上了地氣。說起南京的粗口罵人話,源遠流長。賈母的潑辣魯直,如今在13號線公交車的售票小姑娘身上,仍然薪火相傳。有關於此,我在長篇小說《朱雀》裏寫到過,「難得南京話裏的罵人話﹐句句都是擲地有聲。含義裏是透徹骨髓的怨與怒。說多了﹐融到了說話人的字裏行間去﹐也融到了這個城市的血脈裏去。這些骯髒的字眼﹐就好像這種方言裏的『之乎者也』,鑲嵌進去,倒是成就了一番韻味。沒了它們的南京話,是不地道的南京話。在南京話裏,好得一逼,就是,就是 pretty good。你習慣了它,也明白了它的用途,並沒有這麼刻薄與怨毒。也就曉得,有時候,它不過是作為句逗或者語助詞。它像是情緒的催化劑。有了它,表達的快樂是加倍的快樂,表達的親熱也是加倍的。比如,你說一個「好」 字,遠沒有說「好得一逼」 這樣淋瀝而由衷。」
當年曹雪芹的一縷鄉情,流瀉筆端,倒替現代南京話保留了許多遺跡。《紅樓夢》裏頭寫到的「孤拐」(顴骨)「馬子蓋」(即「馬桶蓋」,兒童的髮型)、「小杌子」(沒靠背的小板凳),如今大約除了老一輩,年輕的南京人已經不懂什麼意思。南京話與許多方言一樣,也在走向式微,凋落。不過,我常感慨歷史的強大與曼妙,南京與南京話有它的幸運之處。前兩年,我專程去了一次黔西腹地,去尋訪安順當地一支奇異的部族,屯堡人。這部族也稱「京族」,在貴州少數民族雲集的省份,他們保留着完整的漢民習俗。與其他民族不通婚,與外界交流也不多,在語言、服飾、飲食、信仰、民居建築及娛樂方式等方面與周圍本土村寨絕然不同。究其緣由,他們世代相傳:「應天府乃我故鄉,有我族人,有我良田美宅。」他們的原鄉,便是南京。一三七一年,明太祖朱元璋封傅友德為征西大將軍,率領三十萬大軍自南京抵達今貴州安順地區,成為大規模進入黔西的第一批漢人。這些漢兵主要來自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一帶。緊接着太祖又下令將留戍者的家屬全部送到戍地,衛軍就地屯墾,七分屯種,三分操備。一留便是六百年,外界世異時移,這裏卻猶如歷史的定格。屯堡人有自己的頑強的堅守,在這偏遠的貴州腹地,複製與傳承着自己念念不忘的江南風物。他們成為了古南京的化石,這化石的肌理中,當然也包括語言。遵循「離鄉不離腔」的祖訓,依然是明代的江南口音,與昔日的老南京話同聲同氣。
在一處四合院的廂房裏,我面前坐着一位身着天青藍的老太太。陽光透過鏤空隔窗在她身上投下光影。她的神態安詳寧靜,和我用一新一舊的南京話交談着,竟沒有障礙。臨走的時候,她對我說,她七十二歲了,從未出過天龍屯堡。她知道南京很遠,但她很想去南京看一看,和與她一樣老的人說說話,或許這輩子,就心滿意足了。
葛亮:一九七八年出生,原籍南京,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現任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已出版小說《北鳶》、《朱雀》、《七聲》、《謎鴉》、《浣熊》、《戲年》、《北鳶》,電影隨筆《繪色》等,作品譯為英、法、俄、日、韓等多國文字。曾獲台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二零零八年香港藝術發展獎、首屆香港書獎、台灣梁實秋文學獎等獎項。長篇小說《朱雀》曾獲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小說。




老派的南京话,是相当好的
我本人就是南京人 感谢作者对南京话的解释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