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民主派又一次輸掉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泛民主派老將李卓人在另一泛民元老馮檢基不接受協調堅持參選的情況下,在與建制派屬意的候選人陳凱欣的單對單對決中敗選。李馮二人的票數加起來,甚至仍及不上陳凱欣的得票。這次敗選,令非建制派完全失去僅餘的分組點票否決權。
為何昔日的民主派,會從擁有「六四黃金比」的選戰優勢,最終淪為在單議席單票制下都連戰皆北?到了今時今日的破局,非建制派應該如何回應?這些問題說來話長,亦難以一下子回答。今時今日,纏繞香港非建制派最深的政治問題,應是不同派別之間不能和衷共濟,泛民主派和本土派在屢次運動中不能同心,互相指責,雙方仇恨愈積愈深,寧願互相「攬炒」(同歸於盡)也不願合作,甚至在泛民主派當中,也出現這種撕裂情況。以往,民主派對建制派的優勢,最多也只在六四比之間,近年非建制派分裂成本土、泛民兩翼,泛民的愈收愈窄,早已無法盡收反建制陣營的選票,原本就非太強的微弱優勢結果全銷。
內部不和,應是今日香港民主運動的最大問題。(關於這種情況為何出現的討論,可參考筆者前文[1])這種寧願敗選也希望泛民主派落敗的想法被稱為「焦土派」,這一派的假設是,與其繼續讓和稀泥一般的泛民獲勝、繼續含淚支持這些不成器的政客,那就寧願讓建制派得到議席,置之死地而後生,之後人民就會醒覺反抗。
這種想法長期存在於香港的公共討論空間中,但「焦土論」背後有多少實證基礎就鮮有人論及。到底,民主運動者把時局弄得更糟,透過焦土戰術,有可能擊倒威權政府,最終否極泰來實現民主化嗎?

民怨,產生顛覆性政治運動的必要條件
威權國家如何才會民主化,是一個經久不衰的研究議題。人類社會在過去數百年間經過了幾波的民主化,比較政治學對於「民主過渡」(democratic transition)的研究也頗為豐碩。一般而言,出現「民主過渡」的條件說法紛陳,但政治學者一般同意,顛覆性的政治運動要出現,首要前提是民怨的累積,而民怨的重要量度指標,則是「經濟是否低迷」和「分配有多不平等」。所以,一旦某國出現明顯的經濟下滑及分配不平等,則會增加政權倒台的可能性(註1)。在民主國家,那往往是政黨輪替,威權國家沒有政黨輪替的機制,便有可能以政權倒台而終。
但縱觀人類歷史,經濟低迷不一定等於政權倒台,短暫的經濟低迷一般不足以摧毀人民對威權政府的信任,北韓、早期的中共以至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經驗甚至告訴我們,長期的惡劣經濟情況也可以和長期的獨裁並存。民怨和有規模的反抗運動之間有著頗大的鴻溝。人民對管治有怨言,當然會增加他們投入反抗運動的可能,但最終導致威權政府倒台的卻不是民怨,而是有組織的反抗運動。民怨不一定能兌現成實質性的反抗,即使經濟情況每下愈況,也有可能被人民習慣而成為政治常態。
那為何顛覆性的政治願望無法變成集體反抗?對此最常見的解釋之一是所謂的集體行動難題(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集體行動難題」的奠基人之一,經濟學者奧臣(Mancur Olson)曾經作過這番解釋(註2),即是在一個龐大的群體當中,惡劣管治的後果是由所有人一起攤分的,但如果有人受不住,決定要出頭改變現況,那麼,首先強出頭的人,就要為群體付出不成比例的個人抗爭代價,而且爭取回來的利益都是屬於「公共」的。
為何顛覆性的政治願望無法變成集體反抗?對此最常見的解釋之一是所謂的集體行動難題。
簡單而言,就是差勁的獨裁統治會令人民想起義反抗,推翻專制政府,但誰先反抗,誰就要有拋頭顱灑熱血的準備。先行者許多時都是「炮灰」,縱然最後成功,能爭取來良好的民主管治,但也只是社會整體獲益,既然人人獲益,那麼首倡議者的獲益就不見得很大。於是,只有「傻子」才會率先投入反抗運動(縱然歷史上不乏這種人),大部分人都寧願默默忍受,等待其他人為「大圍」爭取權益。
顛覆的關鍵,集體行動
所以,民怨只是顛覆性的政治運動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另一個重要條件是要克服集體動行動的難題。一般而言,政治學者均認同,民主運動要成功,除了民意支持,亦需要成型的政治組織代理,即所謂「代理人」(agent),在許多國家這些代理人就是「政黨」等。這些組織的存在,能夠提供途徑讓個體聯結起來,令每一個想反抗的人在面對巨大的獨裁國家機器時都不至於那麼孤獨無助,個人投入反抗運動的成本即被團體所分攤,它們可以是民怨兌現成運動的中間聯結。
簡單而言,社會分配愈不平等,社會的改革的壓力就愈大,政權就愈「頭痕」(頭痛),如果管治不善帶來了社會民怨,那這方面的「焦土」的確可能促進民主運動的進展。但民怨沸腾,也要有組織工具和政治代理讓人民去組織反抗運動,反抗力量愈沒有組織,愈在公共議題上缺乏空間、陣地,反倒會拖慢民主運動。由這個邏輯去看,如果「焦土派」希望「焦」的是具體的管治質素,期望經濟搞得更差以令人民反抗政府,這種「焦土」是能夠幫助民主運動的。
但如果是打算把反抗陣營一把火燒掉,那卻不怎麼說得通。當國家崩壞,哀鴻遍野,那政權一般也長久不了,這種「天下大亂政權倒」的傳統智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同時也簡化了歷史經驗,例如,在大躍進時的中國,毛澤東並沒有倒台;史大林(斯大林)時期的烏克蘭饑荒未有動搖蘇聯管治;在「苦難的行軍」當中,北韓也沒有出現成型的反抗運動。由實證的角度而言,要擊倒獨裁政府,民怨和組織,兩者缺一不可。

中共是挺知道這一點的。當代實證政治研究大師金加里(Gary King)在2013年發表一篇關於中國網絡政治審查的研究(註3),就曾經找到一個有趣的結論。研究者大量下載中國互聯網上的貼子,然後再分析這些數據,發現中國的網絡審查,其對於人民批評政府有很大的容忍度,但對於任何形式的人民網上聯結,審查部門都會將其扼殺於萌芽之中。
也就是說,罵政府可以,但想自外於中國政府來搞串連?非政治組織也不一定讓你搞,或其必須受黨直接控制。這種做法的目的,顯然是為了防止任何潛在的危機——今日並不一定政治化的組織,如教會、工會、沒有議政傾向的社經團體,只要時局一變,隨時就可以變成強勁的異議團體,一般鍵盤戰士打打嘴炮,倒構不成威脅。該研究的結論亦符合一般中國人今日的生活經驗:一般人是有一定的言論自由的,甚至在友儕間或在網上稍微批評一下政府,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有人企圖把任何批評轉化為綱領、行動或組織,即使訴求再溫和,都將被嚴重打壓。這些案例見諸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或任何異質化的少數族群,令到神州大地上並沒有團體能自外於中國共產黨。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鑄十八銅人以防人民反抗,今時今日這種進化了的社會審查機制,卻是把人民精神上的兵器收走了。
香港非建制派不同的政治派別,如果把太多的心力放在互相攻訐、清理舊有的代理人上面,卻不在意民主運動是否能再生出新的組織資源,那並不理想。
抽空一切來說,最理想的民主運動是反對派能夠積蓄力量,擴大支持,等待政府管治不善,令民怨累積;威權政府最希望見到的情況,則是經濟良好(不等於分配公平),人民生活穩定,而政治舞台上,完全沒有潛在的挑戰者。
因此,香港非建制派不同的政治派別,如果把太多的心力放在互相攻訐、清理舊有的代理人上面,卻不在意民主運動是否能再生出新的組織資源,那並不理想。我絕不是為泛民主派辯護,若泛民主派表現不濟,他們當然需要反省重組,但其他派別的支持者即使和泛民主派水火不同爐,也不應放棄自身組織的可能,不應坐等泛民主派失敗,而應多考慮如何取彼而代之,成為民主運動的領軍者。如果香港的本土派沒有自己的反抗組織,清走了泛民主派,他們亦難以發起具規模的抗爭運動。在顛覆性政治運動的角度來說,「大台」上的是誰都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組織力的維持,一旦天下有變,也能把握隨之而來的政治機會。
那麼,到底民主運動要如何再出發和組織呢?這裏有兩個建議。
對本土派的建議——組織和議題
對於本土派而言,首先是要摒棄近年出現的「不要大台」或「去組織化」傾向。筆者的印象和認識中,歷史上並沒有人民不去組織而又能反抗成功的例子。不論是主流的民主民權運動(例子:黑人民權運動、東歐劇變、台灣或南韓的民主化),或極端的血腥獨立運動(例子:如哈瑪斯、愛爾蘭共和軍等),都需要透過組成反對團體,來組織具威脅的反抗。中共是瞧準了這一點,斬首式地DQ有本土傾向的議會候選人,其目的就是令本土派或自決派失去潛在議會陣地,令潛在的分離主義失去短期政治目標、舞台和議席帶來的資源。這種戰略非常成功,在不能再參選後,整個本土/自決派確有點不知所措。
本土/自決派要再組織,首先要思考的問題是,在沒有了議席這一明顯的目標後,他們用甚麼來維持向心力和行動力。不論是民主化、自決或獨立,在與中共強弱懸殊的勢力對比下,中短期內都沒有實現的可能,所以,長期的成功,更加依賴運動的持續性。
香港的本土派確實正面對北京的強力打壓,但在威權統治下,反對派被行政手段打壓,例如取消參選資格或取締組織,情況亦非香港獨有。要應付這種打壓,一個常見的處理方式,是反對派可以採取外判式的政治分工,參選議會的人和負責推動民間議題的人,可以作出某種程度的政治切割,卻互為奧援。這種政治聯盟方式很常見,亦不只是反對派使用,例如俄羅斯政府就以外判「dirty work」聞名於世——政府一邊扮演較文明的角色,並和出手攻擊反對派的黑道和政治流氓切割,但雙方卻保持某程度上的默契。
另一個方向,是本土運動不止於爭取獨立或自決一個支點,而引入更多的輔助議題,並以這些輔助議題為組織的根基。至於甚麼樣的政策、民間議題最能和本土運動相連結,那就是一個需要智慧的政治決定。

對泛民派的建議——人與意識形態的革新
相對於本土派,泛民主派已經有一套政治組織,但多次補選結果已反映他們面對支持者流失,光譜慢慢收窄。這點其實可以理解,試想想,近年幾乎每一場的大型民主運動,他們都處於被動的位置,在迎合網上年輕人的較激進主張及平衡較年長者的保守傾向之間,愈來愈難找到平衡,可謂「順得哥情失嫂意」。
另一方面,泛民主派亦給人強烈的混日子之感,一連串DQ事件之始,在於泛民元老梁耀忠莫名其妙地拒絕棄任立法會代主席,引來一連串風波,他道歉一聲,摸摸鼻子,事件也就不了了之。泛民主派也「人才輩出」,馮煒光、湯家驊、狄志遠、黃成智等先後被統戰,更不要說直接走入政府的張炳良、羅致光,李華明退出政壇後長袖善舞,周旋於建制派財團之間,而鄭家富、馮檢基等都先後拒絕協調出選立法會,更或多或少導致了「攬炒」或「攬炒」危機,而這些人都是泛民主派元老。
更甚者,是溫和民主派中人對這些人的所為盡管不以為然,但批評力度也不強,遠不能和針對本土青年的批評相比。泛民主派並非鐵板一塊,當中有許多不同類型的人,但民眾卻沒有這種認知,只能模糊地憑印象去分辦李卓人和馮檢基有甚麼不同。客觀的政治效果,是年輕人只會覺得泛民主派沒有甚麼能力,而且近年大批「投敵」,又不喜被人爭奪自己的地盤,很是戀棧,甚至已屬建制的一部分,面目模糊又民主意志不堅等。
泛民主派的形象,愈來愈成為政治包袱。而主流政黨形象老化慢慢被摒棄,也非香港獨有現象。在美國,不滿政治體制的民眾投票予特朗普,在台灣有柯文哲、韓國瑜。這些新晉成功政治人物的共通點除了「民粹」外,就是「素人」,標榜自己並非由主流的政治系統出身,不受他們制肘。這種說法不一定是事實,但卻是一種伴隨特定候選人的論述。「素人」當選後的表現也不一定優異,甚至在做跟他們的前任同樣的行為,但反正他們就是代表一條「不同的出路」,投票予他們的民眾其實是在對整個舊體制說不。時至今日,泛民主派要重新出發,第一項任務是要大批換血,逐步挑選政治包袱較少的新人來代替舊人,以尋找較大公因數。而只要新人具有潛質,近年在國際上的經驗都顯示,「素人」掀起的旋風,可以比政治老手更強。
第二項任務是要調整其意識形態論述,以扭轉無能兼搖擺的政治形象。首先,溫和路線需要有合理的政治註腳,從以令溫和泛民日後和政府以至北京的談判,要和「被統戰」有明顯的區分;第二,是新一代泛民中人要解釋自己對本土路線的看法為何,並理清民主路線和本土派路線之間的關係,令到兩者找到合作和區分的可能。而這些問題所需要的答案,並不止是想出幾條「lines」,而是需要一個持續的政治工程,來有效更新泛民主派的形象。而這些意識形態工作,老一代的泛民已很難做到,只能寄望於新人。所以泛民主派的根本戰略,應是加速更新世代,並應主動掀起意識形態的討論,來重塑整個派別的政治形象和定位。
即使民主運動不能一下子成功,也需要爭取階段性的成果。
最後一點,則可能對所有政治派別都適用:即使民主運動不能一下子成功,也需要爭取階段性的成果。香港的時代背景是我們處於一個極強大的專政政體當中,所有長期抗爭的打算,都應該充分考慮雙方強弱懸殊這個困境,想清楚自己的最終目標為何,並向民眾公布自己的路線圖。民主運動在香港現時的時空,實無一蹴而至的可能,但手執一把爛牌,仍有盡力周旋跟自暴自棄兩個選項,香港民主運動在當下最需要的,是要有把一盤爛棋下好的魄力。最合理的方法,是先做好基礎的組織建設,這些工作並不特別拉風,不能刺激參與者的腎上腺素分泌,長遠而言卻是民主運動所必須。即使由小處著手的改善,都可以慢慢累積為結果,是我們當下最需要的。
(梁一夢,自由撰稿人)
註:參考書目
(1)抱持這種觀點的研究眾多,作為例子可以參考: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King, Gary,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 326-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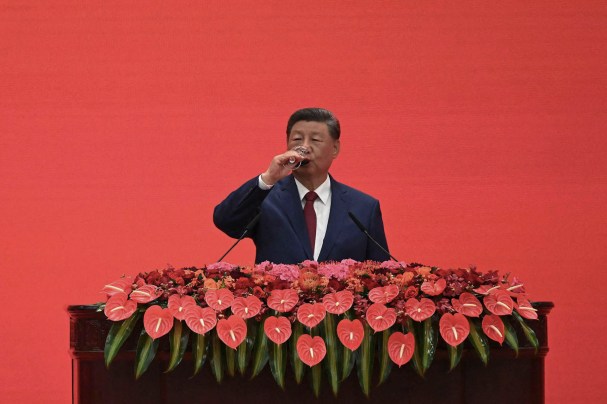
,但看檢特區政府也知道堵塞了這個最後的排氣口(按國安法,端傳媒也難存在)就真的會漲破
香港刻下的社會也就是一種不生,不死,不破,不立的低氣壓狀態,儘管建制中人常有人為表忠吵著要搞國安法,但看檢特區政府也知道堵塞了這個最後的排氣口(按國安法,端傳媒也難存在), 老泛民是失了氣,但建制中各種利益集團尤其地產紛紛檢要利益,也使香港完全談不上真規劃,人口政策亦早失控,政府明顯自己先來“焦土”不想理,各類人材,科技指標不斷墜後,出生率極低,加國中文媒介已見談“二次回流”,樓價世界最高,很老實特區政府不敢完全威權否則兩制報銷,但另邊面和建制聯盟也只勉強叫壓著反對力量但自己甚麼真正長期建設也做不列,只是等待20470701來臨前當看守政府(甚至這天也未必能達到),這就是真焦土,大家一起縛著下沉
DQ本身就是去除真正有威脅對手的手段
真正可以焦土是在北京,一個23條已夠正中特朗普下懷,香港再不是獨立關稅區,就不會再可能生意歸生意,經濟打擊是空前的,有上次的研究報告已反映美國朝中有人已有此想法,絕不是跟大家玩笑的
“最下面那位真的是典型的鐵拳下的青蛙思維⋯ 無言以對,”<<<<<這類說話和其討論也多餘,原用為其浪費時間
“民主派能有今天也是自己作出来的。闹港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攻击大陆游客,歧视大陆人……触碰这些底线后,谁会支持你?”<<<完全不了解香港目下“選舉”制度的夢話
最下面那位真的是典型的鐵拳下的青蛙思維⋯ 無言以對,
文章很翔實,立論高大。唯一問題是:焦土戰術在主流本土派網民的心目中就壓根不是什麼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戰略,而是屢戰屢敗後再無作戰意志舉手投降的美化說辭。
把議會交給建制派,反正泛民掌握關鍵一席的時候照樣無法阻止議會通過這樣那樣的“民主最黑暗一日”之類的議案。還不如不和你們玩這個消耗巨大又看不到勝算的遊戲。
上街上過,簽名簽過,投票投過,訓街訓過,佔領佔過,燃燒彈掟過,參選又選過。
什麼都試過了,還要無止境地打下去,而且對手越來越下三濫越來越泰山壓頂。拜託,讀過政治101的都知道什麼是exit,voice和loyalty吧。人民如此選擇,很難理解麼?
如果民主派始終把自己當做是啟迪者甚至拯救者,而民眾被認為是愚昧無知不識大體。那麼他們獲得成功的那天就是自己成為獨裁者的開始。於鄰人有隙,我們知道要心平氣和互相理解去化解矛盾。為什麼當我們組成“黨派”就失去了這最基本的謙遜態度?
佔中失敗嘅陣痛仲未緩解,又嚟一鑊 DQ,後者對民心嘅打擊實在太沈重唉。
投票意欲低係因為有機會嘅更生反對派候選人都被DQ!
正如一場打黑哨嘅球賽, 冇必要同你守規矩去繼續!
焦土政策反而是正好成為獨裁政權介入的最好藉口,以保護神(至少他們自我宣傳一定是如此)的面目大肆介入政局。所以香港民主派不應該破罐破摔。中共有槍,靠武力太難獲勝了。一定是靠人心。
焦土政策不就是小孩对家长“不让我玩游戏我就不学习”的翻版嘛。熊孩子的方法有时真的能闹得家长没办法而同意了,但是成年人都明白这不是什么正确的方法。
至于通过弄乱社会来让人民加入反抗阵营,其实就是通过他人不可抗拒的力量限制他人追求生活、自由的权力,来达至让他人听从你的政治主张嘛。要不是政治主张说服不了别人用出此下策?
民主派能有今天也是自己作出来的。闹港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攻击大陆游客,歧视大陆人……触碰这些底线后,谁会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