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華語語系研究理論學者史書美的新書《跨界理論》中「翻譯女性主義」一章的部分內容,這章從後殖民理論學者史碧娃克在台灣的一個茶座講座中的小小衝突講起,探討在翻譯脈絡下對女性主義的認識。端傳媒獲聯經出版社授權轉載。在這本書中,史書美探索台灣在地論述的跨界思維與實踐,發掘並批判不同層次的權力關係與各種階序(如種族、殖民、性別、知識等)的運作,並以這樣的批判為基礎,進一步提出有創意、符合在地社會文化實況,又有一定程度普遍性的理論思維。現標題為端傳媒編輯所擬。
「Feminism」一詞在台灣有兩個不同的華語翻譯: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這兩個不同的翻譯的區別在於每個譯名的第二個字:權和性。
至於「女性主義」這個詞,我只想說任何自稱是「女性主義」的運動或思想必須與這個詞的西方起源相協調,儘管有關女性的能動性(agency)的類似思想早就存在於非西方的很多地方。因此,這個詞的使用,不論是不是有問題,都蘊含與西方女性主義的密切關係。由於西方的認識論特權使它的批評者都促成了它的流傳的不斷擴大,以致這個詞擁有了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的價值。和其他任何起源於西方的概念一樣,這個詞的傳播,獲益於西方蒸汽機、飛機、電腦這些東西以及優越的武器裝備的優勢, 支撐起其預設的普遍性(universalism)。
「Feminism」一詞在台灣有兩個不同的華語翻譯: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這兩個不同的翻譯的區別在於每個譯名的第二個字:權和性。在不同的語境裡,權可以有權利(rights)或權力(power)兩個意思,所以女權主義有兩種可能的字面意思,分別為「女性權利主義」或「女性權力主義」。而許多傳播「女性主義」概念的著作和實踐,已經把第二個含義與第一個含義區分開:女性的權利不等於女性的權力,因為權力暗示與男性的權力鬥爭。相反,擁護女性的權利是為了尋求男女之間真正的平等,這也應該是男性們所希望的。
另一方面,因為「性」一字多義,可以是性、性質或性別的三重意義,所以女性主義可能意味著「女性的性本身」、「女性的特質」或「女性的社會性別」,強調女性區別於男性的獨特之處,倡導婦女的性自主權和性自由,或者社會性別取向。因此,女性主義在台灣的脈絡中,至少在其一九七○年代的演繹中,被稱為「新女性主義」,從而擺脫「女性」一詞的三個含義可能導致的各種麻煩。
《跨界理論》
作者: 史書美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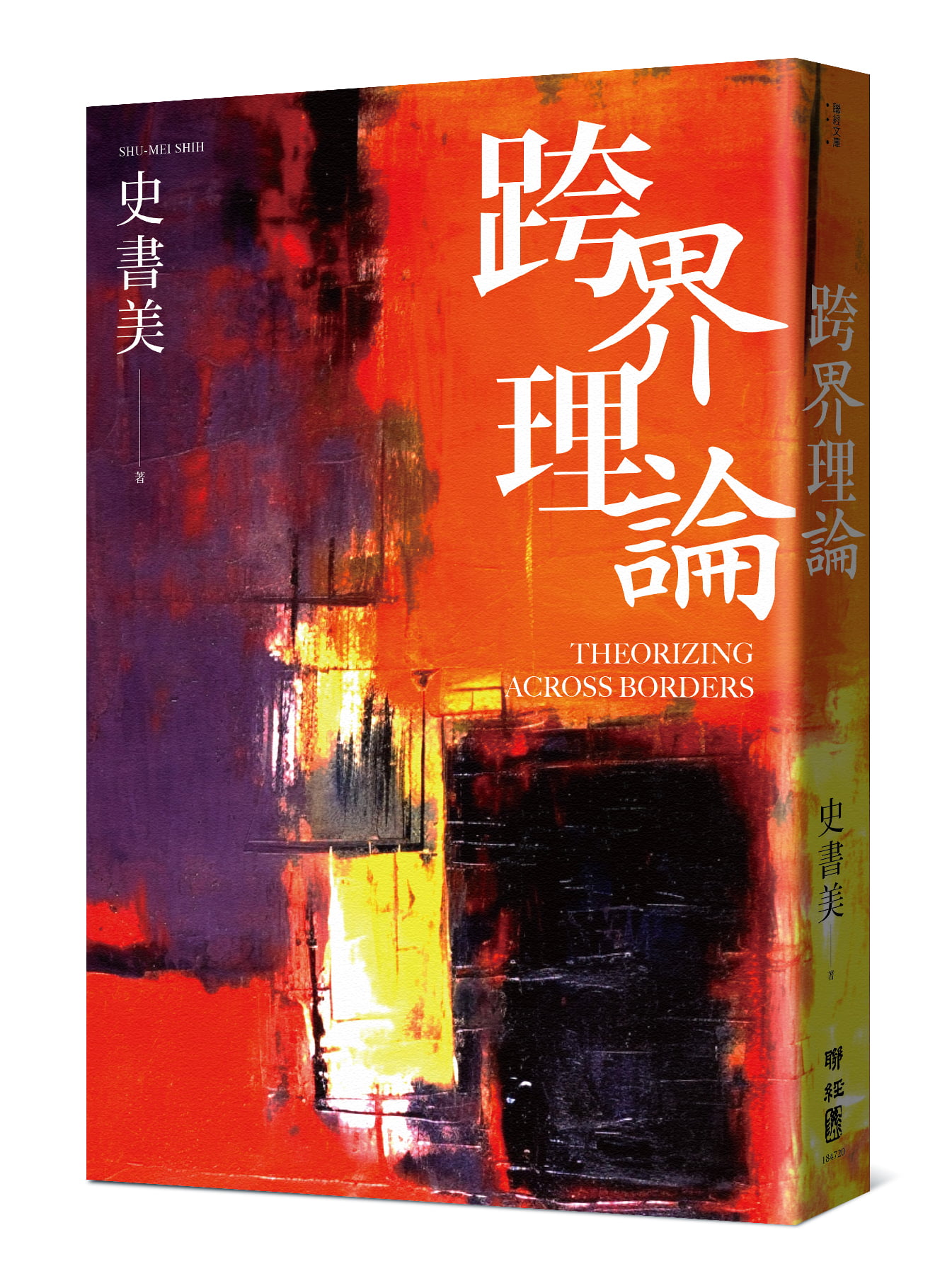
「女性主義」一詞的傳播和本土化在這個例子中是不可預期的。在翻譯的行為中,有兩組差異上演:一方面是原文及譯文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是不同翻譯版本之間的差異。台灣女性主義與西方女性主義之間,不同版本的譯名之間以及這不同的翻譯對台灣的女性意味著什麼,所花的商討之功幾乎一樣多。在許多情況下,不同的本地華語含義之間而非與原文含義之間的不同的探討,往往受到更大更多的警覺性的注意。
由於台灣學術界的女性主義(academic feminism) 的興起, 被翻譯為女性主義的「feminism」成為二十世紀後期通用的詞彙,而有關性權利的話語與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利一起越來越受到注意。在通俗的用法中,這個詞在社會上仍然被很多人質疑,有礙於這個詞被誤解為擁有性別極致化的傾向,甚至積極參與女性主義運動的女性都不一定願意稱自己為女性主義者。但在學術界的女性主義,引人注目的卻是缺少在第三世界的脈絡中反對西方女性主義(如莫漢蒂〔Chandra Mohanty〕那樣)的聲音,這是前文描述的史碧娃克和本地女性主義者相遇的重要潛在背景。畢竟,對在場的本地女性主義者來說,史碧娃克並不被看作是印度的女性主義學者,而是一個美國(儘管很多人知道史碧娃克拒絕成為美國公民)或西方的學者,只是剛好把印度作為她研究和學術活動的領域之一。
在學術界的女性主義,引人注目的卻是缺少在第三世界的脈絡中反對西方女性主義(如莫漢蒂〔Chandra Mohanty〕那樣)的聲音,這是前文描述的史碧娃克和本地女性主義者相遇的重要潛在背景。
第一,其他任何來自印度的印度女性主義者不太可能被邀請到台灣。第二,台灣的學者並不一定熟悉西方學術界對史碧娃克或任何其他西方女性主義者的著作之批評或抵抗。在所有譯入台灣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中,由於史碧娃克對後殖民的注重以及她對另一個「亞洲」(南亞)脈絡的關注,因而也許與台灣的情況更為相關,但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女性主義對巴特勒(Judith Butler)、克莉斯蒂娃或西蘇之理論的使用也非常的廣泛。
例如,一本顧燕翎主編,由九位本地女性主義者起草的女性主義理論的重要教科書《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其各章節的標題對西方的女性主義者來說毫不陌生,而且好像西方的女性主義被看作是普遍的女性主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女同志理論及酷兒理論、後殖民女性主義和生態女性主義等。
由於台灣連續性的殖民主義,其中包括當代美國的新殖民主義的特殊情況,台灣女性主義的發展是一個斷斷續續的故事。這個故事可以從一些台灣原住民部落,如果不是母系也至少是偏母系的社會之觀察講起。另外,歷史學家們曾經指出,在十七世紀最初漢人來台定居的時候,定居者們不得不充分利用所有可用的勞動力來「開拓」土地,而這誠然是一個典型的定居殖民主義觀點的敘事。同時,這意味著定居者中的女性勞動力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視,因此當時定居者中女性與男性的地位比之前在中國更為平等。
但隨著定居殖民變得更成熟,舊中國的性別觀念不僅開始介入也變得越來越死板(楊翠: 32-37)。這是被稱為「移民泡沫」(immigrant bubble)現象的一個實例,舊日的規範從起源地的語境中脫離,但像殭屍一般殘存,彷彿在時間中凝固了,變得更為死板。這種移民泡沫的去語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本質也使定居者與原住民以及他們母系傳嗣的做法疏離。原住民,當時被稱為 「熟番」(指那些生活在平原的「番人」)和「生番」(指那些生活在山區的「番人」),後來被稱為「山地同胞」,成為恆常被壓迫的對象。這種情況歷經島國歷史所有斷斷續續的動盪而持續惡化。
台灣女性主義的發展是一個斷斷續續的故事。這個故事可以從一些台灣原住民部落,如果不是母系也至少是偏母系的社會之觀察講起。
故事接下來的部分是在日據的一九二○至三○年代對西方、日本和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的譯介。這些運動被譯介,主要為的是非原住民的漢人提高了女性自我意識。然而,當日本殖民主義統治在一九四五年結束,這一章的歷史在國民黨一心清除日本影響(重新)漢化台灣的極權統治下被徹底抹去。當一個更自覺的女性意識在一九七○年代初浮出水面的時候,日據時代的先例很大程度上已經被遺忘了。直到一九九○年代,通過系譜學的方式向日據時期的婦女運動追溯才成為可能,從而將表面上斷斷續續的台灣女性主義的歷史,重新詮釋為另類形式的延續。日本殖民時期婦女解放的努力,現已被看成為台灣定居者女性運動新的系譜的第一波浪潮,作為開拓的努力,為後世的開墾鬆動了原先乾涸的土地。
這段歷史的斷續表明,一方面,在創造本土歷史中缺少本地的能動性,但它也突顯出來某種可以稱之為台灣女性主義中跨國的內涵。日據時期,民眾和思想在台灣、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流動帶來的經過反覆譯介的西方思想,是這一早期女性主義出現的最基本的條件。為了與後來跨國主義的形式相區分,我們可以把這日據時期的女性主義稱為殖民跨國主義(colonial transnationalism)的一個例子。
由於殖民主義和現代性之間矛盾的結合,殖民跨國主義作為一個歷史情境既記錄了殖民主義強加給台灣的、對外國勢力被迫的開放,也記錄了殖民時期漢人居民樂於接觸其他文化。日本殖民主義以殖民現代性的形式為殖民地帶來了某種現代性,這必然導致多重的、矛盾的後果。至少可以這樣說,這兩種接觸——殖民主義和現代性——的關係頗為複雜。馬克思曾錯誤地把前者當作是後者的條件,好像殖民主義幾乎是一個必要之惡,或者說對亞洲歷史的發展有終極性的幫助(見Avineri)。這種觀點,當然是不加掩飾地以歐洲為中心的。還有人認為西方殖民主義造成了被殖民國家文化上更加雜糅因此更加世界主義/大都會,甚至比西方的宗主國本身更甚(Buell)。作為歷史的後見之明,這種觀點的出現主要問題在於它對後殖民世界主義的讚揚不經意間錯置了殖民主義的創傷。
此外,它沒有對不同種類的混雜性(hybridity)和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之間做必要的區分:混雜性和世界主義可以是被強迫的,也可以是自取的特權,和個體的權力地位有關,必須分別清楚。考慮到這點,學者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和米格諾魯排斥時髦的後殖民的話語,而主張「去殖民」,旨在重新聚焦於導致了實際的政治和文化後果的殖民地的解放行動和話語的能動性,從而使我們可以遠離那些模棱兩可、並且往往削弱分析的去政治化的混雜之談。
日據時期女性主義思想的跨國流動,曾經是由在日本和中國留學的台灣學生促成的。日本作為台灣女性主義的中介的一個突出例子,是一九二八年的「紅色婦女國際」宣言,這是由一個在上海的台灣知識分子們提供的性別化版的國際馬克思主義。這一宣言的發布恰逢作為日本共產黨的一個分支和團結對象的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其中台灣共產黨的成員包括著名的唯物主義女性主義者謝雪紅。她生於一個貧窮的家庭,在父權體制下一直飽受侮辱,直到她後來在日本接受教育,並活躍在中國和台灣(陳芳明;楊翠 148-149)。
這個左翼婦女國際的成立本身就是一個多重調和的結果: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的舶來品,但在這一段時間內,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日本帝國主義是抱有批判態度的。後來許多日本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和作家們很快經歷了意識形態的轉化,聲明放棄馬克思主義而接受日本帝國主義。但一九二○年代末直至一九三○年代,卻是見證了一個橫跨日本、台灣和中國的包括女性、男性都在內的國際性的馬克思主義聯盟。同時,台灣有對中國婦女運動的一個相當全面的介紹,而有關西方女性主義的翻譯文章也源源不斷地發表在當時主要的報刊雜誌上。

在楊翠書寫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的日據時期的婦女運動史中,她指出了台灣的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一貫矛盾,當涉及本地女性時,卻是例外的。
正如許多被殖民國家的解放運動一樣,在殖民宗主國接受教育,是被殖民者以殖民者自己的規則擊敗他們的一個重要策略,這種思想和政治結構是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在印度的背景下提出的民族主義的「衍生話語」(derivative discourse)的潛力和局限的問題之基礎。也就是說,是否人們真的能夠,用洛德(Audre Lorde)的話說,用主人的工具拆掉主人的房子呢?對於台灣本地女性來說,和其他殖民社會一樣,她們在殖民的組織結構和性別等級中,大致被指定了特定的角色,但殖民的性別體系由於原住民女性受到的另一層壓迫而複雜化了。日本殖民政府採用典型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建立了由本地漢族女性組成的名稱明確的隊伍「討伐番界隊」,以彰顯漢族女性比原住民女性更文明,並把後者毫不含糊地稱為野蠻人,是需要被征服和鎮壓的對象。這裡漢人女性借著日本殖民主義之勢,或者說被日本殖民主義所利用,更加深了對原住民的壓迫。
在楊翠書寫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的日據時期的婦女運動史中,她指出了台灣的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一貫矛盾,當涉及本地女性時,卻是例外的。她指出,台灣的男性知識分子當時對於本地女性的問題,甚至對她們一些最激進的方面和最具爭議的措辭,都給予了同情的聆聽,並把這些看作是反殖民的現代性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被剝奪了參與政治的權利(除了幫助殖民者管理原住民之外),同樣缺乏甚至最基本的人權,男性和女性的知識分子和活動家認為他們的命運是密切相連的。因此,相較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情況,女性主義對本地女性來說,其在廣義上沒有與民族主義的訴求相衝突(楊翠 83-93)。
相較日本、中國和西方的女性主義,台灣女性主義日據時代的殖民跨國主義有幾個明顯的特點。首先,由於在嚴密的殖民管治下沒有參與政治的可能,台灣女性主義者沒有也不能主張政治權利,因為擔心受到迫害。其次,台灣的女性主義由於其邊緣化的位置,多半是中、日女性主義知識的接受者,而這些知識在台灣必然本地化的特質和內涵,並沒有反過來影響其來自或曾通過的地方。第三,由於涉及原住民女性,台灣漢人女性主義無論有何成就,都立刻背上種族不平等和階級不平等的嫌疑。隨著台灣脫離日本殖民主義的統治以及後來的解嚴,女性參與政治逐漸增多,但後面兩個問題繼續存在直至今天。
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女性主義知識只沿著一個方向旅行、它的循環是不完整的,導致了台灣及其強大的中介載體(日本、中國和西方)之間不平等的認識論情況。見證了這種單向傳播的當代跨國主義因此背負上沉重的新殖民主義性質。此外,我們也注意到由於原住民女性的訴求和主流的女性主義一樣,在台灣的民族主義中不斷被邊緣化,因此基礎上的斷裂也在持續。從這個角度來看,主流民族主義和女性主義,也不能免於定居殖民主義的指控。因此,「主流女性主義」和「原住民女性主義」這個差異的形成,讓我們需要用一種三角辯證法(trialectical)——台灣女性主義在被西方女性主義邊緣化的同時,也邊緣化了原住民女性主義——這樣一個三邊的辯證去分析。
這裡參與者有三方,所以需要用多個平面和多種關係的深度模型,而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平面或二維模型來觀察這個領域。由原住民女性主義者阿提出的「樓上樓下」比喻,就是這樣一個深度模型,並提供了一個三角辯證政治的潛力的驚鴻一瞥。
由於原住民女性的訴求和主流的女性主義一樣,在台灣的民族主義中不斷被邊緣化,因此基礎上的斷裂也在持續。從這個角度來看,主流民族主義和女性主義,也不能免於定居殖民主義的指控。





最後講的,提出「樓上樓下」的原住民女性主義者應該是「利格拉樂‧阿𡠄」。
争取权利和拥有权力不冲突吧,我也更喜欢女权主义的译法。
“拥护女性的权利是为了寻求男女之间真正的平等,这也应该是男性们所希望的。”东亚背景下不常看到这种希望。
男人之间可以进行权力斗争,女人和男人之间为什么不可以?没有权力就没有权利。叫女权主义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