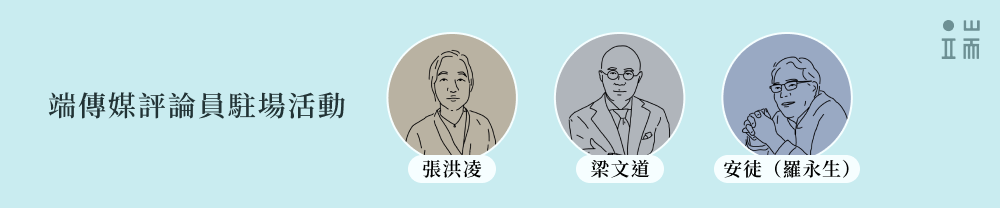三年前我做過一個嘗試用ChatGPT取代同事的實驗(現在想起來,我到底有多邪惡),那次好像是第一次和評論編輯雨欣聊「評論」這回事。那時她嘗試用ChatGPT代替我寫「這時代的愛與希望」評論系列,發現AI取代不了我(當然)。她當時說,一篇好的評論不外乎三方面:
第一是問題意識:大家看到的事實都一樣,但要在矛盾和落差中敏銳發問,並有自己的框架和結構。
然後就是作者性,即是對問題的獨特論述過程。論述過程可能包括作者自己的研究﹑專業領域的知識和經歷。然後作者要有和他人不同的觀點和看法,才是能夠成立的評論。
最後是文筆,但不是要雕花,重點是不僅僅讓讀者看到作者自己,也看到與其他人交流、溝通的意願,並傳達到。
聽起來蠻難的,還好我在她眼中還算是個好的評論作者(不脫稿的時候)。因為要推出駐場評論人計劃,我特意去研究了一下評論這種技藝的歷史。現在評論常被新聞編輯室收編,但其實評論作為一種文體,歷史可能比報業﹑新聞還長。最早期的「評論」,可能是我們在古書裡會見到的註﹑疏:例如中國的春秋三傳(「春秋筆法」的由來)﹑猶太經典《塔木德》正文旁的拉比論戰﹑《聖經》的各種釋經(exegesis)。到了古希臘-羅馬時期,西方的亞里士多德把 doxa(看法)跟 phronesis(實踐智慧)分開,後來也有了西塞羅(Cicero)這種教人如何公開說服人(或吵架)的評論家;中國則出了「太史公」司馬遷這種把歷史變成對權力、命運、制度的道德審判的評論家。
到了19世紀,評論隨印刷術興起完全進入公共事務範圍,甚至我們可以說近代新聞史本身,就是被幾篇「重磅評論」模塑的。1898年,法國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s)後以頭版大字發表著名的《我控訴》(J'accuse...!),直接點名挑戰軍方、司法、政府。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10個月,作家 Henry Luce在《LIFE》雜誌刊出6千多字長文《美國世紀》,直指當時仍置身二戰事外的美國對塑造世界秩序有歷史責任,預言了戰後美國的自我理解。上世紀美國第一健筆 Joan Didion一句話刺穿60年代看似開放﹑進步,實質虛無而蒼白的時代布幕:「很多人相信六十年代在1969年8月9日戛然而止。」那天邪教領袖曼森的追隨者闖入洛杉磯一棟豪宅,無動機殘忍殺害五人。在眾聲喧嘩中,Didion 直面時代:六十年代我們相信愛與和平會帶來善,但一切「解放」的口號,最後卻導向了毫無意義、純粹暴力的殺戮。
在半世紀後投入新聞行業的我們常想,今時今日的評論還可以做成甚麼樣子。都說我們活在新聞「deskilling」的年代,三年前我做那個ChatGPT實驗時,似乎就是公眾的AI焦慮元年,「取代」敘事開始鋪天蓋地,新聞記者與寫作人,多少都有種「亡國感」。當時我們說,這個隨口就能吐出萬字的工具沒法取代評論作者,起碼沒法取代「好」的評論作者,但「好」的界線會不會隨著劣幣驅逐良幣慢慢改變?2024年底,有研究指出網上由AI生成的文章,數量已經多於非AI生成的文章。在每個人都可以在網上發表意見的年代,評論人還有公共責任嗎?在威權社會不斷擴張時,我們還能像左拉一樣高呼「我控訴!」嗎?還有沒有評論可以告訴我們,我們是誰,身處在哪個歷史節點,應該如何理解自己﹑時代﹑還有歷史與道德責任?
我們是帶著這些疑問來策劃端的駐場評論人計劃的。我們邀請了三位在不同領域已經有極高成就的評論人,來陪我們做一次好玩的實驗:我們想知道,對一件事的深入思考﹑拷問可以去到甚麼程度,能逼我們問出甚麼更深層,更讓我們不敢直視的問題。我們也想知道,「常識」(common sense)或知識在資訊爆炸但注意力太少的年代,還能不能在公共討論中有一席之地。前幾天,audience同事們發放了這三位評論人的「標籤」和剪影,讓讀者競猜駐場評論人的身份。相信答案呼之欲出,但今天終於可以正式公佈(點擊名字可以收藏他們的作者頁!):
- 梁文道:我們這一代的知識青年(包括我自己)肯定都受道長影響甚深。2009年,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他寫了「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而這句在每年春夏之交依然在我耳邊迴響。同年他出版了關於愛情的散文集《我執》,我至今仍能隨口引用裡面的句子(很明顯,2009年的我也比較關注愛情這回事):「等待這種東西並不如我們所想,一定要有目的,一定要有等到的那一天。這種植物執迷不悟地生長,等待就是它本身的目的。不一定等到什麼,只要等,聯繫就在。」多年筆耕不懈的道長會在駐場計劃中,和讀者分享「常識」是甚麼,公共討論之不能及可能,以及回答我們許多人在這個紛亂時代的詰問:文字還有用嗎?
- 張洪凌:洪凌老師是駐美的雙語作家,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獎者門羅(Alice Munro)的譯者。她寫的異鄉人至今仍是我在端最愛的文章之一,我常常想起她筆下那些仍緊緊繫住後來人的,歷史的幽微線索。某年春節我推薦了這篇文章,那時我是這麼寫的:「這篇文章想講的,大概不止古典文學裡常見的『鄉愁』。它在講的是一種我們即使沒有經驗過,但依然不能避免地共同承擔的歷史創傷--因為那些未解的﹑暴力的過去,像幽靈一樣以某種形式「徘徊」到現在。」洪凌老師不久前與文中的柬埔寨老闆夫婦重新聯繫上,並隨他們踏上了歸國的旅途,並會在駐場評論系列中,與我們分享她在旅途中對殖民﹑歷史與創傷記憶的更多思考。
- 羅永生(安徒):許多香港人和我一樣,是從生哥那裡學習「知識分子」應該是怎麼樣的。他的評論不只是對當下的銳利洞察,更是一種道德姿態的示範:始終堅守理性的底線,卻不失去對具體人生的溫暖關懷。他寫過無數篇關於香港身份與殖民遺緒的文章,但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看似談論歷史或理論的文章背後,都藏著對普通人生活經驗的凝視。生哥會在駐場系列中,細緻地拆解香港文化精神內部的撕裂、留港者與流亡者之間微妙的權力不對等,並在「跨國主義」與「流亡政治」的交匯口,提出更清晰的倫理追問,幫助我們理解:在這個香港分裂與重組的時代,評論的責任究竟是什麼。今天我們也刊出了生哥的第一篇文章:跨國還是流亡:拉扯中的香港精神。
端傳媒評論員駐場活動現已登場!這次活動邀請了三位評論人,他們會在端發表一系列評論文章,同時與讀者互動。現在註冊成為會員,即可領取電子報,率先接收最新評論文章推送。
除了能讀到三位評論人的駐場系列,讀者還有機會在端聞聽到他們和端編輯團隊的對談,以及在線上小聚與他們直接對話,聽他們如何思考當下的關鍵議題。三位評論人也將在評論區與讀者進行AMA(Ask-me-anything)互動,打破評論者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同時,他們的推薦書單、文章清單等延伸內容,將形成一個完整的知識地圖,讓這三個月的駐場成為一次深度的思想對話,而不只是單向的評論輸出。
在此,我邀請每個還相信文字﹑知識與思辨的讀者參與我們在2026年的第一場新聞實驗。時局紛亂,也許你也有過覺得「算了吧,世界也不過如此」的時候。我想請你跟我一樣,嘗試直面而不是逃避時代的沉痾:只因未來的可能性,往往蘊藏在我們今日的選擇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