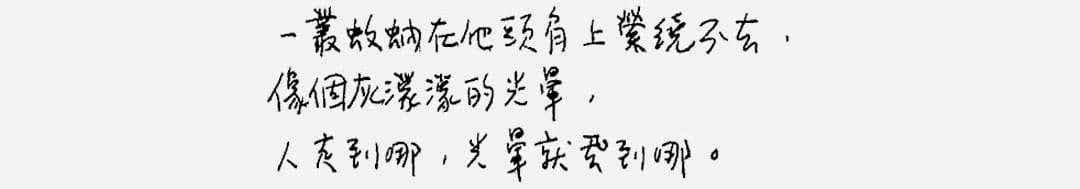久無音信,老郭忽地來一通電話:「我們的紀念集你要不要來一段?甚麼地方錄音都成,架生我帶來。」我想想有些甚麼既安靜又帶點市聲人氣而且可以抽菸的地方,「最好有點野外聲音的。」他說。老郭就是這樣,要野外聲音只能到野外去,我這一帶哪有。不久前我去過弛記的農舍,他那兒風聲鳥聲蟲聲不缺,入夜以後還有海濤般的蛙鳴,盈千上萬的田雞在野地裏我我我我我我我我,該夠「野外」了。弛記的短訊很快就回來了,「當然可以」,「歡迎」。
事情就定了。
錄音那天,非晴非雨半滴風都沒有,空氣很濕重。老郭人瘦力氣大,錄音架生一件不缺全帶來了,弛記在樹下開了酒,「蟲聲鳥聲天天都有,田雞這幾天好像少了。」把周遭聲音說得像個服務設施似的。老郭四下張看了好一會,在芭蕉後頭覓得一個角落,早有幾把椅子候着,「這裏好。」他說,「空曠中有少許樹葉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