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今年是1969胡士托音乐节(Woodstock)五十周年,而1969是那个为理想、革命、激情、实验精神所燃烧的六十年代落幕前的绝唱。作家张铁志新书出版,《想像力的革命——1960年代的乌托邦追寻》,讲述那个年代里对当下俱有启发性的十五个故事。本文为书中选段,讲述六十年代最有名、也是最富想像力的一场审判:1969芝加哥八君子审判。得作者同意,特此转载。
问:你住在哪儿?
答:我住在“胡士托国”(Woodstock Nation)。
问:你可以告诉法官和陪审团那是哪儿吗?
答:这是一个属于所有不被社会接受的青年的国度,但这是一种心理状态(state of mind)⋯⋯是一个没有财产或物质的国度,只有理念和价值。
问:你可以告诉法庭你的年纪吗?
答:我33 岁。我是一个六十年代之子。
问:你可以告诉法庭和陪审团你现在的职业吗?
答: 我是一个文化革命份子。
——1969年9月芝加哥大审判法庭上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的回答。
1.
“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
所有人可能都听过这句话,但却不知道这句话出自六十年代的激进青年杰瑞鲁宾(Jerry Rubin)。
鲁宾在1964年初柏克莱大学读社会学硕士,开始了他在六十年代无比疯狂的冒险。
六月,他和一群青年去了古巴拜访新的革命政权(同行的还有刚和Bob Dylan分手不久的女友Suze Roloto),见到了切格瓦拉。切说:“现在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斗争就是在北美。”回到学校后,柏克莱言论自由运动正在爆发,成为美国大学校园反抗运动的先声。
第二年,鲁宾在柏克莱成立了“越南日委员会”(Vietnam Day Committee),是美国反战运动在西岸的重要组织,1966年黑权运动兴起后,他也积极支持加州黑权运动。
那一年,这个西岸抗争的代表人物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唤作证,这个机构是从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时代留下最恶名昭彰的机构。鲁宾穿上了一套乔治华盛顿时代的军装,代表他是爱国且是传承美国革命传统的,现场议员们瞠目结舌,从来没有人敢在国会听证会上穿起如此恶搞的服装。
把现实当剧场、制造混乱、创造迷思,这是他们之后所有行动的原型。
那两年也是嬉皮文化在旧金山满地开花的时期。1967年一月旧金山举办了名为“Human Be-in”的盛大嬉皮聚会,鲁宾代表柏克莱的反战运动上台演讲,只是台下的花之子们并不喜欢他的激进政治语言。夏天,他接到来自“全国动员反越战委员会”(简称Mobe)领导人戴林杰(David Dellinger)的邀请,希望他协助策划将在十月举办的大型反战示威活动。鲁宾为此搬去纽约,认识了后来和他名字无法分开的重要伙伴:艾比霍夫曼。
他们俩将一起恶搞美国,创造出反抗新文化。
霍夫曼彼时住在纽约的下东区,那是纽约地下文化与反叛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俩相遇后,很快发现彼此的互补性和共通性,霍夫曼说:“我们都意识到融合政治与文化革命的可能性,他的长处是政治判断,我是让事件戏剧化。”
身处于嬉皮大本营旧金山的鲁宾,早就想结合嬉皮反文化与反战运动的政治性,但直到遇到霍夫曼,他才能把疯狂的想像变得真实。鲁宾说,“霍夫曼带来剧场、带来幽默和火花,我则是提供了运动的目的。”
那个八月,霍夫曼第一次成为公众焦点。他和朋友们去纽约证券交易所,把三百张一元美金钞票从二楼往下撒,造成现场的巨大混乱。这事件很快被传开,但因为没有媒体在现场拍照,各种说法四处流传,这行动变成一则传说,一个迷思,他们成为大家眼中的奇怪人物。而这正是他要的。
把现实当剧场、制造混乱、创造迷思,这是他们之后所有行动的原型。
这让刚搬来纽约的鲁宾十分震撼:“我从这事件中学到很多,因为艾比太懂得迷思(myth)的角色:只要创造一个小事件就能让所有人讨论、被所有人报导。这个利用大众媒体的方法实在太聪明了。”
对霍夫曼来说,这是一场街头的“游击剧场”(guerrilla theater),他的信念是,“任何革命最大的错误就是变得无聊”。
2.
全国动员反越战委员会计划在67年十月的反战示威游行,原本目的地是国会山庄前,但是霍夫曼带著点夸张宣称,这场杀了这么多人的越战是魔鬼所创造的,而这个恶魔当然就是五角大厦,所以他提出要对五角大厦进行驱魔仪式(exorcism),要让一群嬉皮围绕著五角大厦,施法让这栋建筑飘起来。
他们原本申请飘起一百呎,但政府单位最后给他们的许可是:不能飘起超过三呎。(那真是一个大家把疯狂当认真的年代。)
警方也警告,若抗议者开始破坏秩序,他们将会使用辣椒喷雾。霍夫曼则开记者会回应他们发明了一种新药,一旦喷到身上会进入人体血液,让人情欲高涨、想疯狂做爱。所有媒体马上开始谈论这种新药(当然有人恐慌有人兴奋),包括当红的电视主持人强尼卡森。(是的,那真是一个大家把疯狂当认真的年代。毕竟那时代经常有新药物出来,LSD也是几年前才开始流行。)
十月来了,十万人来华盛顿参加这场在林肯纪念碑前的示威,其中数万人接著游行到五角大厦参加“驱魔仪式”。新左派、反战派、纽约嬉皮,无数不满的青年都来了,许多著名知识份子和作家如诺曼梅勒都来参加,几周前才在玻利维亚死亡的切格瓦拉也在游行中的照片上现身。
不过,反战运动中的各种矛盾开始日益明显。彼时已有鸽派和鹰派的分裂,或者“甘地与游击队”的区分:后者不想再只是和平示威,认为必须采取暴力。
在五角大厦前,诺曼梅勒和诗人艾伦金斯堡带著群众高喊:“离开吧!魔鬼,离开吧!”。其间,纽约地下乐队The Fugs提供了吟诵的伴奏。
他们本来计划用一台小飞机洒下成千上万的雏菊作为仪式的一部份,不过,当天应征开飞机的人没出现——因为是FBI的人去应征但却故意不出现,他们只能把雏菊带去现场发给群众,也发给士兵。这造就了六零年代最经典的照片之一:带著刺刀的枪口上的雏菊。
嬉皮vs.军队,花的力量vs.战争机器。
五角大厦当然最终没有飘起来,多人被逮捕,但这场运动壮大了整个反战气氛,这个让人难忘的街头剧场更突显了越战的荒谬,让这场示威成为六十年代最鲜明的一幕。(也因为诺曼梅勒在第二年为这场示威写下一本经典著作:“夜里的大军”。)
不过,反战运动中的各种矛盾开始日益明显。彼时已有鸽派和鹰派的分裂,或者“甘地与游击队”(Gandhi and Guerrila)的区分:后者不想再只是和平示威,认为必须采取暴力。
带著嬉皮色彩的鲁宾和霍夫曼则清楚意识到自己与主流反战派的差异,决定走自己的路。
但所有人对于创造一场大运动来阻止战争,似乎更有了信心。那会是在隔年1968年八月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
3.
67年的最后一晚,鲁宾、霍夫曼和东村地下文化的几个家伙在家中喝酒嗑药,乱聊要不要创立一个新组织,因为接下来的68年是总统大选年,会是很重要的一年。他们想要大搞一番,而这或许需要一个新名字。接近午夜时,他们都已经很high 了。根据鲁宾自传,他们的思考逻辑是:
这是一个青年(youth)运动,所以要有y。
这是一场国际(international)革命,所以要有i。
这是人们要在生活中充满意义与乐趣,是一个派对(party),所以要有p。
合起来就是 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 (青年国际党),一个看起来十分有意义的党名,他们的伙伴Paul Krassner大叫,这就简称YIP-yip,我们是Yippies!
一个全新的运动就此诞生。
YIP当然不是一个真正的党,不是一个正式组织,而只是一个概念、一个让人搞不清楚的迷思。
鲁宾说:“美国的迷思/神话,从乔治华盛顿到超人到泰山到约翰韦恩都死了,因此美国青年必须创造自己的神话/迷思。”他知道,迷思/神话比个人更有力量,例如切格瓦拉、狄伦、黑豹党,都有超越他们个人的迷思,而“Yippie的迷思将会推翻这个政府”。
他们号召所有长发嬉皮们离开他们的家、离开他们的工作,丢掉他们的课本,来加入这场政治与文化革命。这些青年对加入SDS的严谨组织感到不舒服,可能也不想只是戴著花整天吸大麻,所以这是新左派和新品种嬉皮的结合。
他们试图创造一种“扰乱的剧场”,想要结合大麻与抗议,“要把孩子们带离体制、要把工人阶级的愤怒带入政治,要让嬉皮政治化。”。
Yippie既是所有反抗者的名字,也什么都不是。
关键是,“要有创意,不要只是跟随既有的模式,要创造自己的行动。”
“民主党提名了一个总统,而他把人民吃了,我们提名了一个总统,而人民可以把它吃掉!”
1968年确实是天翻地覆的一年。那年夏天,民主党将在芝加哥举办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总统候选人。因为68年初现任总统詹森尚未宣布不连任,大家都以为这个升高越战的总统会继续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所以Yippie说那将是一个“死亡的大会”(Convention of Death),而他们想要提出正能量的信息,所以要在民主党大会的同时举办一场“生命之节”(Festival of Life )。每天规划了丰富的活动:空手道和自卫术训练、地下刊物工作坊、摇滚音乐会、诗歌朗诵、梵语颂歌、游泳、做爱,8/28下午则参加反战全国行动委员会举办的和平游行。
Yippie还对媒体放话要采取各种行动来阻挠这次民主党大会,包括:
假装成出租车司机去饭店载大会代表,把他们载到城外让会议开不成;
打扮成越共在路上仿佛美国政客般和民众握手;
进入饭店在代表们的食物中下毒或放毒品;
在芝加哥的供水系统中加入LSD,让整个城市一起开始迷幻旅程。
这一切疯狂主意都被媒体报导,使得他们不需要买任何广告就能操控媒体,但媒体搞不清楚他们到底要做什么,例如芝加哥论坛报会出现这样的标题:“揭露Yippie的秘密计划”——他们可是很乐于被揭露。
霍夫曼不断在媒体嚷著“我们要把芝加哥烧毁殆尽!”、“我们要在海滩上疯狂做爱!”、“我们要求狂欢的政治!”
整个芝加哥都惊慌了,他们不知道到底这些家伙要干什么,芝加哥会被如何破坏。
他们甚至计划带一只猪去现场,并提名牠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他们说:“民主党提名了一个总统,而他把人民吃了,我们提名了一个总统,而人民可以把它吃掉!”
他们公开宣告:
“这个八月来芝加哥加入我们举办的青年音乐和剧场的国际文化祭吧⋯⋯这是八月的最后一周,而‘全国死亡党’会聚在这里祝贺詹森连任。我们也会在!到时会有五万人在街上赤裸著跳舞,我们会在公园中做爱,我们会阅读、唱歌、微笑、印刷报纸,举行一个模仿他们的大会,庆祝我们这个时代一个自由美国的重生⋯⋯一切都是免费/自由的⋯⋯我们追求欢愉的政治(politics of ecstasy)⋯⋯我们会创造自己的现实⋯⋯”
4.
本来没有人想要暴力抗争。
休伦港宣言起草人汤姆海顿在此时是活跃的反战运动者,他希望八月份在芝加哥的大规模抗议可以彻底暴露出“这个国家的政治闹剧”。他和另一位组织者戴维斯(Rennie Davis)写了一份说明指出数百万人反对越战,但战争依然持续,这代表了美国民主体制的失败,外交政策只被一小撮人的“国家安全复合体”所决定,因此他们要透过这场抗争来表达人民有知道真相和掌握政府的权利,并要举行人民的代表大会,实践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的精神,来对比民主党的层级和威权。他们主张行动必须是和平与合法的,因此向芝加哥政府提出申请,但没有获得许可。
Yippie们在整个春天很认真准备八月的“生命之节”。他们想像到时大批长发嬉皮和怪人在公园中享受自由的爱和摇滚乐,这状态就会迫使政府和警方陷入恐慌,对这个城市采取暴力姿势。他们并没有想在街头捣乱,所以也向芝加哥市政府申请集会许可,但也被拒绝。
不让抗议团体合法游行和在公园搭营,注定芝加哥街头将成为一个血腥战场。
当时的芝加哥市长是个凶狠粗鄙的家伙。在四月金恩博士之死造成暴动时,他就下令,手上拿汽油弹者格杀勿论(shoot to kill),抢劫商店者可以开枪打残。面对这场风雨欲来的抗争,他更是部署了重兵,包括警察、国民兵和军队,甚至散弹枪和坦克都准备好上街了。
就在民主党大会几天前的8月20日午夜,苏联军队开进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人们在电视上看见了布拉格美丽街道上的坦克车和长枪。霍夫曼在记者会上将芝加哥比喻成“捷加哥”,批判这个城市是另一个警察城市。
但他们并不害怕。鲁宾说:“美国本来就是个暴力的国家,但其暴力都是对于看不见的人、对有色人种,所以我希望暴力可以在电视的黄金时段被看到!就在你眼前!”
海顿说,“芝加哥将是一个警察国家和人民运动的摊牌。”而“民主就在街头上”。
在这场暴动中,你站在哪一边呢? 在六十年代的反叛中,你是属于哪一边呢?
8月25日,民主党代表大会前一天,Yippie在公园举办“生命之节”。原本预计邀请的很多乐队如杰佛逊飞船等都因为担心警察暴力而不出席,最后只有来自底特律的摇滚乐队MC5和抗议民谣歌手Phil Ochs参加。当MC5这个庞克摇滚先驱用巨大的能量在演出时,警察开始在台下挥著警棍驱赶群众。
夜里十一点,警方实行宵禁,强力殴打路上群众,人们在街头奔逃,血流不断。
这个场景会成为日后每天上演的戏码,而且警察越来越激烈与暴力。
8月28 日是代表大会的高潮,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将正式诞生。
一万多名群众在下午从公园走到街上,聚集在举行代表大会的希尔顿饭店外示威,等待他们的是两万名军人和警察。愤怒与恐惧同时包围著抗议者们。
突然间,催泪瓦斯弥漫了现场,警察疯狂似地殴打群众,甚至包括旁观者和经过的市民,鲜血穿透了灰白的瓦斯迷雾,群众在哀嚎中嚎叫著:“全世界都在看!”(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这句话成为六十年代最重要的注脚之一。
警察甚至冲进旅馆大厅开始打人。“示威者、记者、麦卡锡竞选党工,所有的人都踉跄跑出到旅馆大厅,鲜血从他们的头上和脸部喷涌而出”,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如此报导。
当电视前观众看著民主党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发表演说时,却同时看到不断插播的场外流血冲突。被称为美国最受信任的电视主播Walter Cronkite说,“我的天哪,看看他们对这群年轻人做了什么。”
的确,全世界都看到了,而鲁宾的期待实现了。
对运动者来说,这场血染的抗争是场成功,因为它让美国人看到疯狂的警察暴力——政府在年底发布对这个冲突的报告都指出这是“警察暴动”(police riot),让这场代表大会成为被历史记住最血迹斑斑的一次大会。更多年轻人被刺激励投入运动,且愿意采取更激进的行动。他们相信,这会让政府意识到延长战争必须在国内付出代价。
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在电视机上看到的是一群长发嬉皮、一群暴力群众,在严重破坏这个城市的秩序,让美国的民主蒙羞。并且,如此相信的人数可能更多一些,所以共和党尼克森以代表“沉默的多数”为号召,在几个月后赢得了美国总统(虽然他只获得43%的普选票)。
这是六十年代青年文化革命的巨大讽刺。
尼克森批评芝加哥这场抗争时说,“这是文明死亡的开始。”
所以,在这场暴动中,你站在哪一边呢?
在六十年代的反叛中,你是属于哪一边呢?
这是彼时不同世代、不同种族的所有美国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场最终的审判就要开始。
5.
尼克森总统于69年一月上台。三月时,汤姆海顿、戴维斯、鲁宾、霍夫曼和黑豹党的席尔(Bobby Seale)、反战组织领袖戴林杰等八人被控在芝加哥煽动暴动,被称为芝加哥八君子(Chicago 8)。(后来席尔的审判被分开,所以改称为芝加哥七君子。)
这八个人分属于反战团体、前SDS成员、Yippie、黑豹党,和两位比较不知名的当地学者。政府显然刻意挑选不同团体的代表,因为黑豹党领袖席尔根本没参与组织这几天的抗议,只不过给了一场演讲。后来档案揭露,尼克森政府就是要透过起诉不同代表性团体来打击整个反对势力。
不过,这对他们完全不算打击。鲁宾说:“这个起诉把原本在芝加哥之前没有团结起来的各种力量全都聚在一起了,因此给予运动新的能量。芝加哥之战是一场胜利,即使法庭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在法庭上,斗争仍然必须继续,所以我们很高兴被起诉。”
他们很清楚这场法庭审判可以是最精彩的荒谬剧场现场,戏码会是一场卡通化的正邪之战:法官代表了一切腐化的权威,而他们是正义革命者、是被国家机器压迫的受害者。霍夫曼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希望影响年轻人,希望显示他们和起诉者是不同的人,希望呈现对分裂这个国家的各种议题的剖析….. 我们永远赢不了和有武器的人的权力斗争,我们唯一的武器是想像力。”
在审判开始前的68年十月,芝加哥八君子中的五人被众议院非美委员会传唤。第二次来到这里的鲁宾,这次打扮成切格瓦拉式的丛林游击队员形象(他甚至三周没洗澡来凸显真实感),霍夫曼则穿上国旗装,让议员们抓狂。这只是接下来这场历史性审判的小型预演。
“我们永远赢不了和有武器的人的权力斗争,我们唯一的武器是想像力。”
1969年九月这场八君子的审判正式开庭,全国媒体都给予很大的关注,每天新闻不断。被告们利用法庭陈述机会痛批尼克森和越战,在法庭上对法官恶作剧,七十多岁的法官也恰如其分地“扮演”了最老朽保守的“反派”角色。
被告海顿在一开始被介绍起立时,举起拳头表示抗议。而当霍夫曼被介绍起立时,他给了法官一个飞吻。
出庭时,鲁宾和霍夫曼一度穿上法官的法袍出庭,让台上法官脸都气红了,命令他们马上脱掉,但他们里面穿的是警察的蓝白制服。这简直是“周末夜现场”的喜剧秀。
在席尔生日那天,鲁宾带了蛋糕进来,上面写了“Free Bobby. Free Huey”。 法官说他的庭上不准有食物,让法警把蛋糕拿走,他们大喊:“这是绑架蛋糕(cake-napping)”,另一人对席尔说:“他们逮捕了你的蛋糕”。席尔回说:“他们逮捕了蛋糕,却逮补不了革命。”
席尔曾一度大骂法官是种族主义猪猡、法西斯主义骗子,结果法官下令用毛巾堵住他的嘴巴,且把他绑在椅子上。一个黑人在法庭上被如此对待仿佛是整个美国种族压迫的譬喻,让许多人震惊,连伍迪艾伦都难以忘记。
这场历史性的审判历经数月,许多六零年代的重要人物一一出庭作证,包括歌手Phil Ochs、Judy Collins(他们甚至在法庭上唱歌)、作家诺曼梅勒、艾伦金斯堡、黑人运动领袖杰西杰克森、LSD宗师提摩西赖瑞等。整个法庭成为一座真正的历史剧场,六零年代不同领域的主角们轮番上台独白、唱歌、搞笑、演讲,讨论何谓真理、正义与和平的问题。
于是,法庭上被审判的不只是芝加哥八君子,而是整个六十年代的激情与反叛,是对美国灵魂的不同想像,并且是如此具象征意义地在六零年代的最后几个月进行。
这场六十年代最终的审判在1970年二月结束,他们一度被定罪,但后来上诉法庭推翻他们的罪刑,只有席尔因另外的罪坐了比较多年的牢。
在审判最后,鲁宾对法官说:“你比我们让更多年轻人激进化。你才是最YIPPIE的!”
6.
进入1970年,这场闹剧式的审判结束了,整个狂骚的六十年代也落幕了,曾经的抗议与反文化似乎将逐渐烟消云散,只剩下零星的激烈火花在七十年代初不认命的更猛烈燃烧。
在审判之后,鲁宾和霍夫曼成为超级文化明星,甚至和刚搬到纽约的蓝侬与洋子成为好友,也刺激了后者的激进化。但两三年后,霍夫曼潜入地下——不是因为他成为放炸弹的政治激进份子,而是他变成一名海洛因毒贩,在被捕后逃狱。在地下逃亡期间,他陷入忧郁,几度想要自杀。在七十年代后期,他一度以化名公开出来参与环境运动,直到1980年才公开自首。接下来的几年,他依然是媒体名人、依然参与政治抗议,也依然有严重忧郁症。最后不幸在1989年自杀。
是他们太疯狂,还是那个时代让每个人都如此疯狂?
鲁宾的人生一样出现激烈的转变,只是对他来说那是喜剧,而非悲剧。他看到六零年代反文化对于主流文化(尤其是广告和媒体)的影响,决定去华尔街工作,从六十年代激进颠覆的Yippie转变为八十年代中产阶级Yuppie(雅痞)的代表。他在七零年代中期出版一本书叫《长大》(Grow Up),并在八十年代初和霍夫曼进行名为“Yipppie vs. Yuppie”的公开巡回辩论(这当然也是一种媒体和商业操作),霍夫曼指控他出卖了理想,但他确实成为人生胜利组。
戴维斯在七零年代初继续参加反战运动后,一度投入印度宗教大师门下,后来成为创投企业家。
席尔在69年五月因为被控杀人而与其他几名黑豹人一起入狱,在芝加哥案审判后,这个谋杀案也开始审判,成为全国焦点。他在72年被释放,成为黑豹党的icon。
海顿持续参与反战运动,娶了电影明星珍芳达,在九十年代担任加州地方议员,连任数届。他一生都坚持青春时的理想,积极参与美国左翼运动,直到2016年过世。他是一名永远的异议者。
六十年代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不同印记,悲伤的,讽刺的,愤怒的,或始终昂扬的。
Yippies尤其是六十年代最具想像力的一群青年,他们把现实化为剧场,用幽默和荒诞挑衅了政治,重新定义了抗议文化。
是他们太疯狂,还是那个时代让每个人都如此疯狂?
作家诺曼梅勒在芝加哥大审判时出庭作证说的好:“我可能有点疯狂,但我是一名作家。这些人也有点疯狂,但是是这些疯子告诉你什么是清醒。去倾听他们吧,因为真理就在他们的疯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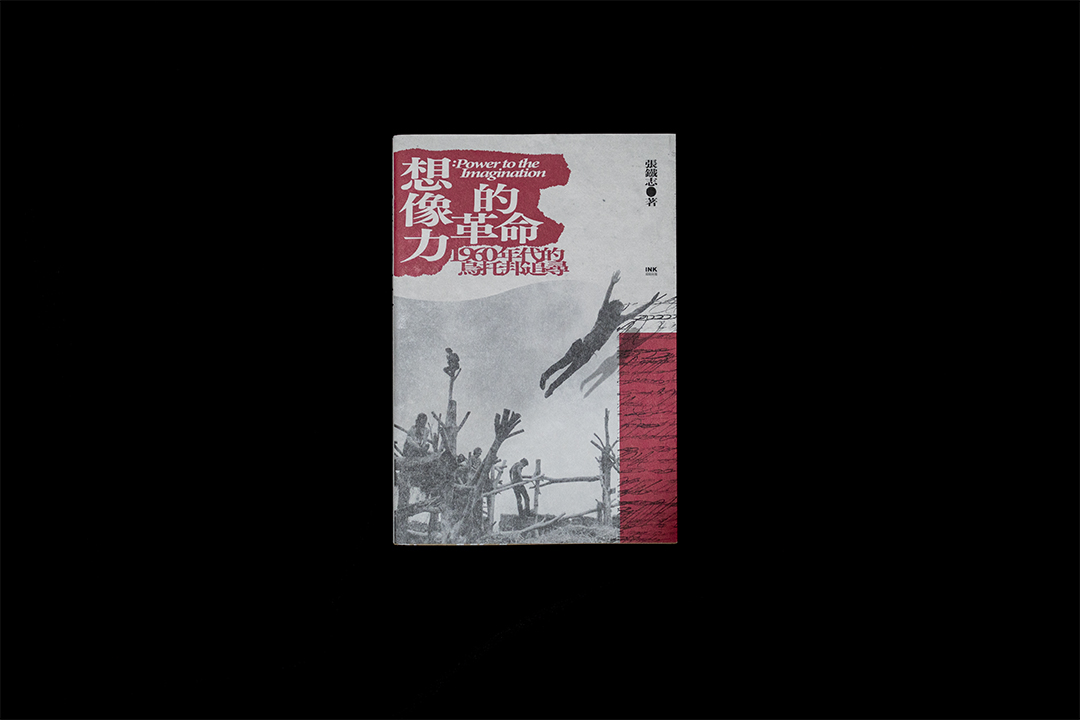




感激不盡,作為一個活人看到生命,如聖經所說「可讓人喜悅的」
精彩,以熱情把生命一點不剩的燃燒。
太精彩了,想要入这本书,想要浸润一下那些年代的疯狂迷思。
這篇文章太、精、采、了。bravo!
用端app中,看到的是繁體
繁體網頁看到的仍然是簡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