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视台湾为其“神圣领土的一部分”[1],并于近年持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在此复杂地缘政治脉络中,陆配网红“亚亚”(本名刘振亚)因在其影音频道“亚亚在台湾”遭检举有鼓吹“武统台湾”的影片,引发广泛争议并遭到台湾当局取消居留许可。
刘某主张其言论只是主张和平统一、反对台湾独立、“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 并无鼓吹战争宣传之意,亦声称家庭会因她遭遣返而分崩离析,指控台湾当局侵害她的基本权利。台湾移民署则认为,刘某的言论“危害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定”,违反了居留许可的相关规定。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经当庭播放审酌有关影片内容后,于3月21日驳回刘振亚停止执行有关处分的声请,认为刘某显然以抖音媒体散布“支持中国大陆武力统一中华民国”,而有鼓吹战争宣传之事实,客观上已足认为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之虞。
笔者身为香港人[2],并非台湾法律专家,但此案所引发有关人权与国家安全之间平衡的讨论,尤其是现今国际武装冲突持续频繁爆发的背景下,有其普遍适用意义。本文将从国际人权法及比较法视角,探讨国家在行使驱逐权力时,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个人权利(包括家庭与私人生活权以及儿童的最佳利益),并以“亚亚”案例为例,分析相关法律原则的适用。

一、国家主权与移民控制权
在现行国际法下,国家主权(sovereignty)赋予国家对其领土的绝对控制权,包括决定外国人是否可以进入其领土,以及在外国人居留期间施加逗留条件。此权力被视为国家主权行使之具体表现,并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国家有权基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经济利益等考量,制定签证制度等移民政策,以有效管控外国人在其境内的活动。因此,国家在移民事务中并无普遍义务必须尊重非本国居民和其伴侣选择居住国的意愿,或无条件容许其于当地实现家庭团聚。
尽管国家拥有广泛管控非本国居民的权力,包括限制或终止其居留权、甚至将其驱逐,但此权力并非毫无限制。尤其是在国际人权法框架下,国家在行使驱逐非本国居民的权力时,当驱逐措施涉及个人基本权利,必须遵守相关国际人权标准。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和《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保障家庭生活及私人生活权,若驱逐措施可能干扰此等权利,则该措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且在民主社会中具必要性,并与其追求的合法目的(如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相称或符合比例。
因此,国家在行使驱逐权时,需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避免对被驱逐者造成过度侵害。上述原则在多个国际判例中得到具体诠释,是评估驱逐措施正当性的重要依据。
二、驱逐案件的衡量标准
欧洲人权法院(由17名法官组成的)大法庭于《Uner v Netherlands》[3]一案的裁决中,奠定及明确了适用于驱逐案件的法律标准。该案申请人为土耳其籍,在荷兰居留多年并育有子女,因暴力犯罪被驱逐,主张驱逐将导致家庭分离。大法庭裁定,国家有权驱逐非本国人,但必须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驱逐措施正当与否需具体判断,依个案情境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1) 该人有否犯罪(或其他严重不当行为)及(如有的话)其性质与严重性;
(2)该人在所在国的居住时间;
(3)该人的国籍;
(4)该人的家庭状况(如婚姻长度、子女年龄);
(5)该人的子女在原籍国可能面对的困难;
(6)该人与所在国及原籍国分别保持的社会、文化及家庭联系。
简而言之,驱逐措施的正当性取决于政府是否具备支持驱逐的公共利益依据,以及驱逐会否导致家庭生活实质破裂。

(1)言论与驱逐的关系
i. 言论自由的根本重要性与民主价值
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乃国际人权法(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明文保障且高度重视之基本权利。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保障个人表达意见的权利,更在于促进多元,使社会得以透过对话实现思想的碰撞与进步。
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在《Refah Partisi (the Welfare Party) v Turkey》 [4]案中指出,言论自由之所以被视为民主社会的根本权利,是因为多元性(pluralism)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言论自由正是实现多元性的基础。言论自由不仅适用于受欢迎或不受争议的意见,更涵盖“令人反感、震惊或不安(offend, shock or disturb)”的言论。
正因如此,言论自由在民主社会中具有特殊地位,允许个人以和平方式表达异议,甚至挑战现有的社会、政治、法律或宪制秩序。若言论仅因不符合主流政治逻辑或宪法秩序而被限制,不但无助民主价值的实现,甚至可能危及民主本身。
ii. 和平挑战现有制度并符合民主价值的言论应受保障
更具体而言,欧洲人权法院在《Stankov v Bulgaria》[5]案中强调,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是民主社会的“至高价值(paramount values)”,其核心在于透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主张自治、分裂国土以至推动政治实体统一的言论,若以合法和平的手段表达,且未否定基本民主原则,均显然属言论自由的保护范畴。
因此,在 2025年的《Ukraine v Russia (re Crimea)》[6] 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确认,已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居民意欲举行和平集会,呼吁维护乌克兰领土完整,表达领土变更的要求,并不当然构成对俄罗斯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的威胁,禁止支持乌克兰之公开集会与示威,并伴随恐吓与任意拘留示威组织者,此举未被证明在民主社会中必要,属违反《公约》的条文及精神。
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445号解释亦反映此保障和平表达政治言论的精神,指出限制集会自由须有“明显而立即危害”之事实,政府不得仅因某人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等政治意见而加以禁止。
iii. 鼓吹武装冲突的非民主言论,应限制与否?
换言之,正如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在《Refah Partisi案》中明确指出,主张体制变革的言论须满足两条件,方受保障:其一,手段须合法且民主;其二,所提变革本身须符合基本民主原则。反之,当言论涉及鼓吹暴力、战争或提出以极权取代民主主张,其保障 - 亦唯有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 - 即受到严格限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明确规定,任何鼓吹战争之宣传应为禁止;同《公约》第5条第1段亦有规定:“国家团体或个人[没]有权从事活动或实行行为,破坏本盟约确认之任何一种权利与自由 …”类似规定亦见于《欧洲人权公约》第17条,禁止滥用人权以从事破坏人权价值的活动。 就此,欧洲人权法院2013年的判例《Kasymakhunov and Saybatalov v Russia》[7]颇具参考价值。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该案申请人所属的“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Tahrir)呼吁暴力摧毁他国、驱逐和杀害平民,并美化战争,暗示会诉诸非法暴力手段变革所在国家的法律和宪制结构,以建立一个否定政治及平等权利的极权统治,显然违背了人权公约和平解决国际冲突和坚持人命神圣性的民主理想和价值,故言论不受言论自由保障。
负责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的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ttee)在其《第34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言论自由的限制须基于正当理由,且被限制的言论和当局认定的威胁之间须有“直接和紧密的关联”。欧洲人权法院同样允许国家当局在“迫切的社会需求(pressing social need)”下限制言论,并赋予国家当局一定的裁量权。尤其当邻国的侵略行为构成现实威胁时,例如过去几年乌克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在俄罗斯侵略威胁下,依当时当地之具体社会背景,判断存在“迫切的社会需求”,进而限制国内支持侵略者的言论,获得欧洲人权法院法院认可[8]。
相较之下,美国最高法院依该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采取的标准更为严格。《Brandenburg v Ohio》[9]案确立“即将发生之非法行为(imminent lawless action)”原则:仅当言论“意图并实际可能煽动即将发生的非法行为(directed to inciting or producing imminent lawless action and is likely to incite or produce such action)”时,方可限制。此为极高门槛,例如《Brandenburg案》中三K党领袖带有恐吓意味、声称要报复黑人从平权运动中“获益”的明显种族仇恨言论,因未达即刻煽动程度,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驳回刘某声请停止处分执行声请时援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0条,强调应禁止鼓吹战争之宣传,似显示台湾司法对言论限制,较之美国对仇恨暴力言论的绝对保护立场,倾向采国际人权司法实践中较审慎的见解。

iv. 外国人鼓吹战争,就可被合法驱逐?
言论自由之保障不分国界,并超越国籍。欧洲人权法院大法院于《Perinçek v Switzerland》[10] 一案中指出,无论系本国人或外国人,其言论自由之权利均应平等受保障,外国人同样得自由和平表达多元意见,冲击现有制度秩序或主张领土变更。
欧洲人权法院在多案中要求,各国若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入境禁令,必须提供具体证据证明该禁令的必要性。反对官方理念与立场的人必须能在政治与言论领域中找到一席之地,若缺乏证据证明个别言论构成实质威胁,仅因国家反对某人观点而实施禁令,无异于以公权力强制个人改变思想信仰,系对言论自由的不当干预。
例如《Piermont v France》[11]案中,被禁止再次入境的申请人支持当地少数政党的反核与独立诉求,其言论是在和平、经授权的示威中发表,未曾呼吁暴力或混乱。法院认为即使在选举在即的政治紧张时期,此言论仍是对法属波利尼西亚民主讨论的贡献,少数意见只要未引发暴力或混乱,应受保护,而非惩罚。法院在《Cox v Turkey》 [12] 一案中亦裁定,身为大学教师的申请人只是就当地政府对独派群体的残暴对待发表强烈意见,其言论即使不符官方立场,亦不代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入境的措施,未能在公共利益与言论自由间取得适当平衡,显然系为压制言论自由及思想传播的非正当之举。
然而,一旦言论涉及煽动暴力、甚至鼓吹国际或国内武装冲突,否定民主原则及和平价值,其保障即被根本削弱。对于非本国居民而言,若发表此类言论,不仅难以主张言论自由的保护,更可能因威胁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而面临驱逐。就此,南非《宪法》第16(2)条明文列举三类表达,即战争宣传、煽动即时暴力及仇恨言论,不受言论自由保障。南非宪法法院在《Islamic Unity Convention v Independent Broadcasting Authority》 [13]案阐明,国家有特殊利益规制此类表达,因其危害构筑基于人性尊严与平等的非种族、非性别歧视社会之宪法目标。
然而,宪法法院亦强调,战争宣传固然可能威胁、分裂社会不同族群,但并非所有可能损害社会不同族群关系的言论皆属战争宣传或煽动暴力,一刀切禁止前者反而不利民主社会中正常的理性讨论,可能构成对言论自由之过度限制。
对于非本国居民(即外国人)发表支持国际武装冲突的言论,其入境及居留的权利于何种情况下可以合理限制,欧洲人权法院及欧洲联盟法院其实已有先例可援。欧洲联盟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的)大法庭在《Joined Cases C-331/16 & C-366/16, K v Staatssecretaris van Veiligheid en Justitie》[14]一案阐明,若有关个人的行为显示其持续抱有敌视人类尊严及人权等基本价值之倾向,包括意图破坏国际和平,则即使该行为未立即导致具体犯罪,仍足以构成对社会基本安全利益的“真实、即时存在且足够严重之威胁”(a genuine, present and sufficiently serious threat)。故在此情况下,限制其居留权即属正当,驱逐(如经考量其他因素后属相称的话)亦成为其中一个合理后果。
在 《Kirkorov v Lithuania》[15] 一案中,俄罗斯籍的申请人因发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武装侵略及美化“辉煌苏联时代 (the glorious Soviet Union era)”的言论,被立陶宛列入禁止入境名单。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虽此举干预了言论自由,但考虑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非法行为,以及申请人的行为似是俄国在欧资讯战一环的事实,有关言论足以构成“应受谴责之行为(reprehensible act)”,当局可合理、合法地视申请人为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威胁,在其与立陶苑社会、经济联系皆不深的前提下,限制其入境或居留权。
同样地,《Zarubin v Lithuania》[16]案中一名俄罗斯记者被认定是俄政府传播官方立场及亲俄宣传的工具,涉及在立陶宛煽动战争、纷争及民族仇恨,加上其曾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侵略性与挑衅行为,立陶宛当局视其为国家安全威胁并将其驱逐,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具备充分理由。

(2)家庭生活与所在国的联系程度
在驱逐案件中,如上述欧洲人权法院案例《Kirkorov案》显示,即使被驱逐者曾发表鼓动战争言论等应受谴责之行为,其与所在国的联系程度或是评估驱逐措施相称性的另一关键考量。就此,欧洲人权法院与英国法院近年实践《欧洲人权公约》的判例提供了不少案例及具体指引。
《Khan v United Kingdom》[17]案中申请人为巴基斯坦籍,自幼随家人移居英国,因犯罪面临驱逐,他主张与英国家人关系密切,而且从未曾返回巴基斯坦,与该国并无实质联系。欧洲人权法院认定,英国政府在此情况下将其驱逐,将对其私人及家庭生活造成过度干扰,违反相称、比例原则。
另一宗案件《Sanamba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18]则涉及一名曾涉犯罪的伊朗籍英国居民,其同样主张在英国已融入社会多年,如遭驱逐至伊朗则难以适应重回正常生活。负责该案件的
英国最高法院,引用并分析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后强调,政府应考虑被驱逐者回国后会否遇到融入障碍:“融入”不仅指经济自立(能否于当地谋生),更包含对当地社会生活的理解、参与能力,以及在合理时间内建立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法院认为,该伊朗籍居民虽已在英国生活多年,但具备波斯语能力及与伊朗的文化联系,足以在伊朗重建生活,所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其在原籍国的融入障碍并非“非常重大”(very significant obstacles),驱逐并无不合理之处。
(3)儿童最佳利益的优先考量
另外,当有关决定涉及被驱逐者的未成年子女时,国际人权法普遍认同儿童的最佳利益应被视为“首要考量(of paramount importance)”,在权衡中予以额外比重 [19]。
具体而言,与评估被驱逐者本身的权利相类似,当局有责任需评估:子女的年龄与依赖父母的程度,若子女融入原籍国和所在国社会的程度,以至驱逐对子女教育、心理及社交发展的影响。在《Jeunesse案》中,申请人因逾期居留面临驱逐,但她的子女在荷兰出生并成长,拥有荷兰国籍,其家庭生活完全植根于该国。申请人作为主要照顾者,每天负责照顾在荷兰成长的子女。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子女与荷兰有深厚联系,且无证据显示他们与原籍国有直接联系,若驱逐申请人,将迫使子女面临必须选择与母亲分离或搬迁至陌生国家的困境,这显然不利于子女最佳利益,故驱逐决定有违对申请人家庭生活权应有之尊重。
相对地,若子女可以留在原籍国与父母其中一方稳定生活,则驱逐另一名家长不一定违反儿童最佳利益[20]。在《Gül v Switzerland》[21]判例中,欧洲人权法院亦认为,申请人虽在瑞士居留多年,但其子女熟悉原籍国文化与语言,其一家在原籍国重建生活并非不可能,驱逐未构成对家庭生活的过度干扰。

三、“亚亚”的情况
在本案中,刘某虽无犯罪记录,但其鼓吹“武统”的言论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定“有鼓吹战争宣传之事实”,视为敌视台湾基本价值并威胁国家安全,表面上符合“应受谴责之行为”的认定,且构成“真实且即时存在之威胁”。然而,刘某在台有配偶及子女,如能证明她已经彻底融入台湾社会,且与留台子女关系密切,此可能成为反对驱逐的重要依据。例如若刘某子女年幼或高度依赖其照顾,且无法随行至大陆,在台湾的具体处境会因驱逐措施蒙受重大不利影响,则驱逐可能对其家庭生活及子女福祉构成重大干扰。
但另一方面,法院或认为,若子女在台有配偶照护,且台陆两地语言皆为中文,即使前往大陆亦无语言不通的问题,在交通与通讯科技发达的前提下,则影响或可减轻;而刘某本人为中国大陆籍,作为网络红人(其抖音帐号目前拥有接近57万粉丝,曾获得超过1500万赞好)与大陆观众互动频繁,与大陆观众密切相关,事业重心(至少部分)在中国大陆,显示其与大陆的联系密切,回国后融入障碍预期偏低。考虑到刘某的职业特性、中文能力及与中国大陆的密切联系,其处境与《Sanambar案》中伊朗籍申请人情况最相类似,回国后的家庭生活预期应不致面临过度困难。
最终,台湾最高行政法院3月27日于114年度抗字第158号裁决驳回刘振亚抗告,认为移民署就刘某言论对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之威胁的评估无明显违法之处,而刘某被废止依亲居留,虽然被管制5年内不得再申请长期“依亲居留”,但其根据《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以短期探亲或观光等其他合法名义来台的资格原则上未被影响可,配偶亦可前往大陆团聚,短期内不致导致夫妻关系破裂;子女在台有配偶照护,以现今两岸交通、通讯便利互通之程度,不认驱逐将造成家庭生活或子女教养的重大难以回复之损害。此裁决与笔者上述基于国际与比较人权法判例的分析一致。
四、结语
面临强大邻国压力时的无奈,无疑为民主价值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增添了复杂性。台湾政府在批评香港国安法之际,自身亦援引国家安全限制言论,定会引来双重标准的指责。
依人权原则,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言论自由,一般而言应保持怀疑态度,若无证据显示言论涉及仇恨或煽动等可谴责行为,应优先保障言论自由。因此,和平倡导领土变更(无论是独立还是统一)的言论因符合民主精神与合法手段,理应受言论自由之全面保障。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其发动“资讯战”与不断散布仇恨及虚假资讯的纪录受到国际关注。分别来自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美洲国家组织及非洲人权及民族权利委员会,由学者担任的四位人权专员,于2023年5月2日就现代传媒自由及民主此一议题发表联合声明,其中指出某些国家透过媒体操纵舆论,散布虚假资讯、错误资讯及仇恨言论,侵蚀社会凝聚力与民主治理,可能威胁国家、区域及全球和平与安全;将资讯武器化以传播仇恨言论及战争宣传,在民主中尤其无立足之地。
这突显出的法律难题是,如“亚亚”事件,在国际冲突风险日益加剧的现实背景下,此类争议较战争前出现更多,法律体系尝试在保障个人权利与防范潜在威胁间寻求平衡。国际人权法虽强调言论自由之重要性,但实践上似乎倾向接受,必要时得依法限制此类特殊言论。
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台湾作为民主社会,须谨慎权衡国家安全需求的同时,尊重人权。刘某案件的处理,须确保法治与人权并重,以维护民主社会的稳定与自由。台湾如何在外部威胁下平衡自由人权与国家安全,值得深思。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
[2]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显然不承认台湾政府的合法主权,然此并不代表得以漠视台湾乃英国最高法院所认定之“尊重法治传统之发达社会(a developed society with a tradition of respect for the rule of law)”(参见 Lord Advocate (representing the Taiwanese Judicial Authorities) v Dean (Scotland) [2017] UKSC 44, 2018 SC (UKSC) 1 第38段),且其法院有能力适用法律并展现“对证据之全面审慎评估及合理结论(a full and careful assessment of the evidence and a reasoned conclusion)”(参见 Dean (Zain Taj) v Lord Advocate [2015] HCJAC 52, 2015 SLT 419 第55段)。关于香港法院如何承认台湾法制下的法律原则与法律行为,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案例《陈丽虹诉丁磊淼》 (2000) 3 HKCFAR 9。
[3](2007) 45 EHRR 14。
[4]ECHR 2003-II 267。
[5]ECHR 2001-IX 273。
[6] (2025) 80 EHRR 1。
[7] App No 26261/05, 26377/06 (欧洲人权法院第一分庭,2013年3月14日)。
[8] 譬如参见《Gapoņenko v Latvia》App No 30237/18 (欧洲人权法院第五分庭,2023年5月23日)和《Borzykh v Ukraine》App No 11575/24 (欧洲人权法院第五分庭,2024年11月19日)。
[9] 395 US 444 (1969)。另参见例如Noto v United States, 367 US 290 (1961)。
[10] (2016) 63 EHRR 6。
[11] (1995) 20 EHRR 301。
[12] (2012) 55 EHRR 13。
[13] [2002] ZACC 3。
[14] [2018] 3 CMLR 26。[15] App No 12174/22 (欧洲人权法院第二分庭,2024年3月19日) 。
[15] App No 69111/17 (歐洲人權法院第二分庭,2019年11月26日)。
[16] (2010) 50 EHRR 47。
[17] [2021] UKSC 30, [2021] 1 WLR 3847。
[18] 參見《Jeunesse v Netherlands》(2015) 60 EHRR 17 (GC)。該判例所述之法律原則近年在MA v Denmark App No 6697/18 (歐洲人權法院大法庭,2021年7月9日)一案中獲再次確認。
[19] 參見《El Ghatet v Switzerland》App No 56971/10 (歐洲人權法院第三分庭,2016年11月8日)。
[20] (1996) 22 EHRR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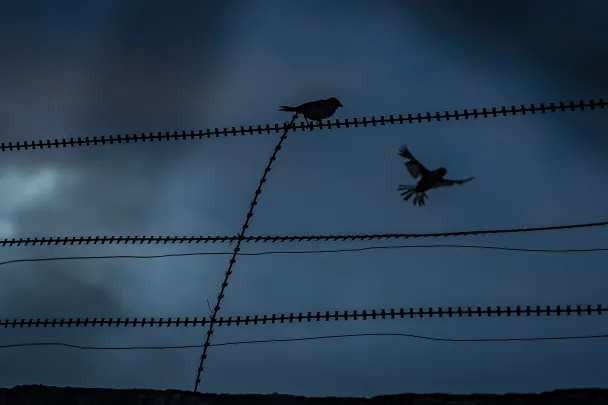

言之有理
写得非常详细具体,这个领域并不非常热门,作者学识渊博
這些愛國賊早晚被反噬。
這就是我想看的!
不過「立即且直接的危險」到底如何裁定?不同於犯罪預告,在灰色衝突的現狀下似乎比較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