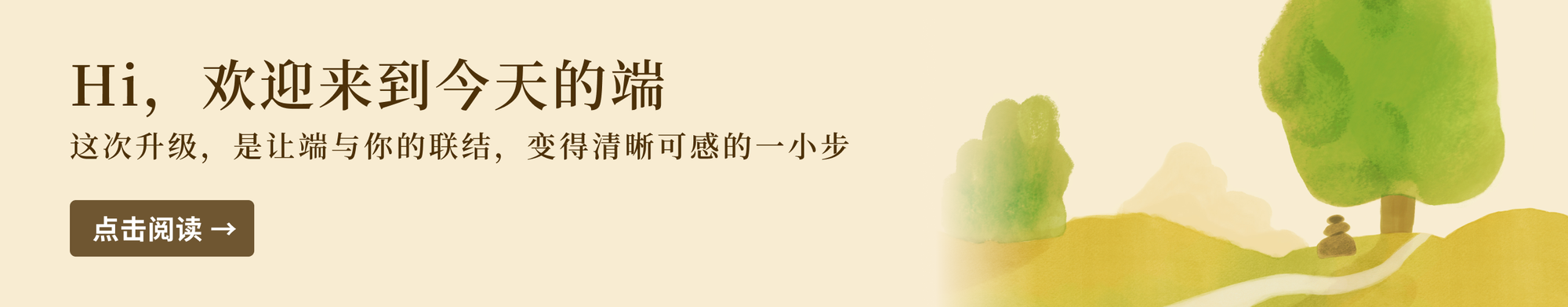编辑精选


/
仅限会员
失落的热带:香蕉种植园和不属于这里的人
这群中国人和越南工人,是两个国家在不同历史进程拥有相似处境的人。种植园将他们放置在了同一时空,是同样没有保障且不确定的生活,是不得已的选择,是背井离乡过一种农民生活。





系列
更多

栏目
更多
不重磅记者自留地-zh-hans
所有文章
我们的作者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