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经陪审团3日半商议后,香港“反恐第二案”(又称“九十二签案”)的首7名被告,遭一致裁定主控罪悉数不成立,惟同时以8比1大比数裁定其中3名被告(何卓为、李嘉滨和张家俊)之交替控罪“串谋导致相当可能危害生命的爆炸”罪名成立。其余4名被告及第8被告的所有其他罪名则一并不成立。
此案是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相关司法审判的最后余波之一,涉及香港法例第575章《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下称《反恐条例》)的控罪。因案件备受关注、而陪审图裁定主控无罪,因此值得解读。
这是继2021年“光城者案”之后,香港第二宗应用该《条例》的刑事案件。指控围绕三宗于2020年1月27日至3月8日期间发生或计划实施的爆炸事件;案犯时值香港首两波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从发生到裁决历时逾5年半。大部分被告自被捕起已还押超过2,000天。案中的8名被告被指控为“九十二签”组织成员,其中部分人更被描述为扮演组织主导角色。
因三宗事件发生或策划之时,《港区国安法》,首7名被告均被控一项《反恐条例》下之“串谋对订明标的爆炸”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即串谋针对特定地点进行爆炸行动,意图导致他人死亡、严重身体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害。另有其他交替控罪。
审讯于2024年11月在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开审,持续逾160天,由9人陪审团审理。而尽管陪审团最终作出无罪裁决,香港警方仍坚持以“极端团伙”及“本地暴力组织”等表述,形容是次事件之性质。依惯例,陪审团之裁决理由不予公开披露或说明,本文亦难以精确分析具体的法理依据。。然则,正如加拿大最高法院于《女皇诉Sherratt》[1]一案所论述,陪审团体现“社会良知(the conscience of the community)”,其在审视各项控罪要件时所间接展现之价值判断,有助于推断相关爆炸行为于社会脉络下之适切定性。
不过,陪审团裁决公布后,香港警方公开宣称今后将更广泛援引《港区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23条)》,以应对类似行为。此番表态意在强化国家安全之执法力度,然而亦引发对法律适用范围之疑虑。

《反恐条例》罪行与国际标准
依《联合国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第2条之规定,任何人在公共场所或针对基础设施等标的,非法且故意引爆爆炸性装置或其他致命装置,意图造成他人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或导致大范围毁灭并可能引致重大经济损失,即构成恐怖主义行为。该《公约》于1997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并自2001年12月起对中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生效,其核心目的在于防范及遏止以爆炸为手段、以平民为目标的恐怖袭击。
《公约》强调行为之客观危险性及主观意图之恶性,并不以行为人之政治动机作为构成要件。此一设计反映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之共识,即其本质在于暴力之无差别性及对无辜民众安全之威胁,故不论行为人是否基于政治、宗教或其他理念,只要其行为符合前述意图及手段,即应受到严厉惩处,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香港《反恐条例》于2004年修订时,加入第11B条罪行,其规范内容与《公约》第2条高度一致,明确禁止任何人意图导致他人死亡或遭受身体严重伤害,而向订明标的(包括基础设施、公用场所及公共运输系统)送递、放置、发射或引爆具导致死亡、身体严重伤害或重大物质损害能力之爆炸性或其他致命装置,或意图造成订明标的遭大范围毁灭并可能引致重大经济损失,违者一经定罪,可处终身监禁。
综观该条文,其本身难谓不合理,且符合国际反恐标准,避免容许以主观动机作为辩护脱罪之借口,确保恐怖主义之定义客观且可操作,从而防止恐怖分子以政治主张掩饰其暴行,亦体现联合国《公约》之精神本质上可谓系维护法治及公共秩序之必要措施。
于本案中,陪审团一致裁定所有被告《反恐条例》下之控罪不成立,可侧面解读为其认为无一被告有“造成他人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或“导致大范围毁灭并可能引致重大经济损失”之恐怖主义意图。
单凭此点,无论被告之动机为何(抑或其是否正当),如警方般继续以“恐怖分子”或其他类似称呼指称被告,即有违陪审团一致裁决之法律效力,并可能损害司法程序之公正性与尊严。

“串谋导致相当可能危害生命的爆炸”罪
就交替控罪之成立要件,陪审团须确信被告怀有意图,借由爆炸品制造爆炸,而该爆炸之性质相当可能危害人命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害。值得注意的是,爆炸事件之实际发生并非定罪之必要条件;即使爆炸未遂,只要其潜在性质客观上符合上述标准,即足认罪成。
在本案中,首宗事件之爆炸乃由一枚主要成分为“火箭糖(Rocket Candy)”之爆炸装置所引发,导致医院急症室男厕内喉管碎裂;第二宗事件之“闪粉”爆炸则释放大量灰色浓烟,致罗湖站月台闭路电视镜头受阻约6至7分钟;第三宗事件最终并未发生,惟政府指控被告等人串谋使用一重达20公斤之炸弹。
警方爆炸品处理课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高级警司于证词中,并不同意“火箭糖”及“闪粉”仅为烟雾弹之论述,强调火箭糖虽可产生大量烟雾,然其亦构成常规军火的驱动火药。就罗湖站事件,李警司认为若爆炸发生于车厢内,高温浓烟或致乘客窒息,甚至引致严重伤害;同样,于急症室厕所释放烟雾,若现场人士吸入浓烟,可能导致不适、肺部灼伤,且烟雾或遮蔽逃生出口标志,致医院内轮椅病人或卧床病患难以迅速疏散。
李展超高级警司作为爆炸品专家,其意见自有高度参考价值,惟其评估损害时,倾向依凭臆测之假设情境(如爆炸地点变更或烟雾引致医院混乱等)为基础,恐未必与法律原则相符。
依据苏格兰高等法院(即该国最高刑事法院)判例《McIntosh诉HM Advocate》[2],于决定爆炸性质是否相当可能危害人命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害时,陪审团须审视被告实际制造之爆炸威力,而非推测若炸弹于其他地点引爆之可能后果;换言之,定罪之基础应限于事实发生之爆炸,而非虚构之替代情境,譬如倘若爆炸实际发生于建筑物外部,则不得以假设其于建筑物内部引爆所致更严重后果,据以支持关于生命或财产损害之推论。
类似地,英格兰及威尔斯首席大法官Burnett勋爵于《女皇诉Thacker》[3]一案明示,“相当可能危害”之评估,须以已知事实(而非被告若采取不同行为可能导致更严重后果之假设)为据。Burnett勋爵进一步阐释,仅创造低度之安全风险之情形,尚不足以构成该项罪行成立要件,因法律要求证明该危险之性质与程度,足以形成真正意义下之“危害(peril)”[4]。例如,即便某爆炸事件导致整个机场关闭并造成高额经济损失,此类后果本身之严重性,犹不足以达致“危害”之门槛[5]。
将上述判例原则适用于本案事实,即可察知三宗事件所涉爆炸之性质,是否构成相当可能危害人命或造成重大财产损害,并不是毫无疑点。以第一及第二宗事件为例,该等爆炸虽释放烟雾并造成局部破坏(如喉管碎裂或视线遮挡),然其能量释放相对有限,证据是否显示已超越低度风险之门槛,或足以形成真正之生命危险,尚且难言;第三宗事件则仅止于串谋阶段而未实际发生,其潜在威力固可考量,惟依判例原则,陪审团不宜过分臆测未实现之替代情境。
从陪审团最终仅裁定三名被告交替罪名成立之结果,可合理推断,三宗事件中至少一宗或两宗,其爆炸性质未被认定为相当可能危害人命或造成严重损害,此或反映陪审团已严格依据实际事实,而非专家之推测性意见,作出谨慎之判断。有鉴于此,本案控方提出之证据,是否完全符应法律要件,实值进一步审视。

如用国安法律检控,结果会有分别吗?
在陪审团对本案中五名被告作出无罪裁决后,国安处警司张伯杰向传媒称将更积极、广泛援引《港区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内已臻完善的相关条文,似乎在暗示若是次检控基础转为国安法相关条文,则有较大机会将被告定罪。
在此脉络下,两部国安法律中唯一与爆炸活动直接相关之规定,乃《港区国安法》第24(2)条。该条明确界定“恐怖活动”为“为胁迫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国际组织或者威吓公众以图实现政治主张,组织、策划、实施、参与实施或者威胁实施 … 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之“爆炸”行为。犯此罪者,若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则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情形,则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依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诉唐英杰》[6]一案之判决,就第24条罪行而言,“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乃控方须予证明之犯罪构成要件。换言之,该罪行之行为要件(actus reus),系被告组织、策划、实施、参与实施或者威胁实施爆炸活动,且该活动已造成对社会之严重危害,或被告主观上意图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
由此观之,至少于爆炸活动未实际造成严重社会危害之情形下,唯有被告主观意图欲造成该等危害,方足以构成第24(2)条之罪行。
然而,如上文所述,本案陪审团一致裁定所有被告于《反恐条例》下之控罪不成立,实已等同认定无一被告具备“造成他人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抑或“导致大范围毁灭并可能引致重大经济损失”之恐怖主义意图。而至少就所有控罪均不成立之被告而言,依陪审团对事实之裁定,他们既缺乏致死或伤人意图,其所致之爆炸客观上亦非相当可能造成真正“危害”,换言之,其行为之客观效果及主观意图,似乎同样不符合《港区国安法》之罪行构成要件。
如此,援引《港区国安法》“恐怖活动罪”之唯一潜在差异,在于依据该法第46条之规定:律政司司长可指示相关诉讼毋须以陪审团方式审理;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随即应即应排除陪审团参与,改由三名指定法官组成审判庭独立进行审理。
亲北京立法会议员如民建联周浩鼎,即于本案判决公布后发文质疑,谓法庭理论上备有多项措施可确保陪审团不受外界报导影响,然法官虽会提供专业指引,但陪审团成员毕竟为一般市民,并未经历法官之长期专业训练,故其裁定可能存有偏差。此一质疑中隐含之假设,倾向于视无陪审团审理为更为适当之模式,尤其暗示本案陪审团已误判事实,若改由三名资深法官之审判庭主导,则将得出迥异之正确结论。
然而,尽管上诉法庭于《唐英杰诉律政司司长》[7]裁定,由三名法官审理且无陪审团之审讯,依然符合被告获得公平审讯之宪法权利,但该裁定之论理,并无任何不信任陪审团作出事实裁定能力之意涵。反之,上诉法庭仅针对陪审员或其家人可能遭受威胁之情境,忧虑此类风险将损害刑事程序之整体完整性。此时,因存在实质风险导致陪审团审讯之公平目标无法实现,唯一剩余之保障手段,乃依第46(1)条规定之无陪审团审讯,改由三名法官组成之审判庭主导。
因此,若如周浩鼎般无端假设三名法官审判庭会作出与本案陪审团相悖之事实裁定,实已偏离《港区国安法》第46条之立法精神,因该条之立法意旨,旨在回应特定威胁情境下之程序保障需求,而非预设司法专业之优越性,或借以贬低陪审团审讯之效能。

“案中案”程序被接纳,即意味警方搜证合法合规吗?
事后,有记者向张伯杰警司询问,不同被告于审讯期间及庭上供词中都提及,曾发生警暴或威胁家人安全事件,警方或国安处是否将展开任何跟进调查。张伯杰警司回应时称,所有相关证据的证据能力,早于正式审讯展开之前,即已透过另一项法庭程序(即所谓“案中案”程序)接受法官的严格审核。在此过程中,法庭已全面检视被告的口供是否属自愿形式作出,并认定该等证据均在合法框架下获取且有效。
言下之意,即表明调查程序并无任何不当或违规情事。
惟张伯杰警司之立场,在法律原则上并非全无可议之处。诚然,英国上议院判例《Hunter诉Chief Constable of the West Midlands Police》[9]阐明,刑事被告若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已有充分辩护机会,但败诉后未上诉,嗣后却在民事诉讼中对刑事法院之定谳发动“附带攻击(collateral attack)”,以回避正当上诉途径,即属滥用法庭程序(abuse of process)。
以该案原告Hunter为例,若他不满原审法官认定其未遭警方殴打而采纳口供呈堂,则应以该裁定属法律错误为由,向上诉法院提起对定罪之上诉,而非另起民事诉讼。此原则旨在维护司法程序之最终性(finality),避免重复诉讼之资源浪费,并确保公众对司法体系之信赖不因无谓之重审而动摇。
但是本案情形与《Hunter案》有显著差异:鉴于陪审团已对至少五名被告一致作出无罪裁决,该等被告实无透过进一步上诉程序,获取“充分机会争辩”原审法官于“案中案”程序中,就警方未施加殴打之认定进行挑战。在此意义下,无罪裁决不仅标志整个刑事程序之终结,更意味被告无法借由上诉途径,质疑庭审前就证据可采纳性所作之初步裁定。
是以,若被告或相关利害关系人欲追究警暴指控,转而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或要求警方进行内部纪律调查,则难以援引《Hunter》案之原则,认定其构成滥用法庭程序。
此见解获香港本土判例《Chan Kwok Wai诉律政司司长》[10]一案有力佐证。时任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石辉于该案中,审理原告主张于警方羁押期间、遭受警员殴打致个人伤害之民事诉讼时,细致检视先前刑事程序是否已对相关争点作出最终处置,以及陪审团之无罪裁决是否已排除原审法官于“案中案”程序中认定无原告所指警暴事实之可能性。
石法官明确指出,原告获陪审团无罪释放后,即便欲挑战原审法官于“案中案”程序之裁定,亦无法独立提起上诉,盖因其刑事程序已因无罪裁决而告终结,原审法院该项裁定遂不具“最终裁定”之性质。唯有于陪审团作出有罪裁决后,原告选择不循上诉途径救济,却另行发起民事程序,方可能构成滥用法庭程序之滥用。
结语
司法非仅系惩恶扬善之器,更是社会价值之试金石,确保法治于动荡中坚守公正本质。本案历经逾5年半审讯,终以陪审团对《反恐条例》主控罪一致无罪裁决告终。此裁决严格限缩于具体事实,拒绝以政治抗议一概冠以恐怖主义标签之简化论调,彰显陪审团不仅为事实把关之守门人,更为价值捍卫之化身,体现社会良知之集体智慧。
香港经历2019年风暴后,正急需谋求长治久安,尤须坚守“一国两制”下之法治框架。执法机关宜以此案为鉴,自省证据搜集过程之严谨公正,避免标签化取代实证基础。警方于无罪裁决后之公开论述,虽强调法庭“案中案”审查之程序,然此仅为最低程序法律门槛,并非对证据强度之肯定,亦不阻碍当事人另循民事途径追究警暴指控之权利。过度解读此类程序裁定,易滋养执法机关内部之自我满足情绪,进而侵蚀公众对司法独立之信心。
展望未来,若国安处更广泛援引《港区国安法》,仍须严格依据行为与意图要件,依事实为断;虽该法于特定威胁下免除陪审团审讯之适用,然不可轻忽陪审团作为公共价值体现之核心功能。司法体系由此续彰社会良知之声,确保每项定责皆经公正试炼,方能维系法治风雨飘摇下之公信。
[1] [1991] 1 SCR 509第523页(L'Heureux-Dubé法官语)。
[2] 1994 SLT 59第62页。
[3] [2021] EWCA Crim 97, [2021] QB 644第79段。
[4] 《Thacker案》第80段。
[5] 《Thacker案》第83段。
[6] [2021] HKCFI 2200, [2021] 5 HKC 100第37段。
[7] [2021] HKCA 912, [2021] 3 HKLRD 350第43段。
8 63 EHRR 10第94、103段
[9] [1982] AC 529第541页(Diplock勋爵语)。
[10] (未经汇编,HCPI 134/1999,2000年2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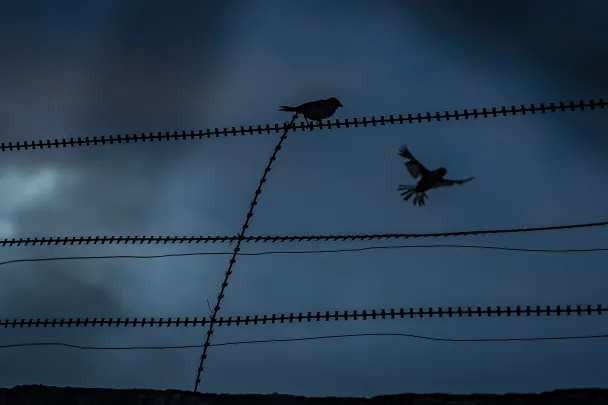

“因三宗事件發生或策劃之時,《港區國安法》” 这一句缺了字。